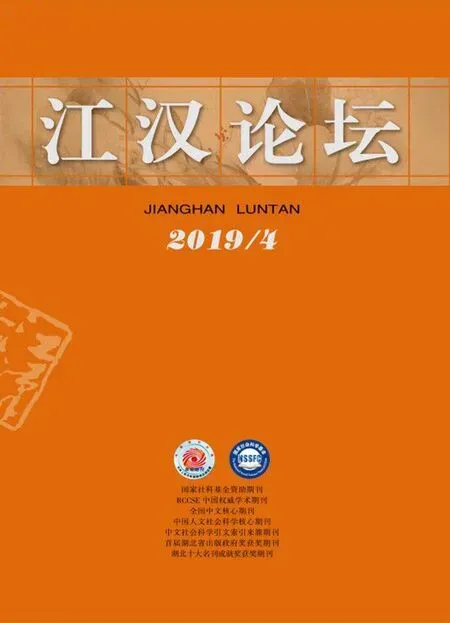拉美民众主义的当代解析
刘雨萌 曹亚雄
“民众主义”来源于“populism”一词,也被译为“民粹主义”。但拉美“民众主义”与欧美“民粹主义”内涵不尽相同,“民众主义”更具中性特征。民众主义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俄国和美国。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俄国小资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舞台。“他们自诩‘人民之友’,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①然而由于小资产阶级目光短浅,无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漠视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仅仅依靠个人野蛮斗争,注定走向失败。19世纪末期,美国出现了“平民党”运动,“平民党”是由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民以及工会组织成员组成的政治联盟,它公开谴责现行体制是“数以百万人民的劳动成果被肆意窃取,只为少数人积累巨额财富”②,主张实行自由铸造金银币及铁路国有化等政策。由于领导阶级缺乏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又将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和黑人农民阶级排斥在外,“平民党”最终分崩离析走向衰败。20世纪初以来,拉美成为民众主义的试验场,民众主义在拉美地区影响日益深远。必须说明的是,“民众主义虽是世界性政治现象,但在各国之间不一定有继承性和关联性。”③拉美民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拉美自身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密切相伴的,有着该地区独有的特点,与其它民众主义样态也不尽相同。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欧美等国民粹主义盛行。以当代视野审视拉美民众主义,透过其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全方位多角度剖析其特点和属性,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拉美民众主义的成败得失,厘清民众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妥善应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拉美民众主义的潮起潮落
纵观拉美历史,民众主义虽起起落落,却是拉美发展进程中最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拉丁美洲这片神奇又独具特色的土地,政治民主化发展阻力重重,经济政策复杂多变,社会阶级结构剧烈变动,贫富差距鸿沟日增,种种社会问题频发,这些都为民众主义生根发芽孕育了深厚的土壤。总体来看,拉美地区民众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进程中,掀起过四波浪潮。
1.早期民众主义浪潮
20世纪初,外有英美等帝国不断入侵,内有工农起义反对剥削压迫,民众对少数寡头和贵族专制垄断日益不满,拉美地区新兴阶级和有识之士开始谋求出路,民众主义社会改革运动应运而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亚·德拉托雷,他被称为“拉美民众主义之父”,美国学者罗伯特·亚历山大称其为“整个拉美左翼民主政党在意识形态和哲学方面的带头人”。德拉托雷创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简称APRA),联盟影响了许多拉美民众主义政治运动,也是秘鲁至今历史最悠久的政党。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都涌现出民众主义代表人物和实践运动。“社会改革是这次高潮的主旋律,虽然民众主义者的改革是保守、温和的,但改革为推动拉美从寡头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④
2.经典民众主义浪潮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拉美地区。拉美地区长期以来实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弊端显露,因难以抵御外部冲击,拉美许多国家陷入困境。大多数底层民众受此影响,加上长期以来对现有体制的不满,谋求政治参与变革现状的情绪日益高涨。面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双重矛盾,拉美国家必须寻求出路。在此背景下,政治上宣称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民众主义领导人主张反贫困、争取社会福利、缩小收入差距等举措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经济上,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意在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扭转颓势。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齐头并进,民众主义不仅成为最重要的思想潮流,更推动了民众主义性质的政权、政党、政策全面繁荣。克里斯玛型的领导人通过极富针对性的政治动员,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发展。拉美民众主义浪潮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民众主义形式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巴西的瓦加斯主义、秘鲁的阿普拉主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等。此阶段“民众主义对拉丁美洲有着深刻影响,削弱了传统寡头的政治力量,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扩大了政治动员,还提高了大众消费水平”⑤。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军人夺取了政权,军人政府认为民众主义运动蛊惑人心,导致国家动乱,遂以捍卫祖国的名义对有关运动进行暴力镇压,经典民众主义浪潮被迫趋于宁静。
3.新民众主义浪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沉寂了20多年的民众主义浪潮又席卷而来。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科洛尔、秘鲁的藤森政府是此阶段影响深远的代表性民众主义政权。这次民众主义浪潮与之前的一波民众主义浪潮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具适应当时时代背景的新特点:虽有鼓动民心的宣传口号和动员行动,但实际上只针对腐败的统治阶级,忽视了经济寡头的垄断腐朽;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激发经济活力,却不再关注与民众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平与福利政策;广大民众不再是民众主义运动的活跃主体和积极力量,而是一个力量庞大的被动群体,民众的意志和利益极易被领导人操控。如藤森上台以后打着自我变革(self-coup)的旗号,解散国会,重组司法机构,名为选民支持的民主实践,实则是为了加强个人权力。建立自由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了民众主义领袖执政时的金科玉律,而反帝国主义与之相比已无关紧要。此番浪潮中民众主义的各项宣言和举措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潮流,经济、政治、社会也得到相应发展,但随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失效,拉美地区发展后续无力,经济危机连发,社会问题频出,民众主义领导人逐渐失去民众支持,新民众主义浪潮走向沉寂。
4.21世纪左翼民众主义浪潮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拉美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民众主义浪潮再次来袭。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主张革新的左翼政权获得民心,走向前台,拉美江山出现了一片“粉色浪潮”(pink tide)。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是左翼民众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前一波民众主义浪潮的引领者不同,这批左翼领袖在政治上主张泛拉美主义和地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抵制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在社会生活中,坚决捍卫平民福利和尊严。由于这些国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他们自信满满地宣称必须走出一条惠及大多数人的全新发展道路。查韦斯这位个性鲜明又富有领导才能的总统的执政模式被称为“查韦斯主义”,得到不少拉美国家的认可。“查韦斯主义”的两大支柱是“玻利瓦尔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主要特征是政治集权化、经济去市场化和社会超福利化。出身底层的查韦斯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社会福利,不计成本地进行财政投入,以求牢牢抓住民心(也为后来委内瑞拉陷入困境埋下了重重隐患)。作为最激进的左翼民众主义领导人,查韦斯四次当选总统,执政超过14年,是拉美历史上极有传奇色彩和影响力的一位政治家。对于21世纪左翼民众主义的兴起,德州大学著名拉美政治研究学者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认为:“民众主义政治在拉美的再次勃兴,缘于过去20年来拉丁美洲对于‘华盛顿共识’及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所许诺的繁荣前景的幻灭。”
二、拉美民众主义的四维解读
拉美民众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政治工具、执政理念,甚至是一种经济政策,在拉美地区影响巨大。由于该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轨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民众主义各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环境、根本立场、学术背景、世界观等不同,学者们对民众主义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对民众主义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有时还相互矛盾。对民众主义的相关认识无需强求共识,但应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这一独特又重要的政治、社会现象。笔者认为,应从四个维度解读拉美民众主义:
1.结构主义维度
结构主义源于19世纪,经过多年发展和批判,已成为语言、文化与社会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核心在于透过某个结构关系来解析社会文化现象。从结构主义维度解读民众主义,可以发现拉美地区民众主义的兴衰与该地区极富特色的社会结构联系密切。其一,众所周知,拉美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使得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人民财富收入也不平等。因此,拉美社会总体上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少数掌握政治、经济核心权力的精英寡头,另一部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大众。与这种社会结构相伴的社会极不平等,使得“人民大众”的概念格外突显,“人民大众”又是孕育民众主义最有利的温床。其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进入社会大变革和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各要素、各部分发生变化并相互作用。赫尔马尼(Gino Germani)认为,“当时的发展模式为一种新社会阶级模式开辟了道路,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复杂,边缘群体被纳入整体。”⑥新兴社会力量(破产农民、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城市工人、知识分子等)逐渐壮大,开始寻求在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拉美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变化,这种地区特殊性和非均衡状态为民众主义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三,在拉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作为民众主义社会基础的多阶级集团虽然逐渐明白要争取政治权利,改变不平等地位,但缺乏对改革具体实施的全面认识,同时这种多阶级结构为民众主义领袖的诞生孕育了有利的条件,于是抨击现状、主张变革的民众主义领导人走向前台。因此,尽管拉美民众主义的特征和形式有地区差异,但几乎所有领导人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众主义政治动员(mobilization)时,都会高喊“‘我们’(正直而高尚的‘人民’)和‘他们’(邪恶且贪婪的‘寡头’)”⑦这种极富蛊惑性的口号来奠定群众基础,直白表明社会结构一分为二、根本对立,而见识相对落后的人民大众非常容易被克里斯玛型的领导人所操纵,阿根廷民众主义领导人庇隆、巴西民众主义领导人瓦加斯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
2.意识形态维度
民众主义体现了不满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诉求于“人民”而非无差别的各个阶层。卡茨·穆德(Cas Mudde)认为,“归根结底,民众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将整个社会分为两种同质却对立的团体,‘纯粹的人民’和‘堕落的精英’,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政治是‘人民’共同意愿的体现。”⑧这种摩尼教(Manichean)的二元对立根植于拉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中,对拉美民众主义有着重要影响。从意识形态维度审视民众主义,可以发现:第一,拉美民众主义客观上淡化了民众主义领袖个人的作用,将拉美民众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有机团体,而不是将其看成毫无思想的操控对象,从而否定了领袖个人决定论的唯心史观。第二,在拉美民众主义看来,“人民”和“精英”两大团体本质上谋求的利益理应相同,区别两者的是道德划分。“人民”是纯洁、善良、公正的象征,“精英”(寡头)是万恶之源,拉美民众主义就产生于两者的对立关系中。第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拉美民众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以人民为主体、反精英主义、集体共同意愿和反建制主义。在民众主义看来,“人民”的内涵丰富,不仅仅是被动个人的集合,而是具有思想和动机的整体,包括各个阶级甚至选民;民众主义的天然属性绝不是简单的“左”和“右”之别,“人民”的界定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左”或“右”的划分;“人民”以民众主义形式支持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诉求,而非领袖绝对主导和推动,领导人和“人民”处于一种彼此供给的互动关系之中;“人民”长期以来积压的不满变成集体的话语和诉求,成为共同意愿,这种共同意愿根本上体现为要求改变现有制度,推翻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当权政府,现有体制的维护者和受益者——“精英”(寡头)于是被视为“人民”共同意愿的敌对方和民众主义行动的目标,“反精英主义”和“反建制主义”成为拉美民众主义的突出特征。
从意识形态维度剖析民众主义,意识形态的“非排外性”也是拉美民众主义的一大特色。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指出:“民众主义不是‘完整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弱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⑨这表现在:第一,拉美民众主义浪潮虽然源源不断,但是这种循环往复的现象大部分是昙花一现,缺乏完整意识形态影响的持久性和内生复杂性,相对简单直观,不够长期;第二,拉美民众主义没有系统完整的理论支撑和构建,大多时候随波逐流,根据国内外形势加以改变;第三,没有完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环——“对于社会公平、资源分配、矛盾处理等问题的解决方案”⑩。简单来说就是设定了将要实现的最佳政治、经济制度,但没有具体、全面、可操作的各项措施来实现预定目标,甚至从频繁的政策左右摇摆上就能看出,有时要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其它意识形态。拉美民众主义的两个典型:秘鲁藤森主义大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右”派主张)和以查韦斯为代表的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左”派主张),都是将民众主义依附于其它完整意识形态才能持续推动。
3.经济模式维度
经济学领域也长期关注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进程。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学者把民众主义和经济发展模式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宏观经济政策范畴。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拉美民众主义宏观经济学》。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民众主义领导人上台后,为了稳定政权,往往会运用国家权力大力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从实现经济目标的具体政策来看,民众主义的核心在于: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国内需求;提高名义工资,控制物价,推行收入再分配;在非出口商品部门实行汇率控制,通过货币升值来降低通货膨胀;等等。⑪不得不说,民众主义政权制定经济政策时的初衷值得肯定,其试图改善拉美长期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还重点关注了贫困民众。从短期看,这些措施颇有成效,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得到增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然而一旦短时利好期结束,前期埋下的隐患便逐渐凸显,如通货膨胀急速加剧、财政赤字恶化、物价飙升、企业竞争力锐减、失业率猛增、工资水平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使民众陷入更大的困境。“此类政策一再失败,严重伤害了那些它们试图去取悦的群体,即穷人和中间阶级。”⑫这些经济政策盲目夸大再分配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无视市场客观规律,无视财政赤字和外部风险对政权稳固的关键影响,最终导致更加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例如,秘鲁总统加西亚在任的第一个五年里,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和原则,施行典型的民众主义经济政策,“将资源转给最贫困的群体……必须要花钱,即使以财政赤字为代价”⑬,使得本国通货膨胀不断扩张,工资购买力水平缩水60%以上。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民众主义政府积极施行扩张型经济政策和扩大社会福利政策,将此作为维系民众的基石,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民众主义也随之从高潮跌落低谷。
4.政治策略维度
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认为,“可将民众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个人化突出的领导人行使政府权力的基础在于,大批无组织追随者直接的、无中介的、无制度的支持。”⑭民众主义领导人为了完成政治工程和实现政治目标,需要获得大量且广泛的群众支持,而只有满足民众的期望才能获得民心,于是各种迎合民众的政治策略相应产生。在民众的支持下获得政权,领导人必须继续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以压制反对力量。以政治策略作为切入点来理解拉美民众主义,远离了长期争论不休、模棱两可的内容解析,转向实现民众主义的切实手段上,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实用方法。民众主义的政治策略主要表现为:
大众动员。“民众主义动员指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政治工程,它将大众动员和民众主义话语结合起来。”⑮拉美大部分群众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政治上没有话语权,经济上无法占有生产资料,生活中难以享受社会福利,充满被剥削和压迫感,可以说“民众主义萌芽深深根植于群众的不满中,不仅对政治不满,更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不满”⑯。群众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对社会现状的不满,非常容易被设计巧妙的动员策略所鼓动甚至操控。因此对民众主义领导人来说,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具备了,制定富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政治策略来动员大众赢得政权极为关键。自传回忆录、成就纪录片、党派宣传册、铺天盖地的报道,各种造势手段层出不穷,追随者情绪高亢,甚至自发进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要求进行变革,这为民众主义领导人上台奠定了基础。
个人主导。拉美民众主义运动的定海神针是众望所归的领导人。领导人的指导思想、领导方式、政治策略在民众主义运动兴起、高潮甚至低谷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甚至决定性作用。如,“阿亚·德拉托雷在秘鲁人民党内被正式授予领袖称号,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该党的一切重大决策往往取决于他个人。”⑰领导人的大政方针勾勒出美好蓝图,对文化水平不高又迫切渴望有所改变的人民大众充满了诱惑。人民将未来命运寄托在领导人身上,领导人成为了民众的救世主。高度个人主导化倾向成为了民众主义的一大突出特征。民众主义领袖在施行各项战略计划时,常常越过立法、司法等民主制机构,直接以个人面向群众,而缺乏制度化的政治体系。政治权力被领导人所把持,政权笼罩上了威权主义、庇护主义等阴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主义的口号是领导人获得民心的政治策略,而其根本上是为巩固个人权力服务的。在委内瑞拉长期奉行查韦斯主义与非查韦斯主义,这种绝对的二元对立划分充分体现了唯领导人意志论的模式。同时,由于民众主义领导人的群众基础极其薄弱,如果民众要求得不到满足,社会现状未发生改变,民众主义政权的基石——人民就会发生动摇,民众主义领导人的境遇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政策摇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状况不同,因此拉美地区各国的民众主义表现样态不尽相同,这突出表现在不同的政策上。民众主义在政策倾向上大体可划分为政治上的左翼、政治上的右翼、经济上的左翼、经济上的右翼。必须说明的是,拉美各民众主义政权在政策倾向上并不绝对,有时会采取多种倾向结合的方式。比如,政治左派和经济右派结合的庇隆主义政权,政治左派和经济左派结合的查韦斯主义、莫拉莱斯政权以及科雷亚政权等。民众主义在拉美没有单一固定的特点和定义,表现形式多样,政权采取的政策也左右摇摆,但根本上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维护领导人统治和政权稳定而进行的自我调节。
三、民众主义在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拉美民众主义发展与拉美民主化进程紧密相关。但国内外学界对于民众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却莫衷一是,总体来看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种,以吉诺·赫尔马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民众主义在克里斯玛式领导人的主导下混入了威权主义⑱,是一种“民主的异态”⑲。第二种,有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给以高度肯定,将其视为“最纯粹的民主表现形式”⑳。第三种观点相对来说得到学术界较多认可,“民众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一言难尽无法界定,将异见者视为威胁,却能提高包容性。”㉑这种阐释形象地说明了民众主义的民主两面性:一方面将长期被排斥的边缘群体推向前台,扩大了政治参与主体,客观上促进了民主发展;另一方面又视少数对立派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主张剥夺对立派的一切权利,给庇护主义和威权主义留下了漏洞。
综上来看,单纯静态地探讨拉美地区民众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存在某些逻辑缺陷。民众主义(populism)和民主(democracy)这两个概念在学术界本来就争论不休。如果先入为主地界定好民主概念,然后再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规定性的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就好比让两个活蹦乱跳的有机体强行静止,让其被动接受摆布,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拉美地区是民众主义最为活跃和丰富的地区,探讨民众主义的定位或是影响应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纵观拉美独立以来的200年,拉美民主一直在发展,但多次被迫中断。虽然民主已被写入宪法,但实际上却常遭到破坏……从全球范围看,拉丁美洲是一个过去200年里宣称始终捍卫民主的地区,虽然有时会剥夺民主,但又重新恢复民主。”㉒因此,深入分析民众主义在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整个宏观动态发展史切入,视角将更加全面。
向民主体制转化的动态过程牵动着拉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这个过程时快时慢、时进时退,总体来看是在曲折中前进,民主化是拉美地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与之如影随形的民众主义现象,有关运动、变革、政党、领导人、政策、话语等在民主化进程中也产生了巨大却非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民众主义在拉美民主化这场扣人心弦的大剧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唤起政治觉醒的引路人”
拉美民主化就是由传统寡头制度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过渡阶段,大体来看,拉美地区民众主义运动赋予了民主化鲜明的色彩和力量:第一,关注边缘群体,倾听被排斥群体的政治诉求和意愿。比如,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为消除种族歧视,保护当地土著人的合法权益,专门制定了相关政策。第二,广泛的民众动员和宣传,唤起了民众长期以来因社会不公而积压的不满,唤醒了民众捍卫自身权益的民主意识,激发了民众改变现状、谋求变革的决心。第三,民众主义者通过完善民主选举模式,不断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在巴西、秘鲁和智利,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并赋予文盲投票权。”㉓庇隆政府执政时期,妇女也获得了投票权。民众主义运动促进民众政治觉醒,积极推动了民主化进程。
2.“心思诡谲莫测的两面人”
拉美民主化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然而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各方力量博弈、各种矛盾交错,所以发展起起伏伏。贯穿始终的民众主义时不时也会暴露其隐藏的阴暗面,给民主化发展狠狠一击。首先,民众主义将社会一刀切式地划分为两大对立群体,视对方为死敌,没有任何政治协商和沟通的可能,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全方位压倒对方。因此,民众主义领袖的直接民主领导方式非常容易走向极端,演变成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或独裁倾向。秘鲁前总统藤森一上台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将政治体制变成个人把持的执政工具,完全无视民主化的要求和法则,实际上削弱了民主制度,加剧了政治腐败和庇护主义。其次,民众主义领导人都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民众非常容易被那些美好的话语和承诺所煽动,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引起社会暴力和动乱,社会环境动荡不利于民主化的推进。最后,民众主义领导人通过美好的构想赢得民众,自称是公众愿望的唯一代表,抵制多元化发展。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甚至在上台前后表现截然不同:“我们给了阿根廷人民选举的机会,进行了阿根廷历史上最诚实的选择——选择我们还是对手;民众既然选择了我们,那么阿根廷就应该由我们决定做什么。”然而若政府对民众的承诺(“确保人民幸福和国家尊严”㉔) 无法兑现,便会丧失民众支持,致使政权岌岌可危,社会重陷不安状态。
四、拉美民众主义的借鉴与反思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系列的疯狂举措、欧洲右翼民众主义愈演愈烈等无不表明民众主义(说“民粹主义”更为确切)正在回潮。有学者甚至断言,“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㉕细看拉美20世纪至今的历史,民众主义一直寸步不离,能量巨大。但几乎所有实践都难逃魔咒,一开始雄心壮志满怀信心,几经波折终归落寞收场。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众主义运动高举“一切为了人民”的旗帜,最终却让人民黄粱一梦,深受其害。拉美是民众主义样态最丰富的地区,是民众主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典型地区,客观、全面地分析研究这一突出现象,对于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于身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中国,对于各种思潮交织碰撞的中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一,拉美民众主义进行的变革实践,是对社会矛盾作出的被动回应。民众主义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反而往往成为选举的把戏和领导人的工具。民众主义后期对西方制度盲目迷信和追随,众多国家出现了民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怪象”,最重要、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激化了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安。同时,民众主义违背世界全球化、多极化的发展大势,逐渐蒙上极端民族主义、庇护主义和本土主义的阴影,有逆历史发展大势之嫌。第二,执政理念和发展道路应有可持续性。为什么拉美地区民众主义循环反复好景不长?因为民众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其刻意迎合底层民众的心理,而在于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实际上会损害穷人的长远利益。拉美民众主义运动制定的目标举措只注重短期效果,能给予群众一时的甜头,但绝非长久之计。例如,梅内姆以高票当选阿根廷总统后,如火如荼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短期内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没过多久阿根廷噩梦开始,国民经济命脉被外国垄断,失业率和贫困率猛增,社会腐败加剧,政府公信力跌至低谷。委内瑞拉也是如此,该国依靠石油资源丰富这一天然红利,失去理性地大搞社会福利建设,公共支出负债累累,名义上是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民众、为了贫民,可长远看风险巨大。由于国际石油市场低迷、美国经济制裁等影响,委内瑞拉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政府无力为继,人民反而成了受害者。第三,“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畸形发展不可取。拉美民众主义发端于城市,大多数民众主义运动也将发展重点放在城市,落后的农村地区长期得不到关注,曾作出的承诺“征收与重新分配土地被抛诸脑后”㉖,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形同虚设,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农村建设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深火热,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瘫痪。忽视“三农”问题,是拉美民众主义屡陷困境的教训之一。
民众主义是研究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盏导向灯。20世纪初以来拉美的发展史,实质上也是民众主义的演化、实践史。民众主义对拉美国家发展的影响是多向的,其经验和教训也非常丰富。当今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虽然民粹主义抬头,但改变不了世界发展的大势。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挑战,拉美民众主义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避免陷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泥沼,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 肖枫:《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3期。
②David M.Kennedy,Lizabeth Cohen,The American Pageant,United States:Cengage Learning,2015,p.525.
③ 袁东振:《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性及思想文化根源》,《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④ 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探讨》,《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⑤James M.Malloy,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7,p.15.
⑥Gino Germani,Authoritarianism,Fascism,and National Popul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78.
⑦郭洁:《周而复始的政治“狂欢”?——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探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
⑧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4),p.543.
⑨⑩ Michael Freeden,Is Nationalism a Distinct Ideology?,Political Studies,1998,46(4),p.759,p.751.
⑪ Rudiger Dornbusch,Sebastian Edwards,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⑫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拉美新旧民粹主义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⑬Daniel Carbonetto,Marco Teórico de un Modelo de Consistencia Macroeconómica de Corto Plazo,Lima:Instiuto Nacional de Planificacion,1987,p.82.
⑭ 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2001,34(1),p.14.
⑮R.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Sociological Theory,2011,29(2),p.82.
⑯Bram Spruyt,Gil Keppens and Filip Van Droogenbroeck,Who Supports Populism and What Attracts People to It?,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16,69(2),p.342.
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编:《拉丁美洲各国政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⑱Gino Germani,Authoritarianism,Fascism,and National Popul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78.
⑲Pierre Rosanvallon,Counter-Democracy:Politics in an Age of Distrus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67.
⑳Torbjorn Tannsjo,Populist Democracy:A Defence,London:Routledge,1992.
㉑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The Ambivalence of Populism:Threat and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Democratization,2012,19(2),p.196.
㉒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Towards a Citizens’Democracy,New York:UNDP,2004,p.36.
㉓Michael L.Conniff,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9,p.17.
㉔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㉕Benjamin Moffitt,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Performance,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
㉖Rosemary Thorp,Progreso,Pobreza y Exclusión:Una Historia Económica de América Latina en el siglo XX,Washington DC:IDB Publications,1998,p.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