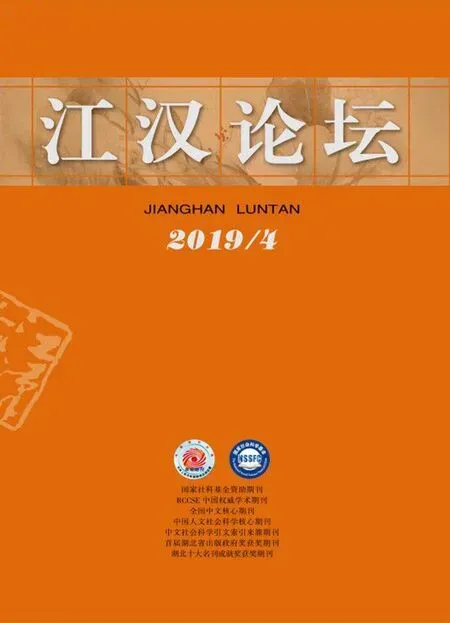“政治性道德”何以可能?
——阿伦特的道德—政治之思
朱蔷薇
无论是在政治哲学中,还是在道德哲学中,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是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作为极权主义灾难的亲历者和艾希曼审判的见证者,阿伦特在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尤其是遭遇了此书的出版所引起的舆论风暴之后,也开始关注道德与政治的相关性问题。正如她自己曾在一封信中所透露的,她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新的政治(性)道德的基础”①。诚然,阿伦特从未发表过一篇专门论述道德的政治性的成熟论文,也未能在此议题上最终达成一套令她自己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但她的孜孜以求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益。
一、后极权主义时代的道德困境
面对20世纪上半叶道德崩溃的种种现实,阿伦特忧心忡忡地意识到,现代世界极有可能不再为道德哲学保留容身之所了。首先,随着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人类精神中的那些永恒卓绝的道德规则和标准已经难以延续下去了,它们的合法性丧失了自明性。其次,随着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所有的传统道德也成了上帝的殉葬品。阿伦特认同尼采的这一观点,即发轫于柏拉图的整个西方道德传统已经形同死灰,无以复燃了。在她看来,西方传统中一直信奉着道德绝对主义的神话,无论是希腊哲学传统还是希伯来宗教传统都确信,存在着某种超越此世的道德标准和尺度,而且这些超越性的真理只为少数特权人物所知,对于他们而言,关于这些真理的经验——无论是心灵的眼睛之所见(哲学家的经验)还是良心的耳朵之所听(基督徒的经验),都是令人信服的。然而,普罗大众却并没有关于这些真理的经验,于是他们不免要怀疑,难道这些超越性的真理不是那少数特权人物所强加给他们的外在的行为指导标准吗?为了使这些真理更能俘获人心,那少数的特权人物们又言之凿凿地教导大家要相信来世的赏罚。
在阿伦特看来,柏拉图就是这个关于来世赏罚的神话的设计者,但是,这个最初纯粹为了政治统治的目的而设计的神话却在罗马晚期被吸收到了基督教教义之中,在后世,主要以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的地狱形象而被呈现出来,并以宗教的名义与权威和传统结成三位一体,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三大支柱性要素之一。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笛卡尔式怀疑的兴起,这个三位一体渐显颓势。尽管崩塌的厄运难逃,但丧钟却并没有立即敲响。当尼采兀自宣布上帝以及一切现存的欧洲道德的死讯时,他不过是大胆指出了一种逻辑上的后果而已。阿伦特认为,直到充满苦难的20世纪,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民众才从这个关于来世的神话中醒过神来,而源于哲学传统和宗教传统的、作为衡量人的行为的超越性标准的道德观念也才算气绝了。进一步的后果就是,“道德”一词又回复到了其源初的“习俗”(mores)意义上,显现为习惯和风俗,即具有相对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正常的年代里,习俗性道德的确有助于维持文明的体统,但是,阿伦特也发现,在面对现代极权主义浪潮中的极端恶时,它们毫无抵抗力。最好的情况是,传统的道德标准蜕变成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最坏的情况是,它们直接被抛弃,并代之以纳粹所提供的道德规范。而最让阿伦特感到震惊的则是,一旦道德标准失却了超越性原则或上帝惩罚的支撑,而仅仅被理解为“价值”(values),它们就很容易像货币一样被拿来交换。也就是说,人们只是习惯于对“规则”(rules)或“价值”的拥有,而并不在意它们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的后果则是,近代兴起的世俗社会虽然在道德议题上热衷于兜售相对主义(例如,以效用性为标准的道德功利主义),但实质上仍然在道德绝对主义的迷宫里打转,只不过由超验的绝对转换成了形式的绝对。因此,在阿伦特看来,那些行为举止不拘泥于成规的人其实要比那些衣冠楚楚的道德卫士们更容易成为纳粹的反对者。那些有教养的德国人之所以能够在1930年代转向纳粹的道德标准,战后又迅速回复到常态的道德标准,正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中,道德原则被还原成了可以像货币一样拿来交换的“价值”。然而,事实上,无论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当道德生活蜕变为一系列价值之间的量化权衡时,道德虚无的深渊也就敞开了。
二、重审“基本的道德命题”
阿伦特指出,既然超越性的原则和传统习俗都已经不能给予我们道德上的引导了,我们就应该“无所凭栏”(without a banister)地生活,不要再寄望于道德上的绝对真理了。不过,超越性的绝对真理的缺场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经验的缺场,因为它并不能掩盖这一基本事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些人确实作出了道德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显然不是随意作出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于是,阿伦特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过去,试图在那些作出过艰难的道德抉择的人们的经验报道中或者在哲学和文学作品中为道德生活找到某种世俗的、非超越性的基础。
阿伦特的研究起点是,即使一些个体未必信奉超越性的原则,即使他们显然也处于社会习俗的重压之下,但他们拒绝与纳粹极权主义政体同流合污却是个不争的事实。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很值得玩味的道德现象——这种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的“拒绝”是如何可能的呢?具体说来,促使阿伦特对道德现象展开研究的两个现实契机是:第一,我们无法揣度究竟哪一类人会拒绝纳粹,因为在所有人中都能找到这样卓然自持的范例,无分阶级、学历、宗教信仰与职业——“抵抗者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找到,不管是在贫穷而完全无教养的人中间,还是在优秀的上层社会成员中间”。从而,分辨对错并合乎道德地去行动似乎是所有人都拥有的一种能力。第二,阿伦特宣称,那些拒绝纳粹的人通常也并非是出于某种超越性的道德原则或宗教诫律,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自有一条判断的标准——“他们只是这么说:我不能那么做,我宁愿死掉,因为我要是那么做,生活就不值得过了。”②因此,阿伦特认为,从这些人身上,我们所能得出的一条道德命题就是,人们一旦涉身不义,就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无以自处,无以抵御过去所做的不义之事的反噬。
在阿伦特看来,拒绝行不义并非全然是现代的新经验,在西方的道德与宗教传统中,也不难找到类似的表达。例如:“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康德所说的“要这样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准则能成为所有理性存在者的一个普遍法则”(即不要为你自己破例);或者苏格拉底所说的“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③。根据阿伦特,这些基本的道德命题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这些命题虽然都貌似是“来自理性的命令”,但其实是自明的,即不能被证据或论证所证实。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要接受道德的观点呢?为什么要爱邻如己呢?为什么与其行不义还不如遭受不义呢?面对这些问题,理性是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第二,这些命题都无一例外地诉诸“自我”(self),“都把自我以及人与他自身的交流作为它们的标准”,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道德的一般认识:道德从本质上来说是无私或忘我的,而自私自利则是不道德的④。
阿伦特认为,对这些基本的道德命题的本质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当属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曾提出过三个论断:“(1) 遭受不义要比行不义好;(2) 对罪犯自己来说,被惩罚要比逍遥法外好;以及(3)那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的暴君是不幸福的。”⑤然而,当时的希腊人对这三个论断却不以为然。无独有偶,在柏拉图对话——《国家篇》的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也论证过他的这一观点:即使义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吃亏,而不义之人却往往可以不受惩罚,我们也应当(should) 让自己成为一个义人。因为即使在离开同伴之后,我们也不是独自一人,我们还必然要与自己为伴,既然如此,又有谁会愿意与一个罪犯处于朝夕相对的亲密关系之中呢?然而,结果同样无人信服。在这里,阿伦特发现,苏格拉底所谓的“作为一的我”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而是包含着一种我与我自身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我是一个,但我是二而一(two-inone)的”⑥,我与这个作为我自身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尽管是亲密的,却既可以是和谐的也可以是不和谐的。而我与我自身之间的对话(dialogue)就生成了良心的命令,它既不是对真理的消极观看也不是由论证所证明的,而是主观的;道德命题的自明性也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在思维与自我的关系中产生的。按照阿伦特的理解,由于苏格拉底的良心观依赖于思维活动这个“隐含条件”,像艾希曼那样完全无思的人就难以意识到自我内在和谐的需要,从而也就不大担心自己会去作恶了。
阿伦特宣称,在苏格拉底那里,个体道德(personal morality)之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就在于:“道德关乎个体,即单数的人。……是非的标准,即对于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依赖于我与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习惯和风俗,也不依赖于一种有着神圣起源或人类起源的命令,而是依赖于我对我自己作出了什么样的决断。”⑦这就是衍生于西方传统的最基本的道德命题,也是最具世俗性的道德命题。在传统道德失落之后,它也就成了西方重建道德的唯一地基。在一次讲演中,她还谈到:“在今天,随着宗教权威的衰落,作为基准的是我们能否达到完全理解不作恶的真正根据……(即)遭受不义要比行不义好……不能与一个罪犯一起活着,特别是当这个罪犯恰恰是你的时候,更是如此。”⑧因此,为了给人们的道德生活找到某种世俗的基础,阿伦特在对西方的道德经验进行了初步挖掘之后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如果我还想坦然自处(live with myself),那么有些事情是我一定不能去做的。但是,哪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以及我是否希冀坦然自处却完全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诚然,这一结论弥漫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所有世俗的基本道德命题都倾向于诉诸对自我的兴趣。按照阿伦特的看法,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想与他自身不和谐的原因就在于,如果他与他自身之间是不和谐的,那么思维(think)——即个体与其自身之间的内在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因此,道德命题的最为深层的基础就蕴含在思想者的这种对自我的兴趣之中。为了弄懂她这样说的意义何在,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她对“思维”的独特理解。
三、思维:道德判断的前提性条件
作为理性存在者,人类活动与完全受制于本能驱使的动物性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伴随着人类活动的还有更为高级的心智生活,即人们时常会停下自己手中的活动并追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或“我的所作所为其意义何在?”因此,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哪怕人在自然界中脆弱如芦苇,人也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也就是说,按其本意,思维是一桩人人都力所能及的事情,它产生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平凡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自己做过的事情——我们的习惯性做法、我们的道德主张以及我们用以谈论它们的语言都在我们的思维射程之内。
阿伦特认为,在人类所从事的诸般活动之中,唯有思维活动要求内在的和谐。当人们在世界上和其他人一起忙忙碌碌的时候,或者当人们完全投入到某种生产性活动或体力活动之中的时候,是不必担心与自己相处的问题的。然而,思维却是一场我与我自身之间的对话,而且这种对话只有在我与我自身之间是朋友关系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我的内在和谐,即我与我自身之间的和谐,是我进行思维活动的一项基本前提。在阿伦特看来,虽然这一前提性条件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主观意味,但它也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力。事实上,按照阿伦特的解释,若说思维活动提供了某些限制以抵抗恶行,那么这不仅是因为某些事情是思维中的人所无法接受的,而且是因为“停下来想一想”(stopping to think)这个动作本身就意味着,追问自己被要求去做的事情之理由或合理性是什么?这一追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人们由于盲目随大流而犯下无心之过。特别是,当官员们对纳粹指令的机械性服从和民众不假思索的因循守旧(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危机的时候,重申这一前提的道德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正如阿伦特所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我们也不宜对这一前提的道德作用寄予太大的希望。一方面,人们对自己可以接受的人或事物的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另一方面,它仅仅适用于那些热爱思考而且仅仅将自我(self)作为关注焦点的人。它既不意味着对其他个体的责任,也不意味着为了纠正荒诞世事而积极采取公共行动。换句话说,遵循这一前提的人将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福祉的责任都留给别人了。这正是阿伦特对苏格拉底不满意的地方。在她看来,尽管苏格拉底坚信他的思维和审查活动对雅典人而言是很有益处的,但这并不是他投身思维和审查活动的出发点。其实,无论这些活动将对雅典人产生何种影响,他都不会放弃——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名言就是,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苏格拉底对思维活动的热衷,并非出于城邦的公共目的,而是为了他自己内心的和谐。站在阿伦特的立场上来看,可以说,苏格拉底的这一观点对于“世界”(即公共空间)而言并无多少建设性意义,因此,阿伦特更为同情马基雅维利激进的行动主义。在她看来,只有马基雅维利严肃对待了这一事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以恶制恶,那么“作恶者就会肆意妄为”⑨。也正是在此语境下,阿伦特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位道德思想家。然而,从传统上来看,马基雅维利对积极行动的倡导却和者寥寥。难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行动的风险吗?难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原是这世上稀松平常的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激进地主张以恶制恶,既不是为了逞强斗狠,也不是认为内心的和谐不重要,而是因为,为了他的邦国,他愿意献祭出自己的灵魂。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常常遭到误解一样,当阿伦特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公民”(citizen)视角来驳斥形形色色的“私人”(private)视角时,舆论被点燃了,人们纷纷指责她是空洞的激进主义或者政治上的浪漫派,因为她坚决主张我们不能用道德标准去判断政治行动,在她看来,“行动只能以是否伟大(greatness) 的标尺来衡量”⑩,而且,只有表演活动本身所展现出来的秀异(virtuosity)才算得上是政治上的成就。
四、在公共与私人之间:“政治性道德”的基本构想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虽然阿伦特最终并未完整地构建出一套关于政治性道德的理论,但如果我们将她不同时期的著作串联起来看,则不难发现,这一“未成文的”政治性道德(political morality)理论要点有二:一是阐明对政治进行道德限制何以必要,二是阐明用“友谊”(friendship)去调和公共领域(政治)与私人领域(道德)何以可能。
前已述及,阿伦特非常赞赏马基雅维利对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认为我们应当让自己的私人性完全沦为公共性的牺牲品,也不意味着她认为私人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更不意味着她赞成一种完全游离于道德原则之外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形式。诚然,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充斥着对私人领域的贬斥和对公共领域的颂扬,根据她的描述,私人领域往往暗影沉沉,不及公共领域明亮壮丽,但如果我们过于计较阿伦特对它们的字面刻画,就会错失字面背后的写作策略和真正意图。究极而言,她之所以采取如此鲜明的对比手法,是为了找出“范例”(exemplary cases) 或“理想型”(ideal types),并利用它们来帮助我们从传统观念的泥淖中超拔出来,从而使我们在认识或理解新经验时不再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让那些老掉牙的调子就此打住吧,范例的光辉会照亮我们的思索之路,引领我们真切地看到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由此,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划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操作,是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之后的抽象表达。从现实层面来看,以家庭生活为典型代表的私人生活绝非一团漆黑或纯属奔命于生计,而以政治生活为典型代表的公共生活也并非完美无瑕或绝对不食人间烟火,两个领域的重叠或融合是一个基本事实,很难完全切割开来。我们不能设想阿伦特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只是随着社会领域在近代的兴起和成型,现代人已经在阿伦特所谓的“劳动动物的胜利”中沉迷日久,政治观念逐渐变得淡漠起来,无法敏锐嗅出现代社会中潜滋暗长的极权主义的危险气息了,她才不得不一再重申政治生活的光明图景。而这决不等于阿伦特对政治领域的无批判地接受和对私人领域的无来由地敌视。说到底,思维活动需要从世界中抽身出来并回到我们自身之中,也就是说,思维活动出现在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更重要的是,正如阿伦特所再三强调的那样,思维能力和思维活动是我们据以抵御时时威胁着现代社会的平庸之恶的必备武器,政治也决不能冲破一切道德原则的限度。
事实上,在阿伦特看来,政治与道德并非全然是相互外在的关系,道德原则其实就内在于政治的本性之中。在《人的境况》中,她曾指出,宽恕与承诺这两条道德原则就是从政治行动中提炼出来的。宽恕是将政治行动和人际关系从过去的不可逆性中拯救出来、使人们摆脱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的能力;而承诺(对他人作出承诺并恪守它们)则是将政治行动和人际关系从未来的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中拯救出来的能力。事实上,虽然阿伦特常常将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推崇为政治的理想形态,但她也批评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仍未触及不可逆性问题,并且缺乏一个宽恕概念。
相应地,阿伦特还认为,勇气(courage)和节制(moderation)是两种不可或缺的政治德性。为什么说勇气是政治行动的一项必要条件呢?因为在世界上与他人一起去行动就是去开端启新、去肩负起对未知的乃至于不可控的行动过程的责任。不仅如此,行动也需要割舍下对安逸的居家生活的留恋,将自己曝露于睽睽众目之下。因此,行动离不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离不开从私人生活的匿名性和安全性中出走的勇气,离不开向着未知的结局溯游的勇气。同时,在阿伦特看来,节制、不逾矩是“最卓越的政治德性之一”,而节制的反面——僭妄——则是“最可怕的政治诱惑”⑪。也就是说,政治行动并非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而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展开。阿伦特非常反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起行动,因为这样很容易使政治行动演变为僭妄,因此,她曾多次批评法国大革命以“人权”这一道德概念之名而行伪善之实。另外,对节制的强调也引导她将善功与政治行动中的成就分别开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并反对人们在行动中自诩为他人的代表。因为政治行动是新颖的、不可预测的,我们不能臆想它必然会奔向一个先行预期的好结果;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准确代表他人的意愿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阿伦特看来,渲染自己对他人福祉的使命感,即宣称自己是为了他人而行动(而非和他人一起行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僭妄或逾矩,因为这一做法将他人摆在了与自身不对等的对象或客体的位置上,违背了人际之间最为基本的平等原则。尊重和自己一起行动的人,愿意听取和商讨他人的观点,这是政治行动的内在要求,是由人的复数性境况所决定了的,也正是这一蕴含着平等与差异的双重特征的基本境况,为政治行动设置了最起码的道德限度。在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下,阿伦特认为,人际之间的相互尊重就“类似于……‘政治之爱’(philia politikē),是一种既非亲密也非封闭的‘友谊’;它是从置于我们之间的世界空间的距离中产生出的对他人的敬意”⑫。因此,和亚里士多德的友谊一样,阿伦特式的友谊也是一种既存在于政治领域之中也存在于私人领域之中的德性,它为两个领域提供了某种共同的基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阿伦特所说的友谊并不是人们在日常观念中所认为的那种兄弟之情或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平等却又不同的个体之间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互动和对话。相比之下,兄弟之情往往出现在底层民众中间,那些处境艰难的人们常常会因为相同或相似的遭际和诉求而聚在一起抱团取暖、惺惺相惜。在兄弟之情中,人们虽然得到了亲密感的慰藉,但世界却消失了,因为兄弟之情会使人们过度地关注个人情感,甚至会遮蔽真正的友谊。因此,阿伦特非常担心,在黑暗时代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会使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求和自己类似的人挤在一起,畏惧冲突,或许他们也会容忍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但他们却永远不会真的去倾听、去参与对话。相反,“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⑬。较之于兄弟之情,友谊的特征则在于,向他人的观点敞开,与持有不同想法的人真诚交谈。这种在朋友之间或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交谈和对话可以营造出一个空间,让参与者们既相互分离又彼此联结,就像大家共同围坐在一张桌子上一样。阿伦特认为,人的“世界”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空间组成的,但是,如果社会或必然性的压力使我们彼此靠得太近的话,这个世界就消失了。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于友谊而言,还是对于政治而言,同质化或同一化都是致命的,因为“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⑭。
进而,由于在阿伦特那里,友谊是思维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因此,这种同质化对于思维来说也是致命的。在阿伦特看来,思维,即我和我自身内在的对话,以语言(speech)——即交谈(conversation)——为先决条件,而交谈则又显然预设着作为交谈对象的另一个人的在场。无论我是与自己交谈还是与其他人交谈,“指导性经验是友谊,而不是自我(selfhood);在我与自己交谈之前,我首先与其他人交谈。在与其他人交谈的时候,我检查双方的谈话可能涉及的东西,然后我发现我不仅能与其他人交谈,而且也能与自己交谈”⑮。并且,先于思维的、我与其他人的交谈也预设着我对差异性——即我与交谈对象之间的分歧、异见——的尊重。
可以说,在阿伦特的语料库中,思维、尊重、友谊和复数性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群。进行思维活动就像是与一个朋友交谈,而与一个朋友交谈就像是拥有了另一个自我。阿伦特指出,在被她视为思想者之典范的苏格拉底那里,始终没有放弃与雅典人的交谈,尽管他本来也可以独自在静默中思考。真正的思想者会在交谈中不断地扩大朋友圈子,就像苏格拉底那样,“经由希腊过去的杰出人物,俄狄浦斯和缪塞斯、赫西俄德和荷马,在冥府里扩大……朋友圈子……永不停歇地与之开展以他为主宰的思想对话”⑯。从而,“苏格拉底的合二为一消除了思维的孤独,其固有的两重性指出了作为普遍法则的无限复数性”⑰。
在阿伦特那里,人际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维系着复数性,而复数性则维系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平衡。因为尽管私人领域中的个体(包括思想者)关注的是个人的利益或兴趣,而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即公民)关注的是共同体或国家的利益,但这两种视角无疑都包含着对“世界”的关注,这个世界既不是纯粹自我的世界,也不是纯粹他人的世界,而是一片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交集地带。也就是说,只有当思维伙伴们共同投身于政治行动之中时,这个空间(即世界)才是实在的。在此意义上,友谊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同时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性”。一方面,就公共领域而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维系和容许复数性或公共空间的存在,那么它向民众许诺的一切个人权利终将沦为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就私人领域而言,在家里、在夫妇之间或者亲子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友谊。首先,在夫妇之间,“如果两个人不沉迷于‘牵系我们的纽带使我们成为了一个人’的幻觉之中的话,他们就能在彼此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⑱。其次,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当孩子作为“爱情自身的产物”而降生时,就“切入”了“两个相爱的人中间”,也就是说,孩子是一个“居间者”,他/她“把相爱的人联系起来并且为他们共有”,从而,“孩子意味着在现存世界中切入了一个新世界”⑲。阿伦特之所以严厉批判古代的家庭领域,并不是因为它的私人性,而是因为那里的人际关系过于胶着,在平等者之间既缺乏倾听或表达不同观点的机会,也缺乏相互尊重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的家庭领域中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交流和相互尊重,从而,那里是单调而贫乏的。
总之,对于阿伦特来说,一种完整的人的生活既需要公共领域的存在,也需要私人领域的存在。不过,当人际之间的无形空间得到确保、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也划分停当之后,人们还须在某些政治德性上达成广泛共识。也就是说,个体必须具有应时而动的勇气,并且尊重和恪守这一行动所涉及到的那些对他人的承诺。个体也不能信誓旦旦地臆想行动的成功,而必须愿意去面对和宽恕意料之外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个体必须尊重人的复数性,尊重他者的独特性,并积极培养阿伦特式的友谊。这种政治性道德并不自我标榜为绝对真理——它既不要求超验的绝对,也不要求形式的绝对,但它依赖于人们对人的境况的基本共识,并主张尊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因而与人们关于现代自由社会的愿景是相容的。
注释:
①⑧ 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408页。
②③④⑤⑥⑦ 阿伦特:《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59—61、60、64、71、77页。
⑨ 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⑩⑪⑫⑭⑲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61、150、188—189、38、288页。
⑬⑱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0页。
⑮⑰ 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09页。
⑯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