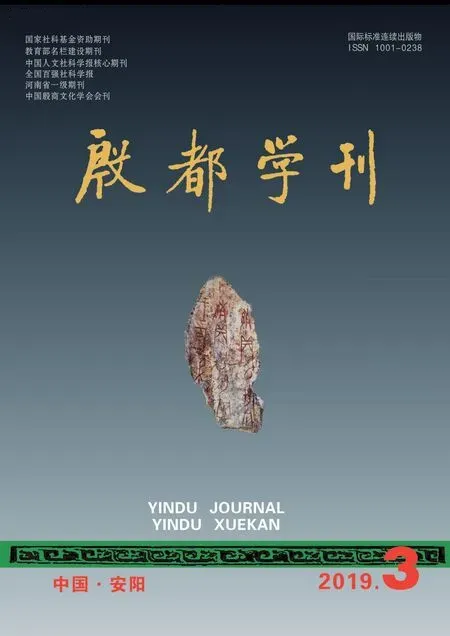从阴阳调和到夫妇合和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故事研究
吴 枞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汉画像石作为古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而且包含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是研究汉代文化的重要资料。汉画像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题材具有非常强的故事性,其故事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生动,用图画的形式再现了汉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伏羲女娲图像作为汉画像石中的一类重要题材,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从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汉画图像来看,伏羲女娲传说故事在两汉时期已经非常流行,而且伏羲女娲的故事文本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也有相关记录。
另一方面,汉画作为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表达对祖先纪念的一种寄托方式,是家庭关系的特殊表达形式,汉人通过墓葬图像来体现家庭和谐的人伦秩序。家庭的和睦得益于家庭中夫妇男女关系的和谐,伏羲女娲所表现的理想两性关系是阴阳调和思想在人类社会的反映。伏羲女娲故事作为阴阳关系的象征在汉代广泛传播,并大量出现在汉画中,凸显了伏羲女娲故事在汉代独特的思想价值,是以夫妇之道体现阴阳和谐,其形象是重要的性别象征与伦理符号。
一、伏羲女娲的阴阳调和象征
从目前已知的先秦文献看,伏羲和女娲并没有关联性,二者分属于不同的传说故事。关于伏羲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庄子·大宗师》和《荀子·成相》出现了“伏戏”,《管子·轻重戌》记载为“虑戏”,《易·系辞下》作“包牺”。目前学界将《庄子·大宗师》和《易·系辞》的创作时间定为战国末年,而《易传》记载了伏羲制八卦的传说,由此可知,伏羲制八卦的传说应该产生于战国末年之前。而从记录文本的特定地域来看,关于伏羲的传说流传范围较广。从《易·系辞下》载“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1](P343-344)可知,此时人们认为伏羲教导人们稼穑渔猎,更重要的是制作了八卦,因此可以推测阴阳之事。关于女娲的记载首先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楚辞·天问》中,郭璞注《山海经》载女娲可以“一日中七十变”[2](P355)。而《天问》则已经开始将女娲作为化育万物的始祖神。汉代以后,《淮南子》《尚书大传》《论衡》中开始出现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
伏羲女娲最早并列出现在《淮南子》中,高诱《淮南子·览冥训》注曰:“女娲,阴帝,佐虑戏治者也。”[3](P146)这里的伏羲女娲开始与阴阳联系起来。《论衡·顺鼓篇》云:“俗图画女娲之像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4](P205)《论衡》将阴阳与男女结合,并以伏羲女娲为载体。此后,《鲁灵光殿赋》中也将二者并列描述为“伏羲鳞身,女娲蛇躯”[5](P79)。在图像当中,洛阳卜千秋墓已经出现了伏羲女娲的图像。此后汉画中,伏羲女娲逐渐成为了固定的对偶神出现,极少出现单独的伏羲或女娲图像,二者逐渐发展成为两性关系和夫妇关系的象征。
关于二者之间为何会形成对应关系,姜亮夫先生在《羲娲合德说》中指出,伏羲女娲虽然从现有文献来看分属于不同的神话传说,但二者本质上是由生育十日的月神羲和分化而成。《尚书》将“羲和”分为“羲”与“合”,而《山海经·大荒西经》则认为“羲和”生日月,是“主日月之神”,姜亮夫先生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传说的分化作用。[6](P147)由此,战国以后,伏羲女娲分别成为了日神与月神,并形成了对应关系。从图像来看,马王堆帛画正反映了羲和演变为日神、月神的现象。冯时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也提出了这种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伏羲女娲作为对应的阴阳神,化育四神,从而衍生出万物[7](P15-18),代表着阴与阳的“生生”本质。
作为阴阳的代表符号,日月始终与阴阳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表现这一哲学思想的重要形式。《史记·天官书注》中记载:“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8](P1289)日月与阴阳之间构成对应关系。同时,在汉画图像中,伏羲通常配以日轮,女娲则与月轮联系起来,如洛阳西郊前井头的彩绘壁画(见图1),伏羲男身蛇躯,八字长须,头戴冠,身旁有一日轮,女娲人首蛇身,头戴冠,旁有一月轮。图像中伏羲女娲与日月的组合与二者作为日月神的身份有密切关系。由此来表现伏羲与女娲如同日与月一样,分属于阴阳二性,二者并列用于表现阴阳二物间的互补关系。作为阴阳象征的伏羲女娲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二者间差异性和同一性相辅相成,互补性为其平行性提供了保障。
二、伏羲女娲的夫妇合和象征
男性作为阳的一面,女性作为阴的一面,分别与阴阳和日月呈对应关系。而夫妇结合,更体现了阴阳的交合,正如《白虎通·嫁娶》描述曰:“男二十五系心,女十五许嫁,感阴阳也。”[9](P456)阴阳思想的核心是双方相互渗透交合,促成平衡和谐的动态关系。同时,夫妇关系是两性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也是两性伦理关系的开始,《易》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1](P360)人伦开始于夫妇,因此以伏羲女娲表现夫妇关系是重要的图像类型之一。
日月与阴阳的意象中包含着夫妇之意,如《礼记·礼器》云:“大明(日)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10](P523)阴阳关系中所隐含的两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夫妇关系,如河南唐河出土的画像石(见图2),女娲正面立,双手托举月轮,伏羲倒立,双手托举日轮,二者尾部相交,且呈现上下颠倒对应状态,表达了阴阳交互的寓意。
然而,从文本来看,两汉时期仅有《风俗通义》记载:“女娲,伏希之妹。”[11](P599)确认了伏羲女娲的兄妹关系。真正详细记载伏羲女娲故事的文本首先出现在唐代,李冗在《独异志》中详细描述了伏羲女娲由兄妹而成为夫妇的故事。而从出土文献来看,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已经记载了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的故事:“曰故(古)大能(龙)雹戲(戏),出自□(华)□□(臂),居于(雷)□(夏)……乃取(娶)……之子曰女皇,是生子四□,是襄天□(地),是各(格)参□(化)。”[7](P15-18)这是伏羲女娲结婚生子的创世神话,也佐证了最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将伏羲女娲作为夫妇的传说故事。
从已经发现的汉画来看,表现伏羲女娲夫妇关系的题材在图像中反复出现,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故事早在两汉就已经在民间流传。表现伏羲女娲夫妇关系的图像基本构图模式多为伏羲女娲相向而立,尾部相交或多次缠绕,如《公羊传》载:“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12](P190)交尾象征着阴阳和谐、男女交合的协调状态。图像所表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且从图像的具体构成来看,构图模式复杂多样,这是因为不同地域所流传的伏羲女娲故事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汉人心中,伏羲女娲作为婚姻与人伦关系的制定者,规和矩是她们制定婚姻关系的象征和代表。那么,图像中的伏羲女娲交尾,且手执规矩,是否也预示着二者制定并遵守婚姻的制度,作为汉人婚姻的示范呢?武氏祠将女娲纳入三皇体系当中,肯定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巨大贡献(见图3),在这幅图像中再次出现伏羲女娲呈现手执规矩、交尾的情态,且图中出现一对缩小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似在学习伏羲女娲,按照他们制定的婚嫁规范,维系着夫妇间的情义。
文献中虽然对夫妇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法律伦理要求,但是从汉乐府等民间歌词“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13](P1355)可以看出汉人在生活中对夫妇恩爱的追求。《白虎通》与班昭《女诫》也将夫妇间的恩义作为维系夫妇关系的重要因素。汉画图像中表现夫妇间合和的景象呈现出了较大的地域差异,其背后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四川地区的图像生活化气息较浓,与当地灵动泼辣的地方风俗相关,图像生动地再现了两汉时期这一地区夫妇间的亲密互动与恩爱,较为直观地表现合欢场面,主要包括伏羲女娲拥抱、依偎、贴脸亲吻、交尾,而且表现多重交尾的状态。两次、三次交缠龙尾的情况较为普遍,如郫县一号石棺的图像(见图4),伏羲女娲一手托举日月,一手挽过对方肩膀,贴面亲吻,龙尾两次缠绕,表现了伏羲女娲间的亲密互动。
两汉时期,南阳地区作为中原腹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因此该地区的画像伏羲女娲的表现形式较四川地区委婉,且多以象征物来表达对夫妇关系的美好寄托。如南阳汉画像石馆收藏的一幅图像(见图5),伏羲带冠,女娲梳高髻,二者相向而立,共执一灵芝或伞盖。伞盖和灵芝象征着美好品德,由夫妇二人共执灵芝,表现了夫妇合和,同时表达了对“男女礼顺”的追求,正如东汉王符所提出的,个人品德在夫妇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他地方的汉画也各具特色。陕西地区作为西北的繁荣地区,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夫妇间平行的性别关系。山东地区作为儒家文化的腹地,始终倡导传承践行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的规矩,强调婚姻关系、人伦秩序和夫妇关系。图像的差异反映了地域特色,同时差异性的变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图像的对偶特征与共性特征,所有的图像中,伏羲女娲多呈现交尾状态,主题皆为凸显夫妇间的情义。
表现伏羲女娲夫妇关系的另一类图像为高禖与伏羲女娲。媒人的出现,体现了传说中伏羲女娲为兄妹而成婚的故事,由高禖为媒介,才能更好地解释二者的结合。如沂南北寨汉墓的图像(见图6),伏羲女娲手执规矩,被高禖神紧紧抱住,表现了二者在外界力量的帮助下结为夫妇的传说。同时,在二者正式结合之后,由于高禖的存在,夫妇婚姻的规范得到了遵循,起到了垂范的作用。
表现夫妇关系的伏羲女娲图像始终以二者之间的交合与协调为表现的重心,体现了夫妇间的情义,充分体现了“夫妇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此类图像的数量及分布范围来看,汉画对夫妇和谐关系的追求并不是个别人的愿望,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追求。
三、伏羲女娲的伦理典范象征
表现中下层伦理诉求的伏羲女娲图像其实并不完全来自民间的朴素愿望,还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阴阳思想融入儒学是汉代儒学的重要特征,董仲舒用天人感应思想解释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强调世间的人事都是由天命来主宰,人事要顺应天命。董仲舒借此为君权神授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为汉王朝天赋神权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保障。
在董仲舒提出大一统的儒家政治理论后,汉代儒家学者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来阐释汉代政治的合理性,巩固汉代儒家思想文化。所以到汉代,汉儒在征经明圣的论述中进一步对上古时代进行了神化。三皇五帝在汉儒心目中不再是普通的帝王形象,而是圣王,因为他们都是秉天而生,自非凡体。所以他们是感孕而生,天生异象,伏羲女娲也是如此。从伏羲女娲故事发展看,自董仲舒对儒学重新阐释之后,他们的事迹开始广泛出现在汉儒作品中,而神异的故事增长迅速,尤其是在两汉之交谶纬思想泛滥的时代。《诗·含神雾》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12](P364)《孝经·援神契》曰:“伏羲山准,禹虎鼻。”[12](P1689)《淮南子》也开始有了女娲补天,再造天地之事。由此,伏羲女娲本身所具有的理想人格也成为人类道德的象征,他们践行着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实践。因此伏羲女娲成为了道德实践的权威,也是理想伦理关系的象征。
此外,董仲舒认为天地自然遵循阴阳五行的变化规律运行,自然的和谐,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阴阳平衡的结果。而“人”是万物之灵,禀天地之气,循阴阳之理,自然应当效法天地的高厚覆载之德,成人伦之道。儒家之于人伦,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并演化成仁、义、礼、智、信五德,五德与五行相对应,天德与人德相合。其中夫妇是人伦道德之纲,在社会关系中尤为重要。董仲舒提出:“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夫为阳,妻为阴。”[14](P439-440)人类的绵延承继是男女阴阳和谐交感的结果。夫妇关系和谐甚至影响社会秩序和谐,荀爽提出“夫妇人伦之始”是“王化之端”[15](P2052-2053)。伏羲为三皇之首,在后世被誉为人文始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地位真正被确立是在汉代。伏羲女娲图像在汉画中如此普遍出现,说明伏羲在汉代人心目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先秦时期伏羲和女娲并无关联,而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则基本固定为男女关系、夫妇关系,伏羲女娲实际已作为人伦表率为汉代人敬仰。
自孝武帝施行崇儒政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出于颂赞大一统汉代政治和弘扬儒学的需要,汉代儒生创造了许多神化儒学的故事,其中包括伏羲女娲,将伏羲女娲尊为圣王贤后形象,他们生活在天界,与日月相伴,有祥云衡枢环绕,并且可以驾龙御凤,飞升天地。外表形象上,他们常常为人首蛇身。这一奇异形象在汉代小说故事中也常常可见。如《春秋·元命苞》载:“伏羲大目,山准龙颜……伏羲龙状。”[16](P589)而《春秋·演孔图》道:“伏羲大目,是谓舒光,作象八卦,以应天枢。”[16](P573)综合来看,伏羲的形象为眼睛很大,鼻子很高,就像是龙的脸一样。这种龙形其实与汉画的人首蛇身很相似。这种特异的形象只有在上古的圣王身上才会出现。而汉画中伏羲的面部实际上也是按照帝王的形象塑造的,浓眉髭须。为了与伏羲圣王的形象匹配,女娲的形象也与贵妇的形象相类,女娲浓眉小口,河南新安磁涧镇里河村壁画墓的女娲甚至还留了汉代流行的堕马型发髻。这说明社会中下层百姓接受了神化的伏羲女娲形象,并利用这一形象寄托他们对夫妇间伦理关系的美好希冀。伏羲女娲图像表达社会中下层对儒家社会伦理道德的认识,反映汉人伦理思想的形态,从而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
在汉画题材中,伏羲女娲的故事题材特别引人注目。从伏羲女娲故事的生成到图像中故事主旨的转变来看,伏羲女娲故事脱胎于先秦时期的阴阳思想,但在图像中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合和的主题,这也就意味着伏羲女娲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存在一个从抽象阴阳思想到具体夫妇关系的发展过程,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不仅是两汉儒学对伦理道德的提倡与推广,更是社会中下层对和谐夫妇关系的推崇,而伏羲女娲图像所特有的教化作用使其成为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表现载体,同时也成为了表现美好愿望的载体,图像的形式再现了汉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主要是汉人基本的性别观念和伦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