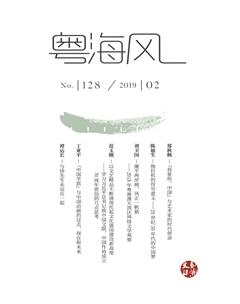严复与梁启超的小说观之比较
王岫庐
谈到小说这种文体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学界通常认为促使近代小说进入兴盛状态的关键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小说思想的论文,如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提出“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联系起来,对近代文学的发展确实产生多方面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启超之前,严复、夏曾佑1897年发表于《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已经开启了“小说界革命”的先声。严、夏二人对小说的文体特点和影响力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该文对小说的普遍主旨、小说通俗喻众之原因,以及说部之毒的根源,都给出了相当有见地的观点。
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首先试图从人类普遍性情的角度,拈出“公性情”三字概括小说之主旨。文中指出:“凡为人类,无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之地,石刀、铜刀、铁刀之期,支那、蒙古、西米底、丢度尼之种,求其本原之地,莫不有一公性情焉,”各种政教,亦由此“公性情”而生。该文更明确指出:“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严、夏二人援引中国及西方神话、历史,尤其是荷马史诗所描绘的公元前 13 世纪中叶的特洛伊战争、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传奇时代,最终得出一个普世性的结论:“问尝发陈编,考前事,见夫兴亡之迹,波谲云涌,而交柯乱叶,试讨其源,大都女子败之,英雄成之;英雄败之,女子成之;英雄副之,女子主之;英雄主之,女子副之。”换言之,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英雄”“男女”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公性情”,两者之间有无限可歌可泣之事,足以流传后世,因此小说乃至文学以“英雄”“男女”为主旨,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严、夏二人文中所归纳的小说主旨,并非凸显个体经历,亦非中国古典小说强调的人伦道德,而是一种跨民族、跨种族、跨文化的共性,是一种科学、人类学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普世本质。
这一点与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所提及的“英雄”“男女”对照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晰。梁公将中土小说不入流的原因归结于:“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将“英雄”“男女”分列“诲盗”“诲淫”两端,这一评价更多中国古典人伦道德标准的评判。与“英雄”“男女”相对,梁启超提出“政治”作为小说之主旨,开篇即言“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后文又进一步说明,欧洲学者将“政治之议论”寄于小说,为各国变革带来契机和推动。这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文所提出的“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主张,一脉相承。梁启超看重的是小说之“用”,本质上说,是一种传统实用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承担道义、道德、敉化的工具。相比之下,严复的文学观已经在很大程度发生变革,体现出特定时代的科学主义精神。
小说对人心民俗的影响力,后世多引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文所说的四种力:熏、浸、刺、提。梁公借用佛教用语,总结艺术审美移人性情的四种力量,指出小说之所以“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是因为小说可以潜移默化(熏)、持之以恒(浸)、突发移情(刺)、与自我领悟(提)。梁启超的论说是一种符合(个人)文学阅读审美体验的描述,而严、夏二人的论说则更多从社会、历史、语言、文字等角度,以客观而科学的方式解释小说影响力之原因。
严、夏二人文中谈及文字、语言,以及“经”“史” “子”“集”的关系,指出“纪事之书”(“史”“稗史”)的流传有易、有不易,而二者取决于五种原因:一、“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其语言文字为此族人所不行者,则其书不传”;二、“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若其书与口说之语言相远者,则其书不传”;三、“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四、“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五、“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这五个原因,前两个说的是媒介,以通用的、与口语相近的文字语言写成的作品,更易流传;第三个原因在于写法,细节描述详细,一览无余无须耗费读者太多心力的作品,更易流传;后两个原因在于内容,书写之事与日常生活关联密切,情节发展符合人心愿望的虚构作品,更易流传。严、夏二人从作品之媒介、写法、内容三个方面,总结了文学作品流传的规律,阐明史书(如《二十四史》)不容易传,而稗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等)书行自远的原因。
将梁启超与严、夏二人的论说对照来看,可见两者思考路径的异同。梁公所言小说“熏、浸、刺、提”四种力量,与小说本身的形式无关,而关心小说对读者的影响,论说路径符合重感悟轻论证的经验主义批评传统。相比而言,严、夏二人关心小说的媒介(即语言和文字)、写法、内容,对小说的本体的思考更客观、科学。
对于利用小说的影响力使民开化,严、夏二人与梁启超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对国民性的理解,以及小说能够发挥的作用,各人理解又有差别。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并具体阐释为“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将“人心”“人格”与“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并列,均视为小说发挥影响、造成革新的领域,且“人心”“人格”的塑造,是小说发挥影响最根本、最终的旨归。为了实现群治的目的,梁启超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人妖巫狐都看作是毒害社会的思想根源,而转而提倡政治小说。
严、夏二人对中国古代小說的困境有和梁启超不一样的理解。《〈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将宗教、政治等社会现象的本源,追溯至“公性情”:“政与教者,并公性情之所生,而非能生夫公性情也”。换言之,晚清中国亟须革新的方方面面,均可以归为对“公性情”(即英雄、男女)的营构。中国古代小说多写“英雄”与“男女”,这原本是人性最本质及社会最本源的“公性情”,但是“浅学之人”从中只能看出诲盗诲淫,而无法理解隐藏的精微深意,因此造成“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的局面。严、夏二人在文中并没有阐明小说的理想范式,但却道出了以古代小说的困境之源:读者之浅学。这背后,又隐约显明了一个更大的逻辑困境:若没有通情达理的读者,小说又何以营构通情达理的人心?
梁启超眼中,通过小说实现新民的路径异常清晰明白。旧式小说诸如才子佳人、江湖盗贼之列一概不足取,应该以政论为主旨。由于小说“熏、浸、刺、提”,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取小说为载体,传播经世济国的大道理,也应该能直达人心,实现新民与群治的目的。而在严、夏二人的笔下,这个问题却变得更加复杂乃至吊诡。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的影响力,源自小说作品之媒介、写法、内容三个方面的共同合力,小说内容书写“日习之事”、符合读者愿望的“虚事”,恰是小说影响力原因之一。说得更浅白些,小说“公性情”(“英雄”“男女”)的出色描绘,往往是小说能够书行自远的原因。如果看不到内容和形式的一体性,而只是从经验出发,认定小说这一文体形式易传,于是直接借来包裹上大道理,并认定这样的新小说可以塑造新国民,就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事实上,单纯依靠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样充满政论色彩的政治小说,确实不可能完成星火燎原的启蒙任务。
严、夏二人文中没有阐明小说的理想范式,但其中对“浅学之人”造成“说部之毒”的观点,与严复后来一贯秉持的精英主义之立场是一致的。即便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呼吁要效法欧美日本,广为采辑并翻译小说以使民开化,但同一时间严复本人并没有走上翻译通俗小说启发民智的道路,而正潜心以桐城笔法翻译后来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天演论》。除此之外,在1902—1909年间,严复还翻译出版了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英国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八种重要西学著作。
1902年,梁启超和严复就《原富》翻译问题曾有一番商榷。《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梁启超介绍严复译英国亚当·斯密《原富》,一方面肯定严复的译作:“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时提出批评:“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墓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提醒严复“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以国民也”。对此,严复的回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严复的西学翻译,以“多读古书之人”为自己的目标读者,而非“浅学之人”。梁启超和严复这番就翻译方法、目的和读者的商榷,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小说界革命”之初,二人对“小说新民”方案的理解和期待早有差别。
梁启超曾说“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把小说看作是天下人都会读的东西,又试图借小说之俗,传播新知与道理。严复从小说本体的角度,分析出小说对于人心民俗的影响,但并不预设小说是人人都会读,能读懂的,对“浅学之人”之人而言,小说的精微之旨依然深隐难求的。因此严复虽然也表达了通过小说营构人心,改变现实的愿望,但对于如何着手通过小说改变这个“通人少而愚人多”的世界,严复并无明确的计划。而事实上,后来严复转向西学翻译,走上与梁启超提出的以小说实现新民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读者的设定,梁启超与严复或有不同,但无论设定读者是普通国民、还是饱学之士,二人都将读者放在异常重要的位置。借用李欧梵的观点,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读者的重视,是因为他们“想象的读者和他想象的中国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晚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李欧梵的这一理解,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理论启发。严格意义上,这两个概念都无法完全适用晚清中国的语境,因为当时文化政治领域均并不具备相应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对政治进行理性批判与探讨的空间,是中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基础,在时间上早于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晚清中国,理性对话的“公共领域”尚未正式成型,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已经不可遏制地涌现,二者几乎同时出现,互相冲突而又合二为一。
梁启超、严复二人新民路线的差別,对读者设定的差别,也正是体现了他们在缔造期对“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的不同理解与设想,乃至对何为中国的理解差异。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和发展,没有哪一个设计最终完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背后既有印刷媒体逐渐促成的“公共领域”的影响,也混杂着对民族国家的重新理解和定义,而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也为现代中国“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和解与共进,开拓了新的可能与方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