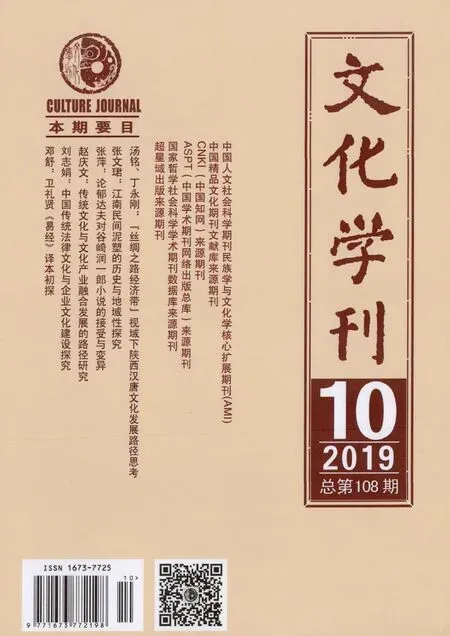浅析小说《碧奴》中的主要意象与主人公的救赎之路
叶 塑
《碧奴》是作家苏童2006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作者对中国神话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一次大胆而创新的重述。新故事仅保留原故事的起因(女主人公的丈夫被抓丁)与结尾(丈夫死,女主人公哭倒长城),其余都是全新的讲述。《碧奴》讲的是一个有关眼泪的故事。女主人公经历了一个由“泪的禁忌”到“泪的解放”的自我救赎的过程,因此眼泪是全书最重要的意象,而碧奴的唯一旅伴——一只盲眼青蛙,与她在人物设定上有种种相似性,让人不禁探究它在故事角色之外的象征意义。因此,笔者将从这两个意象入手,对碧奴由奴变神的救赎之路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一、源起:碧奴之罪
尽管故事的开头没有提到碧奴的罪,但她显然是有罪的,所有北山下的人都有罪。而且,“碧奴”的“奴”字本意是奴隶。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奴婢,古之罪人”,可见,“奴”即有“罪”。
那么,碧奴罪在何处?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眼泪之罪,二是女性之罪。眼泪的罪追溯到好多年前,北山百姓因为给国王的亲叔叔信桃君哭灵而获罪,从此眼泪成了不可触犯的禁忌。碧奴作为哭灵人的后裔,生来便有罪,生来就不能哭泣。另一桩罪来自她的女性身份。在北山下,男孩的出生令父亲“骄傲”,男孩的来历“与天空有关”,给男孩起名时,“父亲抬头看天,看见什么,儿子就是什么”。女孩出生时,父亲必须离家“以此逃避血光之灾”。给女孩起名,父亲看地,“地上有什么,那女儿就是什么了”。女儿家如此“低贱而卑下”,加上“更容易犯(哭)戒”,便多了一桩罪。
这就是碧奴的身份设定,她一出生就背负了这两条原罪,但比起身份的低贱,更可怕的是她的生活环境,周围人的刻薄与恶毒,政府的官僚与残忍,给全书定下了黑暗又抑郁的基调。
刻写民众之恶,是新故事与旧神话的一大区别。叙述者不仅批判了统治者,“更指向芸芸众生,指向围绕在碧奴周围的那些底层被统治者”[1]。
民众之恶表现在“妒、贪、奴、狠”这四点上。先说妒。肃德老人从哭灵事件中幸存,原因是想到自己“只有羊,一头猪也没有,信桃君偏偏送(猪)给堂兄,不送给他……一生气,眼泪就消失了”。因嫉妒而幸存,此处极具嘲讽之意。再说贪。当哭灵的百姓发现是国王下令赐死信桃君时,“他们的心情不那么悲伤了……有人还顺便把自家的羊赶到信桃君的菜园里,啃了点萝卜秧子”。奴指的是奴性,当哭灵者发现是眼泪惹来了杀身之祸时,他们不与官吏辩解,不作任何反抗,反而大叫,“他也是去哭灵的,她也是去哭灵当,为什么不抓他们?还有好几百人呢,大家都哭了!”从这么一幅民害民的可悲景象可见奴性人格早已根深蒂固于百姓心中。至于狠,柴村的母亲们在面对止不住哭泣的婴儿时,“她们解决烦恼的方式是秘密的,也是令人浮想联翩的……那些啼哭的婴儿不见了,那些啼哭的婴儿,怎一个个都不见了呢?”平淡冷静的文字反衬出事件的可怖与民心的残忍。
读到这样的身份设定与社会心理背景,我们不难预料,碧奴得到众人协助完成寻夫之旅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她将面对无数的嘲讽与艰险。这趟旅途注定是一条通过受难完成自我救赎的路途。
二、在路上:泪与成长
碧奴的个体觉醒与精神成长是围绕眼泪展开。北山下的各个村庄都是禁止哭泣的,所以各村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应对方法。桃村的女性琢磨出了“奇特的排泪秘方”,每个人都能自如而隐秘地排泪。碧奴一开始“不如别的女孩聪明,也就学不会更聪明的哭泣方式”,但随着故事展开,一次次的遭遇与绝望迫使她的内在力量逐渐苏醒,她排泪的方式越来越丰富,泪的力量也愈发强大。笔者通过表1将这种变化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一一列出。

表1 碧奴流泪方式与眼泪力量的变化
碧奴流泪是出于难过和委屈,泪水也无形中洗刷了她的罪。从她的泪水能感化众人的那一刻起,她开始脱下为奴的罪衣,到最后泪水感化了山石和动物,哭断了长城,她彻底完成自我救赎,成为一个传奇。
选择眼泪作为碧奴精神成长的标志性意象,是因为女性与水有隐喻层面的互指同一性。首先,水是沉静、温柔、包容的,这些特性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一致。其次,“女性爱哭啼……‘眼泪’与女人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关系”[2]。小说中特别将柴村女性与桃村女性作了对比。柴村女孩由于从不哭泣,“面容普遍枯瘦无光”,她们“没有青春……看上去都像游荡的鬼魂”,而桃村女孩因为懂得排泪,会哭泣,所以“灿烂如花”。碧奴是桃村的代表,长着“一张清秀端庄的脸”。可见眼泪/水正是女性的青春魅力所在,是女性生命力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碧奴的母亲。她母亲“死得早,传授(排泪)的秘方也就半途而废”,碧奴因此控制不好泪水,从小遭人耻笑,但细想一下,也许正是这“半途而废”减缓了碧奴奴化的进程,为她的固执与叛逆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对控制泪水技能不娴熟,让她的个体力量得以被唤醒并逐步壮大。
三、旅伴:盲蛙
丈夫被征了役的女人很多,却没有一人愿意与碧奴结伴寻夫,还用“冰冷的目光审问她”,骂她“疯女人”。于是,最后成了她旅伴的竟是一只盲了眼的青蛙。
青蛙的出场牵出了另一条故事线。它不可测的怪异行径,给故事又增添了几分魔幻色彩。青蛙是小说中又一个重要意象,与碧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她们因为相似的目的踏上了相同的旅途:碧奴寻夫,盲蛙寻子。其次,青蛙与碧奴一样固执,一样“疯”。盲蛙原是一位寻找儿子的盲妇人,别人告诉她,男人都被征往北方,应该弃筏北上,但她依然固执地乘筏而下,日夜不停地叫喊儿子的名字。最后,青蛙与碧奴都有特殊的武器——眼泪。碧奴的眼泪能哭断树枝,哭成泪箭,还害人犯了“思乡病”;盲蛙眼泪中“那奇异的光芒”能打动马人,让他放走自己。更巧的是,“碧奴”的“碧”正是青蛙的颜色,这是否暗示着两者间更紧密的联系?
这就要谈到青蛙意象的普遍象征意义。
蛙意象的形成可追溯到人类早期的蛙图腾崇拜。广西壮族在农耕社会时期出于对雨水的需求,“把与雨水有关的青蛙作为崇拜对象,奉为氏族的图腾”[3]。澳洲土著地区与北美印第安地区也都把青蛙当作“雨季的象征”。除此以外,由于“雨水的降临也预示着多产,旧时墨西哥人就把蛙与多产联系在一起”[4]。另有学者指出,蛙的生理特征——多产与丰殖“更加凸显了蛙的母性特质”,且捏泥造人的女娲也本是蛙身[5]。综上所述,蛙意象常与雨水、多产、母性、重生等概念紧密联系。水自不必再提,上文已提到盲蛙与碧奴都有用泪水感化人的本领。而说到蛙的多产,不得不说说碧奴的来历——葫芦。由于葫芦“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攀援性和旺盛的繁殖力,被视为生殖崇拜的信仰物”[6],所以在生殖/多产这一层面上,青蛙与碧奴再度吻合。
基于两者间的种种相似,笔者认为,盲蛙绝不仅是一个故事角色、一个旅伴,它还代表着碧奴的精神意志,在碧奴决心坚定时它出现,在碧奴彷徨迷惘时它消失。当碧奴最后背负着重石艰难地爬行在官道上时,盲蛙再度出现,“轻盈地指点着她的爬行路线”,且随着逐渐接近目的地,碧奴的决心与意志力越来越强,“无数来历不明的青蛙排成一条灰绿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大燕岭方向跳,跳”。也可以说,盲蛙既是故事里那个寻子的母亲,也是碧奴的精神母亲,在精神上激励、指引着碧奴走完这条救赎之路。
四、内在动力:女性的爱与欲
回过头来看,最初是什么力量驱动着碧奴走上这一条千里送寒衣的死亡之路?柴村的女巫早就警告过:“你别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你会病死在路上。”但碧奴不为所动,带着未涉世的焦虑感,她埋葬好自己的魂魄——一只葫芦,而后便迎着宿命走去了。我们都知道,碧奴的目的是为丈夫岂梁送去一件冬衣,但正如女巫所问“什么男人的冬衣抵得上你的一条命?”这大概也是许多读者心中的疑惑。万岂梁这个角色自始至终没有出场,两人的互动片段大多来自碧奴的回忆和幻想。虽然有学者提出:“这既削弱了爱情的温度、感染力与神话色彩,又多少减少了碧奴形象的逻辑力量”[7]。但笔者认为,岂梁不直接出现,反倒给读者留下更多空间去想象一个美好丈夫的形象。小说中碧奴几次“看”到岂梁。她看见岂梁“穿着她送去的那套崭新的冬袍,多么英俊多么威武”,看见“岂梁的脸在九棵桑树下面尽是阳光,开朗而热忱”,表现了她对丈夫外貌的喜爱;“她忘记了自己的模样,但岂梁是不可遗忘的”,这是一种忘我的爱;“她记得他的手……粗糙而有力,夜里归来,她的身体便成了那九棵桑树,更甜蜜的采摘开始了……碧奴思念岂梁的手……思念他的时而蛮横时而脆弱的私处,那是她的第二个秘密的太阳,黑夜里照样升起,一丝一缕地照亮她荒凉的身体”,这是结合了性欲的爱。可见,千里送寒衣的内在动力便是碧奴内心的爱与欲。所有女子都有爱和欲,但它们与眼泪一样,被禁锢久了,便爆发不出来了。所以,她们虽然掌握了巧妙排泪的技巧,却也丧失了那一点反抗与爆发的可能性,不能像碧奴一样忘我地踏上生死未卜的千里之途。
五、结语
这篇小说与《镜花缘》的风格十分相似,都是用一个个怪诞的故事来嘲讽世风日下、民心不古的社会环境。不同之处在于,这部小说的落点在女性。苏童在自序中写道:“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一个性别的认识,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孟姜女的故事是传奇,但也许那不是一个底层女子的传奇,而是属于一个阶级的传奇。”所以,虽然受时代和身份的限制,碧奴是狭隘而无知的,而且她疯狂、固执、迷信,她的力量非常朴素,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力量。但也许打动作者的正是“底层女子”的这颗“纯朴的心”,他想让所有人都看到女性身上那水一般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