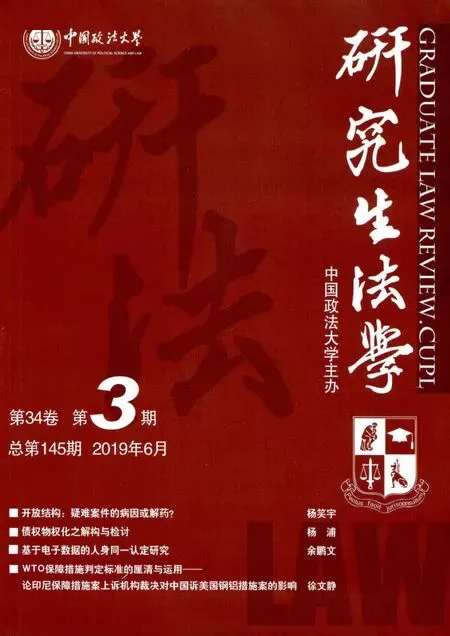全球行政法在国际规制主体中的互补适用
李欣玥
“中美贸易战”后,国际组织的多维规制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任务之一。截止2018年6月,美国已连续九个月拒绝启动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法官的甄选程序,上诉机构濒临瘫痪,WTO的民主性受到了挑战。9月20日,继威胁包括WTO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后,美国再一次对国际组织公开发难,要求“已经沦为服务于石油输出国的垄断组织”OPEC立刻下调石油价格,对OPEC的问责性、合法性发出了质疑。上述举措引起了学界对整个全球治理空间的问责性、合法性和民主性的关注,国际组织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了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即使面对定义模糊、规则不确定等重重困难,国际组织的实践仍然寻找并确定了发展全球行政法的两大进路——“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与“设立专门国际行政法”。本文将对其产生背景、发展情况进行阐述,并对两大进路的实践方法与相互关系进行探究,以期从中找到完善全球行政法的方法,推动其在国际治理空间内的实践。
一、 全球行政法的崛起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孕育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公法。在国际事务的交流往来中,各主权国家很快意识到保证国家和平与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国际合作。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于19世纪正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为各国追求共同利益、解决共同问题提供了平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监管、国际环境保护、国际人权保护以及国际武装冲突中对敌对行动的管制都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1)See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and Richard B.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3)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16.当国际社会的治理与监管责任从有界的政府转移到分解的、又相互紧密关联的治理主体上,一个以国际社会为中心的国际公法(亦被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公法)得以建立,从而促使了国际组织法的成立。(2)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38.
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下,国际组织法是一门涵盖法律原则、规则、体系与制度的,管理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独立学科。(3)See Henry G. Schermers and Niels M. Blokk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Unity within Diversity, 5th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pp.8-16.其调整主体包含五大类国际组织:(1)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2)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3)国际公共企业,如非洲航空公司(Air Afrique);(4)私人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5)混合型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由于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有可能同时属于上述几种类别,国际组织法并未采取分类法对国际组织进行规制,转而将每类国际组织的共性——“三大关系”——作为了规范的轴心。(4)See Jan Klabb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其中,“核心关系”代表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关注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权力,构建起了较具批判性的功能主义框架;(5)功能主义理论是国际组织法领域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该理论认为,国际组织由各国共同建立,以行使特定职能为目的。因此,每个国际组织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其所有行为均服务于该特定目标。尽管这一学说具有争议性,但其仍在全球治理领域为国际组织的管理提供了权威性解释以及可行的法律规则。“内部关系”系指国际组织与其内部部门以及工作人员的关系,体制的权力制衡与民主性是其研究的重点;“外部关系”则为国际组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要涉及国际组织行为的可归责性、合法性问题。自国际组织产生以来,“核心关系”一直是学界、实务界研究与发展的重点,而“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则鲜少得到关注。
批判法学家认为,国际公法之主体与调整对象决定了其必将在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之间左右摇摆。(6)See Jan Klabb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后现代时代中,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已从国家主权转移至国际合作。各主权国家借助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搭建了合作的桥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监管责任也不再独属于政府。在后现代时期的治理、监管责任碎片化、分裂化的倾向下,国际规则也必须随之以外向化、灵活化的角度得以建立与完善。(7)See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0-43.在国际组织法领域,仅在功能主义框架下研究核心关系(即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实现国际社会的深刻愿景——维系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微妙平衡,国际法学家将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视为行政行为,认为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和机制正在履行确实具有行政性质的职能,并在实践中采纳了行政类型的机制、程序、规则与原则以对国际规制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行规范。然而,由于并未在国家范畴之外形成对行政行为的共识,且其机构形态也更为多样化,国际法学界先后提出了三大全球公法(Global Public Law)理论学说:全球行政法(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公权力学说(Public Authority)。(8)全球行政法由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律与正义研究所所长Benedict Kingsbury、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初级研究员Nico Krisch以及纽约大学教授Richard B. Stewart提出;公权力学说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主任、歌德大学法学教授Armin von Bogdandy主要倡导;宪政主义则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Jan Klabbers与上述两大理论共同总结为治理国际组织的重要方法,并视之为保证国际组织行为可归责性、合法性与民主性的有效进路。2016年,伦敦政治与经济大学副教授Devika Hovell梳理了国际组织近年来的发展,对全球公法进行了证成。 Hovell教授认为,当前国际法专家与国际法律师的首要任务并不是阻碍全球公法的形成,恰好相反,他们应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一个管理国际组织的持久的法律框架,去除其官僚主义属性,形成正确的、适当的行为准则。See Devika Hovell, The Idea of Global Public Law: Response to Unbound Symposium Essays, 11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2016-2017), pp.80-83.全球行政法既包含由国际规制主体通过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和具体规则,也包括在监管和运行国际规制主体过程中作出的非正式决定。其有效吸收了各国具有普遍性的行政法原则与规则,以国际组织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价值,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行政法范式规制方式(如设立内部监管机制)以确保国际组织的行为满足透明性与参与性的标准、决策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9)See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and Richard B.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3)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p.15-61.宪政主义则寻求在理想主义视角下,根据世界性普遍价值设定固定的法律规则与稳定的法律框架,在此框架内,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和对话,使国际组织获得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并有效制约和限制国际组织滥用权力。(10)See Jan Klabbers, The Paradox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1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08), pp.151-173; see also Jan Klabbers, Constitutionalism Lite, 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04), pp.31-58.公权力学说则立足于欧洲的宪政主义理念和公法传统,借鉴和参考了欧洲大陆法系,具有鲜明的欧洲公法特色。通过对宪政主义理念、全球行政法范式以及其它学说的结合,强调国际法的公法性以实现有效的权力规制,是较为温和的学说。(11)See Armin von Bogdandy,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Authority: Sketching a Research Field, 9 German Law Journal (2008), pp.1809-1938; see also Armin von Bogdandy et al. eds., The Exercise of Public Authority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Heidelberg, 2010.三大学说中,全球行政法被视为全球治理空间中较能辅助国际组织法以确保国际组织行为具有可问责性、合法性、民主性的新兴理论。(12)以“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为标题关键词搜索HeinOnline数据库,共出现105篇论文。以研究内容划分,65篇论文对全球行政法是否能够有效提高国际规制主体行为的可归责性、合法性、民主性进行了讨论,15篇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全球行政法的发展,其余则探讨了全球行政法在具体国际事务中的适用、以及其在个体国际组织、国际法院或仲裁庭中的实践。从时间来看,第一篇相关论文发表于1988年,直至2005年仅有15篇文章相继面世。2005年之后,全球行政法的有效性成为了争议焦点,并有61篇论文在2005至2010年期间发表。2010年至今,共有44篇论文得以发表,其中大多数承认并强调了全球行政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这一趋势反映了国外国际法学者对全球行政法的积极态度,并进一步说明全球公法在未来全球治理中不可估量的潜力。(检索日期:2019年5月1日)
二、 全球行政法的适用现状
全球行政法学说源自菲利普杰赛普于1956年提出的理念——超国界法(Transnational Law)。(13)See Philip Jessup, Transnational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8.超国界法涵盖了一切调控跨国行为的规则,并承认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相互交互的关系。作为超国界法的衍生理念,全球行政法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有别于国内行政法的特质。根据其定义,全球行政法包括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之标准以及为其形成规则、作出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14)See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and Richard B.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3)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p.16-17.全球行政法不仅规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为,也规制超国家的、以及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或机构;不仅应用了行政范式,也同时吸收了部分公法规则与私法规则,尝试寻找高政治敏感度的问题与社会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法;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国际法,也是与其他国际法以及国际标准相辅相成的国际规则。因此,全球行政法从学术理论到法律的转变是举步维艰的。(15)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37.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进路被采用: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即“自下而上法”)、以及设立专门性全球行政法(即“自上而下法”)。
(一) 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自下而上法
行政法最初的设立目的在于对一国国内公权力的运行进行规制。然而,当具有国际性的主体开始拥有在全球治理空间内执行公权力的能力、并肩负相应责任之时,国内公权力机构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归责难、不合法、民主缺失等问题亦极有可能发生在国际性机构运行过程中。从这一角度出发,借助现存国内行政法对国际组织的行为加以规制似乎是一个成本较低、可行性较高的选择。
1. “自下而上法”的实践
在“自下而上法”的指导下,为国际组织设立决策审查机制成为了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的有效方法。为了能够成功在设立决策审查机制,有三种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了使用,但是只有第一种——决策审查法——具有可行性。(16)See Richard B. Stewart, U.S. Administrative Law: A Model fo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p.65-67.
决策审查法旨在将跨国规制主体的决策处于国内法庭的管辖中,使国内法庭适用一国国内法对国际组织的决策进行审查与规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关于《国家边界服务法》案”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践。该案中,波斯尼亚宪法法庭被要求对审查由《国家边界服务法》(LawonStateBorderService)进行合宪性审查。《国家边界服务法》是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国最高代表在《总体框架协议》(GeneralFrameworkAgreement)授权下签订和平协议,这一授权暗示了《国家边界服务法》实际上是不属于两国国内法庭管辖的。(17)Also known as the Dayton Peace Agreement.然而,波斯尼亚宪法法庭主张该法案在事实上干涉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国的法律秩序,并且两国最高代表在法律上的性质为“事实上的国内权力机关(a de facto domestic authority)”。(18)Constitutional Court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 the Law on the State Border Service, Case No. U9/00, Official Journal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No. 1/01 of 19 January 2001, pp.5-6.因此,由两国最高代表签订并施行的法律在两国国内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可受波斯尼亚宪法法庭的审查。从这一案例中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首先,在特殊情况下,当跨国主体所作决策在事实上可归因于国内公权力机关,则国家法庭可依照本国法对决策进行审查;其次,上述“特殊情况”必须具有高度特殊性。就目前来说,以决策审查法实施全球行政法是“自下而上法”中最具可行性与有效性的手段。
第二种设立审查机制的方法为国际条约审查法。不同于国内法庭审查法,国内法审查法之被审查对象为主权国政府对国际条约的转化、实行程度,而非国际组织所作决策本身。适用此方法后,国内法庭有权依据本国法对本国政府转化、实行国际条约的情况进行审查。若国内审查法得到适用,则将贬损国际法在国际层面的实施,并成为建立外向化全球治理框架的实质性阻碍。(19)See Chris Finn, The Concept of Justiciability in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 in Matthew Grove and H P Lee (eds),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 Fundamentals, Principles, and Doctrin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3.第三种方法为职权审查法。该方法将国内行政官员依照国际条约(或转化后的国内法)行使职权的过程置于国内行政法的规制范围内,不再审查作为行使立法权产物的国际组织决策,而是直接审查权利的行使过程。这一方法将行政审查“宪法化”,使之不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难以得到理论证成。(20)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50.
2. “自下而上法”的不足
“自下而上法”实际上是对国内行政法进行“拿来主义”的实践,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只有程序性概念或规则被“移植”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运行之中。(21)See Chimni B. S., Co-Option and Resistance: Two Face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37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2005), p.804.早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透明性原则、可诉诸司法原则、程序正义原则、参与性原则成为了“自下而上法”的适用核心,而较具争议性的实体行政法规则往往被忽视。这一适用“偏见”的问题在于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划分的界限极易模糊,且实体规则的移植对于建立全球行政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大多数程序性概念或规则都具有不精确性,因此单纯移植程序性原则难以维持全球治理空间的程序正义。以比例原则为例,在决策者适用比例原则之前,其必须确定合比例的标准是什么、比较的对象是什么。(22)See Jan Klabb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36.比如,拒绝承认某人难民身份的行为应该与其母国现实情况合比例?还是与某人所遭受的苦难合比例?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性标准的模糊性只会导致决策者自我裁量权的无限扩大,对全球行政法的实践产生致命影响。其三,“自下而上法”极易让全球行政法染上其来源地的法律习惯与特性,可能导致全球行政法的单一化或倾向化。从实践来说,对不同法律传统与特征进行融合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行政性传统。即使在欧洲,行政性传统也并非千篇一律:英国将行政法视为有效控制政府的工具,而法国则将行政法视为能够促进政府进步的激励机制。此外,不同的国家亦具有不同的行政目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目的必然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一个产生并根植于西方法律思想的法律理念,“自下而上法”极易导致全球行政法的不公平适用。
因此,不论“自下而上法”所试图构建的蓝图多么美好,单独在国际层面上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是极其危险的。寻找吸收国内行政法的妥当进路是“自下而上法”的当务之急。
(二) 设立专门性全球行政法:“自上而下法”
由于国内行政法的延伸适用只能通过设立决策审查机制而有限地增强国际组织决策的可归责性、合法性与民主性,制定专门的、全面的行政法原则和规则成为了更有潜力的进路。(23)See Eleanor D. Kinney, The Emerging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Its Content and Potential, 54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2), pp.416-417.与粗浅地照搬国内行政法原则不同,设立专门性全球行政法能够提取国内行政法的精髓,从实体与程序二维角度保障跨国规制主体决策的可归责性、合法性与民主性。换言之,该“自上而下法”意指在国际层面建立行政管理机制,为不同的跨国规制主体设立各自的运行规范,并最终促进全球治理的优化与改革。
如前所述,全球行政主体包括多种国际组织,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跨国规制网络与协调安排、按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度运作的国家监管机构、混合型国际组织、以及具有特殊公共职能的私人跨国规制主体。(24)See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and Richard B.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3)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p.15-61.在实践中,多数机构因其性质和职能可同时被纳入多个类别之中,(25)See Christoph Mollers, Ten Year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Through the Lens: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After 10 Years), 1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5), pp.469-472; see also Lorenzo Casini, Beyond Drip-painting? Ten Years of GAL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dministration, 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5), pp.473-477; see also Richard B. Stewart, The Normative Dimensions and Performa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1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5), pp.499-506.故应首先侧重于两大类基础国际组织的运行规范建设: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1. “自上而下法”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有效适用
政府间国际组织系国家间依据条约成立的国际组织,是最为传统和经典的跨国治理机构。此类典型国际组织行政管理机制的设立,能够为专门性行政法在非典型国际组织中的适用提供有效参考。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为其自身设立的检查小组(Inspection Panel)是专门性行政法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适用的典例。(26)See World Bank, The Inspection Panel,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inspectionpanel,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该检查小组设立于1993年,作为独立机制对世界银行的运行进行内部审查,以提升其决策的可归责性和信息公开性。(27)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53.在该机制下,受世界银行某项目影响的利益关系人有权要求对决策进行全面审查(full investigation),世界银行必须全面配合。(28)See David Hunter, Using the World Bank Inspection Panel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Project-Affected People, 4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pp.201-212.审查程序共有四个阶段:首先,检查小组评估世界银行管理层(World Bank Management)对该项请求的反应;其次,根据该评估,检查小组就是否有必要进行全面调查向世界银行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提出建议;之后,一旦核准,检查小组获得广泛的调查权力和获得信息的机会,并完成其检查报告;最后,董事会就所要求的事项作出最后决定。(29)See David Hunter, Using the World Bank Inspection Panel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Project-Affected People, 4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pp.201-212.
检查小组充分呈现了一个具有透明度和参与度、并积极利用审查机制的全球行政法范式,故被视为国际组织在决策过程中可自愿采用的行政管理机制之一。(30)See Request for Inspection: World Bank, Cases, and Reports of the Inspection Panel,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inspectionpanel,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然而,该模式仍有两大不足。其一,检查标准有失公允、且过于僵化。检查小组只能调查决策过程是否符合世界银行的内部政策,而非一般国际法原则。该限制极易致使审查结果丧失公正性,减损国际社会对“自上而下法”的信心。其二,检查程序具有过度政治化的嫌疑,易导致检查机制的官僚化。(31)See Dana Clark and David Hunter, The World Bank Inspection Panel: Amplifying Citizen Voi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Gudmundur Alfredsson and Rolf Ring (eds), The Inspection Panel of World Bank: A Different Complaints Procedure, 2001, p.167.
图一 ADB两级问责程序

尽管世界银行检查小组制度具有一定不足,但其设立仍启发了其他国际银行制定类似的、但更优化的内部审查机制。(32)See Eugenia McGill, The Inspection Policy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 Gudmundur Alfredsson and Rolf Ring (eds), The Inspection Panel of World Bank: A Different Complaints Procedure, 2001, p.191.以亚洲开发银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ADB”)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为例,其在世界银行检查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加系统的、分级的审查机制(详见图1)。(33)Se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vailable at: http://www.adb.org/Accountability-Mechanism,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第一级为争议解决(Problem Solving),基于公平、透明和协商一致原则,由ADB特别项目协调员(Special Project Facilitator)对直接参与项目的股东之间的任何争端进行调解。这一程序让受影响的人(project-affected people)能在还未出现问题的时候请求审查;同时,特别项目协调员具有解决争端的高度灵活性,能够有效解决纠纷,保障各方权益。(34)Se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vailable at: https://www.adb.org/site/accountability-mechanism/problem-solving-function,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第二级为合规审查(Compliance Review),由合规审查小组(Compliance Review Panel)执行。(35)Se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vailable at: https://www.adb.org/site/accountability-mechanism/compliance-review-function,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与世界银行检查小组相似,合规审查小组的调查重点是受影响人所指称的直接的、物质的损害,以及该损害是否是ADB在制定、处理或执行项目时违反其业务政策和程序所造成的。
ADB两级问责机制有效解决了世界银行检查小组的主要不足——审查标准有失公允且过于僵化,其成功预示着“自上而下法”的繁荣前景。经过进一步完善,适用专门性全球行政法以保证决策的可归责性、合法性与民主性将成为规范政府间国际组织运行的更为妥当的路径。
2. “自上而下法”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适用缺陷
检查小组问责机制存在的前提为强有力的内部规则,其保证了政府间国际组织职能机构和审查机构之间的完全独立,使调查、审查与评审具有实际意义。(36)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55.然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通常无法满足这一重要前提,故相对成熟的检查小组模式并不适用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还需另辟蹊径,建立专门适用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问责机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简称“BCBS”)创建了一个适用行政法原则的混合机制。(37)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银行监管的主要全球标准制定者,为全球银行监管合作开展定期论坛。目前共有45名成员,包括来自28个司法管辖区的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bcbs/,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该委员会成立于1975年2月,是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简称“BIS”)的常设监督机构。其工作内容为发布协议、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以完善全球银行业监管工作,稳定国际金融秩序。(38)See Michael S. Barr, and Geoffrey P. Mille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The View from Basel, 17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pp.15-46.起初,只有十国集团(G-10 Countries)国家可受益于委员会建议。(39)十国集团(G-10 Countries)系由一群共同参与一般借款协定的国家所组成的团体。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日本。随后,为了加入核心国际金融市场,其他国家也自愿以无代表权的身份加入委员会。这一做法形成了十国集团在委员会内部的霸权局面,使BCBS在早期阶段严重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
为了改善委员会内部机制不足的问题,BCBS对《1988年资本协议》(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CapitalStandards)进行了实质性修订。首先,委员会发布了多次通知和评论,向公众提供修订草案及修改理由;同时,委员会邀请各方就其提案发表评论意见。这一措施使得委员会与其成员以外的有关各方能够进行公开对话和互动,提高了BCBS决策的透明度和参与度,被视为有效的、适用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问责机制。(40)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56.其次,委员会于2012年启动了监管一致性评估方案(Regulatory Consis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简称“RCAP”),以监测和评估其标准的通过和执行情况,为国际银行创建可预测的、透明的监管环境。(41)Se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el standards,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bcbs/implementation.htm?m=3%7C14%7C656,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
监管一致性评估方案由互为补充的流程构成(详见图2):其一,根据成员国提供的监测报告(Monitoring Reports),评估BCBS监管标准转化为国内法规的情况;其二,进行法域评估(Jurisdictional Assessments),审查国内条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委员会商定的最低要求,并帮助查明这些条例中的重大差距;(42)具体评估方法和原则参见Regulatory Consis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 Handbook for Jurisdictional Assessments,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bcbs/publ/d434.pdf,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同时,借助专题审查(Thematic Assessments),评估巴塞尔协议在各银行的执行情况,并力求确保各法域的银行一致计算审慎比率,以提高各结果之间的可比性。(43)See RCAP: Role, Remit and Methodology,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bcbs/implementation/rcap_role.htm,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尽管这一方案的实施须其成员高度配合,其仍然体现了委员会制定专门性行政规则的倾向。
图二 BCBS监管一致性评估程序

然而,BCBS监管一致性评估方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规范。首先,作为非政府间跨国规制机构之一,委员会自身不受任何条约或协定的约束,缺乏合法的决策程序。同时,委员发布的所有建议、通知和评论都不具法律约束力,其执行完全依赖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赖和一致共识,故其问责机制的有效性有待考量。其次,由于BCBS实现职能的唯一方式是在国内执行其标准,让国内机构依据国内法进行审查(即“自下而上”地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是更为可行的路径。
因此,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设立专门性行政规范不可一蹴而就,必须把握此类机构的关键性质。一方面,所有非正式跨国规制机构都在全球治理空间中运作,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灵活性与多样性致使此类组织在国际社会上普遍存在,故必须建立更加规范的行政机制,保障非正式跨国规制机构行为的合法性、民主行与可归责性,促进其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非正式跨国规制机构所形成的全球治理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国家界限,是国内与国际活动、公法与私法的混合体。(44)See Andrew D. Mitchell and Farnik Joh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Can It Br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37 Federal Law Review (2009), p.257.以BCBS为例,其既要通过通知、评论程序对成员是否应采纳巴塞尔标准提出建议,亦须对巴塞尔标准的国内实践进行审查。因此,必须采用系统的、互补的行政机制才可保证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行为的规范性。
三、全球行政法的适用完善
在后现代时代全球治理责任碎片化、分裂化的倾向下,将成千上万的国际组织视为全球行政机构(45)20世纪初,世界有200余个国际组织,到50年代发展到1000余个,1990年约为2.7万个,21世纪初超过5.8万个。截至2019年,世界上有来自300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个国际组织,包括38000多个活跃国际组织和大约32000个处于休眠状态的国际组织。每年新增国际组织数量为1200个。See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th Online Edition, 2019, available at: https://uia.org/yearbook, last access on 20 April 2019.,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在全球治理空间中的职能和局限。(46)See Lorenzo Casini, Beyond Drip-painting? Ten Years of GAL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dministration, 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5), p.477.基于对全球行政法两种实践进路的解读,可知其并非单纯的学术概念。通过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其将成为解决国际组织内部机制不足的强有力工具。
(一)以互补方式建立健全全球行政法
全球行政法适用完善的第一步即应在国际层面上以“自上而下法”建立行政规则,并补充适用“自下而上法”。“自上而下法”能够根据不同类型国际组织的特性,为其设立不同的问责机制。其具有三大明显优势:在适用范围上,其同时融合了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47)Monika Ambru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Different Stories about the Crisis in Global Water Governance, 6(1) Erasmus Law Review (2013), p.49.为全球行政法提供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从适用方法来看,专门性全球行政法强调每个跨国监管机构的可归责性、合法性和民主性,为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设立了符合其特点的问责机制,增强了全球行政法在实践中的可预测性和有效性;以规则内容来说,专门性全球行政法使具体行政规则、原则与其来源地法律传统分离,使不同地域的跨国规制主体能够公平地适用全球行政法。与此同时,应辅助适用“自下而上法”,利用国内行政法程序性规则、原则,巩固全球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为其在国际层面上的实践提供参考。
(二)强化个体国际组织对全球行政法的多层次适用
当国际社会和不同全球规制主体共同承认全球行政法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前置义务时,全球行政规则就完成了从简单的、审慎务实的实践方法到“法律”的转变。(48)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2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 pp.23-57.因此,在建立健全全球行政规则之后,应强化个体国际组织对其原则、规则及机制在不同层面的适用。
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为例,其规则体系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全球监管治理的复杂性,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全球行政法的实践提供了平台:(1)WTO的内部机构管理,具体包括部长级理事会、争端解决机构以及行政机构;(2)WTO对其成员方国内相关行政决策的监管;(3)WTO与其他国际标准制定主体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49)Richard B. Stewart and Michelle Ratton Sanchez Bad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1), p.558.尽管全球行政法无法解决WTO所面临的、由政治利益和价值冲突所驱动的根本问题,但行政规则的妥当适用能够确保其行为民主性、减轻内部机构决策过载、促进其实现贸易自由。
(三)促进不同国际规制主体对全球行政法的积极实践
根据“公共主体间(Inter-Public)”理论,为了其他规制主体,全球行政法的适用应是决策的前置义务。(50)See Benedict Kingsbury, International Law as Inter-Public Law, in Henry R. Richardson and Melissa S. Williams eds., NOMOS XLIX: Moral Universalism and Pluralism, 2009, pp.167-204.这一理论强调,全球公共当局(不论国内机关还是国际规制主体)在决策过程中遵守程序规则、提供合理理由,不仅有利于其自身公民与成员方利益,更有利与其他公共规制主体和其公民与成员方利益。以WTO为例,随着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全球行政法不仅是恰当的、更应是强制性的,WTO将不可能在拒绝自身适用全球行政规则的情况下,要求各成员方遵守全球行政法;同时,这也意味着WTO将采用其他全球规制主体也正在适用的全球行政规则,并坚持与其他主体共同适用全球行政法以决定具体适用标准。因此,不同国际规制主体之间在全球行政法适用问题上的相互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其在实践中的普及与成熟,避免公共权力滥用,确保公共决策可归责。
(四)从多维角度推动全球行政法的长足发展
为了保障全球行政法的公正适用,还应将其明确区别于政治机制,提升国际社会对国际组织内部审查机制或其他监督机构的信赖。审查机构的根本任务并非一概而论地维护国际组织利益、为其不当行为寻找替罪羊。内部审查机制的建立必须以程序正义为价值核心,提高决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还须保证审查机构、问责机构与职能部门的独立性,强化监督效力。
此外,全球行政法的充分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国际法理念、制度的配合和国际法专业人士的推动。一方面,全球行政法的实践需要国际公法、国际组织法、和国内行政法的共同帮助。若其任何实践路径都无法适应后现代的法律体系,则只能被视为“皇帝的新衣”,无法实现其立法目的。另一方面,国际法专家与国际法律师应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一个管理国际组织的持久的法律框架,去除其官僚主义属性,在国际层面上形成正确的、适当的跨国规制主体行为准则。(51)See Devika Hovell, The Idea of Global Public Law: Response to Unbound Symposium Essays, 11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2016-2017), pp.80-83.
结 语
随着新全球化运动(Neo-Globalization)在国际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为了保证跨国规制主体内部机制的“分权与制衡”,确保其行为的可归责性、合法性与民主性,全球治理制度规范和行政规则亟待确立。在此种趋势下,全球行政法以及其他全球公法(Global Public Law)的建立健全是大势所趋。
到目前为止,全球行政法在国际组织中的实践主要有两种进路:延伸适用国内行政法的“自下而上法”、以及设立专门全球行政法的“自上而下法”。基于对两种不同实践的分析可知:全球行政法的全面发展需要“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并举,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说,专门性行政法(即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适用符合其特点的行政机制)应被视为全球行政法的支柱。其可直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实施,提高跨国规制主体决策的透明度、公众参与度,保障其行为的可归责性、合法性与民主性。在此基础之上,因国内行政法为全球行政法的运行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能够有效应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行政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其应作为辅助手段得到适用。此外,还应强化全球行政法在个体国际组织内部机构管理、成员方监管、以及对外关系层面的适用;促进不同国际规制主体对全球行政法的积极实践,通过其相互影响使全球行政原则、规则和机制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前置义务。最后,为了增强国际社会对内部审查机制及其机构的信赖,全球行政法的适用必须以程序正义为核心价值,保证审查机构的独立性。在其他法律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国际法专业人士的持续努力下,全球行政法将茁壮成长,在为国际组织的运行保驾护航的同时,推动整体国际规则在“新全球化(Neo-Globalization)”时代中的持续进步与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