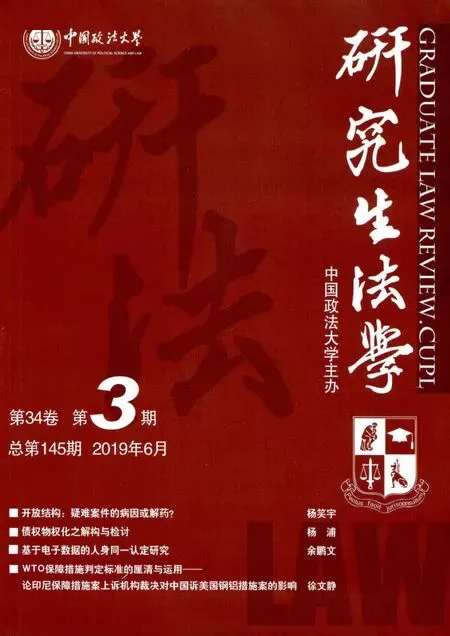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现状、不足与完善
孙世民
武装冲突指的是国家之间、国家与其他政治实体之间或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武力对抗。(1)参见周忠海主编:《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1页。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和阶段都伴随着不同规模、不同大小的武装冲突与战争。可以说,自从有了初民社会,就有了武装冲突与战争。(2)本文认为,“武装冲突”与“战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而不加以区别。时至今日,由于在武装冲突当中使用诸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环境控制技术武器等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武装冲突在对环境造成了极其深重的损害的同时,还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参见林灿铃:《国际环境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页。不仅如此,无论是国际性武装冲突,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造成城市、乡村基础设施损毁的同时,还会造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与退化,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其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仍然长期存在,这些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有时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可以说,自然环境在每一次武装冲突当中都是受害者。(4)See Patricia J, West Earth: The Gulf War’s Silent Victim, Year-book of Science and the Futur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93, p. 332.因此,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早在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就开始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的形式探讨如何保护受到战争与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例如1856年的巴黎会议、186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868年的圣彼得堡会议等。直到今天,国际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一、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
随着国际社会对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关注,一些国际条约陆续生效。这些国际条约对受到战争与武装冲突所威胁的环境的关注是从间接保护开始的。而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受到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和武器所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与环境破坏的后果的影响,国际社会开始制定和通过了对自然环境进行直接保护的国际条约。这些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对于明晰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的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条约对武装冲突中环境的间接保护
在国际社会最早制定和通过的有关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当中,“环境”一词并没有被明确规定到相关国际条约的条文当中。在这一时期,环境当中的一些具体要素,例如土地、森林、湖泊等,是被作为个人或者国家的公私财产进行保护的。例如,在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即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后文简称《海牙公约》)第55条当中除了规定交战双方对对方森林的占有和使用的具有权利的同时,还特别规定双方均有保护森林的义务;(5)《海牙第四公约》第55条:“占领国仅仅是的公共建筑、不动产、森林以及农田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占领国必须保证这些财产不会因不正当使用而遭到破坏。”又如,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后文简称《日内瓦公约》)当中规定的是,如果不存在绝对的必要性,占领国不得对被占领国的动产和不动产进行任何破坏行动,也不允许对这些财产进行大规模的破坏。(6)《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53条:“除非符合军事行动绝对必要性原则,占领国不得对被占领国境内的财产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显而易见,这些国际条约直接保护的是受到战争与武装冲突所威胁的公私财产,并没有直接规定对环境的保护。但是,森林、土地、湖泊等在可以作为有形财产被这些国际条约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属于环境当中的具体要素。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国际条约当中,虽然“环境”一词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具体的条文当中,但是可以通过这些国际条约当中的具体条文对环境当中的具体要素进行保护,这就是国际法最早对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视角和方式。简言之,在这些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当中,虽然“环境”没有直接和明确的出现在相关条文当中,但对环境的保护是通过这些条约当中规定的具体内容而得以间接体现的。当然,这种对环境的间接保护的方式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国际法对受战争与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是不够重视的,保护的力度也可想而知。
(二)国际条约对武装冲突中环境的直接保护
如所周知,在1961年到1971年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采用了一系列改变环境的战术。(7)See Asit K. Biswas,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long-term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in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7.例如,为了扫清越南的热带丛林对美军军事进攻的阻碍,(8)See Karen Hulme, War Tron Environment: Interpreting the Legal Threshold, Martinus Nijhoff, 2004, p. 5.美军对这些森林使用了大约1200万加仑的剧毒化学试剂(例如落叶剂与除草剂等),(9)参见朱利安·怀亚特:“国际环境法、人道法和刑法交叉领域的立法: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环境损害问题”,朱利江译,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0年文选,第265页。对该地区的居民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有的损害甚至是难以恢复的。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植被的继续生长,美军还采取影响天气的技术实施对环境的改变。(10)See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有鉴于美军在越南战争当中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和武器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到战争与武装冲突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11)参见米夏埃尔·伯特 等,朱莉译:“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不足与机遇”,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0年文选,第236页。并开始了相关国际条约的制定。
例如,1976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后文简称《公约》)是第一个在武装冲突法律中通过限制使用改变环境技术而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其调整的范围主要是利用环境致变技术伤害敌人的手段和方法。(12)See A. Roberts, The law of war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7.该《公约》明确禁止将具有“广泛、长期或严重”损害后果的环境致变技术利用到武装冲突当中,并对“广泛、长期、严重”进行了具体的界定;(13)See Understandings of ENOMD, available at: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Article.xsp?action=open Document&document Id=A951B510E9491F56C12563CD0051FC40, last accessed on 1 May 2019.又如,1977年《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后文简称《议定书》)是一个明确规定环境内容的武装冲突国际条约。(14)See Waldemar A. Solf, Article 55: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in Michael Bothe,Karl Josef Partsch, and Waldemar A. Solf, New Rules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 Commentaries on the Two 1977 Protocols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Martinus Nijhoff, 1982, p. 347.其中第35条第3款规定了禁止在战争当中使用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之上,第55条进一步规定了禁止使用因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损及居民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以及禁止以报复的名义攻击自然环境的内容;再如,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后文简称《规约》)在第8(2)(b)(iv)条当中纳入了武装冲突时期的环境保护条款。(15)《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b项(iv):“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该条规定,在武装冲突当中从事环境破坏行为的人可能构成战争罪。
从对环境的间接保护到对环境的直接保护,这些主要与战争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国际条约体现了即使是在战争与武装冲突当中也应当保护环境地国际法义务,这是国际法的一大进步。尽管这些国际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尽相同,在具体内容方面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它们构成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现有国际法体系,这对于保护受到战争与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继续加强对在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并且开始从环境的独立价值和内在价值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从而使得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新的特点。
二、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新动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些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既有保护受到战争与武装冲突威胁的环境的国际条约的基础之上开始了新的努力。在这些努力当中,以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进展最为突出,从而使得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联合国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对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联合国的工作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的研究和联合国大会关于《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商谈最具代表性。
1.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2013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后文简称委员会)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当中,并为此任命了专题特别报告员。截至目前,现有的《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可以分成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关于适用于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以及占领后局势的相关原则。其宗旨是预防武装冲突造成的环境损害、减少武装冲突期间对环境的损害以及进行造成损害之后的环境修复和补救工作。其规定了国家在武装冲突中具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例如划定保护区的形式,以避免自然环境受到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还强调了在武装冲突中区分原则、相称性原则、军事必要性规则和预防措施原则的重要性,禁止为了报复而对自然环境进行攻击。其规定了在武装冲突结束之后,各方应当进行战后环境评估,共同协商被损害环境的恢复和赔偿问题,并发挥有关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还具体规定了战争遗留物、海上战争遗留物的处理和其他信息获取和共享机制等内容。(16)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seventieth session (2018), A/73/10, pp.240-260.
委员会暂时通过的《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部分条款中结合了国际人道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武装冲突之前的环境保护侧重于准备和预防,对于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侧重于限制军事手段和武器装备的使用,对于武装冲突之后的环境保护则侧重于赔偿、重建和恢复,还要求占领方履行保护被占领土自然环境的义务。这意味着,环境保护贯穿整个武装冲突的过程,应当被冲突各方所重视。不仅如此,委员会现有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原则,而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最新报告,委员会在下一阶段要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原则纳入工作安排当中,以期整合一套包括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内的环境保护原则体系,最大程度地保护受到武装冲突所威胁的自然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联合国大会
2018年5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143票赞成、6票反对和6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主题为“制定世界环境公约”(Towards a Global Pact for the Environment)的编号为A/72/L.51的决议草案。由于该决议并没有对《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后文简称《草案》)本身进行表决,也就未对其中的具体内容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该《草案》仍然是以2017年6月24日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公开发布的《世界环境公约(草案)》为蓝本。因此,该决议草案的通过意味着,这部由来自南北半球四十多个国家的不同专业领域的一百多位法学家编写并经法国政府主导并由全球九十个国家联合提交联大讨论的《草案》进入了联合国大会的正式讨论议程中,开始在联合国的层面上进行正式的协商和谈判。
《草案》的目的是首次制定一部涵盖所有环境领域的一般性、综合性的国际环境条约。《草案》一共有二十六条,其中第1条至第20条属于实质性条款,具体涉及到环境权与普遍的保护环境义务、缔约国义务以及代际公平和预防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内容,而第21条至26条属于辅助性条款,具体涉及事务性的规定和要求。不仅如此,《草案》虽然继承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纪议程》等重要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所体现出的基本原则,但是也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与发展。例如,第16条关于生态系统和各人类群体复原能力的规定和第17条关于环保水平不得倒退的规定都是首次被引入到综合性国际环境条约当中;又如,第9条将环境知情权赋予所有的、任何的社会公众,尤其是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利益相关方,这就是一次针对现有只有利益攸关方才能获取环境信息规定的重大发展。(17)参见杜群、郭磊:“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统一立法走向——《世界环境公约(草案)观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6页。
《草案》第19条是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定,该条要求缔约方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并且特别提到了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国际法义务。(18)《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第19条:“各缔约方必须按照自己所应遵守的国际法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草案》从缔约国的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义务出发,规定了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履行这种义务,避免自然环境受到武装冲突的威胁。《草案》的出现因而成为了国际社会最新的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动向。而且与其他条款相似,第19条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体现了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国际共识,但其具体实施机制有待于后文的进一步研究。虽然包括第19条在内的《草案》仍然在联合国大会的商谈过程当中,但是该条仍然可以体现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的新动向。
(二)国际刑事法院
2016年9月15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案件选择及优先性的政策文件》(Policy Paper on Case Selection and Prioritisation)。在该政策文件中,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将特别考虑起诉,通过破坏环境、非法滥用自然资源或非法占有土地的方式实施的,或造成这样结果的罗马规约犯罪”。(19)See Policy Paper on Case Selection and Prioritisation, Available a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official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itemsDocuments/20160915_OTP-Policy_Case-Selection_Eng.pdf. last accessed on 1 May 2019.这一着重强调对破坏环境罪行关注的表述被视为国际刑事法院在新时期的“环境保护宣言”,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报道,并引起热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强调,该文件将“在检察官办公室选择调查起诉的案件及决定其优先顺序时起关键的指引性作用”(20)ICC Prosecutor, Fatou Bensouda, publishes comprehensive Policy Paper on Case Selection and Prioritisation, Available a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official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Pages/item.aspx?name=pr1238. Last accessed on 1 May 2019.。
该文件指出,在进行案件选择及优先顺序决定时,检察官办公室将以更加聚焦该案的视角考虑“管辖权”“可受理性”及“正义的实现”等方面的法律标准,具体将考虑“罪行严重性”“被告人责任程度”及“指控”本身;在考虑一情势下的某一具体案件是否具有“严重性”时,该文件不仅强调应在“罪行的影响”方面考虑环境因素,还提出在“从事罪行的方式”方面要考虑“那些通过破坏环境或被保护目标或造成此种结果的犯罪”。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政策文件首章“引言”中还强调:“检察官办公室也寻求同国家的合作,在国家请求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帮助,打击在国内法下构成严重犯罪的行为,例如非法滥用自然资源、走私武器、贩卖人口、恐怖主义、经济犯罪、占用土地或环境破坏”。(21)参见陈玥:“论国际刑事法院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能”,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13页。正如前文所述,根据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2)(b)(iv)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可以以战争罪的罪名判处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造严重自然环境损害的行为人以刑罚,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的这份文件的内容并没有超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受案范围,该文件表明的是在未来第8(2)(b)(iv)条的规定可能很快得到应用,体现了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国际法的又一个新的动向。
三、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新特点
对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现状的分析离不开对相关国际条约条文的理解,而这一定要涉及到国际条约的解释问题,这就离不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中的内容。(22)《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条约应依其用语按期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确有之通常含义,善意解释之。”该条款是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问题,而自从1994年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案”当中明确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属于习惯国际法之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内的国际裁判机构适用这些规则的实践日益增多,例如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美国汽油案”中也明确了该条所规定的解释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基于该条的规定,李浩培先生也认为,对条约的解释应当遵循善意解释、按照用语的通常含义解释以及按照上下文并参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这三个基本原则进行。(23)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页。
在条约解释的这几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从早期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发展到《公约》《议定书》《规约》,再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研讨的《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以及联合国大会正在商谈的《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第19条中所规定的在武装冲突当中应当保护自然环境的缔约国义务,可以体现出当前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的新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
(一)将自然环境独立于人类财产进行专门保护
与《海牙公约》以及《日内瓦公约》仅仅把森林、土地等自然环境中的某些具体的要素作为一种人类的财产进行保护相比,《公约》《议定书》《规约》以及《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将自然环境进行独立保护,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对财产的保护相分离,是真正意义上地保护受武装冲突所威胁的自然环境。这是因为,今天的环境伦理学认为,自然环境具有独立价值和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依附于是否可以被人类社会所利用。那种认为只有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环境要素才具有价值的认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人类中心主义已经被今天的环境伦理学所扬弃。今天的环境伦理学倡导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人为什么要保护环境以及人应当如何与大自然相处,即自然环境具有本身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4)参见陈文彬:“环境正义与国际环境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4~66页。
因此,自然环境也有生存权,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环境的生存权,以最终建立一种平等、和睦、协调和统一的关系。(25)参见裴广川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这种“去中心化”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意味着人不应当以征服自然为目的而应当科学地改造自然,还意味着从前那种强调自然环境的价值依附于人类社会的观点既不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臭氧层空洞、跨界大气污染等现象证明了人类以自身为中心,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这种没有将环境作为人类的财产进行保护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是在“去中心化”的新型环境伦理观基础之上的进步。这种进步体现了在作为一种立法理念的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影响之下,国际环境立法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这种进步更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尊重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实现代内环境公平和代际环境公平。
(二)扩大了对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保护范围
《议定书》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规约》第8条也是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规定了战争罪的构成要件,而《公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适用的范围是国际性武装冲突,但是其在第1条当中规定了缔约国保证不对其他缔约国使用环境致变的技术以及不帮助、不怂恿任何国家、国际集团或者国际组织使用环境致变技术,这表明《公约》的适用范围仍然是国际性武装冲突。这说明,无论是《公约》还是《议定书》《规约》,其中的相关条款所保护的仅仅是受国际性武装冲突所威胁的自然环境。
但是现在发展的趋势是,无论是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还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都应当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对自然环境进行区分保护不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从《草案》第19条的具体规定来看,并未进行这样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从条约解释的善意、基本用语以及联系上下文这三个基本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草案》只保护受国际性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根据第19条的规定缔约国都应当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义务。这就将保护的范围从现有的国际性武装冲突扩大到了所有性质的武装冲突。除此之外,第19条并没有对破坏环境的门槛进行限制性规定,而在《公约》当中是“广泛、长期或严重”的门槛,在《议定书》和《规约》当中是“广泛、长期和严重”的门槛。值得一提的是,《议定书》和《规约》当中规定的这个门槛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难以达到的。这是因为,实践当中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这就不利于《草案》目的和宗旨的实现。这就意味着,《草案》扩大了现有国际条约体系中的在武装冲突中受威胁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力度。由此可见,《草案》规定的是无论在何种性质的武装冲突当中,都不应当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或者污染,这相比于《公约》《议定书》以及《规约》等国际条约具有进步性。不仅如此,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的问题,《草案》所体现的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都应当保护自然环境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三) 淡化军事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
军事必要原则指的是在战争与武装冲突当中,为了实现军事目的,可以不遵守国际法中的一些规定。(26)参见朱文奇:《国际人道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该原则与军事技术和战略思想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27)See George Abi-Saab, The specificites of humanitarian law,in Christophe Swinarski(ed.), Studies and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Red Cross principles in honour of Jean Pictet,Martinus Nijhoff, 1984, p. 266.比例原则要求在对军事目标进行攻击时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的附带损害,要求这种附带损害不应超过在军事行动中所要达到的直接的军事利益。(28)参见周忠海主编:《国际法(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6页。这两个原则都是战争与武装冲突法中的基本原则,在已经生效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是因为,现有的已经生效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条约都是在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当中发展起来的,而早期一般性、综合性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是不够的。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为例,该宣言只是在第26条当中提到了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环境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扩大到武装冲突对环境损害的其他方面。但是随着关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一般性、综合性的国际环境条约的不断发展,这两个原则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破坏环境的比例是一个实践难题,例如为了评估损害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则,不仅需要确定武装冲突之前已有的损害的数量,还需要确定遭到攻击之后的污染和破坏情况,甚至可能需要预测未来那种不确定的损害;(29)See Asit Biswas,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 of war, in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8.另一个问题是,这种为了军事目的而破坏环境的做法不利于实现全球环境保护的目的,也不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环境。
而意图成为一般性、综合性国际环境条约的《草案》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因此其在第19条当中并未规定这两个战争与武装冲突法中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全面保护自然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这种不能为了军事目的而破坏自然环境的限制可以提高进行战争与武装冲突的法律成本,有助于降低战争与武装冲突所造成的损害程度,甚至有利于减少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发生。这体现了国际环境法不仅可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草案》当中没有提及军事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可以说是《草案》最大的进步,这有利于从国际环境法的角度限制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发生,有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总而言之,从《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到《公约》《议定书》《规约》再到联合国层面对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关注内容,当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特点主要是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范围、保护力度以及基本原则等方面的进步。这个进步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不仅仅从保证军事活动顺利进行的角度保护环境,而开始从保护环境的角度限制军事活动的手段和方式。显而易见,这种从保护自然环境的角度规定在战争与武装冲突中应当遵守的国际法规则的方式比从实施军事活动并尽量减少附带性损害的角度规定如何保护受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国际法规则的方式更加有利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此外,这种方式还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在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时的意义和作用。
四、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从《海牙公约》开始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研究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保护受战争与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国际法的这种新动向和新特点体现了明显的进步之处。然而,随着相关国际条约的的逐渐增多,这些国际条约中重叠或者冲突的地方也不断增加,这不利于国际法的实施,也不利于保护受战争与武装冲突的自然环境。因此,如何促进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的实施与完善,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弥补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这种不足,未来国际社会应当以《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的商谈为契机,从建立“世界环境组织”和以该组织促进相关的国际条约协同履约这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建立“世界环境组织”
如所周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英文简称UNEP)是目前联合国系统内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务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环境方案,协调环境方案的实施以及提供环境规划方面的咨询意见等等。显而易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缺乏促进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以及解决环境争端的职能。尤其是在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方面,囿于机构职能方面的因素,虽然其已经在诸如南苏丹战后环境恢复工作以及中非共和国内战中野生动物保护中做出了积极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辅助性的工作,并没有对未来类似事件的发生起到终局性的作用。
因此,为了推动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以联大第72/277号决议推动关于国际环境法相关文书实施为契机,努力将《世界环境公约》修改为世界环境组织的章程,以促进包括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有关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虽然目前在《草案》第21条中规定了实施监督机制。该条规定,应当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公约的执行提供便利、接受缔约各方按期汇报的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而且还特别规定了该专家委员会不具有法律诉讼或者惩罚权。(30)《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第21条:“应建立监督机制,使得本公约各项条款的实施更加顺畅,保证公约内容得到遵守。监督主要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其主要任务是为公约的执行提供便利。委员会运行完全透明,但本身不具有法律诉讼或惩罚权。委员会要特别考虑到各缔约国各自的国情和能力......”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于解决《草案》第19条所规定的保护武装冲突当中的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尤其是未赋予委员会实体性权力的规定更是限制了委员会职能的发挥。这是因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公约的执行提供便利,由此可见,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是辅助性、程序性的,缺乏解决在实施第19条时产生的环境纠纷的功能,不足以满足应对由于武装冲突所致的环境损害的要求。而且这样的委员会不具有实体性的权力,不能公正有效地解决包括武装冲突所致的环境损害在内的国际环境纠纷,不利于公约目的和宗旨的实现。
具体来说,世界环境组织(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英文简称WEO),旨在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分歧、法律裁决等方式建立一个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并有效解决环境争端的机制。(31)参见林灿铃:《国际环境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其具体职能除了信息和数据交换的作用之外,主要是解决在执行《世界环境公约》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端,以此形成一套国际环境争端的解决机制,以保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例如,在缔约国产生关于在武装冲突中环境所受破坏的争端时,该组织可以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和调解,促进争端双方的谈判和协商,甚至作出有拘束力的法律裁决,以确定相关的环境恢复工作和生态赔偿责任等问题,以保障保护受武装冲突所威胁的自然环境的义务得到最终落实。不仅如此,从长远来看,世界环境组织还可以建立与国际刑事法院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从而建立更加全面的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国际环境法实施机制。建立这种机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于,根据《规约》第8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那些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因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而构成战争罪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构成这种国际罪行。因此,世界环境组织的成立将负责解决那些不构成战争罪的、因为在武装冲突中破坏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国际环境争端,以弥补现有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实施机制的空白,促进国际环境法的直接实施,最终构建一个从终止环境不法行为、恢复原状、损害赔偿乃至国际刑事责任的全方位的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国际法律直接实施机制。当然,该组织不仅解决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纠纷,还可以解决其他国际环境纠纷。
(二)促进国际条约协同履约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已经生效的有关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公约》《议定书》以及《规约》等等。而这些国际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尽相同,其所保护的自然环境的范围和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这些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或者重叠,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此外,鉴于自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之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具体体现在许多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国际条约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规定,国际法委员会也在2013年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当中,到目前为止已经讨论了四份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32)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seventieth session (2018), A/73/10, pp.240-245.因此,如何使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进行协同履约的问题应当是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和解决的实际问题。
国际环境条约的协同履约指的是为了解决不同的国际环境条约之间因为不协调或者重叠而导致缔约国陷入履约困境问题,通过协同增效的方式促进缔约国对国际环境条约义务的履行,以实现这些国际环境条约的宗旨和目的。(33)参见蒲昌伟:“国际环境协定协同履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现有的与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都提到了缔约国有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自然环境的义务,根据“条约必须得到信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缔约国应当承担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否则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也就是说,各国必须按照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履行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自然环境,这就从实体上建立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条约协同履约的可能性,也可以整合现存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
当然,仅仅在实体上建立这种可能性是不够的,因为再完美的实体性规范如果没有程序层面的执行,都不会最终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商谈型协同整合方式,坚持共治的原则,形成各缔约国积极参与的模式。(34)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这种模式应当充分体现缔约国的一致,调动各缔约股参与协同履约的积极性。而在协同履约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大量的沟通与协调等事务,这就需要缔约方大会、各个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这种专业的复杂的程序性制度的安排离不开世界环境组织的运行,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根据《世界环境公约》而建立的世界环境组织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信息和数据的交换,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建立世界环境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仅如此,除了应当建立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相关国际条约缔约国大会的沟通、协商与谈判机制,通过秘书处的紧密联系与工作来往,从程序上保证这些国际条约在适用的过程中实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之外,在各个相关条约的实施发生不协调的时候,还应当考虑世界环境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协同履约机制,这种协同履约的程序性机制也有利于实现与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的宗旨和目的,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结 语
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是随着《海牙公约》体系和《日内瓦公约》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由于这两个体系是国际人道法的基石,因此可以认为这个问题诞生于国际人道法的研究之中。但是,由于战争与武装冲突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体现在这种损害的影响范围可达数百平方公里,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可能产生严重的损害或长达数个月的长期不良影响。(35)See Alexander·Nicholas, Airstrike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Held Liable for Operations Allied Force? 11 Colo. J. Intl Envtl. L.&Poly. (2000), p.491.同时,囿于国际人道法中的军事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等从军事活动顺利开展的目的而保护自然环境对自然环境保护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置环境的价值于军事活动的价值之下,这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不足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表明仅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是不够的。因此,需要从国际环境法的视角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而随着国际环境法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出现了新动向和新特点。例如,对自然环境独立价值和内在价值的肯定,相关原则的转变以及所保护自然环境范围的扩大、力度的增加等。此外,针对目前在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所存在的争端解决以及履约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以《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的商谈为契机,通过建立世界环境组织以及实施相关国际条约的协同履约等方法来进行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在武装冲突中受威胁的自然环境,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