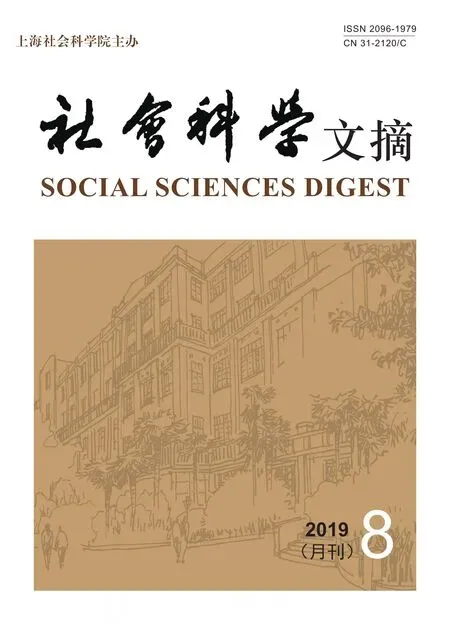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文/裴长洪 刘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增速,有时甚至高达GDP增速的两倍。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速。世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由金融危机前的接近50%,迅速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40%,倒退到21世纪初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分工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尽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阴霾下,中国对外贸易仍然“韧性”十足,2018年中国出口保持了10%的增速,2019年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4%。
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
(一)互联网和跨境电商减少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匹配成本
一是从生产链的协调成本看,产品生产环节的“区域化”分离是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跨区域链条的不断延伸,生产一项最终产品可能会涉及多次中间品的进出口以及频繁跨境流动,产品“工序化”和“分段化”生产愈发平常。在生产最终品之前,中间品会经过生产链条的多个生产环节,产品“工序化”和“分段化”对生产链条不同环节间的协调和沟通成本产生“放大”作用。互联网疏通了生产环节间信息流通的“脉络”,缩减贸易的交货时间,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二是从生产链的信息成本看,大量文献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打破信息不对称等非正式性贸易壁垒(蒙英华和黄建忠,2008)。国界分割导致信息流通受阻提高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信息流通障碍加大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面临的不确定性,企业在获取信息时面临有效信息不足、质量不高、及时性不够、信息同质等问题,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贸易的隐性成本。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搭建起全球信息自由流动“桥梁”,“互联网+贸易”的电子商务模式突破了时空限制,加速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高速融合。
(二)互联网和跨境电商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组织结构、要素结构和网络关系
首先,互联网可以促进全球价值链由“蛇形”生产模式向“蛛行”生产模式转换,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更为扁平化,形成了既具有线性分层特性、又具有多节点交互的新型生产布局。其次,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要素结构。数据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键要素,国际生产分工的响应时间可被完整记录。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资本是决定产出的主要因素。但当前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函数中的关键要素。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由于实际贸易时间难以测度,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也就很难判断,出于简化的目的,贸易时间这一变量往往被忽略。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企业生产的响应时间可被“记录”,企业库存能够实现最优化管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生产环节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完成,生产分工能够实现即时响应。再次,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关系。集身份认证、授权管理、责任认定于一体的的跨境电商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信任体系的建立,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韧性”。
(三)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微观主体及其组织结构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使得大量非高生产率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可能,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中“异质性主要体现为生产率差异”这一假设。不可否认,生产率的企业异质性很大程度上被证实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巨大,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但是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之后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商业交易条件下的贸易现象,新新贸易理论实际上已经滞后于贸易实践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同质性”是普遍的。在中国4000万家中小企业中,有500万家中小企业专注于国际贸易,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2011年以来,在跨境电商平台新注册的企业中,中小企业与个体商户数量占比超过90%。中国既存在数量庞大的同质性生产性企业群体,也存在大量综合服务型外贸企业,它们创造的供应链商业模式,通过高速联通的互联网形成的社会分工网络赢得了竞争力,数量庞大的同质性生产性企业因此进入国际市场。
(四)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培育了国际贸易的新业态
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主要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分离。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购买到任何地区的产品。第二次“解绑”则是指生产者之间的空间分离。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使得不同地区的生产者之间可以合作生产,国际生产分工成为可能。前两次“解绑”过程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当前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实现全球化的第三次“解绑”,第三次“解绑”主要指服务贸易领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分离。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服务贸易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在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服务要素是否能由生产者向消费者的即时传输是决定服务是否可贸易的最关键因素。互联网为服务要素跨区域即时转移提供了路径,使得服务“生产”和“消费”的远程交易成为可能,实现了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分离,拓展了服务的可贸易边界,延伸了服务的生产分工链条。
中欧班列改变了海运作为国际贸易主通道的格局
(一)中欧班列具备了海洋贸易模式中所没有的综合分销功能,重塑了供应链生态体系
中欧班列的大量开行、国际陆港和海外仓库的建立不仅开创了新陆地物流运输的贸易方式,而且改变了以往“投资-生产-贸易”的传统经济合作形式,形成了“运输物流-贸易-生产-运输物流-贸易-生产”新的经济循环形式和国际分工格局。货物运输不再是单纯的空间位移,借助于发达的物流运输体系,中欧班列构建了完善的分销生态,通过运输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一体化,实现了国内生产商和国外消费者的直接对接,掌握了产品出关后的定价权,不但提高了企业出口在运输环节的附加值,而且也提高了企业在分销环节的附加值。
(二)中欧班列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拓展了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首先,中欧班列是“点对点”的出口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出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企业出口的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降低了企业出口的门槛,促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选择出口,从而优化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其次,中欧班列能够减少出口厂商的可变成本,增加企业的出口规模与贸易流量,进而优化了出口的集约边际。相对于空运而言,中欧班列运输成本更低,相对于海运而言,中欧班列速度更快。中欧班列全部采用标准集装箱运输,实现了各国间海关检查检疫的协作机制,一票到底、中途免检,降低了“冰山运输成本”,这对配送效率要求极高的全球价值链产业(电子、汽车等)显得尤为重要。中欧班列“点对点”的出口模式可以选择最优的运输距离,可以避免海洋运输过程中因气候变化、海盗活动等因素导致的航线绕道。
(三)中欧班列的运输服务优化了企业库存管理体系,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响应速度,改变了微观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今后的国际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供应链的竞争,中欧班列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创新。中欧班列日行一班的高频率满足了国内生产商小批量、多频度的运输需求,有助于企业压缩库存投资,提高库存周转率,减少企业的资金占用,这对企业供应链管理十分重要。传统的订单式产销模式(Build to Order)意味着企业只在接到订单之后才开始安排车间生产,产品生产完毕后才进入运输链条,产销之间势必存在时间差。中欧班列具备很强的分销优势,可以下沉到细分市场,企业可以通过精致化生产和零库存管理提升市场的响应速度,保持物质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生产中的同步,进而实现准时化生产,提高用户的体验。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复合比较优势初现
(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具备很强的“试验优势”
自贸区的试验既包括制度创新的测试,也包括企业创新的先行先试。从制度创新的视角看,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体现。自贸区提供了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一系列“试错”机制。与2017版自贸区负面清单相比,2018版自贸区负面清单再缩短50条,减至45条,不到第一版负面清单的1/4,逐步实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融合。自贸区充分发挥示范效应,截至2018年5月,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153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2018年自由贸易试验区代表性制度创新中,既有中欧班列的贸易便利化议题,也涉及了供应链金融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包含了首次建立的服务贸易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田”的作用充分彰显。
(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集聚效应初现,规模经济和资本要素禀赋引致的内生性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是外生的,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动态性特征。产业结构取决于要素丰裕度,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存量变化对一国要素丰裕度的影响最大,资本存量的积累取决于储蓄倾向和经济绩效。近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要素密集度逆转”,中国人口规模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红利显现。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位列世界第一,资本要素积累明显加快,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中国不但并未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且内生性比较优势的形成比美国还要快(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更是成为人才、资本、技术和服务业集聚的新高地。
(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制度比较优势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构成比较优势是因为制度创新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在可能性。企业生产需要两种不同的投入要素:一种是具有“私人物品”特征的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力与中间品。该类产品由市场竞价获得;另一种是具有“公共产品”的投入要素,如制度,该类产品由政府提供。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体现于第一类要素的禀赋,还体现为第二类要素的提供质量。制度质量不但影响第一类要素的供给能力,而且还对企业竞争力提升产生了不同的激励和约束。因此,比较优势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建立起来的技术效率优势,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提供的制度质量。
(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三重优势叠加,复合比较优势开始形成
一是试验优势和制度优势相互叠加。新业态的创新特别是颠覆式创新需要高昂的试错成本。企业创新试验的激励需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中国政治制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是稳定的,政策是连续的,这在中国由经济特区到各类经济功能区再到自贸区的改革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扩展自贸区内企业的可“试验”的空间,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潜力。二是制度优势推动了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再集聚,提高了分工效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各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于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配置资源,优质要素可以通过“用脚投票”(跨地区流动)进行制度选择。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优势会整合全球创新创业要素,形成人才、管理、技术、资本、服务等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优势。
结论与启示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新常态”,仅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角度观察,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趋同化、市场同质化和规则差异化三个方面。发展和提升中国外贸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既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
首先,互联网技术和跨境电商可以有效缓解中美产业趋同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中美产业的互补性是中美贸易稳定发展的根基,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美国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美国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与营销环节),而中国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美国寄希望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状况并没有发生,反而中国发生了“要素密集度逆转”。以往中美贸易的根基变得不再稳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中美产业呈现出了趋同现象,产品相似度日益提高。趋同势必会引致竞争,而竞争必然带来摩擦。面对中美未来可能更为激烈的产业竞争,依据“逃离竞争效应”,创新驱动和差异化发展变得尤为重要。互联网技术运用下的平台企业和跨境电商在创新驱动和差异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跨境电商有利于形成新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以“逃离竞争”,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对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跨境电商模式有利于形成差异化优势,通过定制化、差异化发展满足异质性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在竞争中存活。
其次,中欧班列可以解决中美贸易的市场同质化问题。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市场,导致了美国就业的下滑,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与美国企业产生了直接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战略的重心是“向东开放”,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城市布局看,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出口的目标市场看,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伙伴国主要集中于美国、日韩和东盟市场,而同样这些市场也是美国的目标市场,中国出口市场呈现出与美国目标市场高度趋同的现象,中美出口市场的拥挤问题凸显。以中欧班列为重要抓手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向西开放”打开了“一扇窗”。中国“向西开放”战略既可以降低中国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也可以缓解出口市场同质性引致的中美贸易争端。中欧班列有助于建立海陆贯通的新型贸易模式,最终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共轭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