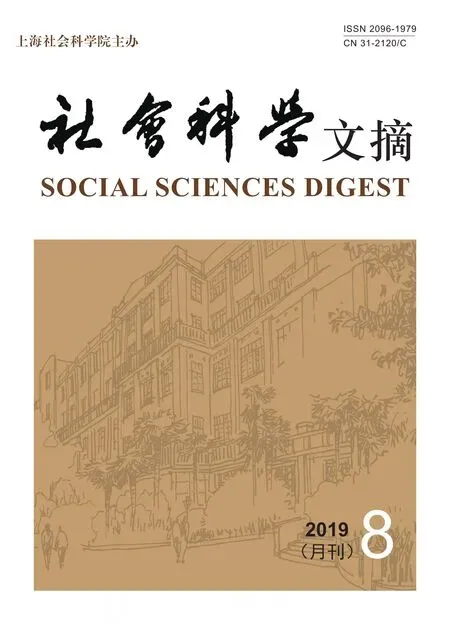经典与时代
——关于“父子相隐”的争议与反思
文/华军 杨猛
“父子相隐”之道
关于“父子相隐”,《论语·子路》有如下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结合原文可见,叶公言“直”在于讲述治下之民能够遵行法则而不顾亲情,体现了法则至上的原则;孔子言“直”重在“父子相隐”,体现了自然直情至上的原则。两者由此出现了观念与实践上的冲突。作为地方执政者,叶公的立场是肯定这种“直躬”之行。而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既是讲人之实情,又是讲人之情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表达。儒家仁者之爱可谓是普遍意义的具有沟通性的通情意识,而亲亲互隐则是特殊意义的具有限制性的别情意识。儒家重亲情,但并不与公义相违。可以说,孔子所谓的“直在其中矣”,本身既是真情流露,又是人之分位情理的具体表达,它自然包含着明辨是非、公义,绝非徇私枉法、无视正义。在此认识基础上,那种脱离具体的真情实感而执守抽象道义原则的“直躬者”,要么难逃“沽名买直”之嫌,要么便是为所谓现代普世主义教化所扭曲以致成为一无视人之自然生命之情的抽象存在。这恰是当下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我们所要着力建构的所谓的现代性当不能以此为基础,更不应以此为目标。
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议
“亲亲互隐”在本世纪初曾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有文章指认“亲亲互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的讨论。这些讨论大体呈现为赞成与反对两个方向:
赞成者认为儒家的“亲亲互隐”可以导出“亲情至上”,是社会公德、正义与法制的对立面,是滋生腐败与贪污的根源之一。其理论根据各异,以下简列三条:第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血亲宗法专制文化,反对“爱有差等”的伦理特殊主义,肯定“爱无差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以之为先进的现代文化精神;第二,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才具有道德普遍性,拥有至上的价值地位;第三,认为“亲亲互隐”对于维护血亲宗法制下的人伦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现代社会在情与法发生冲突时,作出法不容情的理性选择是社会正义的根本要求。
否定者以为,儒家的“父子互隐”首先反映了人的普通的心理事实,是人自然的情绪;其次,它并非指向一种特殊的专爱,其所谓“互隐”存在一定的限度,即隐于小过而不违大义;再次,“亲亲互隐”所代表的“差等之爱”在体现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的同时,经忠恕与絜矩之道的推拓而具有普遍性,故其仁爱虽然于具体情境下有差等之别,然又有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义;最后,“亲亲互隐”及其引出的“差等之爱”固然源出于血缘宗法制社会,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它已经转化为一种民族意识,具有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特性,亦是民族内在自我认同的一个要素。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现代性问题并不应以牺牲民族文化精神、屈从西方文化精神的化约方式来实现。至于其理论根据,亦简列数条如下:
第一,“亲亲互隐”首先体现了一种建基于血缘关系上的最切己自然的孝亲之情。孔子以“亲亲互隐”为“直在其中矣”,即是对其自然真情、不矫揉造作的肯认。
第二,“亲亲互隐”是儒家仁德践行中的一个基始环节,而非全部意涵,故而不能因为儒家孔子肯定“亲亲互隐”,即认定儒家讲究“亲情至上”、没有普遍的仁爱之体。儒家的仁体奠基于天道生生之德,其仁体实践并非是一种基于独立个体上的普遍意义的平等对待,而是一种“差等之爱”。儒家的“差等之爱”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来变现,而不能抽象化来认识。此外,还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其文化心理也是存在差异的。正如西方从一神教信仰的立场出发讲普遍伦理一样,“差等之爱”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立足自己的文化心理而对普遍之仁的特有诠释。二者基点不同,评价标准自然也不同,故只能寻求同情性理解,不能强求为一。
第三,“亲亲互隐”反映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在一定的特殊情境中,当私情与公义发生冲突时,对血亲一方维护血缘亲情的肯定。一般而言,仁爱公德的合理性必建基于私德基础上。离开私德讲公德,公德只能成为一种抽象原则。但是对于私德,不同文化系统的诠释是不一样的。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对血缘亲情的维护无疑是个人私德一个重要的方面。所谓社会公德必始于真实的血缘亲情伦理。其实,“子告父”“妻告夫”此类废私情而循政法以求公义的情况,在不同历史时期皆曾发生过,且多发生在尚法、集权时期。古人以为“直”道乃是以人之自然血亲直情为奠基的。违反此道的直则是值得反思、警惕的。近现代以来,此类矛盾现象亦不断出现,而其现实抉择的方式则颇为堪忧。所谓公德是不能抽象地凌驾于私德之上而标的其存在合理性的。
第四,“亲亲互隐”固然体现了儒家“差等之爱”的仁体实践特征,但是也有其内在的自我约限,这集中体现在“亲亲互隐”之“隐”的内涵限定上。首先,“亲亲互隐”之“隐”乃是指不主动称扬,属于消极的不作为、不显扬,而不是积极主动的窝藏、隐匿。因此,这个意义上的“隐”乃是人之自然血亲之情的当下真实展露,亦是对人之真实情感的一种肯认,绝非是表明儒家孔子赞成作伪证、消灭违法证据以及主动窝藏犯人。其次,“亲亲互隐”之所“隐”者是有约制的,乃指亲之小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亲亲互隐”则是不适用的。总之,儒家“亲亲互隐”有其内在的约限,它固然不会主张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公义原则至上,同样也非无限度地讲“亲亲至上”,其要在于中道合义。
第五,“亲亲互隐”作为儒家仁体的一种实践原则,原初就具有反抗统治者暴刑、滥用公权力以及维护个人正当情感权益的意义。随着统治者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它在中西法律和法律史上皆有着明确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亲亲互隐”的事实义与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对“亲亲互隐”问题的合理诠释与恰当安顿是法律自身是否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历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亲亲互隐”的观念,如《国语·周语中》有云:“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秦律中也已隐含了类似容隐的内容。汉宣帝时则首次将儒家“亲亲互隐”的思想纳入法律,并集中体现在“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上。其所包含的对象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对于他们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依律也不追究。《唐律》的制法精神就在于“一本于礼”,即将礼乐教化之责纳入法律之中。明清律在容隐制度规定上大体继承了唐律,甚至部分规定更为优惠。在西方思想史上,同样存在着重视与突出家庭伦理的思想倾向。例如,在《回忆苏格拉底》的第二卷第二章中,色诺芬详细记述了苏格拉底教导他的儿子应尊重其母亲的情形。苏格拉底认为,不敬父母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也是不义之人,法律对他们会处以重罚,且不让其担任国家公职,因为不尊重父母的人不可能很虔敬地为国家献祭,也不会光荣而公正地尽他的其他责任。再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把家庭伦理放在神的规律而不是人的规律的层面加以讨论,区分了家庭法与国家法,强调家庭法属神圣法。认为家庭伦理的神法应该高于国王的人法。至于西方古今律法中有关亲亲容隐的具体规定更是比比皆是,对此,范忠信先生曾多次属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明,此不赘述。
总之,作为一个法制社会,体察与尊重人性是其法治的前提与基础,而不是相反。否则的话,无论如何标榜其正义、公理,都是对民意、良心的变相强暴与扭曲。
围绕“父子相隐”之争的反思
总的来看,除却基本观点立场上的差异外,以上讨论还提示出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一)当代视域下的经典诠释问题。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已经被当代学者们讨论得太多了,实在乏善可陈。因为结合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通常说来,经典诠释无非是考据训诂与义理阐发二途,由此形成的学术风格通称“汉学”与“宋学”。前者侧重历史再现,寻求文本原义的解读;后者以“道器一体”、“体用相即”为诠释原则,依循“道通为一”的文化精神,结合个体视角与时代问题,对经典进行一贯义理的发挥,以把握道体的具体显现。在现实的诠释进程中,二者往往又交互并行。然而,在当代的经典诠释活动中,除了以上的理解外,另有一些诠释现象则有必要深入检讨:一是脱离经典文本本身,既非解诂,亦非体道,只是凭藉简单的望文生义而随意解说,实难达意,徒增曲解。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恐怕都是不当的;二是无视经典文本的文化属性,以其他文化系统为基础,刻意对经典文本的核心观念进行穿越式的解读,肆意褒贬,实为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三是抱着随风唱影、紧跟潮流的心态来对经典文本进行简单的、附和性的、极端性的、积极或消极的认定与诠释。以上种种文化诠释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以便我们能够通过现时代的经典诠释以实现求实与体道、传道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二)文化的价值评价问题。
当代文化价值讨论经常涉及到一个现代性问题,而围绕现代性的讨论则又习惯性地存在两个理解误区,即:“去古存今”与“以西非中”。
“去古存今”关涉的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现当代以来一直讨论不休的话题,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谓是关联一体的。因为传统文化往往具体体现为民族文化。当代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文化问题就是如何梳理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以往的一种做法是首先将这一问题归为古今问题,而后依据价值对立的判断,基于发展的目的,或做出“去古存今”的选择,或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2012年中国哲学史年会的时候,李祥海先生就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化约为时间上的古今关系。同样,时间上的古今关系也并不能化约为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李祥海先生指出,需改变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来裁断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价值的思维定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不可简单化约为古今关系问题。因为所谓现代是一个关于传统的现代,事实上并没有一个脱离传统的现代存在。黄玉顺先生则指出:“现代化或者现代性,它一定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不可能离开民族性来谈现代性”,“现代性的事情也就是民族性的事情”,“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涵项,一个基本的涵项,一个本质的涵项。离开了民族性,你就无法理解现代性”。由此我们就要肯定在当代发展中传统之于现代、民族性之于现代性的合理性意义,而不能继续秉持思想启蒙时期矫枉过正的极端态度与偏激认识。
“以西非中”关涉的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审查。首先,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皆有其相应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民族文化代表的是民族内部彼此的认同,他要回答的是你是谁的问题。由此来说,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即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取缔了民族性,而一个缺乏民族性的国家恐怕也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存在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说历史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改朝换代,但是文化没有动;二是国家亡了,文化也被颠覆了。前者叫亡国,后者顾炎武把它称之为“亡天下”。今天这种担忧恐怕仍然是很突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否定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比亡国还要严重、深切的问题。其次,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既有自己成熟、完整的观念体系,也有着开物成务、易简通达的务实、开放精神,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绝非如某些沉溺于传统民族文化自戕者所描述的那样呈显为一封闭性的存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思想家们一面自觉反思以往的文化资源和价值理念,一面了解与融进新的思想,以求在承继一贯之道的基础上形成契合于时代的新的价值观,以救世图存。如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即秉持实事求是之精神,主张“去中西之见”、“兼采中西”、“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以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强调“理求其是,事求适用”。再次,文化发展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确定是一个核心问题,而文化主体的确立必然依托自身的民族性和传统民族文化来进行。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亦不能背离这一基本原则。因为一个背离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只能是被转化直至异化,丧失自我。这种简单的同约并不能代表文化的发展,反而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同则不继”。最后,现代性转化并不等于就是西化,更不意味着“以西非中”的合理性。因为现代性问题是世界不同文化传统当下普遍面临的问题,其中蕴含着许多共同的关注点,但是如何诠释、评价乃至解决这些关注点,进而达成各自的现代性转化,不同的文化传统的选择只能是差异性的,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谓“现代性转化”绝不应成为当代西方文化霸权的代名词。
问题是,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近代以来,我们知识界的一些人一直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戕,总是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有问题,自己否定自己,由此出发,历史上无数入侵者没有办到的亡国灭种的事,我们今天这些自谓先进、现代、后现代的人可能反而办到了,即自己消灭了自己。用彭林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在办古代匈奴、清军、八国联军、日本武士道想办到而没有办到的事,即亡国亡族。为此,彭林先生描述了一种清华精神:“清华大学最初是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从建筑到学制全部西化。但是当时的清华师生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国家要自强,除了物质科技的学习以外,还需要民族精神的自强,科技可以引进,民族精神也需要引进么?科技可以进口,民族精神也要进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只能是西方的附庸,民族独立与自强则无法谈起。因为即使是积极学习西方、拜服西方的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主动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1925年清华大学废除了欧美教育体系,成立了自主的教育体系,设立大学部,创建国学院。曹云祥校长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而‘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为此方能实现中国之自强。由此开始聘任了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个举措就是要为当日之中国找回国魂,魂没了,国灭族亡还会远么?这也是老清华人的精神。”此言足以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