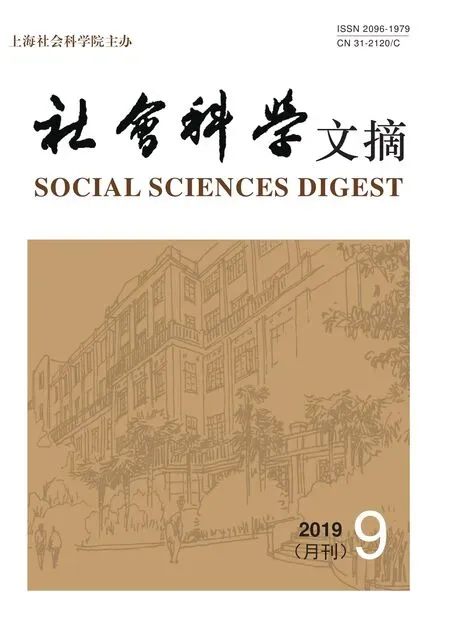文学社团与公共领域
——京派文人集团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比较研究
文/文学武
公共领域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由市民社会所产生的、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领域除了担负着重要的政治批判功能之外,它所生产出的社会公共舆论,还具有文化批判及文学批评等功能。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本质上具有与其他阶层的显著不同。“在任何一个阵营里,知识分子都是把意见或利益转化为某种理论的人;依其定义,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生活,他们还想思索自己的存在。”知识分子往往本能地通过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全面地介入公共领域空间。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还是京派文人集团,它们对公共领域的参与都是主动的、积极的,在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现代公共传媒的利用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舆论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公共媒介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知识者的声音在很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公共传媒才能得以传播。公共传媒的出现使得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诸如读者数量急剧增加,书籍、报纸等出版物数量猛增,一些组织群体开始形成,社团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现代媒体日趋成熟、发达的社会形态之中,知识分子如果想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力,通过公共传媒的方式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京派文人集团作为在现代社会诞生的文化社团,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媒介的力量,因而通过自办刊物、出版社以及报纸等现代媒体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最早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剑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进入到非常活跃的黄金时代。这群知识分子成为英国社会中非常醒目的人物,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知识贵族”的身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背景之外,这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媒介自觉的介入和运用。在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主要成员中,不少人都曾经从事过大众媒体的工作,能深刻感受到现代社会中公众媒介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辐射力。罗杰·弗莱、德斯蒙德·麦卡锡、凯恩斯、E·M·福斯特、伦纳德·伍尔夫等都曾经广泛参与期刊杂志的创办、编辑及撰稿工作。
当然,这其中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贺加斯出版社的建立。从1917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开始接手贺加斯出版社一直到1946年伦纳德·伍尔夫将其转让给查图-温都斯书局(ChattoWIndus),它存在了整整30年,对英国的现代文化思潮作出了重要贡献。弗吉尼亚·伍尔夫刚开始收购贺加斯出版社,就在这里出版了她们夫妇的《两个故事》,包括伦纳德·伍尔夫的《三个犹太人》和弗吉尼亚的《墙上的斑点》,出版取得了初步成功。随后,贺加斯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许多著作,其主要作者包括凯恩斯、福斯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一些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有交往作家的著作也在这里出版,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T·S·艾略特等,甚至也包括D·H·劳伦斯、里尔克、奥登、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弗洛伊德等人。1924年,贺加斯出版社开始出版系列图书“贺加斯论文集”(The Hogarth Essays)。美国批评家雷内·韦勒克曾经说英国谈不上有什么象征主义运动,当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席卷欧洲大陆之时,英国几乎还没做出什么反应。这表明英国确实一度在文学领域落伍了。针对这种现象,贺加斯出版社表现出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它有意识地倡导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出版了很多现代主义作品,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都表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运用大众传媒介入社会和文化空间时是积极、主动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发挥出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难以产生的影响力。
京派文人集团对现代公共传媒的利用
中国自从晚清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印刷媒介的作用也日渐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申报》《时务报》《时事新报》《新民丛报》等纷纷出现,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更是有着成功的实践。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媒介更为发达,知识分子对此更为重视。京派文人集团对于创办属于自己文化圈子的杂志、报纸、书店等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一旦掌握了现代媒介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作为京派文人集团前身之一的新月社,在这方面曾经有过很好的实践。他们在1928年3月创刊了《新月》杂志,一直到1933年6月停刊,持续了5年左右的时间。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罗隆基等都先后担任过该刊的编辑。《新月》刊发了大量的时政性论文、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文章,曾经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过很大的反响,甚至形成了一股政治的力量,对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提出强有力的挑战。
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非常相似的是,京派文人中不少都曾经有过编辑报纸、杂志和创建出版社的经历。可见,这种情形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样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满足于作家、艺术家、教授这样较为单一的身份,他们有着更大的抱负,同样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和文化使命,希望通过大众媒介的渠道去影响和改变周围的社会和民众。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知识者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双重角色,这一点通过京派文人集团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文学杂志》等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来。
《大公报》是当时中国一家历史悠久、也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因为它长期秉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它的副刊《文学》最初由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所负责,影响力非常有限。有感于此,《大公报》决定由杨振声、沈从文来负责改造这个副刊,使之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1933年9月,沈从文接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一上任就在《大公报》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尖锐批评海派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引起“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酿成文坛上的公共事件。从媒介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具有典型性,表明大众媒介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新闻报道阶段,强大的舆论力量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受众,进而培养大众的文学审美趣味,这样的行为具有了思想和文化传播的属性。在这种转换中间,编辑承担了关键的作用,甚至身兼“编”和“写”的双重角色。随着公共领域的兴起,编辑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高涨。可见,沈从文的这种编辑意识和举动正是一个主编的自觉行为。而朱光潜1937年所主编的《文学杂志》也秉承自由主义文艺理念,高举文学独立、尊严的大旗,践行“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主张,成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大本营,对自由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京派文人所创办或负责的报刊、杂志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象征性公共空间,对民众的文学启蒙以及作家、编辑、读者之间的互动都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文艺的繁荣和高峰的出现,这些印刷媒介也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知识分子在文化权力场中的角色也展露无遗。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通过读诗会、艺术展览等方式扩大影响力
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方式与传统社会相比也有着质的区别,之所以如此,这主要因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媒介、交往方式。除了印刷媒介之外,还有诸如学校、结社、展览、朗诵、演戏、沙龙等多种形式。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不仅充分运用现代大众传媒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还通过读诗、读剧本、演戏、举办艺术展览、集中出版作品集等方式来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生活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读诗会始于星期四的聚会,他们吟诵诗歌,充分展现出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膜拜。读诗之外,他们也读其他文学作品。利顿·斯特雷奇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一书,因而名声鹊起,他本人就亲自朗读这本书的相关章节,有时也朗读别人的著作。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特别重视阅读剧本。1907年,他们在戈登广场46号成立了“剧本阅读会”,创建者包括贝尔夫妇、阿德里安·斯蒂芬、弗吉尼亚·斯蒂芬、斯特雷奇、锡德尼·特纳等。这个阅读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朗读活动,一直持续到1914年。他们经常朗读的有拉辛的剧本以及伊丽莎白时期剧作家的作品。在读剧本的同时,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也热衷演戏。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虽然带有较强的贵族精英意识,但他们同样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艺术象牙之塔很难有立身之处,只有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中才能真正产生影响。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千方百计地吸引人们的视线。比如他们多次举办巡回画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在艺术界形成轰动效应。由罗杰·弗莱组织的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于1910年11月8日至1911年1月15日在伦敦格莱夫顿(Gratton)美术馆举行。此次画展集中展示了塞尚、毕加索、德兰、马蒂斯等后印象派的画作。紧接着罗杰·弗莱在1912年11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后印象派画展,展出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画家的画作。其后他们还举办了一系列比较有影响的画展,这些举动无疑扩大了他们在艺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大都身兼艺术家、文学家和评论家的多重身份,他们对公共领域空间的介入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文学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的,其中最常见、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从事文学和艺术评论、出版自己文化圈系列的作品集。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等在文学和艺术批评领域都曾经发表过重要的著述,在文学性公共领域表现异常活跃。罗杰·弗莱不仅是一个画家,而且在绘画美学领域发表过许多评论文章,在美术界有巨大的影响力。克莱夫·贝尔是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美学家,曾提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命题,对形式主义的艺术思潮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斯特在文学批评界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这种同人之间的批评不仅从整体上扩大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影响,而且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也是很有必要的。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还依托贺加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贺加斯论文集”(The Hogarth Essays)、“贺加斯文学讲座”(The Hogarth Lecture on Literature)、“新署名”(New Signature)等系列丛书。这些宣传和出版方式强化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公众眼中的社团属性和声誉。
京派文人集团也通过读诗、演戏等方式扩大影响力
虽然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中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公共领域所呈现的形态也未必完全相同。然而,京派文人集团在参与公共性领域的过程中,也采用了包括读诗、演戏、出版作品集、评奖、开展专栏批评和同人批评等一系列方式,在这些方面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十分相近。他们尽最大的可能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公共领域的自觉意识和积极姿态。
京派文人非常注重诗歌的朗诵,他们经常在朱光潜所住的北平地安门里慈慧殿三号举行朗诵诗会。朗诵诗会上的气氛十分热烈,有时人们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林徽因和梁宗岱曾经因为新诗的某个问题就争论得不可开交。京派文人不仅读诗,也读散文等作品。定期举行的朗诵诗会极大地活跃了北方文坛的空气。
除了朗诵诗,京派文人也格外重视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如林徽因、李健吾、杨绛、丁西林都曾经写过戏剧作品。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些剧目搬上舞台,公开演出,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戏剧《委曲求全》的演出。《委曲求全》出版后,人们感到这部剧作很有讽刺力量和戏剧冲突的因素,因此决定把它搬上舞台演出。全剧共排练了三个月,后在协和礼堂公演,引起轰动。在这个过程中,李健吾、林徽因等花费了很多心血,林徽因参与舞台的美术设计工作,李健吾亲自在剧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
由于京派文人掌控了相当多的媒体资源,他们能够较为充分利用现代媒介传播快、覆盖广等特点来组织文学评奖、发起文学论战以及出版作品集等,进而传达自己的文学和社会理念,扩大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37年的“大公报文艺奖金”事件和《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1937年颁发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是20世纪30年代很重要的一次文学评奖活动。关于此次评奖活动的动因和经过,当事人萧乾曾有过详尽的回忆。人们从他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京派文人集团在这次评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京派文人集团占据了评委人选的大多数,而评奖规则的制定和最终评选的结果,也显示出京派文人集团对评奖事件的掌控力。
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树立明确的文学社团意识,京派文人在组织评选文艺奖金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出版作品集,凸显他们的集体文学成就。1936年,《大公报》约请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为了配合这本书的出版,《大公报》很早就开始连续登载了出版广告,对这本书进行宣传。林徽因编选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中的作家,大多和《大公报》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是由《大公报》所提携、扶植起来的,如芦焚、萧乾、杨绛等。林徽因在题记中对他们的评价客观上代表着对这个文学社团的肯定。
与其他文学社团和流派有着很大的不同,京派作家尤其重视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建设,他们通过这种职业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介入公共性的文学领域,承担着文学公共领域启蒙的重任。不少京派作家往往也都兼有批评家的身份,如周作人、李健吾、梁宗岱、沈从文等,而朱光潜、李长之更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上。京派文人之间彼此的这种批评,使得他们承担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这一文学社团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也使公众加深了对于文学世界的感悟和理解,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京派知识分子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其对公共领域介入和参与的热情和方式,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