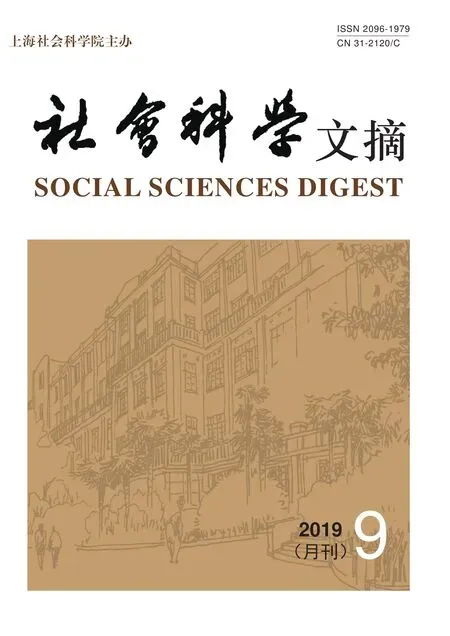西方文论关键词:后人文主义
文/陈世丹
后人文主义的提出
后人文主义思想是在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人类”的字面意义是指存在于超越人类状态的个人或实体(entity)。这一概念提出了伦理学与正义、语言与跨物种交流、社会制度和跨学科知识等问题。在批评理论中,后人类是一个思索性的存在,它代表或追求对人类的重新设想。在现代高新技术盛行的背景之下,后人文主义首先意味着一种试图克服人类身体有限性的超人形象,这也是后人类给予人最直观的印象。后人文主义以人类作为自己批评的对象,它批判地质疑人文主义。
后人类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和智能技术越来越互相缠绕的状况。更具体地说,后人类是一种人类设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那些信仰后人类的人所说的信息模式使我们成为所是之物,这种模式的开放将把对人性关注的焦点从我们的外观转移到那些信息模式。这样,关注的焦点将会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形式上:人性将被根据一个物种如何起作用来定义,换句话说,根据它是否像人那样加工信息——即它是否是有感情的、感情移入的、智慧的,等等——而不是根据它的长相来定义。
后人文主义派生于后人类,因为后者代表人文主义主体的死亡。构成主体的品质取决于作为一种特殊的独立实体的特权地位,这种特殊的独立存在拥有使它在宇宙中例外的独特性,例如对于所有其他生物而言它具有独特的优秀的智力,或拥有一种获得自由的自然权利,而这种自由是其他动物所不能同样获得的。如果焦点是在所有智能系统本质的信息上面,物质和身体本质仅仅是携带生命的全部重要信息的基板,那么在人类与智能机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智能系统,例如动物、外星人或一些构成智能存在的物质,例如一群蜜蜂、某一行星的生态层、一组演算法、一组细胞自动机或一群细胞(毕竟它们就是人类的身体)之间,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异。换句话说,人类例外主义死了。我们面对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仅仅是与其他系统结合的系统。这就是人文主义的主体之死,它导致了如何考虑后人文主义主体地位困境的问题,这也是“后人文主义”所应对的学术上的当务之急。
后人文主义的发展
后人文主义的根源可追溯到后现代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但是“后人类转向”完全是由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理论家所创造的。它发生在文学批评领域,所以后来被界定为“批判性后人文主义”。同时,文化研究也接受了它,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文化后人文主义”的看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批判性后人文主义和文化后人文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更聚焦在哲学上的探究,如今被称为哲学后人文主义(philosophical post-humanism),它是一种综合的尝试,通过一种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主义假设的新认识,重新进入哲学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后人文主义经常被解释为后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anthropocentrism),因为它出现在人类概念之后和人文主义历史之后,而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分等级的社会建构和以人为中心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物种歧视(speciesism)变成后人类批评方法整体构成所必需的一个方面。不过,后人类对人类首位的克服不应该被其他种类的首位(例如机器的首位)所替代。后人文主义可被视为一种后排他主义(post-exclusionism),即反对人的任性和自以为是的状态:一种调解的经验哲学,它以其最宽广的意义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和谐。后人文主义并不使用任何正面的二元论或对立面,通过解构的后现代实践使任何本体论的对立非神秘化。
后人文主义是一个后现代的明确特征。被后人文主义置于危险中的不仅是传统西方话语的中心,这一中心已经被其外围(例如女权主义理论、批判性种族理论、酷儿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从根本上解构了。后人文主义是一种后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心,而是认为有许多特殊的兴趣中心;它既以其霸权的模式又以其抵抗的模式解散单数形式中心的中心性。后人文主义承认多种兴趣中心;但这些兴趣中心是不确定的、游动的、短暂的,其视角必须是多元的、多层的,尽可能是综合的和包容的。
哲学后人文主义的出现
到20世纪90年代末,批判性后人文主义和文化后人文主义的发展成为更多聚焦在哲学上的探究,如今被称为哲学后人文主义,它试图通过一种新获得的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主义假定(assumption)的认识,重新进入哲学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家伊哈布·哈桑曾阐明,当人文主义把自己变成人们无助地称为后人文主义的某事物时,人文主义可能就行将结束了。这种观点在时间上早于后人文主义潮流的大多数观点,后人文主义潮流是在20世纪晚期以多样化的但互补的思想和实践领域内形成的。例如,哈桑的理论著作清楚地提出了后工业社会中的后现代性。后人文主义超越后现代主义研究,被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家展开和利用,经常作为对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中成问题的形而上学的内在假定的反应。
后人文主义通过把人类降回到许多自然物种之一而与经典人文主义不同,从而拒绝了基于以人类为中心统治的任何要求。根据后人文主义,人类没有破坏自然或以先天道德理由使自己高于自然的固有权利。先前被视为世界的规定性方面的人类知识也被降至很少控制性的地位。人类权利、动物权利与后人类权利都存在于一个范围。人类智能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是众所公认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抛弃人文主义的理性传统。
后人类话语的支持者们认为,创新进步和新兴技术胜过了笛卡尔等与启蒙运动时期哲学有关系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人类传统模式。后人文主义话语追求重新界定现代哲学对人类认识的边界。后人文主义代表一种超越当代社会边界演化的思想演化,被放在后现代语境中追求真理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它就抛弃了其早先要建立人类学共性的尝试,那种人类学共性被灌输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假定。
哲学后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
后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挑战的第一个关键点是作为人文主义理论基石的“人”的概念。因为事实上,至少自17世纪以来,所谓的人文主义不得不依靠某种从宗教、科学和政治借来的“人”的概念。后人文主义在解构了传统人文主义赋予人的一系列特权,例如优先权、中心性、绝对性、超越性、自主权等之后,宣告被传统人文主义奉为神圣的“人”死了。依据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话,上帝已死的时代已被人已死的时代所取代;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公开宣布,我们必须抛弃主体(人)这个令人讨厌的宠儿,因为它占领哲学舞台太久了。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萨特发展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主观性哲学。实际上,自笛卡尔以来,法国哲学一直是被主体的概念所控制。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其他真理,我们必须选择另一种观点,一种不同的观点。于是,后人文主义就用下列方法围剿作为中心而存在的“人”。
首先,后人文主义向人的中心性和优越性发难。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哲学人文主义都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它们假定的理论前提,都抬高人类,认为人类至高无上,而且将主体置于现实和历史的中心。根据后人文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自大狂(megalomania),一种渴望将人类自己变成上帝的征兆。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在其《人文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Humanism,1981)一书中认为,所谓人文主义的终结就是自大狂传统的终结。人类的这一特权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特权。在后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文主义所尊敬的主体性并非根深蒂固地隐藏在表面作用下被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所研究的哲学现实。它是一种不需要解释的深层结构或深刻理性的表面现象。后人文主义将“去中心”作为武器,使自我非中心化。作为中心的传统自我被当作幻觉、信仰的产物而被抛弃。后人文主义的结论就是“我们是非统一的、多元的存在”。
关于对人的中心性的抨击,后人文主义进一步破坏了人的优先权和自主权。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用考古学方法对“人”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其研究成果震惊世界。根据他的分析,值得尊敬的“人”本身的西方概念不是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而是一种特殊时代和特殊知识的有条件的产物。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而且它肯定人的存在性,所以存在主义就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哲学。对此,福柯的反应是所谓的人的概念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认识论的建构。不仅人是有限的,而且所谓人的自主权和创造性也只是一种“神话”,人并非人文主义者以为的能动的创造者,而是被想象出来的,其存在是“现代思想所构成的”。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个人或人类主体是首位的,其实个人或人类主体只不过是无个性特征的语言或思想体系的表面结果。因此,对后人文主义者而言,主体就被放逐了、被边缘化了。最初在传统人文主义中被认为是终极根源和构成主义的人被变成了后期生成的、派生的和建构的事物。
后人文主义另一重要的理论内容是对人性论、不变的人性和人本质的讨伐。后人文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普遍的、一般的和不变的人类本性和人类本质,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本性”和“人类本质”的概念应当抛弃,因为人并非人文主义以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和一种独立存在的事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根据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激进的实证主义观点,人们不再对解释的动机感兴趣,而只重视行动。人们不再设法查明不同的人实际上是否是不同形式的相同的个人,而只认角色为唯一可以被认识的关于个体的真理。
人文主义认定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和无限的认知能力,人的思想能够绝对地认识关于一切的真理。后人文主义用怀疑论颠覆了人文主义在思维和存在关系上的自信。在此基础上,后人文主义进一步推翻了人文主义的人类进步的概念。这种人类自信主要表现在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的格言上面。后人文主义挑战这一信仰,其挑战首先从尺度开始。根据伊哈布·哈桑的分析,“尺度的理想模式是封闭在真空里的计算器,但这一用来计算长度的仪表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一直是通过早期的白金(platinum)到铱(iridium)到光谱(spectrum)、光的波长(light wavelength),再到86氪(krypton)桔红线(the orange line)”而反映的。其特征是越来越非实体化、非物质化。然后,哈桑以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画《罐装机遇》(Canned Chance)为例,又解释说关于同一理想长度我们可以有三种观点。既然所谓的客观的准确的尺度总是变化的、各种各样的,那么作为“尺度”的人必定不可能是绝对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作为尺度的人开始变化的门槛上。那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绝对向相对转变。
在后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类只能相对地认识事物,不可能绝对地掌握事物。确实存在我们不能讲述的事物,它们自己显示自身,可称为神秘的事物。人并非是传统人文主义以为的那样无所不能,因为一切都不是特定的,一切都不是已知的。作为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先驱,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谈到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未加思考的(unthought)事物。传统的人文主义错误地理解了未加思考的事物,或视其为客体的抽象形式或视其为主体的抽象形式。换言之,所有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通过人为地把复杂的、多重的事物还原为简单的、单一的性质而犯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错误。海德格尔的“精神”(spirit)、尼采(Freidrich Nietzsche)的“权力意志”(power will)、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力比多(libido性冲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都与此类似——把复杂的、多重的事物还原为简单的、单一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后人文主义把思想看作一种进一步产生复杂性的事物,并且认为不存在任何不证自明的思想。知识不再是笛卡尔式的个人考查思想内容的确定性结果,而是社会地产生的。笛卡尔的“我思”不是认识的前提,而是认识的结果,而且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化认识的结果。此外,笛卡尔式的内省、自省、自我研究方法将不再起作用,因为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不再是自我透明的”。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认识和我们将认识什么。
在后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文主义还有一个盲目乐观主义的谬误,其理论基础是把人置于上帝的位置,并把人类自由的进步等同于人类理性的进步。这种盲目乐观主义无法回答后人文主义提出的下列问题:人类有文明,可是为什么他们日益焦虑和孤独?人类有科学,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地感到困惑?人类不断获得丰富的知识,可是为什么他们觉得自由离他们更加遥远?与传统人文主义相比,后人文主义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这显然是对人文主义的廉价乐观主义的否定。这种否定是有深刻的历史内容的。与此否定相联系的是对进步概念的幻灭。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所曾经讲述的各种各样关于“人类不断进步的故事”现在仅仅被后人文主义视为一种“虚构”,“一种人为的虚构”。
总之,后人文主义是一种时代的哲学、一种当代西方正在进行的具有广阔影响的哲学文化思想。它既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思,也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回应。它既是一种对现实的哲学反思,也是对哲学本身的自我反省。从哲学的视角看,后人文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使我们重新认识人在世界和现实中的地位,重新认识曾自以为是“万物的尺度”和“中心”的人,重新认识曾经以为是清楚已知的世界。具体地说,后人文主义使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人的存在相对化、多元化、复杂化了,因为世界本身是相对的、多元的、复杂的。可见,后人文主义完全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主体观念”。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抽象的人类本质这一点上,后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殊途同归——他们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人文主义者所说的“人之死”是指“被主观主义地理解了的人的死亡”。一旦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本质”和“特权”被剥夺,人就会被还其本来的、相对的、多元的、复杂的真实面目。与经典人文主义不同,后人文主义通过把人类降回到许多自然物种之一,从而拒绝了基于以人类为中心统治的任何要求。在明确人类权利、动物权利和后人类权利都存在于一个范围内的认识基础上,后人文主义形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建构尊重自然、不同物种相互依存的生态社会;(二)人类必须用后现代伦理道德与政策法规指导、规范科技实践,合理利用高科技;(三)人类要尊重和关爱非人类,平等对待智能机器人赛博格(Cyborg),建构多元物种和谐共生的后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