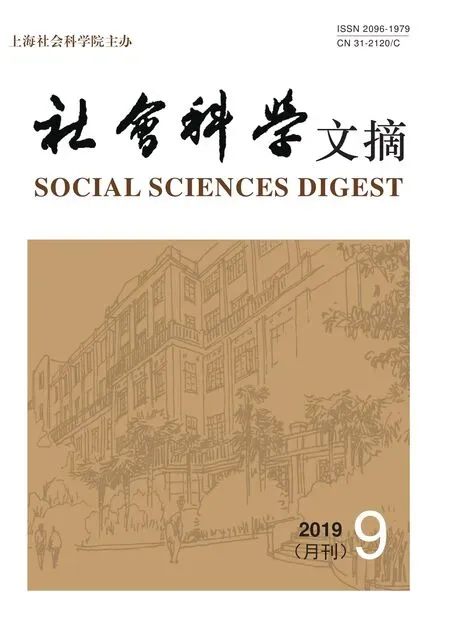“社会学转向”与章太炎的“文学”界定
文/史伟
晚清、民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文学”的界定也出现了多歧的现象,一种仍坚持传统观念,以传统的“文章博学”界定文学,另一种则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但即使同样接受西方文学观念,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有从语言和语言学的角度界定文学者;有从文体学的角度界定文学者;有从情感、想象的角度界定文学者,而强调情感、想象之文学界定也多落实于文体。
相较而言,章太炎的文学界定方式最为独特,因其所涉学理和研究目的的复杂性,也最不易为人理解。有的认为他所持者仍是“文章博学”观念,是退回到传统的大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有的认为其文学观是出于小学家或经师的偏见。邢公畹在《论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纪念罗莘田先生90寿辰》一文中指出章氏文学定义的另一面向,即“近于文化人类学对文学所给的定义”,“‘书于竹帛’的‘文’,实质上就是一些‘要求照原样常加复述’的言辞”。不过,邢文所说的文化人类学,置于章太炎的学术语境下更确切地应该说是社会学,虽然章太炎很早就接触了人类学,但其学术研究的学理基础实为社会学。
“尔雅之故言”:《文学说例》所见之“文学”观
在1902年《文学说例》(以下简称《说例》)一文中,章太炎最早对“文学”作系统论述。《说例》篇首即云:“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定义典出《大戴礼记·小辨》:“公曰:‘不辨则何以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於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陆胤将之解释为“把依据故训以正名作为其所谓‘文学’的本旨”。从“尔雅以观于古”的上下文来看,“尔雅以观于古”与“循弦以观於乐”的礼乐风俗是联系在一起的,“观于古”就是先王、诸侯、大夫、士等风俗礼乐、典章制度之事,这与《尔雅》作为名物训诂之书“虫鱼草木,爰自尔以昭彰,礼乐诗书,尽由斯而纷郁”的特点是一致的。当然,这绝不是说,章太炎要把“文学”复古至礼乐风俗,而是说在“尔雅以观于古”的层面,“文学”是一个涵盖极广的范畴。《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中也有以礼乐释“文”的内容,可以说是对《说例》的延续。
《说例》将文学起源归于语言,谓:“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自书契既作,递有接构,而二者殊流,尚矣。”然而,在语言、书契殊流二分之后,章氏所重在于书契,故他是立足于文字而非语言界定“文学”。而《说例》的主旨就在于“率取文学与雅故神恉相关者,观其会通,都为一牒”。因此《说例》之论文学,实为两条线索,一是小学、文字,所谓“雅故”;二是文学,即以文字之引伸假借解释文学之踵事增华而愈失其真。
联结文字和文学的是“表象”,“表象”一词指“人类用直观、感性的形式,来表示抽象的概念,表达内心的欲求”,这来自日人姉崎正治《宗教病理学》:
凡有生活以上,其所以生活之机能,即病态之所由起,故凡表象主义之病质,不独宗教为然,即人间之精神现象、其生命必与病质俱存。马科期牟拉以神话为语言之疾病肿物。……要之,人间之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
姉崎的逻辑关系相当清晰。首先,姉崎的主旨在于以“表象之病质”来沟通宗教与神话。从“表象主义之病质”的角度出发,宗教和神话具有同质性,都是“人间之精神现象、其生命必与病质俱存”。其次,为了支持“表象主义之病质”这个论证的基点,他又引马克斯牟拉(今译“麦克斯·缪勒”)“神话为语言之疾病肿物”之说,以语言之讹误为证,而归于“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
章太炎移用了这套逻辑,他用“表象”来连接文字或“符号”与文学,更重要的是,用表象拟文字之引伸假借。一者,他称举凡“号物之数”“人事之端,心理之微”“动静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为其号,而多以一言隐括;在无形者,则更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表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也就是姉崎所说的“人间之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而皆不离“病质”;二者,在姉崎以“语言之疾病肿物”来解释“表象主义之病质”这一点上,章太炎认为“其推假借引伸之起源精矣”。章氏对缪勒的理论并不陌生,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知识就得自缪勒,成为他以后“寻其语根”的语源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于是,文学的发展也就成为文字“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的历史。章太炎意在“存质”,但他也很清楚“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最终他的“尔雅以观于古”的“文学”观落实在具体文学样式上,就是回归训诂笺疏之体,所谓“表象之病,自古为昭。斲雕为朴,亦尚故训求是之文而已”。
《说例》以“雅故”界定文学,虽与彼时文学界定有差异,但毕竟所讨论的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范围之内,而且在梳理和论证文学问题时也涉及就那个时代而言很有意义、价值的问题,虽则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文学问题,也包括语言文字和修辞学。但章太炎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说例》的主体之后成为《訄书(重订本)·订文(附:正文杂议)》的一部分,又为《检论》所本,但这两部书中都删除了篇首文学定义的部分。这意味着,前面梳理的一系列论证,已不再支持或指向文学。
1902年:章太炎的“社会学转向”
之所以出现此种转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章太炎对社会学的接受。在此之前,支持章太炎文学观念的主要是马克斯·缪勒的语言学、神话学及姉崎正治的宗教学,但此后,社会学成为其文学界定的学理基础。
早在求学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已“开始注意阅读此前江南制造局、同文馆和广学会所译述的一些西学书籍”。1898年,由曾广铨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载于《昌言报》第一册。此后他又接触了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等所著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然其达到学理上的会通,则得力于1902年流亡日本期间对社会学的研习。
章太炎在《社会学自序》中叙述其经由斯宾塞社会学进阶而前的经历十分亲切。他不满于斯氏者在于两方面,一是学理的薄弱,更重要的则在于“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因为这对热心改造社会、为中国社会谋出路的章太炎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吉丁斯“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是其学理优长之处,但吉丁斯以“同类意识”贯穿解释整个社会变迁,则仍不无片面。章太炎所取于岸本氏《社会学》者,在于其折中调和的一面,“日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
在新学理的视阈之下,章氏得以全面审视此前学术训练。章太炎早年服膺西汉刘向、刘歆之学,自称“刘子骏之绍述者”,经由刘歆梳理源出于道家(即先秦管子、庄子、韩非之学)的史学传统。当他接受了社会学,认识到两者在所谓“进化之理”的契合之处,道家史学就成为章太炎从进化论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史学的起点。向下则延伸至他久已谙熟的杜佑《通典》等典志之学。社会学、社会史与传统史学,尤其是“道家”史学和典制之学的会通,是社会学影响章太炎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学与语言文字之学
社会学影响章太炎学术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小学或曰语言文字之学与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会通。章太炎在1902年8月18日给吴君遂的一份信中称:
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音七书。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
章氏在学术志写作中借惠栋尤其是戴震小学,发现“支那文明进化之迹”。章氏在信中所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的研究方式其实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语源学或词源学研究的方式。章太炎的《文始》及《新方言》等,都可以说是以“探考异言,寻其语根”的词源学方式,为社会学研究奠定基础。
不过,章太炎所说的“寻其语根”,其重文字更甚于语言,如《訄书(重订本)·订文》所云:“且夫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揫迫而因于文。”但章太炎并非不重语言。这就需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即章氏立论的学理前提的问题。章太炎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宗旨是社会学和社会史,各方面研究都需要置于这个前提下,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作为一个语言学或文学研究者,可以将语言优先的观念贯彻到底,但作为一个社会学和社会史的研究者,他必须要着重考虑到文字问题。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够全面反映社会历史文化之全貌。
通史、国粹、国故与社会学、社会史
明了社会学、社会史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之后,需要厘清章太炎学术思想中几个重要的概念——国粹、国故、通史——及章氏几部重要著作《訄书》《国故论衡》等与社会学或社会史之间的关系。
(一)通史、国粹。“通史”就是社会史。章氏“通史”的特点,一是社会科学如“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的“熔铸”,这就是“新理新说”。二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之衰微”即进化论和“鼓舞民气、启导将来”为通史写作之宗旨,此两点正是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的基本特点。三是通史的内容和体例主于典志和人物纪传两方面。
“国粹”也具社会史的性质。章氏《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解释“为甚提倡国粹”云:“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广义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二是人物事迹”,这三项正是“国史”研究的核心。故“国粹”即“汉种的历史”,确切说就是“汉种”社会学或社会史研究。
(二)《訄书》《检论》。对《訄书》《检论》的内容体例与章太炎所拟之“中国通史目录”(《訄书(重订本)》附)作一比较,可以看到,《訄书(重订本)》除部分“典”外,缺少大部分的表、记和考纪部分,然综括而言,《訄书(重订本)》包括了典志、人物和语言文字三项,其中尤以典志为最重要,而拟定中的通史本以“志居其半”,故《訄书(重订本)》确已涵括了“通史”中的大部的重要内容,并且完全符合《与梁启超》书或“中国通史略例”所制订的通史写作宗旨。
(三)国故、《国故论衡》。国故也具社会学或社会史性质。国粹就是国故。《国故论衡》上卷小学部分,是综合了《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訄书(重订本)》中“方言”“订文(附正名杂义)”“述图”与《国故论衡》小学实关系密切,“方言”涉及语言;“订文”主要涉及文字,部分地涉及语言;“述图”包括图画、器物、薄录,有一定程度的文献的意义,在顺序和结构上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语言--文字—仪象”之说完全一致。故《国故论衡》“小学论略”“文学论略”宗旨即在于界定“小学”“文学”之畛域,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章太炎拟想中的通史或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概论或导论部分,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部分。
《国故论衡》中的“文学”界定
章太炎小学或语言文字之学与“文学”关系密切,但小学并不能直接地通向“文学”,而是要落实到文字的物质载体才能通向文学。此即章氏所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按照以上逻辑:
第一,章氏从本义上立义释“文”。其一,释“文”为“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其二,释“文章”为礼乐制度:“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章。”其三,即就篇章而言,如王充《论衡》所言,也涵括了“奏记”及“经传、解故、诸子”,仍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为涵盖此广大之“文”,就只能在“文字”上立意。故章太炎云:“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第二,章氏不唯在“文字”上立义,他以“寻其语根”的方式解释何以要立义于文字时,每归至“文”之诸种形态的物质载体,他说:
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诸有句读文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
为了说明“成句读文”“不成句读文”的分野,其实也是为了说明以“著于竹帛”界定“文”的合理性,章太炎提出“语言—文字—仪象”模式,他说:
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足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
此模式中,章氏据“言语、文字、仪器三者功能之不同”将文字析为两类:与语言关联的记录语言“本以代声气”之文字及与语言无关的“表谱图画”之文字,后者在“功能”上只属于文字而与语言无涉:“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也”。之所以强调“不成句读文”,是因唯其如此才能全面、完整地覆盖或反映“一切著于竹帛者”。
而这样的一再推原至其物质载体以明“文学”之义的方式是通向史学的,侯外庐指出:“他(章太炎)把文字学一方面建立在名学上,又一方面建立在史学上,这和他的经史之学相似其研究方面。”从这个角度讲,章氏之“文学”定义近于社会史研究中文献学或史料学的概念,他在“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立义以界定“文”,正是为了求得史料“规模之宏大”与“中国语言文字之全”。
第三,章氏“文”的定义近于文献学或史料学的概念,史料的体制形式和呈现、表达方式涉及“法式”,而其论“法式”也是以“寻其语源”的方式,从“文”的物质载体立义,如其释经为“编丝缀属之称”,释论为“古但作侖。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侖”。但“著于竹帛”适用于文学之始,以后的文学发展必定会离开这个阶段,渐及于文体的发展演进,这就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衔接起来。
从《说例》到《国故论衡》,章太炎所探讨的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问题,而是涵盖了文献史料、文献的形式体制及其表达、呈现诸多层面的内容;而因所涉问题过于宏大和复杂,故分论“文”与“法式”。而章太炎“文学”观,就成为晚清、民国之际新学理的汲取,新学理下传统观念、材料的聚合杂揉,同时又以章氏独持的学术个性镕铸,所产生的奇丽风景。
章太炎晚年自评其学术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在“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之间,章太炎斟酌权度于新旧学理的复杂而富于创造的探求,则不唯为认识章太炎本身学术变迁本身,也为认识晚清、民国之际中国整个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