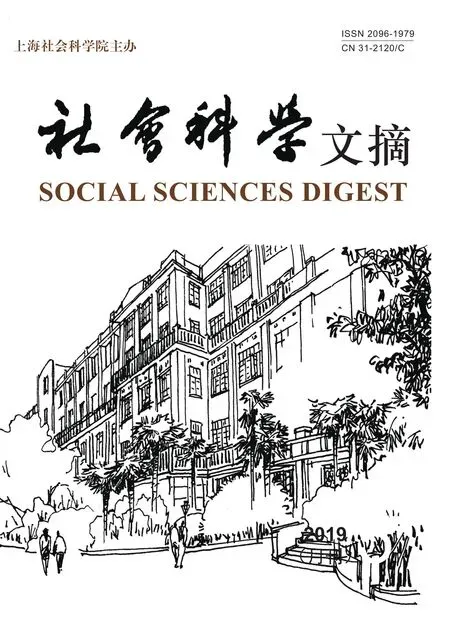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反传统”更是创造性转化的动力
——鲁迅“反传统”再评价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对“五四”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化的不同评价而引发的巨大争议,是百年来中国思想学术领域最重要(没有之一)的文化现象。近年,伴随着中国“国学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推动,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原本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争议现象,又进一步溢出而具有某种政治倾向,或曰“泛意识形态化”。五四新文化在这一范围内有被“污名化”的趋向,它助推了某种“非学理化”倾向的漫延。它主要体现在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把五四新文化对于西方的介绍和借鉴,简单地定性为“全盘西化”,“化”者,已丧失主体性立场之谓也;二是以西方的新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重估、批判,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立场。把“西方”和“传统”都看作一个“定型”的东西,在其背后是“本质主义”一元论思维模式在主导,因而其结论不过一个线性武断的论证 ,但是在某种民粹化思潮的助推下却影响深广。
“五四”与鲁迅研究的学术化努力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显示了五四新文化“实绩”的代表人物鲁迅成为热点话题,但是经过一轮“反思启蒙”“反思鲁迅”之后,鲁迅的思想在这种“反思”旗号下逐渐趋于“消解”,其价值愈发晦暗不明。“污名化”同样表现在对待鲁迅的态度和评价上,主要有二:一是鲁迅被冠以“反传统”,二是鲁迅被视为“中国文化吃人”的始作俑者。其中,最新论调是鲁迅乃西方“殖民主义”的代言人。建构自主的本土化学术体系的诉求和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关于鲁迅的争议又掩盖于某种“学理化”的理论外衣之下。
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和警惕。他们力图将关于五四新文化和鲁迅的研究拉回并限定在学术的范畴内,即使探讨“政治五四”也以学术的和分析的方法对待之。这是富有成效的。20世纪90年代始,王元化对五四新文化和鲁迅的认识较之其前更加全面,他既取“五四”的立场,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思五四”,但他并非有些人那样,借“反思五四”之名解构“五四”。2009年“五四”90周年之际,张福贵、陈平原和钱理群等均有关于五四新文化和鲁迅的研究文章面世。在《为“文化五四”辩护》一文中,张福贵从历史、观念和方法诸多层面对人们习称的“五四”予以厘清,即有一个“文化五四”和“政治五四”之别。而“文化五四”也并非铁板一块,他认为,“文化五四”也有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之分,后一种提法更引发人们的思考。这种从方法论角度的切入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高屋建瓴的宏阔视野。陈平原《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也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中观察“五四”。钱理群是在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中专门谈论鲁迅的,与我们的论题切近。他认为,五四新文化是一个“大传统”,在其中又有诸多的“小传统”,鲁迅就是一个“小传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鲁迅五四”,但它是五四新文化内部的一个小传统,因而其基本方向与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
上述研究都不限于具体的结论或观点,而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尤其是他们通过具体问题的探析,力图切入五四新文化的内部,以期将其复杂性、丰富性的面貌揭示出来。但是,这种研究并没有回答鲁迅“反传统”的问题。有些论著认为鲁迅等以深厚的国学修养“整理国故”,并不一味地“反传统”,然而也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鲁迅何以有“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这样否定性的论断。
“拿来主义”的主体性建构立场
鲁迅的“反传统”,本质上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立场和态度,这是一个具有自省性的民族和主体性的人的立场和态度。新与旧、改革与保守也是鲁迅思考的问题,但在鲁迅那里这些问题从来都是第二层次的,是服从于他的“人”的观念的。鲁迅并不纠缠于传统、不传统、反传统,他探索的基点是“人”,是“现在”的我们的保存和发展。为了这一目的的达成,鲁迅甚至从生物性(生理性)的视角展开了关于“人的观念”的论述。很明显,鲁迅的这一态度是以“人”为先,归根到底是人的独立自主,人的主体性及其建构——“立人”的问题。
“人”的这一主体性方面,是鲁迅将本民族作为“嫁接”的主体、从内部寻找民族“重生”的契机而被其把握到的。我们以鲁迅与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的关系为例延展这一讨论,并借此回答近期成为热点的所谓鲁迅“国民性改造”内在地包含着“殖民主义”立场的问题。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被视为其“反传统”最集中的体现。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就是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刘禾专门探讨了鲁迅及史密斯对鲁迅的影响。她说:
在斯密思(史密斯——引者)断言唯独中国人重体面的30年之后,阿Q似乎一字不改地戏剧化地演出了这一剧本。阿Q在被处决之前,被抬上车游街示众。当他省悟自己正赴法场时,他羞愧自己竟没有唱几句戏而搜索枯肠:“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海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虚荣、可怜、可笑,加上夸张和戏剧化,阿Q的举手投足似乎吻合斯密思对中国人爱面子的描述。然而,其中有些重要细节需要重新探究。首先,鲁迅构思阿Q的故事是在他熟稔斯密思的理论之后,因此他的写作不可能是独立地证实斯密思所言,而是有互文关系的。第二,斯密思笔下的县官身着官服,而阿Q穿的是一件“洋布的白背心”。这两者之间的隐喻关系值得玩味。穿洋布白背心的阿Q代表的是国民性,还是别的什么?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是否也如白背心一样,是洋布编织出来的?
刘禾的论述是顺畅的,但对照史密斯的原文则问题不少。史密斯原文只有一句话,即“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地方官员在被斩首时允许身着官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准,其目的就是保住他的‘面子’”。刘禾的杂糅极易给人造成错觉,似乎有一个与阿Q一样的“县官示众场景”被鲁迅借用了,却原来只有“砍头”和“一件衣服”而已。史密斯在这前后又论述了中国人时时处处的“做戏”本能(鲁迅将其提升并概括为“做戏的虚无党”),并以此断定中国人“重体面”或“面子”。官员死前身着官服,确与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入殓”时的体面庄重要求相类,所谓“走的体面”等等。但是“体面”“恩赐”等荣耀之外,我们认为这里更与中国人普遍具有的“迷信”“鬼神”,尤其是“来世”观念相关,我们称之为一种“准宗教情绪”。如县官这类“今生”活得自在安逸的,“转世投胎”后至少也要与“生前”一样,或者更好。在他们那里,“来世”和“今生”是勾连的。这种中国人特具的“生死观”,并非“体面”所能涵盖的。所以,同一行为具有多面复杂的内容,传教士史密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洋大人”是无法体察的。他对中国国民性的考察是隔膜的,与鲁迅相比更非一个层次。
刘禾同样读不懂鲁迅和《阿Q正传》。刘禾引述的阿Q“示众场景”这一节与所谓“面子”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这段精彩的笔墨,鲁迅力图表现的是:即使示众游街了,我们的阿Q仍然浑然不觉,还陷在“精神胜利法”的某种“虚幻”中,仍然不敢正视自身正一步步深陷下去的困境。这里,“虚幻”并非“虚荣”,是道教式的,与面子不沾边。这一节应该与后一节联系起来对读:在围观民众“狼一样的眼睛”的啃噬下,阿Q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赶赴黄泉的路上。在“死之面前”,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惧,同时唤起了他本能的生之欲望——“救命”。这时候,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才真正有所“触动”:“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虽然这种“恐惧”和“求生”还是本能的,但是这是“人”的生命和本能。这时候的阿Q总是力图摆脱“精神胜利法”之于他的钳制。所以,与其说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毋宁说鲁迅在急切地注视着阿Q能否摆脱“精神胜利法”,从这种关于自身的“虚幻”中走出来,从“阿Q性”中走出来。至于“洋布的白背心”的解读,刘禾似乎意在表明鲁迅思想的“复杂”,自己并没有将鲁迅简化:对于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国民性理论,鲁迅受到史密斯等的影响,但对其保持警惕或反思,因而暗示这“是洋布编织出来的”——“国民性理论”是西方殖民者(洋布)编织的一个“神话”,“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阿Q“洋布的白背心”上的大字应是“盗窃犯”,如此而已。在鲁迅那里,这是“细节的真实性”,并没有刘禾所说的“隐喻关系”。至于《阿Q正传》的整体立意,鲁迅自己早已说的很明确,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概括地说,鲁迅探索的问题是,即使阿Q这样深陷“精神胜利法”的人,是否也能够摆脱并最终走出“精神胜利法”,走出“阿Q性”,从而获得“人”的自觉。这同时也是鲁迅“反传统”的本意及其真正涵义。
激活传统
所谓鲁迅“反传统”,还包含着更高层面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内容。具有“反传统”姿态的鲁迅在自身中接续并完成了传统,以其独创性的文本完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由古典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并开创了一个现代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的一个崭新的形态。借助于鲁迅及其独创性的文本,我们得以目睹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的面影,触摸到它的具体而真实的形态。所以,并非“反传统”或文化传统的“断裂”,恰恰相反,它是中华文明发展至现代,面对世界挑战、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文化创造,是中华文明贡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大成,是这一文明的现代成果,是这一文明仍然是“活传统”因而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见证。这是一个悖论:恰恰是“反传统”的鲁迅,在现代中国却完成了“人的发现”这一伟大转型,并且将中华文明(在现代)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使其绵延不绝。
“反传统”是一种否定性力量,但是它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源自传统本身或传统内部,是来自于传统内部的一种力量,是传统本身孕育出的一种反动力量,它并非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这种关系,它就是传统本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传统结构中的一种自我反省倾向,它的存在使传统具有了一种自我反省、自我调整从而自我更新的能力,从而使传统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永葆某种动力。此其一。其二,关键是“当代人”的发展和创造,“当代人”是否创造出了无愧于其自身的“经典”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这些当代经典的出现(存在),使我们得以目睹文化传统在当代的最新成果。其次,在多种经典、多种文化载体的比较中,本民族文化传统或文明成果的面貌才可能越来越清晰,而且由于“新来者”或“外来者”的加入,其地位和贡献在新秩序中被重估,其意义和价值方可彰显,如果没有这种当代的创造,比较或对话就无法进行,传统的和古典的面目会越来越模糊,以至于晦暗不明,最终湮灭。
今天的研究已然表明,鲁迅身上的传统倾向是极其沉重的。传统所加诸鲁迅的束缚以及因为这种束缚而挣扎的痛苦,归根到底是鲁迅思想的先锋性造成的。鲁迅的思想与其生存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他的思想和生命的时间总是加速度地向前奔跑,而其身后的“现实”(或传统)总是原地不动或将他向后拉。愈是急于脱离传统的羁绊,愈是与其抗争,鲁迅愈是发现自己身上浓重的传统色彩,似乎是这种与传统的对立和冲突,反而放大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或者说原来并不被注意的东西,这时候凸显了出来。这里,有必要回到最受诟病,也被视为鲁迅激烈“反传统”之一端的“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说。首先,要全面而整体性地把握文本,不可断章取义。所谓整体性首先指的是饱含在文本中的鲁迅的价值取向,以及不加掩饰、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好恶是非的坦率立场——甚至这种“意见自由”及其自由地表达,也是纯粹“五四”的。其次,鲁迅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经验”以供读者“参考”,并没有强加于他人的意思,甚或不构成某种主张。最后,相对于青年必读书这种“劳什子”,鲁迅显然站在了“实人生”这一最高的人生哲学层面上,所以他才把与青年相关的问题并举,思考“言”与“行”、“活人”与“僵尸”、“入世”与“厌世”、“乐观”与“颓唐”等诸多人生问题,这是鲁迅对于中国人理想人格的更高的期待吧。在文中,鲁迅是把印度归入中国一类的。无独有偶,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又一次谈到了印度,他设问:“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没有,和无声的中国一样,他们都是无声的;然而鲁迅说,印度只有一个泰戈尔!泰戈尔出现了,印度正在从无声和黑暗中走出,走向“人”的世界。换言之,是泰戈尔发出的“声音”,冲破了印度的沉寂,而被世界听到了,印度因此开始融入世界民族之林。从这里可以体会并把握鲁迅的立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这个立场的高度标记在哪里?这是一个既具有强烈现实感,又具有一定的历史高度的整体性立场,一个不容许有任何割裂的、完整的关于“人”的观念——这同时就是《青年必读书》中的整体性态度和价值取向,无关乎“反传统”的。
历史性态度与世界性视野
缺少分析性态度(即胡适所谓“评判的态度”)和辩证性立场,是论者在评价鲁迅等五四人物时易走极端的重要原因。这种观念上的局狭,首先表现在缺少历史性的态度。历史性的态度有两个内容:一是要求回到“历史语境”,在历史和现实所构成的诸多“关系”中把握、进而“同情”鲁迅等五四人物的立场和选择;二是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运动中,以发展的眼光打量“五四”,把这一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看作是这一历史运动的必然过程。
其次,世界性视野的确立也相当重要。在比较中在世界范围内审视本民族文化、审视“五四”,并由此获得一种相对主义的文化发展观。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近代文化发展来看,“叛逆”和“反动”的时时涌现和大量存在,恰恰是这一文化的表征和发展动力。但是,在定性西方文化时,不仅西方学者认为“激进”和“保守”的变奏是历史运动的主调,即使今天站在反思启蒙的立场上,他们也并不认为启蒙运动是传统的“断裂”;国内学者也不把这种“反动”视为“文化断裂”,与苛责“五四”和鲁迅的态度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