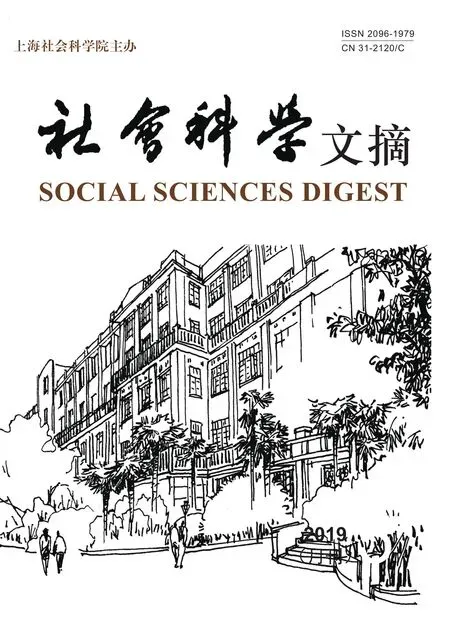孙犁与莫言:从认同走向疏离
孙犁与莫言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孙犁早在战争年代便已获得文学盛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相继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小说;改革开放后,他尽管不再着力于小说创作,但仍继续关注当代文坛,尤其关注文学新人的文学创作。当文学新人莫言刚走上创作之路时,他的小说便得到了孙犁的赏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对莫言的早期创作予以关注之后,便很少再论及莫言的文学创作;同样,莫言对孙犁也鲜有评说。实际上,孙犁与莫言之间的交往犹如两颗彗星,在最初的交汇过后,便转瞬即逝,除了给我们留下简短的几行文字之外,几乎已被淹没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那么,孙犁与莫言何以会从认同走向疏离?在其认同与疏离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又有什么启示?
一
在通向文学圣殿的道路上,作家的起步阶段至关重要。在此阶段,对莫言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蛰居天津的现代作家孙犁。在莫言的小说尚未在文坛上引起反响的时候,孙犁读到《民间音乐》后充分肯定了莫言小说的文学价值。这极大地提升了莫言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莫言走上更为广阔的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孙犁对莫言小说《民间音乐》的评论大约写于1984年3月。在此期间,孙犁以《读小说札记》为题评述了数位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坛上的一些现象。在该组札记中,孙犁从8个方面对作家作品及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评述。第一篇就莫言的《民间音乐》展开评述。第二篇是就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的评述。第三篇是对当时文坛评奖现象的评说。第四篇是对关鸿的《哦,神奇的指挥棒》的评述。第五篇是对汪曾祺的《故里三陈》的评述。第六篇是对古华的《“九十九堆”礼俗》、李杭育的《沙灶遗风》以及张贤亮的《绿化树》所作的评述。第七篇评述了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第八篇对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作了评述。在结尾处,孙犁特别标示出了本组札记为“1984年4月14日写讫”。
在评述小说《民间音乐》时,尽管孙犁没有刻意凸显莫言小说的超人之处,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组评述之于莫言文学创作及其人生道路的作用及意义。当时,莫言的文学创作才刚开始起步。在孙犁同时评述的几个作家中,就当时的文坛地位而言,莫言显然无法和汪曾祺、张贤亮等已经成名的作家相提并论,甚至也无法与同龄作家李杭育、铁凝等并驾齐驱。但是,当莫言的短篇小说被孙犁置于同一个文本中进行评述时,便意味着被评述者似乎在伯仲之间了。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已经迎来了春天,其重要标志便是文学期刊或复刊、或创刊,这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缘于文学期刊主办单位的不同,文学期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最显著的是级别较低的文学期刊影响力较低。如果没有《小说月报》等影响力较大的文学选刊选载、没有参与全国性的小说评奖、没有得到知名的文学评论家的举荐,那些刊发在一般文学期刊上的小说便很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值得欣慰的是,在《莲池》这个地方文学期刊上刊发了5篇小说之后,莫言便如破土而出的幼苗,相继获得了“春雨”的滋润和“民间”的沃土。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短篇小说《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转载,这恰似久旱的“春苗”获得了“春雨”的滋润;二是其短篇小说《民间音乐》获得了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老作家孙犁的赞许,这犹如“春苗”终于植根于“沃土”。然而,让人稍感遗憾的是,莫言的小说虽被《小说月报》转载,但并没有马上产生较大反响,这恰似“春雨”的滋润需要一个“细无声”的过程;不过,《读小说札记》借助孙犁的文学盛名以及《天津日报》这一更为大众化的传播平台,而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莫言自然也借助这一平台为更多的读者所知晓。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莫言要敲开对其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命运大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时,他的小说《民间音乐》获得了当时文学系主任徐怀中的青睐。从徐怀中在全系会议上特别提及孙犁评价这一事情来看,孙犁的赏识对徐怀中的认同无疑起到了强化作用。这种认同,对莫言的文学主体性的确立及其文学创作来说,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孙犁与莫言的交集如彗星一样,在浩瀚的文学星空
中一闪即过。据考察,当莫言开始真正走上文坛并逐渐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孙犁对莫言的作品却鲜有评述。在20世纪80年代,莫言创作出《红高粱》等引起广泛影响的小说,孙犁对此不会不知晓;在90年代,莫言创作出《丰乳肥臀》等一系列具有较大社会争议的长篇小说,孙犁对此也应该有所耳闻。但是,此后的孙犁犹如隐居在世外的修炼者,对这一系列曾经引起文坛波澜的文学事件保持了一种沉默的态度,对莫言其人其文保持了疏离的文化姿态。这说明,孙犁与莫言在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上显然已经相去甚远。具体来说,孙犁对莫言《红高粱》以及之后的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思想及其激情可能并不是非常认同。这也许与孙犁的性格和文学理念有关。孙犁作为一个性情淡泊的作家,对莫言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中的“鱼龙混杂”现象恐怕难以接受。他们之间的“代际文化”差异日渐明显。莫言依循《红高粱》所开创的创作道路越走越远。作为对文学新人呵护有加的老作家孙犁,尽管并不见得会认同莫言的文学道路,但他也不会以文学前辈的身份来规训莫言的文学探索之路。与那些动辄以自己的文学理念来规训莫言的批评家和文学家相比,这一点恰是孙犁值得我们敬重之处。
二
在莫言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文学新人时,孙犁以其独立的文学立场和审美眼光发现了其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的独特文学价值,并对其进行了专门评述,成为莫言小说独到文学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阐释者,这与那种跟风式的文学评论有天壤之别。那么,孙犁为什么会对刊发在一个“小刊”上的“小人物”的短篇小说进行评述呢?换言之,孙犁为什么会对莫言的小说特别赏识呢?
其一,莫言对社会“小人物”生存状态的边缘书写,促成了孙犁对异质文学的认同。孙犁与那些同时代的作家大不一样。当那些一同参加革命的作家相聚北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文化中心时,孙犁依然偏于一隅,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似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多余人”。与此对应,孙犁对那种标语口号式的写作范式极其反感,这主要缘于孙犁本人的独立文学立场和美学追求,以及其独立的思想坚守。孙犁对莫言小说《民间音乐》的评述便体现了这一点。在《民间音乐》这篇小说中,莫言塑造的形象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般文学作品所追捧的英雄人物,更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涵。在这个时期,莫言的这种边缘化书写显然不甚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但是,这种文学书写引起了孙犁的关注,甚至还使孙犁觉得这篇小说“写得不错”。
其二,莫言对农村题材情感的诗意书写,拨动了孙犁的情感之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主潮中,现实主义占据主流,与此相对应,作家注重现实主义的写实原则,突出文学观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具体到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则表现为作家注重对大转折时代下农村社会矛盾的书写。这固然强化了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力度,但文学对自身的审美性追求则显得不够,文学对生活的诗意书写往往就无从谈起。值得肯定的是,莫言在创作起步阶段的美学追求,与文学主潮所呈现出来的美学特点有所不同,他关注的是农村社会身处边缘地带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既难以承载起什么主旨深远的宏大主题,也无涉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由此,孙犁认为莫言所写的这个“事情”“不甚典型”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像莫言所写的这个“事情”,在一些苛刻的批评家那里也许会被视为“不甚靠谱”。那么,对这样一个有可能被人们视为“不甚靠谱”的“事情”,孙犁为什么还“觉得写得不错”呢?这恐怕与莫言小说的诗意书写有着密切联系。孙犁更看重的是莫言所营造的独特的“小说的气氛”。实际上,孙犁所谓的“小说的气氛”便是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特色。在孙犁看来,这部作品“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在孙犁所强调的“现实主义”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主义”。也许,莫言的这部小说打动孙犁的恰是“现实主义”之外的那种“主义”,而这种“主义”集中地体现在“小瞎子”这一人物形象上,他给人“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其实,除了“小瞎子”这个形象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外,花茉莉这一形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莫言在《民间音乐》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空灵之感”,恰好唤起了孙犁蛰伏已久的情感,由此产生了某种共鸣。莫言在小说《民间音乐》中对情感的诗化书写,远离了对“性”的展示,展现的是一种朦胧的诗意情感,这种久违的诗意情感能够拨动孙犁的情感之弦也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其三,莫言对文学阴柔之美的追求,激活了孙犁既有的对阴柔之美的审美趣味。在《春夜雨霏霏》这一短篇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一名在“春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新婚的女性形象。她独守空房,思念着戍边守岛的丈夫,而打着窗棂的“细雨”,恰似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在《民间音乐》中,虽然莫言不像在《春夜雨霏霏》中那样刻意表现人物形象的情感世界,但二者的美学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淡化了人物的情思,增加了一层“虚无缥缈”的“空灵氛围”。但就整体而言,《民间音乐》所显示出来的美学风格是一种阴柔之美的美学风范。孙犁作为一位具有鲜明美学追求的作家,其审美趣味指向的也是阴柔之美。孙犁对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说,正与他对阴柔之美的美学风格的偏爱有关。
孙犁之所以关注莫言这样的文学新人,除了以上我们所论及的三个重要原因之外,还与孙犁特别看重文学传承有关。应该说,孙犁在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新人,尤其是那些与自己有着某种相似文学趣味的文学新人特别关注,这既有利于文学新人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文学的代际传承和良性发展。
三
孙犁对莫言早期文学创作的赞赏,理应激起莫言对孙犁的感念之情。但实际情况是,莫言并没有专门写有关孙犁的文章,即便是在其文章中偶有涉及,也或是片言只语,或是因为在讲座时被专门问及此事而发表评说。
莫言在一些访谈中曾公开谈及孙犁,具有代表性的是在获奖多年之后的一次文学讲座上。莫言充分肯定了孙犁小说的价值,尤其是凸显了孙犁对贾平凹以及自己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风”方面,莫言早期的一些作品模仿过“孙犁的风格”。莫言还肯定了孙犁的文学成就及地位,他认为:“至今还是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替代孙犁的。他对细节的关注,尤其他对年轻女孩的那种微妙心理的把握,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望尘莫及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莫言相信:“像孙犁这样的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会经常地被重读的,即便现在我们好像感觉没人在读,但实际上还是有人在读,我们感觉现在没有人读,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会重新有人读。起码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学到文学史的时候,孙犁是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的存在。”这番话表明,在莫言心中,孙犁依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这一个”;而孙犁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其对年轻女孩微妙心理的把握及其表现能力,更是一般作家无法企及的。在莫言内心深处,他推崇的孙犁与其说是文学上的孙犁,还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孙犁。从莫言对孙犁的推崇来看,他尤其凸显了孙犁作为文人所显现出来的那种高洁的品格、出世的风范。从莫言的片言只语来看,孙犁留给莫言的是“大儒”和“大隐”这两大影像。
其实,莫言后来在文学创作上不仅走出了有意识地模仿孙犁的阶段,而且已经把眼光投向了西方文学。在此过程中,福克纳等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给莫言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使其醒悟到文学创作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本来,莫言不仅是一位在新时期男性作家中情感较为细腻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对情感有着诗化表现的作家。如果循着这条文学创作道路走下去,莫言成为中国情感“唯美主义”的作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莫言并没有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相反,他走上了与“唯美主义”截然不同的文学道路,以至于有些批评家质疑莫言在文学世界中过多地展现了“恶”的东西。
正是缘于观念的变化,莫言建构起来的文学王国开始显示出莫言的鲜明烙印。事实上,莫言正是循着自己的这一感悟路径走出了创作原点,走进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密东北乡,并着手建构起一个属于自己所独有且深深打上了自身精神情感烙印、带有鲜明个性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莫言正是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把西方文学建构的“核心技术”——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视为文学创作的圭臬,从而真正地开启了独立自主的文学创作之旅。在文学创作中,浮现在莫言脑海中的是他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莫言的文学世界已经找到了建构的坚实基石——一个为莫言所熟知和独有、同时也区别于孙犁的“荷花淀”的“高密东北乡”。
当莫言有意识地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王国之后,自然与孙犁建构的“荷花淀”越来越远,由此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与孙犁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远。在此情形下,莫言和孙犁已经不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孙犁对莫言“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的影响已经不再是文学技法及美学风格上的,而仅体现在“荷花淀”这个文学地标之上。反过来看,莫言对孙犁鲜有提及是因为他已经走出了孙犁的文学疆域——莫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也许是一个让孙犁感到难以理喻的文学王国。
总的来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人物。莫言作为一代文学新人要像前辈作家一样,成为彪炳史册的文学巨人,就必须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学传统,又要创造新的文学精神,而且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努力超越前人。实际上,莫言所建构起来的“高密东北乡”,不仅区别于孙犁的“荷花淀”,而且区别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莫言以开疆拓土的气势,建构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确立起了自我的文学主体性。这意味着莫言不仅与孙犁渐行渐远,而且还与中国现代作家渐行渐远。当孙犁与诸多中国现代作家渐行渐远之时,也许表明了莫言及莫言的同时代人的文学时代已渐行渐近。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际更替便在这种历史嬗变中悄然展开。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循着辩证之否定的规律绵延向前的,当莫言建构起来的“高密东北乡”日渐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之时,也就意味着超越“高密东北乡”的新时代文学之春天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