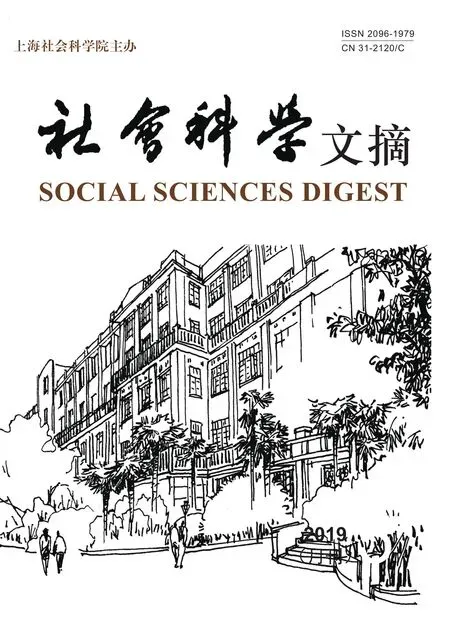汉唐洞窟志怪的文化史研究
——以文学性的生发为线索
洞窟小说是汉唐志怪的独特题材,始于《列仙传》“邗子”,终于晚唐裴鉶《传奇》中的“许栖岩”。其后的洞穴故事多是对这一时期作品的祖述与改写。在汉唐时期的地理书、道教典籍、诗文以及志怪书中都可以看到有关洞窟的故事传说。这类流传了几百年的小说,是汉唐志怪中的一个题材类型,以其流行程度而言,可以视作一种文化史的现象。从中可以寻绎出志怪小说虚构叙事的生发,以及志怪中人对白话小说人物形象的影响。
文化史视野中的洞窟志怪
汉唐间约出现了二十余篇洞窟志怪小说,见于道教典籍、地理书的各类洞窟传说尚不计算在内。其中六朝洞窟小说约有十几篇。六朝志怪类型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很多故事是重复的,似是不同记录者造成的结果。唐代的洞窟小说,因其道教色彩浓厚,故在质朴的故事框架上,生发出了华丽的藻采与臆想。汉唐洞窟志怪成为后代诗词、小说、戏曲反复书写的素材与故事原型,它们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引入了怅望青山、慕恋神仙的心灵维度与空间。
这些洞窟故事在唐宋就引起了文人探究和考察的兴趣。现代学者对洞窟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洞窟小说的现实依据;(2)洞窟小说传播的时代;(3)洞窟小说的主题。洞窟传说被分成“遇仙”和“遇隐”两条主题线索。洞窟故事主要在南朝以前流行,刘宋以后,洞窟传说很少能在小说中再见到了。刘宋时代,山中道馆兴起替代了修道的洞窟,这与南朝洞窟小说的衰歇不应只是巧合。
中古时期,志怪与史书、宗教文献与地记等都属著述性质,并非独创性的文学虚构叙事。从文化史的角度能够从更多面的视角观察志怪的性质及其演化过程的细节。志怪在汉唐时属于“史部杂传”,宋代之后被归入“子部小说”,在古代的学术体系中,都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客观性的著述,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情形下,我们试图将中古时期人们的知识系统与信仰世界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引入到洞窟小说的研究之中。综合史学、宗教、地方地理与文学的文化史视角,能够为志怪小说的研究带来新视野。
首先是时段问题。洞窟小说的流行跨越了汉唐。把汉唐间这些洞窟小说作整体性考察,更能突出其渊源与属性的某些线索。如洞窟小说主要以人物名字和地理标志命名的现象,显示了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性质颇同于史传或地理书。以人物命名者,类史部杂传模式;以地理标志命名者,类地记。从其命名方式就可以看到,汉唐时代志怪在“史部杂传”与“子部小说”之间的游移和不同的发展方向,它们为洞穴故事带来不同的质素与面目。
其次,志怪与其他著述的关系。洞窟志怪与魏晋地记、道教文献的密切关系,提示着志怪作为社会文本历史的公正性质。志怪文本在宗教文献、地理书中的共用与流动,显示了它们在中古时期具有知识性和实录性的特点。魏晋六朝,地记中的洞窟记载,既包含着志怪的雏形,也有情节完整的传说。因其数量众多,故能在整体上清晰地展示出神怪传说在形成中的各阶段的形态。
再次,文学因素的生发与影响。从魏晋志怪的粗陈梗概到唐代刻画细致的洞窟小说,在志怪的基本模式中,藻采与意趣等文学性因素潜生暗长。同时,洞穴故事的现实依据,也使我们注意到故事讲述者的问题。“遇仙”和“遇隐”固然代表了魏晋人的信仰主题,但在这两类主题之下,都有一个凡人“遇险”的现实经历。他们是进入洞窟的凡人,其身份是山民、猎户以及被推坠到洞穴中的人,这些幽闭昏暗空间中的生还者也是洞窟志怪的叙述者。从本质上说洞窟小说是历险故事,但在叙述者口中都成为“遇仙”“遇隐”的神奇经历。这样的洞窟志怪是如何生成与变化的?通过洞窟志怪生成语境的还原,我们看到洞窟小说的本质是对中古知识与信仰的志怪化书写,通过各种故事和传说建构起对知识与信仰的认同。
“遇仙”故事与文学性的生发
洞窟“遇仙”故事本多方士夸诞之言,包含文采与臆想的质素。唐人洞窟小说借助道教的夸饰性修辞,使志怪更具叙事的虚构性。《列仙传》的“邗子”是中古洞窟故事的序曲,紧随其后的《博物志》《拾遗记》《玄中记》《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和《殷芸小说》都涉及类似题材。其中以陶潜《搜神后记》故事最为集中。《搜神后记》“卷一”一共出现了六个洞窟故事。在稍早的王嘉《拾遗记》“卷一〇洞庭山”中,就有了采药人入灵洞,获邀入璇室,饮琼浆金液事。这些遇仙故事让神秘洞窟更令人神往。
虽然在魏晋,大部分志怪还停留在口传阶段的粗略梗概上,但无论是王嘉《拾遗记》那般的方士浮夸,还是《搜神后记》文人式的质朴清新,都具有了超出日常叙事的文采。在原本朴野的叙述中,增加了更多的细节描写成分。文学之优长在于给普通的故事延伸出想象的空间与心灵的感染。如遥望山上的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这类诉诸感官的细腻文字是经过结晶、提炼的文本,在事件的怪异之外还给更多读者带来具有个人感受的亲切意味。
类似的文学性想象在唐人洞窟小说中繁茂滋长,覆盖了志怪原本粗陋的框架。这时的社会已脱离魏晋六朝地理地貌大发现的时代,洞窟志怪不再是具有实际生活价值的知识性传说,而是出于文本的祖述与个人的想象。试举两个例子。其一是皇甫氏《原化记》之“采药民”。其二是《博异志》中的“阴隐客”。唐代的这两篇洞窟小说通常被称为仙乡小说。因为除了模仿前代志怪的情节或祖述道教典籍的洞天想象外,魏晋六朝洞窟志怪中僻远、深险一类的地质特征大为淡化。小说中的洞窟带有很大的虚拟性,有些没有确切地理方位上的实体,洞窟多在人居左近。研究者将魏晋六朝道教典籍中位于山、岛、洞窟之间的仙府,看作其时寒门、寒士为追求个人价值与身份而在人间边缘地区虚构的太平世界。如果说魏晋六朝时代对门阀制度的绝望是建构虚幻世界想象力的源泉,那么这种绝望的感染力在隋唐时代已经被夸示性的金碧辉煌与腐化的肉体享乐诱惑所取代。《采药民》里,采药的凡夫贪顾玉皇左右数百玉女,还有“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对此粗鄙的凡夫倒也不以为忤,反而谆谆诱导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须有功用,不可轻致。”早期洞窟小说那种朴素的仙境描写荡除几尽,唐人在洞窟中构筑了物质与欲望的空间。
“遇隐”故事的寄托与演化
陶潜《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是最著名的“遇隐”小说。这类志怪写凡人通过深山洞窟进入一个封闭、不为人知的人间世界,却最终失却,茫然不可复得。从古代就有了各种考证武陵桃源的文字。这些史实考论在厘清《桃花源记》之纪实性质之外,也涉及了志怪小说的纪实成分。魏晋志怪的洞窟小说中,写洞窟遇隐主题者,以《搜神后记》记录的“遇隐”故事最集中,显示作者有较明显的寄寓隐居理想的倾向。
以魏晋战乱频仍,南方很多地区处于加速开发进程之中的情况而言,位于政权政治秩序之外的深险之地存在的一块块封闭、自治的区域,不单是各地方的堡坞、“依阻山谷,与越相杂”的华夏旧民,还有蛮、僚、俚等族分布于广阔的未知区域。这种地旷人稀的时代,地势险阻,洞窟小说那种入山穿穴,“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的情形,有着相当的纪实成分。
南朝各类地记也有类似“桃花源”的故事,显示在魏晋南朝的特定时代与地域中,这类传说的普遍性。这些被山险阻隔于王化之外的“人世”之所以成为怪异,只是特定的时代与区域现象,离开了那个时代就失去了现实的土壤和意义。因此,洞窟“遇隐”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主题。
唐代洞窟小说中没有“遇隐”故事,洞窟经历被普遍仙化。唐人把《桃花源记》中的人物,也看作神仙。在很多唐人诗歌中,桃源和仙乡是一个意思。桃源与仙人、仙客、仙宫的意象粘合在一起,显示在唐人眼中桃源就是仙乡的别称,洞窟志怪的主题自然只有遇仙一种。唐人常以“神游蓬岛,洞入桃源”对举,将蓬莱岛和桃花源视为神仙世界。从唐人的桃源图画中也可以看到一派仙乡景色。唐代舒元舆《录桃源画记》,记四明山道士叶沈所藏“桃源图”古画,完全是道教的仙境想象。这一点还可以从苏轼的话中得到印证。苏轼《和桃花源诗序》称:“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时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鸡乎?”胡苕溪云:“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苏轼的这种见解在当时可称洞见。盖不但唐代诗人将桃源成为仙乡,唐代小说家也以此为题材,将隐士神仙化。
唐宋之世,随着王朝对疆域内地方统治纵深层面的控制,王化之外的世界基本不存。这时的文人学者再看桃源,就完全忽略了它们的现实依据。宋代叶梦得对前代洞窟小说颇为神往,并一一考据。叶梦得曾考察镇江茅山和华阳洞,言镇江茅山“不至大,亦无甚奇胜处”。华阳洞“才为裂石,阔不满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坛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岁刘混康尝得入百馀步。其言甚夸,无可考,不知何缘能进”。除了地理开发变迁之外,此亦宋人对魏晋道馆起于山中的历史隔膜无知造成的。
瞿佑《剪灯新话》之《天台访隐录》,模仿《桃花源记》,言徐逸入天台山采药,见水中巨瓢,沿溪入石门,见到茅屋石田的村落以及衣冠古朴的老者。这位老者生于宋理宗时,宋末避乱入山。老者虽自称“百有四十岁矣,而颜貌不衰,言动详雅,止若五六十者,岂有道之流欤?”不言而喻,这些长生不老的逃民也已成了神仙。小说虽名“访隐”,却是洞窟“遇仙”故事的翻版。
文化史的解读与志怪的文学影响
从文化史的角度解读洞窟志怪,为我们探讨志怪书写方式及其文学影响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不论是洞窟“遇仙”还是桃花源中的遇隐,这些主题都是以怪异化模式书写的历史与风俗。通过还原不同志怪背后的历史与知识,可以对志怪的书写模式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以洞窟小说而论,求仙与遇隐的一类令人向往的奇遇背后,极有可能是古人艰辛的人生与残酷的风习。在将这些艰难与残酷视为人生不可免除、无需诉说的宿命的一部分后,才有了各种神奇与怪异的慰藉故事。民俗学者对各地弃老风俗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为阐释洞窟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提供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湖北各地都发现了很多老人洞,据民俗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田野调查,这些洞窟应属古代“寄死窑”的遗存。但是这些阴暗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倒是一些志怪故事留下了些许的印痕。唐代薛用弱《集异记》中的“李清”是颇为有名的唐代洞窟小说。这位主人公自愿坠入洞窟寻仙的举动,似乎透露了中古洞窟小说的某些消息。民俗学者将李清入云门山穴故事视为古代“弃老”习俗的体现。弃老这个话题本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但是李清的洞窟寻仙使我们注意到洞窟小说被掩盖的一面——洞窟故事的本来面目是边缘人群的被弃或者历险。我们可以试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洞窟小说的主人公是处于下层的百姓。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一类是处于社会阶层的边缘;一类是处于年龄上的边缘。这些边缘化的民众能够在洞窟中遇仙得道,符合道教宣扬的人人可以成仙、处处皆有神仙的思想。但是这些下层小民进入洞窟是迫于生计的冒险、是被弃之后的无奈。他们对山脉洞穴的认识、对“仙人”的描述是出于贫乏的头脑和恐惧心理的想象,而宗教与民间传说恰为他们的心理提供了自我合理化的途径。
其次,“遇仙”情节的神奇掩盖了主人公因身份低微所遭遇的艰险苦难。这些进入洞窟的人,大都是因为身世的不幸。《列仙传》“邗子”在洞窟中见到“故妇主”,也就是去世的女主人,则可知其为仆从的身份。这个懵懂的仆人闯入山穴,经“十余宿,行度数百里,上出山头”,才见到台殿宫府。对他来讲,这是一种绝望挣扎的经历。今天的读者可能会问,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他叙述是否可靠?虽然志怪小说中并没有不可靠叙述——这类精细的讲述技巧,但是到了洪迈《夷坚志》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于志怪经历者的身份、智力的贬抑,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所志之“怪”的怀疑与否定。
我们从洞窟小说的表述方式,略窥志怪小说对古代叙事文学的影响。概括说来有两点最为突出。
首先是对怪异之事的选择与表现的方式。志怪者记录怪异。什么是怪异,则取决于当时的知识背景与文化认知。洞窟故事大多属于道教的仙话,所以“遇仙”是整个故事的神奇之处,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命运遭际被按压在怪异事件的背后。志怪这种追求奇异,而对人物的命运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不足的特点,与其“小说”性质有关。所谓“丛残小语”“街谈巷议”,很多内容是抄辑书籍、文献以及口头流传的故事成书的,脱离了原文上下语境和丰富的意涵,只是撮取大意而已。志怪以怪异为题材与主题,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深远。嗜奇喜怪的民间审美,成为叙事文学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怪小说不但为后世文学性小说留下了丰富的题材库,更因其审美方式而影响深远。
其次是志怪中的人物设置对小说人物性格设置的影响。那些挣扎在洞窟之中的历险者,他们的凡俗形象、限知性的视角,构成了志怪故事中特殊的力量配比——神仙鬼神高高在上,凡夫俗子匍匐于下。凡人软弱被动的性格,不但是在魏晋、唐宋以及明清的志怪是惯常的设置,受志怪影响的很多白话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也具有某种软弱的共性。志怪故事中,凡人与仙道、鬼神打交道的模式化书写方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以洞窟小说为例,这些历险故事的主题并非讲述英雄的抗争,而是意外的好运——“遇仙”“遇隐”。这使得人物不需要强梁的个性、精明灵活的心计或者积极进取的精神,只需要凡人的本能反应即可。所以,志怪中的人物大多面目模糊,只有身份符号而缺乏个性的辨识特征。主人公本身都只是一个视角与媒介,通过他们传递“神道不诬”的观念。有这样的志怪传统,就使得小说作家很难敷演出人神之间势均力敌、英雄气魄的史诗级的抗衡和战斗。
总之,从文化史的多元角度进行解读,更符合志怪作为“子部小说”的知识性、庞杂化的著述性质。由此,也能够更清晰地认知其文学性的生发与影响。此即汉唐洞窟志怪研究带给我们的初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