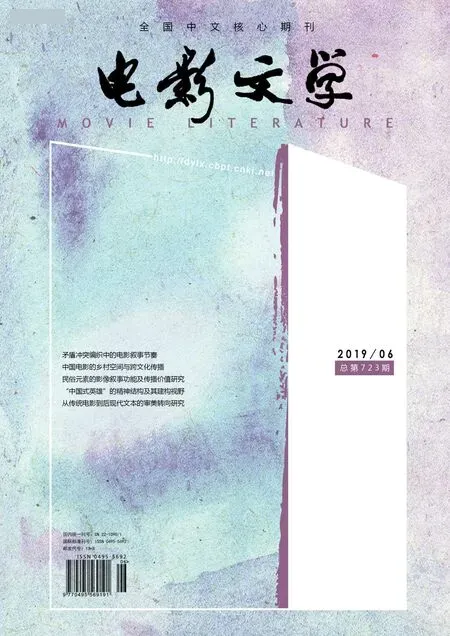人性回归的呼唤:《大寒》的创伤叙事
李 敏 王振平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2018年1月12日,电影《大寒》国内首映,因种种原因,尽管豆瓣评分高达9.4分,但排片占比小于0.1%[1],票房惨淡,后于2018年8月14日,即“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复映,观众有所增加,累计票房669.6万。《大寒》于2018年分别在韩国第十五届日军性奴隶问题亚洲会议上和美国旧金山“慰安妇”塑像揭幕纪念活动中播放,并被一直资助“慰安妇”并无偿帮助她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大森典子女士带回了日本。《大寒》深刻展示了中国农村“慰安妇”的苦难和屈辱。影片以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走访、关心“慰安妇”,披露她们的心路历程为主线,采用纪实与剧情两条线索,讲述了主人公崔大妮从受到日军迫害,遭受村民排斥、歧视,到最后释怀的坎坷经历。
《大寒》的镜头围绕着创伤叙事步步展开,但在创伤中夹杂着疗伤的铺垫。最终,受害者完成了疗伤。与“运用节制的拍摄手法,似乎不想侵犯她们的生活,小心翼翼地靠近,去倾听她们的故事,在远处静静看着她们的生活”[2]的纪录片《二十二》不同,《大寒》的创伤叙事再现了中国“慰安妇”的苦难经历;“疗伤”的完成,体现了对“慰安妇”幸存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关注和企盼她们走出痛苦记忆的美好愿望。
一、战时之伤
盂县,位于山西省的东部,地处太行山西侧。因境内山峦起伏,中低如盂得名。1937年底,日军占领后,盂县人民便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日军的性暴力就是他们的噩梦之一。日军通过“强掳”“摊派”“俘虏”等多种方式征集“慰安妇”,许多女性因此开始了她们一生的噩梦。《大寒》片首是张先兔老人在日本接受心理测试时画的图案,据称画出这种图案的人内心有阴影,过去的心灵创伤随时都会再现,对生活失去兴趣和希望,一生都过得糟糕。在张先兔葬礼的凄凉氛围下,伴随着张双兵的阐述,我们看到了血淋淋的历史和触目惊心的罪恶。
首先,身体创伤。在日军占领的桃园村,村长梁长贵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卑躬屈膝,讨好日军。日军让他找“女人”时,他将逃难到村口投奔姐姐的崔二妮骗至日军军营。大妮得知二妮身处险境,不顾自身安危,前去营救,结果也身陷魔窟,被日军强暴。大妮的丈夫宝生为营救大妮遭日军追杀,还目睹了大妮和二妮遭受强暴。为报复宝生的营救行为,日军扫荡了桃园村,奸淫杀戮,无恶不作。二妮被强奸怀孕,回到家后,饱受非议,她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剧痛,擀肚子、泡冷水,试图打掉肚子里的孽种,最后含恨跳崖而死。村长梁长贵也没有逃过劫难,妻子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女儿兰花在遭受日军凌辱时舍命抗争,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悲愤的梁长贵用面粉捂死了翻译官,把自己烧死在家里。
其次,精神创伤。在对人的伤害中,性伤害具有最强大的攻击效果,是对人尤其是对女人最大的侮辱。深陷魔窟的大妮等人沦为日军的性工具,受到百般凌辱。人性未泯的士兵浅野在大妮遭受凌辱后,总是静静地为大妮画像,安抚大妮。日军侵华战争的最后日子,日军愈加丧心病狂,他们恐惧害怕,不甘于战败,通过强奸女性发泄兽欲与内心的郁愤。面对大妮的不屈,日军小队长健二恼羞成怒,在炮楼顶上强迫浅野强暴大妮。浅野屈服了,众目睽睽之下,强暴了大妮。大妮内心最后的一丝温暖消失了。乡亲的歧视和指责,是在二妮的伤口上撒盐,二妮的死他们也有份。逼死二妮的不仅是日本兵,还有世俗的偏见和人性的愚昧。大妮背负屈辱活着,只是因为丈夫宝生让她活着。为丈夫活着,成了她活着的唯一意义。但是,她没能抬起头来活过一天。她不但心里有一块“冰疙瘩”,生活在寒冷中,她还生活在黑暗中,因为她心中的阴翳从来没有散去过。
二、战后之痛
虽然遭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不在少数,但一直以来大多数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让她们沉默的,是贞洁陋习的压力,他人冷言冷语的无情,自卑心理的阴影,还有日本政府拒不认账的态度。受尽侮辱的她们,能保全性命当然值得庆幸,但有的人保全了性命,却生不如死,屈辱一生。因为她们有过充当“慰安妇”的经历,她们是“性奴隶”。她们一生被误解,被歧视,甚至自己瞧不起自己。“慰安妇”经历带给她们的苦难是多重的、深重的。许多人悲苦一生,最终含冤饮恨,默默离世。
在肉体上,由于日军的暴虐,这些女性留下了终生难以痊愈的伤痕。由于她们被残酷强暴,很多人丧失了生育能力。在农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非常浓厚。没有后代,年老体衰,疾病侵袭,丧失了劳动能力,她们大部分人晚景凄凉。在被日军蹂躏的日子里,她们的身心都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有人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稍有刺激,就会精神失常。她们不敢看有关战争的影视作品,时常被噩梦惊醒,过着自卑自责的生活。
除了要经受被强暴的屈辱与痛苦,这些女性还要经受世俗的风霜冷雨。正如《大寒》所示,日军败走后,回到村里的大妮没有得到同情与理解,而是不断受到流言蜚语的侵扰。宝生从日军魔掌中死里逃生,参加了抗日武装,为了给大妮报仇,他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成了抗日英雄,也成了桃园村的荣耀。虽然宝生深爱着大妮,大妮也深爱着宝生,但背负“不干净”名声的大妮,不能堂堂正正地去迎接壮烈牺牲的宝生,更不能得享烈士家属的光荣。虽然桃园村挑选上好风水的墓地接回了宝生,却不允许大妮靠近半步。她只能隔着深深的沟壑,远远遥望自己的男人。她想过去,可她过不去,“不干净”“坏名声”是她永远抹不掉的耻辱,迈不过去的心坎。由于充当过“慰安妇”,大妮们在生活中备受折磨,甚至下一代都受到了连累。家人的不理解、他人的歧视、社会的偏见,使她们再度受到伤害,这样的精神伤痛和身体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让她们终生难以释怀。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人因暴露了自己“慰安妇”的经历而遭受非人的虐待。她们因为当过“日本娼”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有人不堪屈辱和折磨而自杀身亡。盂县的南二仆就是其中的一例,由于她当过“慰安妇”,还生过日军的孩子(夭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劳改关押两年,后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终因经不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带着满肚子的冤屈,上吊自尽”。[3]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这些人已经被罪恶的日军糟蹋得遍体鳞伤,而在和平年代,却再一次遭到自己同胞的歧视与伤害。难以想象,这些伤痕累累、卑微无助的弱小躯体是怎样承受如此苦痛的。
三、创伤治疗
《大寒》将民族的灾难,女性的屈辱,惨不忍睹的伤口,与人们的无助、无知乃至愚昧全部毫无遮拦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真实还原了战争的残酷。日寇的残暴,让观众看到了失去自由和尊严的中国女性的悲惨,看到了失去人性和良知的日本兵的丑恶。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同胞的麻木和愚昧,流言的冷酷和无情。我们痛恨和谴责日军的残酷暴行,可是,看到那些对崔大妮们翻白眼,往她们身上泼脏水的人,我们想恨,却恨不起来,我们只有痛,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不但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也是丑恶传统习俗的受害者。
面对战争,面对屠杀,面对强暴,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受到冲击。沉默是隐忍,是无奈。但是,一个人站出来了,他要为这些可怜人发声,他要让她们发声,让她们释放心中的苦痛,让她们控诉日军的罪恶暴行,让天下的人都了解“慰安妇”制度的罪恶,了解日军的暴行。他,就是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张双兵。在1992—2007年16年间,他先后带着16位受害老人到日本打官司,实名诉讼日本政府。张双兵的想法很简单,他“要让受害老人们在生命最后和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还她们个名声,这些老人们要走的时候能干干净净,能闭上眼”。[4]59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败诉。法院虽然认可了受害女性的经历,但以诉讼时限、个人赔偿权利缺失为由驳回了上诉。最终,受害老人们没能通过诉讼途径洗清所受的耻辱,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谢罪和赔偿。
但在《大寒》中,大妮最终释怀了。因为人性的支撑,大妮虽然内心悲痛,却没有失去生的希望。大妮受到村民的鄙视与排斥,甚至连养女的婚事也因她“名声不好”一再告吹。但最终,养女回来了。那个曾经让她看到一丝人性之光而又给她带来伤害的日本兵浅野,拿着给她画的肖像跪在她的门前谢罪了。“活着就是个盼头,她们盼到了。”最后,大妮穿着当年出嫁时的大红棉袄,看宝生去了,她释怀地说道:“打春了,你不觉着暖和了?打春了!宝生,打春了!打春了!”经历了寒冷刺骨、痛彻心扉的大寒,如今她终于从内心深处迎来了春天。春天到了,心里的“冰疙瘩”开始融化。
村长梁长贵自焚,既是无助的悲愤,也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赎罪。二妮的跳崖和兰花因反抗被日军刺杀,是不屈,是反抗。她们虽然死了,但她们的灵魂在大妮身上得以体现。大妮代表她们活了下来,冲破了重重的心理阴影后,最终完成了疗伤。正如导演张跃平所述,“我把片名确定为《大寒》,并不是想把它拍成一种寒冷,而是拍成一部最温暖的电影,但这个温暖,必须是从最寒冷中走过的温暖,这个温暖,是善良,是人性的修复”。[4]59如今,“慰安妇”的真相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她们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家人的理解。然而,她们心里的“冰疙瘩”真的能融化吗?日军和日本政府真的能谢罪吗?艺术家的艺术化处理,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人性当中永远有善良正义之光,善良的人性永远不会灭绝,正义之光终会战胜黑暗。“打春了”既是走出寒冷的释然,又是走进温暖的愿望,更是人性回归的呼唤。
“抗战胜利70多年了,我的抗战还在继续,我要抗战到底,直到胜利。”[4]59是的,为了她们过去所受的灾难,为了悲剧不再发生,为了讨回世间的公道,我们的抗战还在继续,尽管前路漫漫,障碍重重,我们依然要坚定地走下去。
四、结 语
在《大寒》中,导演张跃平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让我们体验了大妮等人遭受创伤时的痛苦与窒息感,以及创伤治愈后拥抱新生活的人性温暖。日军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慰安妇”,具有同日本、朝鲜、中国台湾的“慰安妇”不同的特征,那里的“慰安妇”多是被强征和欺骗而成为“慰安妇”,而中国大陆的女性则大多是被掳掠捆绑而成为“慰安妇”的。由于她们的反抗,她们所遭受的暴力伤害就更为强烈,有学者综合各种史料估算,“有75%左右的慰安妇,在战争中已被日军虐待而死”。[5]大妮、二妮和兰花就是中国农村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缩影。大妮虽然幸免于难,但她的噩梦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电影控诉的不仅仅是丑恶、卑劣的“慰安妇”制度,同时也控诉了传统的贞洁习俗和人的自私与愚昧,是对纯洁人性的呼唤。电影中张双兵说他想“让她们在生命的最后讨回名声,能干干净净,有尊严地死去”。可是,我们是不是该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有什么‘坏名声’?她们为什么‘不干净’?”电影的结局是圆满的,人物创伤的黑暗最终被光明驱散。但,这终究是艺术家的美好愿望。描述她们的屈辱与苦难,只要一个多小时;忍受屈辱与苦难,需要她们的一生;而要避免这样的事再度发生,则需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永不停歇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