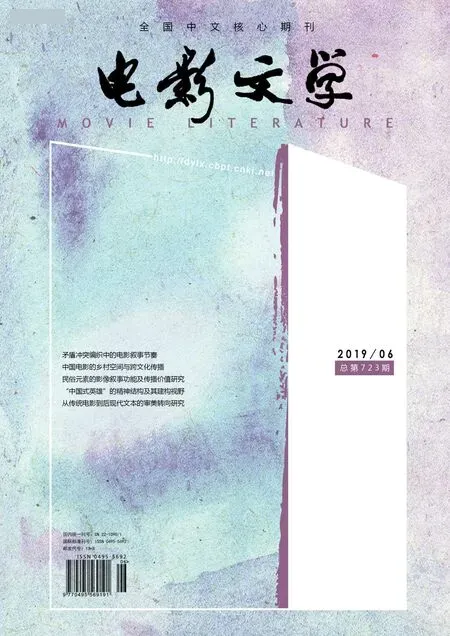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小偷家族》的边缘书写
蒋 秣 (吉林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吉林 吉林 132000)
在日本新电影运动中,是枝裕和成为一个耀眼的名字。电视纪录片导演出身的他极为擅长探讨当代日本的底层人生活,以及人在处于社会边缘时的复杂心态和情感世界。从《无人知晓》(2004)开始,是枝裕和就用纪录片式的技巧来展现边缘者的家庭,在云淡风轻的叙事中揭露残酷的真相。在新作《小偷家族》(2018)中,是枝裕和又一次展现了他对边缘者的关注。电影在看似继续重复是枝裕和的家庭片套路的同时,又显示出了因特殊家庭关系而导致的额外的温情,更扣人心弦的情节反转以及沉重压抑的社会背景。
一、是枝裕和与边缘者
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曾经指出:“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即边缘人是游离在主流群体之外的零散个体,他们因为远离主流社会,远离体制而难以拥有体面、正常的生活,而只能或茕茕孑立,最终无声无息地死去,或寻觅到彼此后资源共享,抱团取暖。由于占有的社会资源极少,边缘者通常是寂寞无名的,他们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既无法进行自我表达,他们在经济、情感等方面的挣扎,也不为人注意。
然而是枝裕和却始终执着于为边缘者发声和画像,在他的电影中,生存困顿,长期被忽略者比比皆是。这一方面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好莱坞不断对电影市场进行抢占的情况下,日本电影另辟蹊径,开启的书写负面情绪、批判敏感时政的新浪潮运动的余韵,一方面也是是枝裕和的个人选择。自198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是枝裕和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纪录片拍摄生涯,在对日本社会的详细记录,对社会事件的调查,以及在对杨德昌、侯孝贤等人电影的接受中,是枝裕和形成了审视现实的阴暗面,传达现实生活感受的创作倾向。纵观是枝裕和的电影,几乎无不是在内容上,勇敢地披露边缘者不堪的生活,但是又在影像上,运用节制克己的长镜头、固定机位等手法,润物细无声地感动观众。在《无人知晓》中,母亲放弃了家庭责任,少年明不得不在母亲离家出走后承担起养活自己和几个弟妹的责任,为此明曾经去找那些曾经和母亲有过恋爱关系的“爸爸”们,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一点钱,然而这些“爸爸”同样身处社会底层,自己尚且为了温饱而疲于奔命,于是对明的到来备感尴尬,只能采取逃避的态度,是枝裕和并没有掩饰这些成人的懦弱,自私与不负责任的一面。
在《第三度嫌疑人》(2017)中,三隅高司年轻时杀死过放高利贷者,在结束长期的牢狱生活后已经人生尽毁,遭受了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抛弃,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隅高司萌生了判处自己“死刑”的念头。于是他策划了一起谋杀案,在死前最后帮助了一个与自己女儿相似的少女。可以说,满怀人文情结的是枝裕和不忘提醒观众,在日本科技飞速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普遍享有便捷、充盈的现代生活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作为“主流者”的人们的心灵则被遮蔽,对他们采取了冷漠无视的态度,这将导致社会的割裂,犯罪行为的频发。三隅高司的杀人,《如父如子》(2013)中仇富护士对婴儿的调换,甚至《距离》(2001)中“真理的箱舟”邪教集团实施的让整个城市为之恐慌的投毒案等。而在《小偷家族》中,边缘者极端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盗窃、对儿童的诱拐、杀人、藏尸等。在是枝裕和的镜头下,电影中的人物成为一个行走着的,有温度,有沉重呼吸的生命个体。
二、《小偷家族》的边缘者
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以既不夸张,也不粉饰的方式,用镜头捕捉了柴田一家由冬入夏再入冬一年的生活,掀开日本社会的一角,首先是对边缘者的灰色生活状态的展现。如前所述,边缘者对于主流群体的参与是“不完全”的,柴田一家亦然。年纪最长的奶奶柴田初枝是一个被儿子和儿媳抛弃了的寡居老人,靠养老金为生,这个破败的平房也面临着拆迁。风烛残年的奶奶选择了与治、信代这一对“夫妻”组成一家人。信代则原本是应召女郎,曾和治一起杀死自己的丈夫,事后治顶罪坐牢,出狱后在拥有一份正当营生——建筑工地工人的同时,还时常与自己当初因为偷车而捡到的“儿子”祥太一起在各种商店行窃;信代也同样在身为女工的同时从事盗窃。两人捡回了被父母家暴的小女孩友里,随着电视上播放寻人新闻,两人给友里改名“玲玲”。少女亚纪则是奶奶前夫的孙女,在一家风俗店从事色情服务,用抢走父母亲情的妹妹纱香的名字作为艺名。是枝裕和通过各种细节展现了一家人生存的凄惨:友里和信代洗澡时发现了彼此身上相似的被电熨斗烫出的伤痕;治在工地受伤后原本希望得到补偿却因为临时工的身份一无所获;信代作为薪水最高的熟练女工也成为裁员时的首要考虑对象。主流社会始终无法接纳他们。一家人的食物中几乎没有肉,面筋、可乐饼和方便面成为最好的美食。正如祥太提到的课文中的小黑鱼和金枪鱼的故事一样,一家人唯一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如小黑鱼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
其次,是枝裕和边缘者的情绪。是枝裕和在电影中充分表现了一家人的温情与羁绊:信代拥抱友里告诉她爱一个人的方式不应该是殴打;治偷偷教祥太青春期的性知识,告诉他晨勃和喜欢女性乳房是正常的,试图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奶奶临终前对着海边家人的背影用口型说了一句带敬语的“谢谢你们”;以及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家人在矮矮的屋檐下听着烟花的声响,共同想象烟花的样子。而另一方面,电影也没有讳饰他们作为边缘者的种种丑陋之处,治先后教会了祥太和友里偷东西,并且告诉祥太小孩子没有必要上学读书。利益先于情感驱动了一家人的结合,在一起生活时他们也不无对彼此的嫌弃和利用:奶奶的指甲,友里的尿床等都是被抱怨的,而奶奶死后,治选择了密不发丧,掩埋尸体,并和信代一起马上因为得到了奶奶的遗产而兴高采烈。可以说,在是枝裕和的镜头中,观众能感受到一个平视的视角,读到一种深切的关怀与无奈。
三、《小偷家族》边缘者书写技巧
黑格尔曾针对文学形式提出:“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一如没有无形式的质料……内容之所以为内容即由于它包含有成熟的形式在内。”即形式理应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形成,电影同样应该根据叙事内容而设计不同的书写策略。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显示出了自己相较《无人知晓》更强大的对剧作结构、形式设计的掌控力,电影虽然表现的是令人几近窒息的生活经验,却因是枝裕和对材料的整合而相当具有可看性。
《小偷家族》中充满各种隐喻叙事。电影中祥太在友里的提醒下,两人一起兴致勃勃地看蝉脱壳蜕变的过程,并充满孩子气地为它加油,以至于两个人都被雨淋湿。这一段情节看似只是日常生活中,两个孩子流露童真的一个细节,实际上也是对祥太意志发生改变的一种暗示。正如蝉必须要完成蜕变,从蛹中挣脱出来,才能获得正常的发育,祥太也必须脱离这个不正常的家庭,避免自己滑向更黑暗的犯罪深渊。从这一次对蝉蜕的观察后,祥太就开始了对偷盗行为的犹豫,加上外在的偷盗者与被偷者的正面冲突,这更激发了祥太内心产生结束这种生活的想法。此时蝉成为祥太的喻体。其后,心怀纠结与矛盾的祥太问信代,偷东西到底算是什么样的事。信代则问祥太爸爸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祥太对治说商店柜台里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信代则说:“那意思不是说,只要商店不倒闭就可以。”此时的信代也已经产生了自己和治无法对祥太负责的念头。只要商店没有倒闭关门,里面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都是可以按需取用的。这无疑是治有意灌输的一种错误理念。而这句话在电影中绝不仅仅是为了表示治和信代作为父母的不合格,商店还是这一家人的喻体。商店因为小偷家族的“不告而取”其实已经处于一种经营不善,随时会歇业的状态,正如这个没有血缘联系,还有案底这个不稳定因素的家庭也是摇摇欲坠的,但是在这个小家庭分崩离析之前,在每个人的隐秘都暴露之前,他们都坚信自己是充满爱的一家人,坚信彼此是自己的选择。
除了隐喻修辞之外,拈连、伏笔等在电影中也层出不穷。如治和信代这一对“夫妻”所从事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便是偷,他们是整个家之所以为“小偷家族”的根源。而电影还特意地表现了治和信代的一次性爱,而这一次性爱也是“偷”来的。由于居住条件的窘迫和经济压力,治之前就已经表示过自己和信代已经很久没有“那种事”了,两个人是靠心连着而不是靠下半身。然而这又是男女之间的正常需要。在祥太和友里看蝉蜕的下雨天,两个人急匆匆地发生了关系,而由于兄妹俩的回家,两人手忙脚乱,当孩子问两人在做什么时,衣着单薄,汗如雨下的他们不得不表示他们也因为淋雨而刚刚在换衣服,并赶紧驱赶兄妹俩去擦拭换衣。在人被挤压到绝境后,“偷”成为生活的常态。又如在信代上班时,与女同事关于卖身后假装良家妇女的闲聊,对女同事“你敢说出去就杀了你”的凶恶威胁,亚纪倾心的“四号客人”是一个同样身处于社会边缘的哑巴,并且手上还有着不知如何造成的伤疤,这些都是能引发观众回味的妙笔。
此外,叙事上的反转也是《小偷家族》中值得称道的书写策略。是枝裕和证明了对落魄、重复生活的娓娓道来与制造跌宕震惊的观影效果并不矛盾。在电影中,是枝裕和在详细地展现了一家人生活的温馨之后,又借由祥太在偷窃时被发现而摔断腿揭开了这层温情的面纱:在警方的审讯中,亚纪才恍然意识到,奶奶收留自己,但是每个月都去向自己的父母要抚养费;在祥太落网后,治马上带着一家人收拾了大包小包准备放弃祥太逃跑;祥太最后告诉治,自己是故意摔倒被抓的,只有这样他才能结束这种畸形的生活,原来是祥太主动造成了一家人的离散。这一层反转重申了现实的严酷,对边缘者而言,对亲人的依恋等情感必须让位于生存。但是如果观众对电影仔细品味,又不难梳理出下一层的反转:奶奶虽然瞒着亚纪去找她的父母要钱,但是这些钱全部保留在假牙盒里,虽然没有直言是留给亚纪的,但是从奶奶取钱时当着亚纪的面念叨出密码可以推断,钱是奶奶为亚纪要的,而这笔钱亚纪是否跟治夫妇分享则由亚纪自己决定;治在带领家人逃跑时还带上了祥太的鞋,他说自己准备抛弃祥太,更有可能是为了祥太能与自己割舍,过上正常的人生;而祥太对自己被抓真相的袒露,其中也很难说没有缓和治愧疚心的意味。
是枝裕和电影的魅力,来自生活流的叙事,纪实性的影像以及内敛而细腻的情感表达,此外,对于易被忽视的边缘者的不懈关注也是是枝裕和电影的特色之一。是枝裕和往往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既客观疏离,又不无主观同情地塑造和探讨日本社会边缘者的生存境遇。贾樟柯曾经表示:艺术家揭示人的生存状态,而如何改良生存状态则是政治家的任务。应该说,贾樟柯和是枝裕和都尽到了作为艺术家的责任。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又一次在日常化的叙事和具有东方意蕴美的影像中介绍了一个奇特家庭存续方式和家庭成员们彼此的牵绊,也留给了观众无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