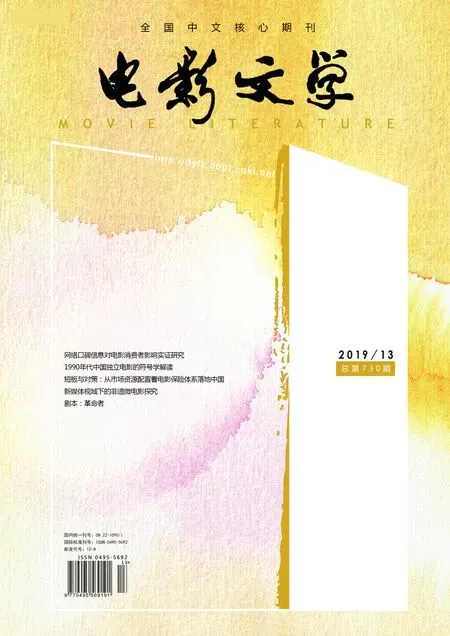电影《猎凶风河谷》中的地域情怀
高 沛(西安航空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早在《边境杀手》(2015)和《赴汤蹈火》(2016)中,编剧泰勒·谢里丹就已经显示出了浓郁的地域情怀,其电影往往执着于表现美国得克萨斯州部分广袤而偏远、贫瘠之地人们的生活状况,在让观众饱览当地独特风光的同时,揭露出其后隐藏的社会问题。而在谢里丹初次身兼编导二职的《猎凶风河谷》(2017)中,他将目光对准了自己故乡怀俄明州的印第安保留地,又一次让电影映射出了特定地域的诸多信息。
一、地域文化的表现
由于生长于怀俄明州,并且在长年于好莱坞郁郁不得志时一度产生过回怀俄明州的农场驯马的念头,谢里丹对于怀俄明州有着深切、独到的理解与情怀。观众能够直观地在《猎凶风河谷》中感受到谢里丹对地域文化的展现。
(一)风光风物
首先,谢里丹在电影中充分地展现了怀俄明州的当地风光风物。在电影的一开始,谢里丹就运用了大量远景镜头,来展现被白雪覆盖的荒无人烟的野外场景,除了少数的黑色植物外,空旷的野外几乎只有白雪,人和车的移动都十分困难。生活于当地,富有经验的主人公科里·兰伯特日常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便是雪橇。而对雪橇的熟悉也成为他后来判断凶手去向的依据。而临时被派来破案的FBI警员珍·班纳则在面对这样的自然风貌面前表现出了稚嫩的一面:她先是只穿着单薄的衣服来到保留区,被当地人告诫她很快会冻僵后,才借走了科里已故女儿的衣物;在开车来到保留区后她又因为迷路而对导航系统大发雷霆,还是在偶遇的科里的帮助下才找到路。在远景镜头中,人物显得极为渺小,是自然环境中不堪一击的弱者,同时阴冷的灰白色调也营造出了一种压抑感。在表现娜塔莉死的一幕时,谢里丹又运用了大远景,观众可以看到披头散发的娜塔莉在雪地的狂奔实际上是无望的,她的四周并没有可庇护、可栖息的地方,娜塔莉在留下了一长串脚印后,死在了壮丽连绵的白色山丘前和一轮明月照映下。娜塔莉口中喷出的鲜血与白雪对观众形成了一种视觉冲击。
又如最终处决犯罪嫌疑人提姆的甘尼特峰,海拔4202米的甘尼特峰是全怀俄明的第一高峰,科里告诉提姆,这里即使是在最热的8月,也有着超过30厘米的积雪,气温低到没有一般的雨雪天气。此时提姆赤裸的双脚已经出现了冻伤的现象。科里在提姆认罪后给了他一个“机会”,即只要能活着跑到公路上,提姆就自由了。然而提姆和目睹了皑皑白雪的观众都深知,这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科里正是要让提姆在绝望中死去。此时肃穆静默,一片银白的甘尼特峰成为一个高大傲岸的见证者,见证了正义的实现。除此之外,牛羊、狮子、狼等也共同构成了当地野蛮、原始,与都市文明隔绝的地域景观。
(二)人文景观
而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地域风光绝不是单纯的物质展览,而是一种昭示了某种人文精神的审美载体,它们承载了谢里丹所想介绍给观众的民族悲情和民族魂魄。《猎凶风河谷》改编自当地一个真实案件,电影中刚满18岁的印第安少女娜塔莉赤脚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奔跑了10公里(6英里多)后,因吸入过多冷空气肺部出血而死。娜塔莉的悲剧实际上是整个印第安民族悲剧的缩影。娜塔莉被男友马特的醉酒白人同事轻蔑地骂为“印第安婊子”,奋起反击,然后遭到暴打和性侵,最终死在野外,这暗示的是昔日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侵害。在电影中一方面银装素裹实则藏污纳垢的印第安领地拥有着自治权,尽管赌博、贩毒等屡见不鲜,犯罪案件频发,联邦也无心或无力干涉,另一方面,探井队的存在又意味着联邦的经济“入侵”其实从未停止。秉承着为原住民鸣不平之心的谢里丹便在电影中大量展现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民俗与民族精神。科里女儿生前写过的印第安诗歌,娜塔莉兄弟的拖车内的印第安装饰,娜塔莉的父亲马丁等人无不保留着印第安人的服饰装扮与发型,马丁还在娜塔莉死后在自己的脸上涂了蓝白油彩,说这是自己的“死相”等,他们顽固地保留自己作为边缘群体的民俗。而娜塔莉则代表了印第安人勇敢、反抗、彪悍的精神,科里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娜塔莉的敬意,他之所以努力破案并非出自对娜塔莉的同情而是出于对一位“战士”的礼敬。正如科里对珍说的:“无论你觉得她能跑多远,她都比你想象中要跑得远。”这其实是对印第安民族的一种赞颂。
二、地域与叙事
从叙事上来看,《猎凶风河谷》的结构上达到了一种对称与呼应,同时还设置了隐喻性的表述,这些也是与电影的地域情怀紧密相关的。如在电影的开头,科里的出场就是在白茫茫的雪地之中,冷静地击杀了一匹狼,科里面无表情地拖走狼尸,地上留下一道血痕。因为不远处就是羊群,狼对于当地人放牧的羊群意味着严重的威胁。而这一场景在交代了科里的职业与技能的同时,也对后续的情节进行了暗示:石油勘探场的几名保卫人员实际上就是狼,他们孔武有力且合法地拥有强大的武器(能击穿珍等人的防弹衣),而当地的印第安少女则是居于弱势的羊。在这样的地域中,终年低温的自然条件极度恶劣,六个警员负责大片地域的治安,而联邦警察又难以插手当地的案件,这使得人和人的关系遵循的实际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代社会的法制难以对人们形成约束。因此,正如当地人需要科里这样的职业猎人来狩猎那些会威胁到居民与牲口的野生动物,在法律和执法者难以为受害者主持公道时,以牙还牙的私刑正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科里需要又一次地扮演猎人的角色,来为当地人除掉这些“狼”。
在电影中,受伤的珍拜托科里前去追唯一逃窜的犯罪嫌疑人提姆,科里对珍说出自己不会让对方活着回来,意即自己要替代法律惩罚对方,得到了珍的默许。随后,科里用雪橇将提姆带到怀俄明州的最高峰,在科里拖提姆的过程中,山上也留下了长长一道血痕。科里脱去提姆的鞋子,在逼提姆认罪后,用枪逼迫他奔跑。在勉强跑出一英里后,提姆在极度的恐慌和疲惫之中吐血而死。至此,科里完成了同态复仇。珍和警察的被围与羊群的被窥伺之间,猎狼与猎凶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称和呼应,娜塔莉之死和提姆之死形成了一种对称和呼应,另外,和《边境杀手》《赴汤蹈火》一样,三部电影在“私刑复仇”上也形成了一种对称和呼应。不难看出,在特定的地域中,文明和法制力量极度薄弱,而人的兽性、血性则得到激发,人们都不得不走上私刑复仇的道路。
此外,科里在整部电影中的任务和行为动机也是对称且互相交错的。科里的本职工作使得他原本的任务是猎杀一头狮子,在科里带着儿子凯西回凯西的外公外婆家。外公丹·克罗哈特告诉科里自己家的牛被一头也许是狮子的野兽吃了。正是在追踪狮子的过程中,科里才发现了死在雪地里的娜塔莉,从此卷入了娜塔莉的案件中,珍作为一个当地的“外来者”也因此而出现。而科里之所以答应珍并不客气的协助请求,一方面是因为科里认识娜塔莉,欣赏这位坚强的女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科里自己的女儿曾经离奇失踪死亡,科里因此而妻离子散,这是科里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并且两位女孩都光着脚被在冰天雪地里发现,科里内心的愧疚感导致他将惩罚害死娜塔莉的真凶当成了一种自我救赎,减轻内心负疚感之道。值得一提的是,科里也并没有因为投入到娜塔莉一案中而忽视了对狮子的猎杀,正是因为他临时决定前去猎杀狮子,脱离了珍的队伍且身穿白色伪装服,才避免了和警察一起全军覆没,并成功地以后来者的视角冷静完成对犯罪嫌疑人的狙杀。在电影中,这种对称还比比皆是,如珍和娜塔莉的两次敲门等。谢里丹并非是单纯地在电影中堆砌生活景观或物质文化形态,而是将地域特色完全融入到叙事之中,让地域造成的问题成为人物行为的基本动机,也让情节的走向因地域而显得合情合理。
三、地域情怀的悲剧指向
谢里丹在表现苍茫博大的印第安保留地时,满怀的是对当地人生存困境的一种悲悯与关怀,电影的地域情怀是带有悲剧指向的。叶朗曾经在《美学原理》中指出:“悲剧的美感主要包含三种因素,一是怜悯,二是恐惧,三是振奋。我们要注意,这三种情绪和情感都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和情感。怜悯是在看到命运的不公正带给人的痛苦而产生的同情和惋惜;恐惧是对于操纵人们命运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恐惧;振奋则是悲剧人物在命运的巨石压顶时依然保持自身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的英雄气概所引起的震撼和鼓舞,这是灵魂的精华和升华。”
首先是怜悯。谢里丹镜头中的风河谷无疑是极度不宜居的。在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进行辩护时,提姆面对科里的枪口说的是:“你知道这个冰冻的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吗?什么娱乐都没有,没有女人,没有乐趣,只有雪和寂静。”实质上,怀着这一想法的并非提姆,包括娜塔莉弟弟在内的当地年轻人,或沉迷于毒品,或动辄使用暴力,其堕落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的:在压抑、苛刻的地域环境中,人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谢里丹也在片尾字幕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即当下的保留地存在一个悲惨现实:每年都有大量印第安女性在这里失踪,但通常她们的家属却不愿意报警,因为警方毫无作为,政府也从没有认真统计过受害者的数字。印第安女性遭受的无疑就是命运的不公正对待。
其次则是恐惧。在电影的结尾,探望医院中的珍时,科里说过幸运是只属于城市的,包括幸运让人躲避车祸等,言外之意即是幸运不属于风河谷。未谙世事,期待走出深山的少女娜塔莉为男友马特吸引,在小屋里两人谈论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甚至已经约好要搬去能在21摄氏度过圣诞节的奥哈伊。祖祖辈辈都定居在保留地的娜塔莉拥有着走出风河谷看看外面世界的理想,然而幸运没有关照她,尽管她试图挣扎、逃脱、反抗,然而她还是在戏谑、侵犯和伤害中死去。人无法从命运中突围,这就是一种恐惧造成的美感。
第三则是振奋。在最后,科里送给病床上的珍一个短吻鳄娃娃,告诉她是自己救了自己,两人萌生了感情。而娜塔莉的家庭也在涅槃中获得重生,兄弟奇普痛定思痛决定回归家庭,慰藉自己的父母。而马丁则面容沉静地和科里坐在一起,两个都失去爱女的父亲给予了彼此无声的告慰。大雪依然积年累月,风依然猎猎苍茫,文明的、程序化的法制审判依然遥远,但印第安文明并未失落,科里等人都在命运的巨石面前显示出了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勇敢、酷烈和决绝的一面。可以说,在《猎凶风河谷》中,谢里丹并未陷入对乡土的自我欣赏,他并不遮蔽地域的负面因素,而是在悲剧美的全面展示中,表现出了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批判立场。
随着《猎凶风河谷》的上映,谢里丹的“美国边境三部曲”也终于宣告完成。对于谢里丹而言,电影与“边境”的关系正如花朵与土地,电影只有生长于特定地域之上才会焕发生机。在这三部电影中,谢里丹都以美国的特定地域为客体,对地域造成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在《猎凶风河谷》中,谢里丹挖掘了怀俄明州印第安保留地有形的自然风貌,以及无形的历史与当代问题,人文精神等。地域启发了谢里丹把握住了美国社会许多严峻的、令人深思的矛盾,促使着美国人展开自我审视与族群对话。应该说,在奇观压倒反思、商业排挤艺术的当下好莱坞,谢里丹和他的《猎凶风河谷》是极为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