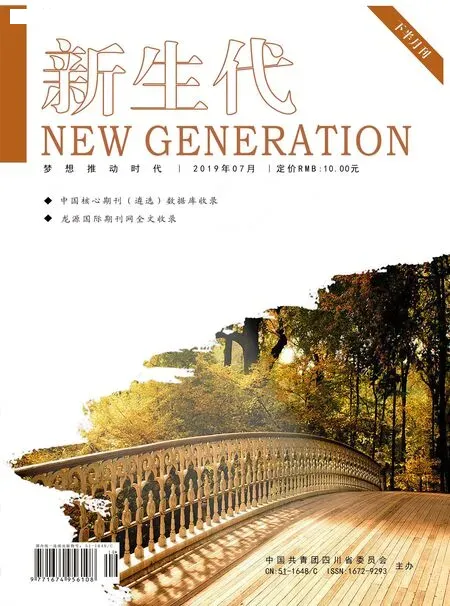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姚伊霖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广州 510006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起步较晚,最初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定始于宪法中规定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来看,宪法是静态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动态的宪法,为维护宪法制度发挥重大作用.
1997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与非法取证,但这一制度真正开始于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吸收后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排非规定》)进一步在该制度框架下细化.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将该制度纳入了法律条文中,至此,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以下,将针对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扩张
(一)非法取证的行为方式扩张
刑讯逼供行为根据方法不同可分为硬性的刑讯方法和软性的刑讯方法 ,《排非规定》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界定包含了这两类.前者即通常意义上的以暴力手段刑讯逼供,通过损害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的身体健康,使其配合侦查人员供述案件实际情况、提供案件侦破线索、提供共同犯罪中的其他成员等 而后者的软性刑讯方法并非直接使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剥夺被讯问人的基本休息权利等方式对其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讯问或者剥夺其基本的饮食来源,使其因为严重缺乏正常休息和生存保障而无法拒绝侦查人员的讯问.
不同于上述的硬性刑讯方法,刑事侦查活动中这种通过剥夺基本休息和正常生存保障的软性刑讯方法对于被讯问人的身体健康也是一大折磨.《排非规定》对变相肉刑这一软性刑讯方法的明确规定,突破了刑事诉讼法与2010年的司法解释,后两者仅规定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变相肉刑即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进一步细化,有利于进一步保障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
但并非出现以上情况均应排除,《排非规定》中明确非法证据达到排除标准的另一个条件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的程度.这一规定为界定非法证据提供了依据和标准,也为审判人员留下了裁量空间.在何种情形会使被讯问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仍需要在审判活动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定夺.
(二)非法取证行为针对的对象扩张
另一方面,侦查活动中非法取证行为不仅包括对被讯问人身体上的暴力也包括心理折磨.《排非规定》第3条规定通过威胁或非法拘禁等手段严重损害被询问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的方法得到的供述也要排除.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还包括相关证人、被害人提供的证词等.其中威胁的内容也不限于以施加暴力直接威胁被讯问人,仍包括损害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将通过施加心理折磨和压力的非法证据列入排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更全面保障了侦查活动的受审人.但不足的是《排非规定》在将其列入排除范围的同时增加了排除的条件 ,同暴力取得的非法证据一样,言词证据只有在受审人难以承受心理压力违背其意愿作出才属于应当排除的范围.但这一类施压行为本身具有难以量化、难以判断程度的特点,要求使受审人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一心理标准更加难以界定.这一限定条件可能使通过威胁行为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避开排除,在刑事诉讼中难以较好实现该制度的初衷.
三、明确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情形
自白任意性规则时国际刑事诉讼中遵循的一大原则,即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被追诉人基于其意志自愿作出的有罪供述才具有可采性,否则应予以排除.我国关于这一原则的基本确立是在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第50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明确规定 .因此在刑事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不得刑讯逼供.但在侦查实务中有一个争议点,即在经历了非法取证后,被讯问人最后自愿做出的供述与遭受非法取证时所提供的言词证据相同的情况下,这一重复性供述是否也属于不予采纳之列, 理论与实务界的争议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不予排除.首先,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类供述作禁止性规定,即排除重复性供述没有法律依据.其次,犯罪嫌疑人在后来没有非法取证手段的环境下作出的有罪供述具有独立性,并非基于先前非法行为的不良影响.但第二种意见坚持绝对排除,认为先前的非法手段会对受审人留下恐惧心理和压力,受审人很有可能为了避免再次遭受折磨作出相同的供述.由于先前的非法手段,受审人供述的自愿性已经得不到保障,这一重复性供述已不具程序合法性,应当排除.除此之外,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宜在立法上一刀切,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具体判断.若重复性供述是受先前非法取证手段的不良影响,则应当将这一重复性供述视为非法证据一并排除 但如果侦查机关积极纠正不当行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影响,为被讯问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并使其明确诉讼权利及认罪后果,这一情形下被讯问人出于自愿再次做出的供述若与之前的供述相同,则不应当列入排除范围,否则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及不利于对犯罪行为的打击.
综上而言,第三种裁量式排除的观点较适合刑事诉讼的司法实务,《排非规定》对于重复性供述的采用也适用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受侦查机关先前非法取证手段影响的重复性供述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但排除先前不良行为影响的供述可以不排除.对于消除先前不良影响的判断标准包括侦查活动中的侦查人员是否发生变更、变更后的侦查人员是否明确告知被讯问人其诉讼权利以及再次讯问的时候、被讯问人是否知悉其认罪的法律后果等.并且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角度出发,绝对地排除重复性供述不利于其享有认罪认罚的机会.因此面对侦查机关积极排除不良影响的供述,审判机关应从多个方面综合考量再做出取舍.
四、制度程序保障不完善
"无救济则无权利",任何法律赋予的权利只有落实具备配套的救济程序才有其存在的实际意义,若无法通过程序救济而使合法权益因不当行为遭受损害的,权利将只停留在法律文本之上,无法得以真正实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救济目前存在以下3个问题:
(一)启动程序可操作性弱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只有在审判阶段.但《排非规定》在第14、17、23条分别对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中,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进行了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各阶段的合法权益.不过也存在一定不足,虽然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初步举证责任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并达到申请条件,否则审判机关可以申请人不符合申请条件为由不予受理.在我国刑事诉讼阶段中,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地位不平等,侦查机关更容易证明证据的合法性,而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证明证据非法的难度更大.并且,即使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该制度是否启动仍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启动是在法官认为可能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形下.这一判断标准过于主观,法院可能以不需要为由拒绝启动该程序.
(二)举证责任落实困难
虽然控方对于非法证据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刑事诉讼》第60条,判断标准是"确认"和"不能排除"两种情形.在实务中,公诉人在面对非法取证行为责任承担的时候,可以不断进行说理和补正,并且可以通过证明证据材料的取得符合法律规定从而证明公诉机关取证行为合法,并不能实现该制度设想的保障.
(三)缺乏救济和保障
《排非规定》第36条规定法院结束证据收集程序合法性审查后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调查结论,但这部分调查结论无法独立于案件的实体裁判.则刑事被告人及辩护人非经抗诉或上诉,无法单独对非法证据的不当裁量结果进行救济.应当增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申请被驳回时,申请人的复议复核权利以及对于程序性裁判的单独救济权利.
五、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整构建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与对于刑事被告人保护的认识保护较晚,在法律规制方面存在较多漏洞,需要立法者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实务问题不断改善.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解读与自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