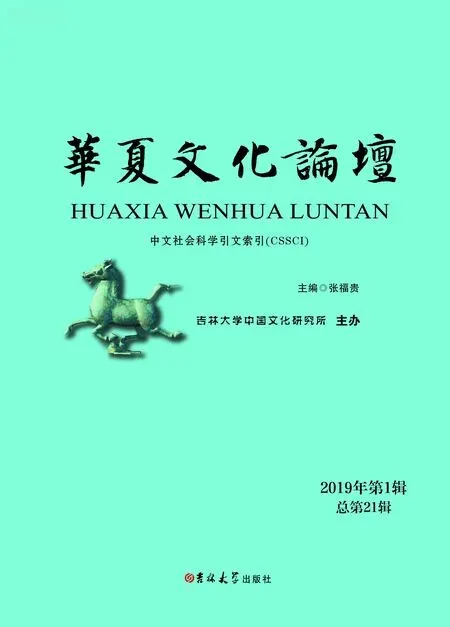新时代《金瓶梅》的整理与出版
黄 霖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四年前,在王汝梅先生的主持下吉林大学曾经召开过一次关于《金瓶梅》的学术讨论会。在那次会上,我曾经也在贵校做过一次学术讲座,主要是为了解决《金瓶梅》长期被污名化的问题而谈了有关《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讲过之后,根据我的录音整理,在《华夏论坛》上发表,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次本来是来看书的,结果王先生又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题目,要我谈谈《金瓶梅》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我事先没有准备,随身带的电脑没有相关的材料,所以今天只能凭空来说了。
讲这个题目呢,实际上王先生应该是最权威的,他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做了多种版本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我对《金瓶梅》的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三大系统的一些主要版本,尽管大多都亲眼看到过,有一定的了解,也写过一些论文,但是在整理出版方面,我只是参与了一些工作。今天就根据王先生出的题目讲一讲吧。
讲《金瓶梅》的整理和研究,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先讲清楚《金瓶梅》的版本问题,随后才能谈得上各种版本的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问题。
《金瓶梅》的版本大致分为三个系统。第一个就是“词话本”系统。最早在社会上知道有这本书是在万历二十四(1596年)年。这是在大名鼎鼎的袁中郎给董其昌的信中提到了这本书。他们看到的是抄本。后来就有刊行本。刊行本前面有一篇署名“东吴弄珠客”写的序言,落款的写作时间是万历四十五(1617年)年,版心也刻着“金瓶梅词话”,不像后来其他系统的本子只刻着“金瓶梅”三个字,所以这部书我们一般称为“词话本”,以后的《金瓶梅》一般都没有“词话”两个字。另外由于那篇序言的落款题了写作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五年,所以一般人也称这“词话本”为“万历本”。“词话本”与“万历本”,其实是指的同一种书,是一种书的两种称呼。
我认为,这部书真正刊成发行,实在天启初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金瓶梅》刊行本当是这一本,即是初印本。这一点,我和王先生两人的观点是一致的。现在对这个版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个版本是比较晚的,比我们认为后出的崇祯本还晚,甚至说是清代印的。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有些先生原书都没有看过,也没有什么过硬的文献依据,完全凭想象去推测,这是不行的。版本的问题一定要从版本的文本出发,要有文献的依据,不能全凭推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本的《金瓶梅词话》,在世界上只剩三部半。最早的一部是在1931年山西介休发现的。因为从清代康熙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大多是张竹坡评本,还有少量的崇祯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本子,所以当时发现后学界大为震惊。书店在山西收购后,由北平图书馆买进,花了八百元大洋(或说是一千八百元、两千元、两千五百元不等)。原书在抗战时寄存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当时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还有好多书。美国人把这些书都拍成了照片,到1975年,把这些书还到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是第一部词话本。
第二部是藏在日本东京附近日光山上的一个叫轮王寺的庙里的慈眼堂里。那个慈眼堂里藏了好多中国古代的小说,而且有不少是艳情小说,还是孤本。其中就有一部《金瓶梅词话》。这是在1941年,东京大学的长泽规矩也教授首先在一本目录书中发现了这部书。丰田穰教授去看了后首先写文章向外界透露这部书的消息。中国学者、后来在北师大工作的王古鲁先生经日本外务省同意后,在丰田穰的陪同下也去看过。到1954年,长泽规矩也教授有机会参加《朝日新闻》日光学术调查团,在轮王寺里看了这部书,并且与这座寺庙的长老结下了友谊,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就有可能借出来供出版社影印。
第三部是藏于广岛附近的德山毛利氏家族的栖息堂。这部书于1962年由上村幸次教授发现,卷首有“德藩藏书”的印章。德藩是江户时代的德山藩,估计此书入藏距今250年以上。这部词话本,粗看起来与原北平图书馆及慈眼堂藏本是相同的,但仔细一校,还是略有差别。最突出的是第五回的末页是不一样的。
这三部之外,还有半部,实际上早于1931年在山西发现的全本词话本,在日本京都大学所藏的一部由学生所赠的《普陀洛山志》中,发现书的衬纸是《金瓶梅》,抽出来一看,内容关系到二十一回,其中全部完整的不超过七回,被编订成三册,当时称为海内孤本,但不知道它也是一种词话本。今从其行格、字样来看,印得不太好,大概是原北平图书馆藏本的后印本。所以一般研究都并不重视它,主要关注的是以上三部大致完整的《金瓶梅词话》。
上面三部词话本原书都难以看到。台湾的那本是藏在博物院,本是不开放的;日本在庙里的一部更难以看到;日本栖息堂所藏的那本书的主人据说是住在京都,而书藏在广岛附近他的老家,又是私人藏书。所以这三部书都难以看到,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所利用的都是经过这样或那样处理过的影印本或排印本。所以有必要讲讲用这三部书影印与排印的一些主要版本。
最早的影印本是1933年由北平的马廉发起一些教授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将北平图书馆刚购进的《金瓶梅词话》影印了104部。鲁迅在日记里就记了这件事。后来,当事人如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及胡适等都谈到了这件事,当时的报刊上也有各种传闻,有些细节的记忆与描述有些出入。这就是最早的一部《金瓶梅词话》的影印本。简称“古佚本”。古佚本印了以后,在民国期间有好几家出版社,根据它出了一些排印本,删掉了性描写的部分。有的将性描写的部分再装订了一册,另外配送。到1957年,在毛主席的提议下,用“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本作为底本,另作了一些修版,印了两千本。尽管当时只在学者与省军级干部中发行,但毕竟发行的量大了,对促进这部小说的流传与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后内地与香港等地的影印本,以及各种排印本,大多是根据这一部而印的。
再说日本在1962年发现了栖息堂本后,在1963年,有个大安株式会社,主要用栖息堂本作为底本,再将它破损的页面用慈眼堂的本子来补,把两个本子相配,影印成了一种新的词话本,简称“大安本”。长期以来,在一些学者眼中,这是最好的本子,而认为古佚小说刊行会的本子相对较差,其主要理由是认为古佚本缺了两页,后来用崇祯本补上去了。另外一理由是,在流传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用不同颜色的笔将正文做了修改与批注。这就使好多人认为这本书不干净了,被破坏了,而日本的大安本能真实地保存原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片面的,那些修改与批注大多是有价值的。
影印本中比较有名的,还有1978年由台湾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的一部词话本,简称联经本。那部书,我在较长时间内认为是印得最好的。这是在1986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学的一位学者的研究室里初次看到时,着实感到惊异。原来的所有影印本,包括古佚本与后来日本印的“大安本”及香港翻印的一些本子,都是把书缩印了,也就是将原书开面比较大的都缩小了。而这部联经本,就搞成和原书一样大。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本子上面有好多批语,其中有不少是用红笔批的,它也将不少批语用红色套印。总之搞得像原书一样。在很长时间内我认为它是最好的。
下面说说词话本的排印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刘本栋与魏子云先生,相继由三民书局与增尔智文化事业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刘本是有删节的,魏本是没有删节的。两本对正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校释。大陆在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种由戴鸿森点校的排印本,删去的性描写的文字是用方框打出来的,全书删减了大概两万字不到,也做了一些校注,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由官方认可出版的《金瓶梅》,到现在还是研究者最常用的书。这时候,香港的梅节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将词话本与崇祯本及其他相关文字进行了校勘,在这基础上,他于1987年出了个“全校本”,后来自己在香港登记了一个“梦梅馆”,多次出版、修订了一种作了大量文字修改的词话本,我还帮他作了后50回的注释。这个本子,显然有利于现在读者的阅读,但直接用它来作为研究用书,恐怕是不适宜的,除非将他后来专门出版的校勘文字对照起来阅读,才比较好。其他的如白维国、卜健的《金瓶梅词话校注》、卜健的《双舸榭重校批评金瓶梅》、刘心武评点《金瓶梅》、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等,都对词话本或评或注时做过不同程度的校改,我没有完全仔细看过,应该是都有不同的参考价值的。这里的《双舸榭重校批评金瓶梅》比较特殊,它不但是没有删节的,而且其评点是自己的评点,不是辑明清人的评点。刘心武的本子虽然也有校点,但重点也在自评,也出过没有删节的本子。白维国、卜健的《金瓶梅词话校注》,开始在岳麓书社出版的是有删节的,最近由中华书局重排后也印了全本。
以上所说的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影印本、排印本,看来都是从原本出发的,其实我们所据的“原本”本身是有点问题的。发现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2011年,我和王汝梅先生一起在台北参加一个纪念魏子云先生为主题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会后组织去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由于我俩过去参观过,就去博物院的图书馆去打听一下那部词话本。那天去一问,意外地听说现在可以看了,但那天是星期天,不行。2012年我又一次去台湾参加一个小说与戏曲的国际会,会后再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接待人员说,需要先提出报告,由上面批准才能看。我说,我就只有今天一天时间,明天就要回大陆了,能否让我今天看一下。终于他们同意,就拿出来让我看了,我就在一天时间内将所有批语抄了下来。到2013年,我专程去台北一个月,主要就是去看这部书,大概花了两三个星期,使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三部词话本中最重要的一部书。
在这期间,也就是2013年春夏之间,我又去了日本,在早稻田待了两个月。那时曾经在复旦进修过的日本学生川岛优子助教授告诉我,那个栖息堂本现在能够看了,因为主人将这部私人藏书,捐给了地方的博物馆了。这个学生特别好,她专程到东京来带我去广岛,还请了我的几个日本同行一起去看。管理员安排我们在一个小的会议室里,将书拿出来给我们看。书保存得很好,用包袱包着,放在一个木盒子里。由于这个博物馆在乡下,我们各路人马从各地去,中间又在一个小饭店吃了中饭,到博物馆大概下午一两点了,可用的时间就比较短了。我们就据大安本后面一张有关栖息堂本与慈眼堂本的对照表,选择性地分工将有关的页面拍了照片。这样通过这本栖息堂本也大致了解了日光轮王寺里的那本慈眼堂本的基本情况。
这样,我在亲眼目验两部原本的基础上,了解了目前存世的三种词话本原本的情况,从而写了《关于〈金瓶梅〉词话本的几个问题》等有关的几篇文章,80年来,或者说60年来、40年来,将三部词话本的原本的情况以及有关的影印本的情况做了分析,最后的结论是:第一,通过三个版本的对照,可见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一部最好,无论是印刷还是保存,都是最好的。至于上面有批改怎么来看?我认为还是利大于弊的。那些修改和评点大多还是合理的,有道理的。那些修改,实际上也是一种校改,把原本错误的字在旁边更正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至于那些用黑色的毛笔将正文中的文字圈掉的,的确使读者看不清楚下面是什么字了,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而且现在有“大安本”对照,还是可以知道原文是什么字,对于阅读与研究并无多大的妨害。总体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本子还是最好的。第二,尽管日本的大安本将栖息堂本与慈眼堂本择优配成一本,比较好地保存了《金瓶梅词话》的原貌,做了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在匆忙之中,还是有不少疏误。第三,我长期以来认为最好的联经版,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并没有真正用原本来影印的,而是用古佚本伪装成原本的样子,实际上它所描的批语或修改的位置和颜色很多都是与原本不一致了。
根据上面所说,目前我们所用的词话本,不管是影印的还是排印的,基本上都没有依据真正的“原本”,而是用的在影印过程中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古佚本”与“大安本”。所以很希望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部《金瓶梅词话》能原汁原味地影印出来,供学界使用。当然,最近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直接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胶卷重新影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词话本,比起“古佚本”来更接近了原貌,但由于不能在彩色照相的基础上套印,与真正的原本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以上说的就是关于词话本的整理情况。
下面要谈的崇祯本的情况就要比词话本复杂一点了。什么叫崇祯本呢?前面讲那个是万历年开印的一种词话本。后来在崇祯年间,有人将词话本修改了。词话本有好多保存着比较“土”的东西吧,崇祯年间有人就将它修改得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了。崇祯本系统中的本子留下来的比较多,有十几本,目前大家注意得比较多的是北大图书馆藏的一本和日本内阁文库与东京大学藏同版的那一种,另外就是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等都藏有不同的崇祯本。崇祯本的出入比较大,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我是根据眉批的不同形式而作不同的分类:有的眉批是两个字一行的,有的是三个字一行的,有的是四个字一行的。两字行排的可能是最早的刻本。可惜的是,这本书的图像还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正文却不见了,现在只能在郑振铎当年出的“世界文库”本中看到第一页的影印件,所以仅此一页是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的。另外就是四字行的,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它的评点比较完整,这本书在“文革”后的80年代影印过。这次影印对于推动崇祯本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次影印我觉得有个问题,即在影印的过程中妄描了很多批语,就是有的原本上的字印得不清楚,就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说自话地描补上去,描错了。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王汝梅先生就是最早把崇祯本汇校后,整理成排印本的,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来由香港三联书店与台北的晓园出版公司等重印过。这是一个没有删节的全本,很受读者的欢迎。不过有的地方开始是沿用了北大影印本妄描的批语。以上说的是四字行眉批的崇祯本。
在三字行眉批的崇祯本中,日本的内阁文库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各藏有一部。这两部是同版。这部书的扉页比较特殊,刻着“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几个字。这里有“原本”两字,所以现在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崇祯本中的初刻本。这个本子究竟是不是崇祯本中的“原本”呢?目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不同意说它是真正的“原本”的,而是认为这恰是书商作伪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它的批语与四字行本的北大本是互有出入的,有的这本有那本没有,也有的是那本有而这本没有,所以应该都是从“原本”翻刻而来的。它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原本”。最近台湾将内阁本也影印出版了。
三字行本中还有一本藏在首都图书馆的,与上面讲的内阁文库与东京大学藏的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卷首的图像之后印了一首词,署名是“回道人”。有人说,这个“回道人”就是李渔,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李渔确实用过回道人的名,但这个回道人绝对不是李渔,更不是崇祯本的修改者。这一点,我与王汝梅先生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这个本子应该是之后翻刻的。王先生有个很重要的发现,即唐代吕洞宾也是叫回道人的,而且这首词的确也是吕洞宾的词。所以很清楚,这是某个读者在阅读时将吕洞宾的这首词抄到了上面,后人翻刻时随手也刻了上去的。而且这本书翻刻得十分马虎,粗制滥造,两百幅图才印了一百幅图,减少了一半,又摹刻得十分粗劣。正文的文字、批语也印得非常的简陋,与北大本、内阁本相比缺略了许许多多,所刻的批语也大多数是刻得难以看清的,所以这个本子绝对不可能是初印本。李渔也不可能是这本书的修订者。
其他的崇祯本,还有藏在天津人民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的、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的,它们的批语比起北大本、内阁本来,都比较少,除了天津的那本最近有人影印之外,其他都没有人去作太多的关注。崇祯本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下面讲清代的张竹坡评本。康熙年间徐州有个人叫张道深,号竹坡,他在崇祯本的基础上做了详细的评点。崇祯本虽然已经有评点了,而且这个评点也很重要,但是相对比较简单,三言两语,文字比较少。张竹坡另做了十分细致的评点,卷首有数篇带有纲领性的批评文字,每一回前面都有回评。这些回评集中起来的文字就相当可观,中间又有大量的眉批、旁批、夹批。这些评点对于我们理解小说的艺术表现还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它提出或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引人注目,所以在中国的小说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就开始关注这个本子。当时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流传比较多的“在兹堂”印的本子。这个本子在扉页天头特别刻上醒目的“康熙乙亥年”几个字。由于在张竹坡本子上有一篇署名“谢颐”写的序言,序后署“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草堂”一语,于是有先生就断然认为它是“最早刻本”了。后来又有另一先生将挖掉“在兹堂”三字的本子称作“康熙乙亥本”,另外一些翻刻这个本子又刻上“皋鹤草堂”“姑苏原板”等本子统称为“康熙乙亥本”,认为“康熙乙亥本为《第一奇书》的最早刊本”。实际上,用“康熙乙亥本”来统称这组本子本身就不确切,因为所谓“康熙乙亥本”乃是将同板的在兹堂本挖掉了扉页上的“在兹堂”三个字而已,由于挖板的手脚并不干净,还清楚地留着挖去三字的痕迹。前几年,张青松先生买到一本“苹华堂”刊的张评本,李金泉先生据此写了一篇《苹华堂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版本考》,在将在兹堂本、康熙乙亥本、皋鹤草堂本与苹华堂本的版页做了认真比对的基础上,得出了在兹堂本系统的本子都是“苹华堂本的同版后印”的结论,“彻底的否定”了包括苹华堂本在内的“在兹堂”本系统的本子为初刻本的说法。我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除了在兹堂系统的本子之外,目前学界比较看重的是一种刻有“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这一系统的本子,就我所见,知道有首都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吉林大学、大连图书馆、张青松先生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处都藏有。但六本之间并不完全相同,情况比较复杂。自前几年王汝梅先生与捷克学者米列娜教授一起发现大连图书馆本卷首《寓意说》篇后多出227字,从而认为此本是“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的初刻本后,大家普遍认同这一看法。但我最近觉得,这一问题比较复杂,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张评本除了上述两个系统的本子之外,后来清代还有不少翻刻本与石印本,尽管大多没有多少研究价值和值得注意的地方,但它的流行淹没了词话本,连崇祯本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到1916年,可能是由王文濡将张评本中的秽语删改后,用存宝斋的名义排印出版了一本《真本金瓶梅》,后来又有卿云图书公司将此书名改为《古本金瓶梅》流行于世。到1933年《金瓶梅词话》影印后,这类本子就逐渐销声匿迹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汇文书局、文乐出版社等曾经影印过康熙乙亥本等,近年台湾影印过在兹堂本和苹华堂本。这些本子,大陆的学人可能也难以看到。内地流行的是王汝梅先生点校的本子。王先生最初是在1987年,与其他两位先生一起点校的,书名为《金瓶梅》,所用的底本可能就是吉林大学的,由齐鲁书社出版。1991年作为“四大奇书”本又重印过。1994年由王先生一人再作修订与校注后重印,书名改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明确标明所用底本是吉林大学藏,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王先生又将前书重校后,交齐鲁书社出版,书名为《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并将评点文字用红色套印。王先生校注的张评本虽有删节,但影响较大,现在大陆学者使用的大多是这一本子。他在整理出版张评本《金瓶梅》的过程中,不断修订,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王先生校点张评本的过程中,据网上消息,三秦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也印过1000本“内部发行”的无删节的张评本的校点本。因未经目验,不知是偷印或盗版,还是正常的出版物,更不知其特点是什么。不过,近几年来,台湾分别影印了张评本中的两种重要版本:苹华堂与大连图书馆藏本,也为大陆学者所了解与购买,这对推动张评本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简单讲一下两种会评本。于1994年在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刘辉、吴敢先生整理的没有删节的《会评会校金瓶梅》,在辑录崇祯本各本的评点文字之外,也会辑了多种张评本上的评点文字,包括文龙在张评本上的手批文字。2010年,因刘辉先生去世,由吴敢先生修订、增辑后出了第二版。这部书的特点之一,是将评点文字用红色套印的。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秦修容整理的《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实际上,此书的“会评会校”只用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词话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崇祯本及“中华书局藏清张竹坡评本”三种而已,没有注意到崇祯本与张评本都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所谓中华书局藏张评本,恐怕是首都图书馆藏本的复印件而已。这两种会评的共同之处,都是以首都图书馆所藏的张评本的正文作为底本的。
上面简单地回顾了一下《金瓶梅》整理与出版的过程,说明了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与出版社一起攻坚克难,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铺平了一条道路,功不可没。但在这里也有几点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一是忠于原著的原则不可动摇。不论是影印还是排印,都要努力真实地反映原貌,不能妄加增删或随意更改。20世纪30年代影印的古佚本,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来的《金瓶梅》研究的基石,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在忠于原著方面还是有欠缺的。当然,其原因有些是受了历史条件所限制,如当时不能用彩色照相来影印,将后人的朱笔批改都印成黑色而使读者误认为原本所刊,但如刊落了大量的批点文字,显然是由影印者在主观上不重视批评而造成的。再如北大所藏崇祯本的影印,将不少原本不清楚的地方只凭自己的感觉添描,致使后来有的排印本据此而一错再错。这在搞影印本时特别要注意,因它的迷惑性更大。
二是整理者要加强版本意识,尽力搞清各版本间的联系与区别,不能拿到篮里就是菜。就版本来说,崇祯本、张评本都比较复杂,虽然目前很难断定它们不同版本中的哪一种是初刊,但优劣大致还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将明显后出的劣本,硬说为初刊,将它作为底本,乃至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用了所谓初刊的A本做会评,但由于A本实在太差,只是翻刻了前人的几条旁批,实际上不得不用B本来冒充。也有的将张评本做会评,随手拿的一种复印件是没有回前总评的,结果不知用了什么本子将回评补了进来,也没有交代。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三是不但要有老实的治学态度,而且还要有细致的工作作风。整理古籍出版,不能大而化之,不能随心所欲,要真实再现原书是最基本的要求。有一些所谓整理工作只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的产物,不讲原则,粗制滥造就在所难免,如联经版的词话本影印就很典型。但有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工作中的疏误所造成的。如日本影印的大安本《金瓶梅词话》,工作基本上是认真的,但也偶有一些差错。当然,整理一部大书,要做到万无一失,是有难度的,但这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现在做《金瓶梅》的整理出版工作,客观方面的各种条件都是空前的好,只要我们坚守原则,追求格调,认真对待,必然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整理本问世,为推动《金瓶梅》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科学作出贡献。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论《历代闺秀词话》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