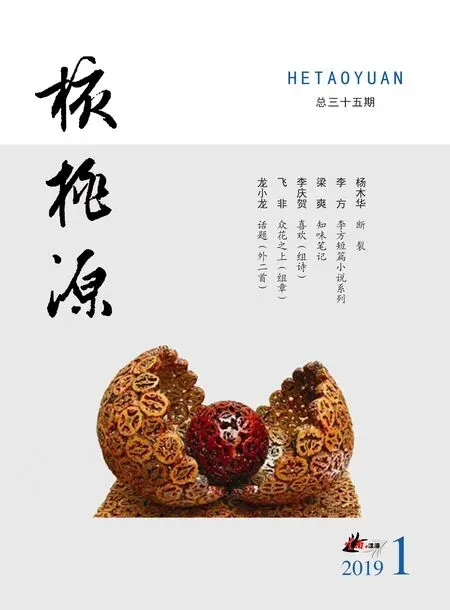遥远的北漂记忆(外一篇)
章 勇
光阴无法倒退,只能用方块的汉字,记录曾经难忘的岁月。
1995年6月,我应聘上海某广告公司被顺利录用,不过工作地点却在北京。当时我既高兴又困惑,因为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虽向往已久,却无缘相识,困惑的是北京离家很远,会牵起我无尽的乡愁。
皇城根下,繁华如烟。北京分部的同事让我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还没等我领略北京站的恢弘和喧嚣,车子就滋溜而去。面包车穿过首都的大街小巷,开进位于海淀区市郊的一个小院子。咋一看,不像从事广告业的公司,院子里堆满破铜烂铁,有点衰败的迹象。当时,我内心突生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黯然而失落。
下车后,一个操上海口音的小伙子帮我把行李从车上拿下,然后把我带到经理室,经理说我的工作就是跑业务,希望我能在短时间内创出好业绩。小伙子在一旁也附和着,我们公司是上海总部在北京刚刚设立的分部,目前分部处于创业阶段,办公及居住等条件都不太好,不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番励志言论,使我精神大振。
当晚,我被安排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的房间,里面搁着两张上下床。四个人住这么小的房间,实在拥挤,我对小伙子说,这地太小怎么住啊!小伙子甩甩头,一言不发地走了。我想,既然来了,就先将就吧,本来外面的世界除了精彩就是无奈嘛。
第二天,我就随着公司的老业务员去跑市场,坐地铁,乘公交,反正不会打车,因为公司规定,除跟客户签约那天打车可以报销外,任何情况的打车一律自费。一个月下来,业务无望,底薪微薄。好在公司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给我们业务员每人配了一部BB机,当时我还不好意思收下。经理说:“我不聋不瞎,你们的辛苦我是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的!”经理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很多天。
那一晚,我几乎彻夜未眠,一轮叫做北京的月光照进来,满室的洁白,使我想起远在安徽的故乡,以及故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睡不着觉,不仅影响同室室友,也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有时打开台灯翻几页新买的杂志,突然被一室友的鼾声惊扰,整个思绪乱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1996年的端午节,算来我来北京有一年了。彼时我在公司的业绩名列第三,收入已然不菲。基于有好的业绩为资本,我找到经理要求改善居住条件,但被经理一口拒绝了,理由是总部与我签的用工合同上没有这一条款。作为一个公司经理,他的说法并没错,我只好忠实服从。不过我提出自己在外租房时,经理倒是立即同意。
就这样,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房东姓吕,以前是农民,因为开发土地被征,于是开了个作坊式的包装印刷厂,将家里的旧平房腾出几间做厂房,剩下的一间收拾后对外出租。或许房东大哥性格直爽,我跟他处的像兄弟。
每逢我下班回来,都热心地叫我过去陪他喝两杯。时间长了,我老觉得欠他很多,便对他说:“吕哥,兄弟孤身一人,没什么报答你,改天我请你下馆子!”他笑笑说,“你挣多少钱啊,兄弟,要牢记一句话,有钱常思无钱日,好好攒足钱,回家娶老婆用吧!”说实话,来北京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没想过婚姻的事。房东大哥的一席话,像一根针管注入我的血液,身上洋溢着不竭的激情和力量。
此时此刻,我沉浸在一种被人关心的幸福之中,觉得北京人就是好,是好在骨子里的好。
有一天,我回来的早,准备把几天堆积的衣服洗一洗,推开屋门,只见一个姑娘在用肥皂搽衣服,水龙头的水直往下淌,非常浪费水,我就上前关掉。再一看姑娘手里的衣裳很像自己昨天换下的,陡然产生好奇。
我随即问她:“你是谁?怎么在这里洗衣服呀!”
姑娘展眉一笑说:“你是勇哥吧,我是印刷厂吕厂长叫我来帮你洗衣服的,你怎么不知道呢,难道他没跟你说吗?”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有数了。是房东大哥心疼我,叫来他厂里的姑娘帮我洗下衣裳。
姑娘年龄二十来岁,个不高,大眼睛,五官端庄,听口音像东北人。衣着朴素,一身秋装裹得严严实实。她利索地洗完衣服说:“衣服洗完了,你自己晾一下总可以吧,我走了啊!”
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感谢的话还没说出来,姑娘一溜烟跑了。
过了两天,房东大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姑娘不错,黑龙江佳木斯人,很勤快,娶回家做老婆蛮好的!”
我说,这怎么行,我和她素昧平生,互不了解,她会同意吗?
你个傻蛋,一回生二回熟,慢慢不就了解了啊,亏你还在外面闯江湖哦!
房东大哥边笑边说,明天你去厂里找她,约她出来吃个饭,我等你的好消息。我没想到爱情这么快就来了,面上虽露出一丝难为情,但心里其实早已乐得开了荷花。
我把姑娘约在一个叫“晴雨”的小酒店。那是个中午,天上飘着细雨,北方的深秋,只要秋雨来袭,气温迅速下降。我们坐在顶里边的位置,稍微暖和些。菜没吃多少,只顾讲话了。我想这就算是我们的恋爱从此起航了吧。
姑娘隔三岔五地来我这儿,和我像一家人,给我洗衣做饭。也许我们都很保守,她从未在我这里过过夜。房东大哥有时拿我开玩笑,有没有把她办了。我说等结婚了再说,他说当心鸭子不煮熟会飞的哟。
有了爱情,等于有了寄托。我开始极力拓展客户,并努力提升业务能力。然而,没过几个月,公司突然被法院勒令停业整顿,说什么涉嫌偷税。如此一来,我将面临失业,甚至要原路返回。
没了工作,爱情也将未卜。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出租屋,正好姑娘也在,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就问我出了什么事。当她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这算什么,就是家常便饭,不要太往心里去!”
她这一说,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工作丢了,爱情还在。那晚,我们喝了好长好长时间的酒,直到夜吞没了整个城市,我要送她回去,她却执意要留在这里。
一年后,我带着她回到安徽老家,姑娘变成了老婆,我则成了有妇之夫。
如今过去多年,北漂的旧时光,在我遥远的梦里,永久地存放着。
时光自此有温度
1978年,正是祖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一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我背着书包,与三两同学走着,春风轻拂脸蛋,柔柔和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村头的广播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纯正而干净的声音,具有一种穿透力,响彻碧蓝的上空。
我家住美丽的青弋江畔,在这里已有三百多年,村庄是美丽的、也是忧伤的。四面环水,圩埂上树木葱茏,田野庄稼纵横一片。尽管风景秀丽,但却抹不去这里的忧伤。多少年,人们勤劳耕种,依然换不来温饱,茅草屋子遍处可见。
也许大队考虑我家宽敞一些,将一名上海下放知青安排在我家。刚来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对我特别亲切,好像很有文化,经常给我讲隋唐演义和封神榜的故事。他叫刘平,上海嘉定人,面容消瘦,皮肤白皙,说话流利,夹带着上海腔。
回到家时,天色将晚。我丢下书包,便来到刘平的房间,他正在批改作业,旁边坐着村上最懒的懒汉余老四,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在生产队里不好好劳动,经常被扣工分,但其家里过得日子却比常人好。刘平说他暗地里编竹篮偷偷在外贩卖,钱来的直接,自然日子好过呀。他时常找刘平玩,而刘平好像也不讨厌他,两人似乎还很投机。他看到我就说,你小子找刘老师干吗?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到处乱窜!我说,我小是小,但你干的啥事我都知道呢,你不就晓得搞投机倒把嘛!许是这句话刺伤了余老四,他居然抬手要打我,被刘平拦住了。刘平呵呵笑着,眼睛朝我眨了下,暗示我出去。
1980年,我们生产队彻底包产到户,余老四家两口人分得两亩多地。余老四在家排行老四,三个姐姐均已嫁人。分田到户后,也没见他勤快,依然半农半副业。种田还是吊儿郎当,敷衍了事,庄稼比别人的总要矮一截。刘平说余老四生性散漫,不是种田的料。余老四听后不但不生气,而且还洋洋得意,甚至觉得刘平的评价最合他的意。
同年,刘平忙着复习迎接高考。余老四听说刘平要考大学,主动施展自己的门路,在县城里弄来一堆高考复习资料,以便刘平备战高考,其中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尤为实用。刘平向余老四投去敬佩的目光,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断重复着“感谢”二字。余老四说:“别感谢了,这里还有一本呢,跟学习资料无关,怕对你学习不好!”说完,从鼓鼓的裤兜里掏出一本书,书名叫《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
刘平看到这本书,眼睛都亮了,抓起书爱不释手,连说感谢余哥感谢余哥,没关系没关系,不会影响我学习的。
大概源于此,我对余老四的印象逐步好转,也乐意走近他。星期天时,我跟着他去上街溜达,或者随他去钓鱼,反正不想再去打扰紧张复习的刘平。几个月后,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刘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上海水产大学。当时的大队和生产队都来为刘平祝贺,鞭炮齐鸣,鼓乐阵阵。我和余老四站在刘平的身旁,鼓着掌,跺着脚。我家的门前槐树下挤满了社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褶皱而暗淡的衣裳,在这一天突然变得妖娆起来。
1986年,余老四在村里开办了一家竹器厂。基于竹器品系手工编织,男女老少种田之余编织箩筐、竹篮、竹席等竹器品。夏天的树荫下,秋天的晒谷场,无不成为编制人的最佳场地。
那几年,我们村子变化大得惊人,原先一间一间的土坯茅草屋子,不觉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换上清一色青砖瓦房。每当黄昏时分,年轻的小伙子拎着一款“燕舞”牌收录机,跳着迪斯科,放着范琳琳的“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站在村庄外面,即可清晰地听见,惹得听歌的人儿浑身是胆。《黄土高坡》的高亢豪迈,以及昂扬的生命激情,有如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中滚滚向前。如今听起这首歌,依然可以勾起我们对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的美好回忆。
1993年9月,我从南京浦口办事回家,在芜湖火车站不巧碰上“农民企业家”余老四,只见他神色张皇,失去常态,上身穿一件西装,领带结松散。原来他在一场生意中被骗,损失好几万。
我想了很多安慰的话安慰余老四,但安慰显然是无力和苍白的,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后来我建议他去找上海的刘平。当我拨通电话,还没跟刘平说上几句,他就答应帮忙,而且让我们立即去上海找他。当时,余老四感动得涕泪纵横,两眼发光,仿佛在生命的绝境中揪到一根救命稻草。第二天,余老四回到厂里,把钱发给村民后,宣布竹器厂即日起停产。
到了2003年,我在政府上班,从事法律工作。余老四又做起了生意,在县城租了门面,据说他已还清刘平的5万块钱。晚上,我给刘平打去问候的电话,他很高兴,并问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如今生活咋样?我说,生活条件自然越来越好,只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些滞后。他马上说,自己不怎么教学,已在江苏和浙江两地建立开发和养殖水产品基地,主要科研由他负责。
我兴奋地说:“刘老师,你可有兴趣来我们这里搞水产开发养殖呢?”
他说:“可以呀,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哟!”
刘平的回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如六月喝凉水滴滴在胸,他的爽快,依旧像当年借钱给余老四那样干脆,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一切都很顺利,刘平教授的到来,引起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的重视,村书记一行人陪同他勘察地质和水情,刘平的秘书熟练地记着笔记。半年后,村里便建起大面积水产品养殖,有台湾草虾、黄鲳鱼、螃蟹等。刘平亲自坐镇指挥,开办技术培训,增强员工素质。新的产业形成,使村里的经济有了质的飞跃。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来这里调货的批发商云集,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舌尖上的一日三餐。
2007年,春二三月,草长莺飞。刘平的满腔热血,激越着这里的人们。余老四把本是经营的小饭馆,改成鲜活鱼虾批发店。许是鱼儿跳,虾儿闹,加上他的厚道、诚实、守法,生意空前的红火,余老四夫妇和两子女忙忙碌碌,月入过万,家庭美满幸福。
这一年,刘平五十三岁,两鬓略白。有次邀他在我家小酌几杯,他喝着喝着就诗兴大发:“革命不分伯与仲,知青下乡放光芒,报效祖国心犹在,不遗余力在江南!”
过后,我在书房整理珍藏已久的信件,翻到刘平教授写给我的信,其中一封像散文诗一样,引领我看日落烟霞,感人生之长勤。曾经,车马很慢,书信很远。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脚踏实地,挥汗如雨,生活于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去年秋天,刘平携夫人过来了。那天清晨,我和刘平夫妇漫步在青弋江畔,顺着河道眺望远方,缕缕清风吹来,散发着水草的清香沁人心脾,流淌着叮咚的河水,令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
一转眼,太阳已上升,秋阳明媚和煦。我们走到河堤的高处,放眼望去,白云朵朵,山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村从早年的茅草屋舍到青砖平房,再到现在的一栋栋居民别墅,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四十年烟尘,四十年变迁。一切心灵的通明都是美妙的。
河水清清,碧草连天。没有西风瘦马,却有丰盈的妩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