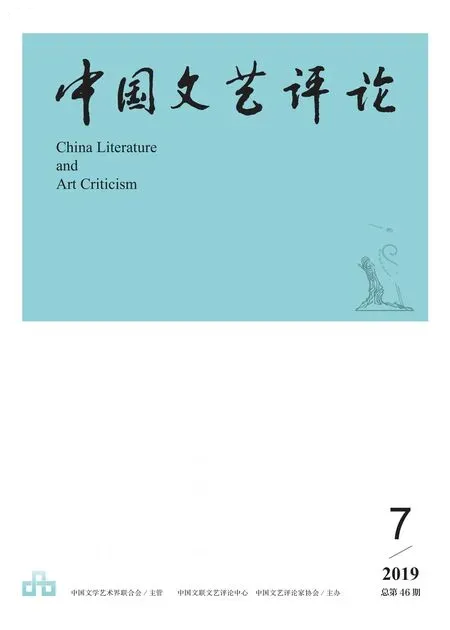孔子乐论之美学特质再思考
周世露 杨广越
孔子的乐论是中国古典音乐思想的重要源泉,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与探究。然,学界研究过度关注其依存美特质,而忽视纯粹美特质,这一现象遮蔽了孔子乐论的本真状态。因而,在笔者看来,孔子乐论的依存美是一种外在的显性存在,容易被捕捉,而纯粹美特质是一种内在的隐性存在,不易被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依存美可以遮蔽纯粹美之灵光。基于此,应当重新梳理文本,在考察孔子乐论依存美特质的同时,充分揭示出纯粹美的特质,并剖析二者之关系,从而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孔子乐论之美学特质。惟其如此,才能对孔子乐论之美学特质产生出新的识见。
一、“尽美尽善”之依存美
当前,孔子乐论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是,正因为学界对其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始终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并没有真正达成其美学特质的普遍共识。因而,笔者以为一方面需要认真梳理学界相关代表性观点,以挖掘出孔子乐论在不同研究视域中的共同性,另一方面需要将这一共同性加以概念化,以促进孔子乐论传统认识的共识性形成与发展。
纵观学界的主流观点,当前孔子乐论的研究存在如下几种学科范式的解读:一是从哲学范畴来解读,以宗白华为主要代表。他主张从音乐的形式和内容来解读孔子乐论,认为音乐不仅存在形式上的构造美,而且还具有内容上的道德美。所以他说:“由于音乐能启示这深厚的内容,孔子重视他的教育意义,他要放郑声,因郑声淫,是太过,太刺激,不够朴质。他是主张文质彬彬,主张绘事后素,礼同乐是要基于内容的美的。”因而,宗白华秉持内容重于形式,道德的善重于音乐的美,孔子乐论依托于道德内容,否则将是无内容的美。二是从艺术学视角来考察孔子乐论,以徐复观、杨荫浏和刘再生等人为主要代表。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孔门之所以重视乐,并非是把乐与仁混同起来,而是出于古代的传承,认为乐的艺术,首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进一步指出“‘美’与‘善’的统一,才是孔子由他自己对音乐的体验而来的对音乐、对艺术的基本规定、要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都从音乐艺术研究的角度认为孔子乐论与其政治教化和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有着紧密联系。三是从中国美学视域来解读孔子乐论,以叶朗、敏泽、陈昭瑛、陈望衡、舒铁等人为主要代表。叶朗在其《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强调了孔子乐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教化作用,认为孔子是音乐美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源头。敏泽在其《中国美学思想史》中肯定了孔子乐论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了音乐的教化功能,指出乐是成人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陈昭瑛强调礼、乐、诗的融合,才能达到整体性的音乐美学思想,实现主客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陈望衡将音乐美学与礼的规范紧密联系视为一体,认为孔子是最早提出礼乐相亲,美善相承之原则的,同时强调礼乐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礼是乐的根本,乐是礼的升华。综上可知,尽管学者们出发点不同,但是对于孔子乐论的研究结果实现了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乐论是以政治和道德为其内容,并且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孔子的乐是达至礼和实现仁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视角来说,学者们对于孔子乐论多学科视角的研究可以归结于孔子乐论中的依存美特质诠释。
康德认为依存美是“作为依附于一个概念的(有条件的美)而被赋予那些从属于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客体”。由此,可将孔子乐论的依存美理解为是一种规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实现道德善的音乐之美。这种音乐美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音乐美学化表达。不过孔子也特别强调情感与音乐、政治或道德与音乐之间表达的均衡适度性,在他看来,音乐只有遵循了美善中和原则,才能真正展现出依存美的魅力和实现依存美的目的性。比如孔子认为《关雎》的依存美在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体现了情感与音乐之间的适度之美;再如孔子认为《韶》的依存美在于“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这体现了政治或道德与音乐之间的适度之美。《韶》在美和善之间找到了合乎度的点,实现了二者的统一,达到了以美配善的目的。《孔子家语·辨乐解》中孔子肯定“奏中声以为节”,反对“伉俪微末”,认为“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孔子家语·辨乐解》)这些都肯定了依存美所遵循的是中和原则,这也是评价音乐依存美的审美原则。
从乐与礼的关系上可见孔子乐论的依存美特质,此处的乐主要以理想的政治秩序和道德准则为目的,受到礼和仁的束缚。礼包含礼仪形式、政治制度和内在道德规范三个方面的内容,意味着区分不同等级,在制度和外在形式等硬件具备的基础上,需要为其找到相配的软件,即内在依据,也就是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克制自己,使言语行动符合于礼,就是仁。“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礼与仁是外与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人们遵循礼的规定,按照秩序生活,其内心需要真正认可和认同,而这一认可和认同是仁在人的内心中发生的作用。建立在内在仁心基础上的礼才是善的,礼不仅依赖于外在形式上的遵守,更加依赖于内心的尊敬,正如“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子曰:‘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乐与仁之间的关系似于礼与仁的关系,乐的内在应该是仁,这不仅合于礼,也合乎仁的要求。
具体来说,孔子将乐与礼视作是“仁”的外在表现,即“仁”的外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乐与礼之间的关系,以呈现出其音乐美学的依存美特质。一者,乐以礼为基,乐的设定与使用要符合礼的规定,也就是说要符合政治道德的目的性要求。孔子特别重视合乎礼的乐,他曾对季氏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而且,孔子认为乐必须要加以规范和约束,否则天下无道可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所以,孔子始终主张音乐的依存美植根于礼,为礼所用。二者,礼需乐来巩固发展。换言之,礼所包含的礼仪形式、政治制度和内在的道德规范等落到实处需要乐的配合。“礼别异,乐和同。”(《礼记·乐记》)“孔子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礼意味着区分不同等级,乐则代表着和,不同的人在群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组成和谐整体。乐可以推动礼制的施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的所学需要经过诗的兴、礼的立,最后在乐中完成,礼规范了人的行为,但是道德人格的形成还需乐的配合。因此,孔子音乐依附于礼,礼也需要乐的和,通过乐来实现教化的目的,达到理想的政治秩序,即有礼之乐、有乐之礼,礼与乐的结合就是秩序的有序,即政治和社会的理想秩序。
除此以外,孔子乐论的依存美在乐与礼、音乐与政治相合的状态下,体现出美与善的相合。康德曾说:“美是德性——善的象征。”同样,孔子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乐记》)音乐是可以与伦理相通的,乐与礼相互依靠,美与善彼此支持,互为象征关系,因此“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韶》乐不仅有音乐的美,也展现道德的善,而《武》乐则仅有音乐的美,这里音乐展现的善是合于礼的要求的善,要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理想秩序的建立,而非其他,因此《韶》乐展现的是舜的道德,其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而来的,而《武》乐展现的则是周武王的天子之位由讨伐商纣而来,虽是正义之战,但与舜相比,不是不善,是未尽善,孔子虽然不排斥武力,但这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善,“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孔子家语·辨乐解》)好的音乐应当是“尽美尽善”“以美配善”的,也就是孔子的依存美的审美原则,在善与美之间取得中和。孔子用善的标准衡量音乐,合善即为雅乐,如《韶》,不合善即为俗乐,如《武》。所以,孔子认为要“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因为“郑声淫”(《论语·卫灵公》)。正如孔子所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综上所述,孔子乐论的依存美特质处在显性地位,它依附于礼、仁,因而这种美是具有条件性、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即是不纯粹的美。如果音乐未依存于礼和“仁”,那么孔子乐论中的依存美特质将会消解。所以,通过对孔子乐论的依存美释义,既明确了依存美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又为揭示纯粹美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二、“游于艺”之纯粹美
依存美和纯粹美是孔子乐论之“一体两面”,但纯粹美却未得到重视,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论语》或其他有关孔子言论的著作中,谈及音乐美学或艺术的较少,论及音乐审美体验时多与政治道德目的相联系,从而导致人们在解读时自然而然地论及孔子乐论的依存美特质;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主要从工具性价值的角度对待音乐,强调的是音乐净化个人思想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但是经过对《论语》的再解读,笔者发现孔子乐论的纯粹美特质确实存在,而且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康德曾将纯粹美定义为:“不以任何有关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纯粹美被“称之为这物那物的(独立存在的)美”,康德的纯粹美也可以称为自由美,也就是说,纯粹美是为自身而美,而不是为了对象或是其他什么概念而美,康德认为花朵、鸟类是美的,“这些美不应归于任何按照概念在其目的上被规定了的对象,而是自由地自身使人喜欢的”。纯粹美“不预设任何一个目的的概念”,这样的审美判断和体验是纯粹的、自由的。一方面“纯粹鉴赏判断是不依赖于刺激和激动的”,刺激和激动虽然对审美判断产生的愉悦感有作用,但不能冒充纯粹美,审美判断产生的美的愉悦不能降低为感官刺激的快感;另一方面这种纯粹的审美判断产生的纯粹美完全不以外在的有用性和内在的对象完满性为前提,因为外在的有用性和内在的对象完满性展现出的是对象客观的合目的性,而对象的客观合目的性是与善相关的,而审美判断和体验具有的是主观的合目的性,与完善性概念无关。由此,可将孔子乐论的纯粹美理解为:不依赖于任何条件和目的,包括感官欲望所带来的快感和善所带来的外在有用性与内在完善性,完全因自身而产生审美愉悦感的音乐美。孔子乐论的纯粹美特征在于与感官欲望无关,即与快适的刺激和激动区分开;与道德教化的功利无关,即与善的完善性概念区分开,因此纯粹美不依赖感官欲望和外在道德教化等功利性目的,只以能否产生自由无碍的审美愉悦感为审美原则。
首先是由“婴儿本然状态”和“三月不知肉味”来看孔子乐论的纯粹美,是与感官欲望无关的纯粹美。刘向在《说苑》中说道:“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说苑·修文》)孔子遇婴儿,被婴儿的视精、心正、行端所感动,便说道《韶》乐将成。孔子从婴儿纯净如渊的眼光中,看到了内心的纯洁和无功利,不似受过道德和教育影响的人一般秉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来看待和利用音乐,孔子将音乐比作婴儿纯洁的眼睛和心灵,展现出的是未受功利目的影响的审美判断,这与孔子对纯粹无目的的美的追求相契合。“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这里孔子将审美体验与味觉欲望进行对比,音乐产生的审美体验高于生理欲望的满足,音乐产生的审美愉悦感超越人的生理性、动物自然性,脱离了动物性束缚,展现出的是孔子对音乐纯粹美的追求,在获得了音乐纯粹的审美体验之后,已不觉欲望本能的自然性。这种音乐纯粹的享受无关乎感官欲望、无关乎道德、无关乎功利,只与当下的纯粹审美体验相关,对音乐的审美体验不需寄托在人性本能上、也不需寄托在道德和教化上,“不图”二字正是恰当体现,孔子认为这种纯粹美的音乐是人所能体验到的至乐。
其次是由“孔颜乐处”来看孔子乐论的审美态度。孔子乐论的纯粹美特质在与感官欲望区分开后,进一步与外在的物质欲望和道德教化目的区分开,形成了“乐以忘忧”的具有本然意义上的审美态度。“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四则例子中所展现的“乐”因宋明理学家所说“孔颜乐处”而备受关注,这里的“乐”已然脱离了对物质基础的渴望和对政治道德的欲求,进入超脱于需要条件之外的纯粹审美的状态。而这指导我们在研读孔子乐论时不能局限于条件目的性维度,而应超越“贫”“箪食”“瓢饮”“陋巷”“疏食饮水”等带来的目的本身,去体验纯粹精神上的内在自由,同时对待孔子乐论时,也应回报“乐以忘忧”的审美态度。
最后是由“游于艺”和“吾与点也”来看孔子乐论自由“游戏”的审美境界。对孔子乐论形成的审美判断不依赖感官欲望,无关于物质基础和道德目的,用“乐”的审美态度观之,达到的是自由无碍的“游”的审美境界,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洒脱状态。“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游”意味着对“艺”产生的是无目的的纯粹审美体验,由此带来的是自由的审美愉悦感,不同于感官刺激和激动给人提供的快适感,也不同于外在有用性和对象完满性给人的完善之感,一旦处在自由的“游”状,拥有纯粹自由的审美愉悦感,就可以不为外在的“矩”所限制,或者说外在的“矩”不再形成限制,做到“从心所欲”。李泽厚曾评价孔子的“游于艺”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快乐之境,而这种自由纯粹的审美愉悦之境正是席勒所说的“游戏”状态,“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是同美游戏”。“游于艺”并非自由“游戏”审美境界的孤证,“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这里的“吾与点也”也可作为有效例证,曾点的志向不同于其他三者致力于政治道德建设,他的志向在于:暮春三月,穿上春装,携五六好友和六七童子,到沂河里戏戏水、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回家。此志向中虽没有直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凭借其“不计利害、是非、功过”的自由审美之境界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和认同,“莫春”“沂水”自然的“风”“舞雩”和“咏而归”无处不在审美体验之中,无处不体现着审美主体达到了忘乎自我的境界,这种不具条件性的纯粹自由的状态正是孔子的“游”之审美境界,正是席勒的“游戏”状态,“游是一种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由的感性活动”,是在超越了物质需求和摆脱了道德束缚之后产生的一种纯粹的审美愉悦感,这种愉悦感正是通过对孔子乐论纯粹美特质的审美体验而产生的。
总的来说,孔子乐论的纯粹美是研究孔子乐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纯粹美与依存美并存,同为孔子乐论的特质,纯粹美不以任何条件和目的为前提,主要包括感官欲望所带来的快感和政治道德所带来的外在有用性与内在完善性,完全因自身而产生审美愉悦感。因此纯粹美不依赖感官欲望和外在道德教化等功利性目的而存在,以“乐以忘忧”的审美态度来观照对象,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审美境界。
三、“一体两面”之关系
孔子乐论中的依存美和纯粹美既存在着矛盾冲突,又具有统一性。其相互冲突表现在上文中所论述的定义不同,依存美是指一种以规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实现道德善的音乐美,而纯粹美是指不依赖于任何条件和目的,包括感官欲望所带来的快感和善所带来的外在有用性与内在完善性,完全因自身而产生审美愉悦感的美。二者依据有无条件性的标准,将孔子乐论之美学特质分为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且从定义上来看,依存美和纯粹美之间不存在由此到彼的可能性,面对同一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不能同时同地产生依存美和纯粹美两种不同的审美体验,因为在纯粹美中是不能掺杂任何条件性、功利性目的的,而这些条件性的前提正是依存美得以展现的根据。依存美的特征主要就包含在“依存”二字之中,即依附于一定的外在条件而存在,如政治教化和道德,且以此为目的,将政治教化和道德的完善作为音乐达到美的目的,不论音乐自身的好与不好。而纯粹美的特征则不仅与道德教化的功利无关,而且与感官欲望无关,是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的。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原则,依存美则要求在美和善之间达到一种统一,即需要遵循中和原则,而纯粹美则以能否产生自由无碍的审美愉悦感为其原则。因而,二者的定义、特征和原则都对彼此独立不依的关系予以了证明。
如果孔子乐论展现出的仅仅是依存美,那么孔子乐论思想则一如其礼论,孔子乐论中最令人心动的纯粹美便被抹杀了。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二者之区别,忽视二者可能的联系,那孔子的乐论似在儒与道之间徘徊。依存美和纯粹美之差异固然重要,二者之联系亦应予以正视。
首先,孔子乐论的两大特质具有同一性的关系。同一性关系表现有二,一是表现在依存美和纯粹美两种审美体验可以由同一审美主体在同一审美客体上产生或是不同审美主体在同一审美客体上产生,面对同一客体,一个人既可以获得纯粹美的审美体验,又可以获得依存美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因人而异,有的只关注到审美客体本身,由本身产生纯粹美的审美体验,有的关注到审美客体的目的存在,由此产生依存美的审美体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面对《武》乐,孔子首先肯定的是它的美,其次关注的是它的善,如果只聆听《武》乐本身,其节奏韵律是能够给人以美感体验的,这也正是纯粹审美体验的呈现,而如果进而关注音乐的目的性或美的条件性,则需要考虑其是否尽善,尽美尽善则如《韶》乐,同具依存美和纯粹美两大特质,面对不同审美主体,从《韶》乐这里可以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但是尽美不尽善则如《武》乐,只能不带目的性地去体验其带来的纯粹美感,而不具目的性的依存美。两大特质可以由同一审美主体或不同审美主体在同一审美客体上产生,《韶》乐既展现纯粹的、无功利的美,又展现出道德、教化价值的美,足以为其正言。正如康德所言:“这个判断者尽管由于把该对象评判为自由的美而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鉴赏判断,他却仍然会受到另一个把该对象的美只看作依附性的性状(着眼于对象的目的)的人的责备,被指责犯了鉴赏的错误,虽然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一个是按照出现在他的感官面前的东西,另一个按照他在思想中所拥有的东西。”按照康德所说,纯粹美和依存美这两种判断方式都是正确的,且是可以作用于同一审美客体上,由此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二是表现在具有共同的审美基础,即都以产生愉悦感为评价标准,只是愉悦感有所不同罢了,依存美是有条件性、目的性和功利性的愉悦感,纯粹美则是纯粹无目的的、无条件前提的愉悦感。前者美的愉悦基于善的条件,要达到的是美善相合的中和状态,后者美的愉悦则是无条件的,达到的是纯美的自由状态。
其次,孔子乐论的两大特质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依存美和纯粹美可以由同一审美客体产生,且都能产生愉悦感是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的前提,但二者相互转化的标志是利害感和功利性的有无。康德认为依存美和纯粹美的关系是:“一个鉴赏判断就一个确定的内在目的之对象而言,只有当判断者要么关于这个目的毫无概念,要么在自己的判断中把这目的抽掉时,才会是纯粹的。”当审美主体将目的性认知抽掉,只对审美客体作出纯粹的审美判断,那产生的只能是纯粹审美体验,所以,依存美向纯粹美的转化只能通过将“目的抽掉”这一手段才能实现,必须要超越对审美客体的存在的依赖和对其目的意图性的考虑,只单纯因审美客体本身而产生无条件的愉悦感;一旦条件性的目的掺杂在审美中,纯粹审美体验就会转化为依附于目的而存在的不纯粹的审美体验,“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所以,纯粹美向依存美的转化只需要在作出审美判断时掺杂一些目的性元素就可达成。两大特质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不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关系问题,二者是不能互相促进的并行关系,否则不同审美体验之间将相互妨碍,正如邓晓芒所说:“这两方面只能并行而不能互相促进,这是不容混淆的,否则就会互相妨碍。所以从自由美和依附美的不同立场我们可以对同一鉴赏对象作出不同甚至对立的审美判断,但双方的争论只是由于没有将这两种美划分清楚的缘故,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矛盾。”可见,孔子乐论的依存美和纯粹美两大特质之间是可以辩证转化的。总的来说,孔子乐论的两大特质之间的关系既彼此区别独立,又具有同一性的关系,且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二者处在独立、统一之中。
可见,孔子乐论中不仅存在依存美,而且存在纯粹美,这两者都应当是孔子乐论的特质,并且依存美和纯粹美之间存在着彼此独立、相互转化的同一关系。至此,笔者已然清晰地给出了孔子乐论“一体两面”体系的研究路径。这一体系的构建既彰显了内在价值,又彰显了外在价值。
对于内在价值的彰显,具体表现在:首先有助于纠偏学界重孔子乐论依存美,而轻纯粹美的传统观念。大多数学者对孔子乐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孔子乐论是以政治或道德等为内容,以完善政治秩序和实现道德教化为目的,相对于依存美特质得到的肯定,纯粹美特质并未受到同等的重视,“一体两面”体系的建立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孔子乐论的特质,不致有失偏颇。其次有益于恢复孔子乐论纯粹美的应然地位。“一体两面”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依存美特质的重视,而且是对纯粹美特质的关照,使纯粹美这一处在隐性状态中的特质凸显出来,完成其由隐到显的地位提升,纯粹美和依存美两种特质在孔子乐论体系中拥有相同分量。最后有利于构建相对完善的孔子乐论美学特质框架体系。“一体两面”体系的建立不仅肯定了依存美特质,而且使纯粹美的应然地位得到彰显,再言,二者既彼此区别独立,又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处在独立又统一的关系之中,这是完善孔子乐论美学特质框架体系的充分必要条件。
对于外在价值的延伸,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有助于全面理解和研究孔子的礼和“仁”等伦理道德概念。礼和“仁”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伦理道德概念,一者,对孔子礼的理解,不仅需要立基于政治道德层面理解礼在礼仪形式、政治制度和内在道德规范中的内涵,而且需要通过对孔子乐论“一体两面”体系的解读来理解,其中依存美特质正是一种规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实现道德善的音乐之美,依存美具有的依附性质和功利主义色彩正表现在礼的完善和目标上,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礼,更具有中和的美感;二者,对孔子“仁”的理解,不仅需要认识到“仁”是礼的内在依据,而且需要通过对孔子乐论“一体两面”体系的解读来理解,依存美所依附的外在条件之一是道德完善,而在孔子这里,道德完善的理想标杆就在于实现“仁”,对“仁”进行审美解读使“仁”的内涵更加立体和鲜活。另一方面有益于启发我们对孔子的理想人格、人生是什么样的问题之思考。大多学者认为孔子的理想人格是至善的道德人格,理想人生建构伦理道德,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孔子的最高目标在于人生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从而达到“自由”的美学境界。孔子乐论“一体两面”体系的建立廓清了依存美和纯粹美两大特质及其相互关系,虽然依存美的解读偏重于音乐美学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目的,偏向于对道德人格的肯定,而纯粹美的解读偏重于音乐美学的独立性,偏向于对自由无碍的审美人格的肯定,但是从依存美和纯粹美的相互关系又可以看出,孔子理想人格的纠结和矛盾之处,似是两者的参合,似是独立的分别的两者。因而孔子音乐美学“一体两面”体系的建立对于思考孔子的理想人格这一问题有着莫大的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