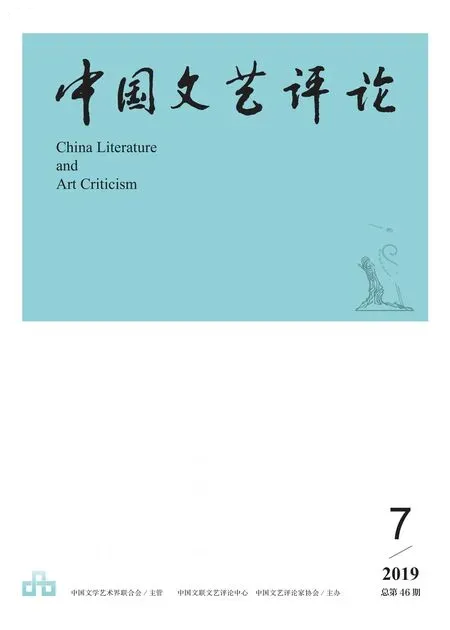身体与世界的融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
梁晓萍 姬宁宁
身体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与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媒介,福柯称之为“话语”,因其如语言般可以承载意义和传递情感,身体也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载体,加缪曾言“身体是我的故乡”,与人息息相关的身体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近现代以来,身体的地位愈发凸显,“回到身体”也成为19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已有对于身体的不同理解,其中,儒道两家的身体观对后人的影响和启迪极为深远,然先秦时期的身体尚被包裹在观念之壳里,轻易不被谈起;魏晋时期,身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往多被作为承载纲常礼法的工具而受压抑的身体渐渐被唤醒,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身体观和高频“出镜率”,“品评身体”成为一种时尚,对身体的品评甚至影响到人们对待人、事的态度。《世说新语》最能集中体现当时士人的身体观念和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从中可以窥察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那么,在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身体的理论和产品也次第出现、西方美学史上的身体观不断被人提起并予以重视,而中国美学史上尤其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身体的理论缺乏深入探索的当今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魏晋时期的身体观,如何借鉴已有的理论资源激活魏晋时期的审美,为当下的我们所用,便成为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身心相融:魏晋身体美的逻辑起点
要考察魏晋士人的身体美,首要的便是对“身体”的意义进行辨析,讨论传统意义上的肉身之体以及作为身心相融统一体之身体的异同,澄清魏晋身体美的逻辑起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魏晋士人身体美的多层内涵。
在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上,身心二分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柏拉图的灵魂独立并高于身体,扬灵魂抑身体,还是奥古斯丁主张代表欲望的身体应当沉寂,或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们所指涉的身体都是通常意义上的肉身之体。这种肉身之体包括人的感官、外貌形态、四肢和躯干,与人的心灵相互独立存在。此种意义上的身体需要我们为之补充种种物质元素和能量,以供其正常运转得以生存,它的痛苦和快乐会给灵魂带来干扰,所以它常被视为低级而需贬斥的对象。一般看来,中国古代没有如西方身心对立二分的意识,但却存在着诸多身心不平等的现象:儒家的纲常礼教将人的身体作为工具载体,实现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道家不否认身体的生理属性,但将其视为欲望的根源;庄子的“心斋”“坐忘”又强调对身体的超越,这些“身体”都是没有意识的身体,实则都是身心不平等的表现。
无论是西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还是中国古代将身体当作无意识之物的理解,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以此来理解身体,必然不能真正明晓身体之内涵,因为肉身之体作为灵魂的寄所,与灵魂相互交织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身体,才会有身体意识。人的身体器官的气质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人的精神状况,而身体的修复和培养也有助于实现自我关怀,诚如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所指出的那样:“身体是活生生的、敏锐的和具有感知能力的,能够将其自身同时体验为主体和客体”,不把身体仅看作工具或手段,而是通过提高身体这个有机中心的意识来完善人们的自我实践,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身心二分之识,使“身体”具有了身心合一的意味。
身体所包含的肉身和心灵的关系实际上是世界当中物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世界所包含的复杂事物对我们产生的各种影响通过身体表现出来,在身体这样一个有机中心里,人们实现的是心灵和身体的统一,心灵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而产生快乐、痛苦等体验或创造出思想灵魂,肉体也不会不受心灵的控制和驱使独自行动,显然,身体已经超越了肉体的含义,它不能被狭隘的解释为肉体或器官,也不能仅被超拔升华为思想或灵魂,这都不是身体最确切的含义。那么,身体究竟是什么?它最本原的状态应当是具备了某种心灵的含义,是在灵魂与肉体之间达到相融统一、具备了一定的身心合一意味的结合体。而且,身体不仅仅指肉体感官,还包括习惯和由社会和文化环境形成的身体性习俗,以及身体所处的环境;身体也并不局限于身体自身,它还能够提高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感知并与之融合。正如亓校盛所言:“我们得时时提醒自己身体美学中的身体不是指和心灵相对的肉体或躯体,不是指我们的肉身,而是指作为身心一体的整体的人。”这种身体观在中国哲学中能够找到其源头,儒家提倡修齐治平,第一步就是修身,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一个人的身体中,由血液、骨骼、皮肤、肌肉等构成的是人的肉身之体,是生理组织或物质之体,也是精神身体的载体。自我意识、情感性、德性、理性、创造性等,则是人的精神性身体,是物质之体在精神层面的角色担当。身体中,物质之体反映着精神心灵状况,身和心是相互作用的,要想修养好自己的品德,首先得端正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的精神控制着身体,左右着我们的言行举止、风貌神情。在儒家看来,身与心是不可分割的,身体就是身心的合一体。道家虽将身体视为欲望的根源,希望人们超越身体追求大道,但也承认身体作为求道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故而在道家这里,身与心尽管不平等却仍紧密联系。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主要是探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反映在身体观上即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因此,研究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应当首先理解身体是指身心一体,而非专属肉身,亦非特指精神,唯有紧密联系“肉身”与“精神或心灵”考察身体,以此为基点,才能真正理解魏晋时期的身体之美。
二、魏晋“身体美”的多维追求
魏晋时期的身体美具有多重内涵,首先体现为感性审美的特质,外在形貌的激赏是魏晋人感性审美的重要体现。宗白华先生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身体”,身体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得到空前提高。魏晋时期,人物品鉴这一政治察举方式成为一种社会审美机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于形体美、外貌美的欣赏和追求,而《世说新语》是魏晋士人思想性情、生活方式、言行举止等风貌最为细致也最为生动的表现文本。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时人给予其极高评价,或“爽朗清举”,或“肃肃如松下风”;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为当时人所称赞;毛曾与夏侯玄坐在一起,当时的人称之为“蒹葭倚玉树”;潘安仁、夏侯喜欢同行,“时人谓之‘连壁’”;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粉丝众多,走在街上,妇女们围着他“欣赏”,“老妪以果掷之满车”;王夷甫“容貌整丽”,手的颜色和他所拿的白玉柄的拂尘没有区别;时人品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裴令公有“俊容仪”,时人誉之为“玉人”;王敦称赞太尉王衍“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评价极高;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好似神仙中人;时人称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谢安说支道林的双眼“黯黯明黑”;还有人赞赏王恭形貌丰满美好“濯濯如春月柳”;更有时人“看杀卫阶”。可见,魏晋时期盛行对士人容貌外形的审美欣赏。除此类种种正面赞赏形体容貌的描写外,还用讥讽丑陋来衬托形貌姣好以受到时人的追捧,如曹操认为“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就让别人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李安国容貌“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好似从容貌就能观透一个人;潘岳容貌身材好,上街会被妇人围住,而左思相貌丑陋,上街则是被众人唾弃;更甚者,陶侃本欲杀庾亮却因为其容貌风韵引人而决定不杀他,看来当时一个人的容貌也能影响生死大事。这些都是对魏晋士人的评价,多是注重外在容貌方面的品评,当时对于容止的欣赏由此可见一斑。
然魏晋人倘若仅停留在对于容止的欣赏,恐怕尚不足以引起后人的关注,在政治混乱,世道不安、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目睹了太多的生死幻灭,更将审美心理向内拓展,向自我生成,对虚灵、真性情、人格美的追求是魏晋身体美的精神特质。人物品藻,使士人自身成为审美对象,而在对于自身身体的审美中,尊重个性价值,肯定自我魅力、追求自我价值是其中的灵魂,形成的是形神兼备的审美风尚。宗白华有言:“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在《美学散步》中又指出:“‘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魏晋人的人物品鉴注重对形体容貌美的欣赏和追求,身体的容貌、神态、形体都是晋人审美观照的对象,但他们并非完全以貌取人,更有对士人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精神气质的欣赏,即所谓重形亦重神,形神兼向往之。魏晋人物品评相当注重身体仪表和神态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精神特质,一个人相貌平平甚或丑陋,然只要气度超俗,就会受到世人的赞许和社会的关注,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二人在外貌上均不占优势,然他们展现出来的自然之气质,却颇为人称赞。中国美学史中,对气质的品评是人物品藻的重要部分,一个人的相貌更多的是天生而不可改变的,气质精神则是通过后天的努力修养出来的,它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本质风貌。晋人人物品评常用“清”“风”“气”、“玉”等词,对人物气质风度加以赞赏,《赏誉》篇中王导评论太尉王衍站立的姿态“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赞王衍屹立在那里就像千丈石壁一样;有人看到杜弘治,赞叹其风采俊秀,本性清高,有大德风范:“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世人品评谢尚“清畅似达”,是说谢尚清明畅通,近似博达;嵇康由于“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甚至其醉态“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有人去拜见王太尉,刚好遇到王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座,于屋又见季胤、平子,回家后对别人说:“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将这些齐聚一堂气质极佳的士人比作琳琅满目的珠宝美玉,是对这些具有不凡气度和品格之士人的极高赞赏;王敦称赞太尉王衍站在众人之中就像珠玉放在瓦砾石块中间,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异常夺目,竟至有珠玉和瓦砾的天壤之别。在魏晋人看来,引人的风貌和脱俗的体态是士人高超内在品格的折射,形色容止的身体美是由内在的生命神气向外发散出来的精神气质,由此可见,魏晋时期的身体审美并不局限于人物的身躯容貌,他们更看重肉身之体所凸显出来的气质精神,更愿意追求的是身心合一、形神兼美的身体之美。
当魏晋士人重新对身体进行审视,达成身心合一的共同审美标准之后,就开始借助饮酒、服药、敷粉、着奇服、裸身等方式对身体进行由内而外地修饰和安置,在“放纵”中实现一种哪怕是短暂的精神“超越”,这便成为魏晋士人身体美在外形、方式与内在追求上形成的一种张力之美。饮酒在魏晋士人当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饮酒清谈是魏晋士人的一种常态。刘伶和阮籍是有名的酒徒,《任诞》篇中描述阮籍在服丧期间依然在宴会上喝酒吃肉,刘伶因为饮酒过多导致病态仍然要酒来喝,通过饮酒麻醉身体,他们可以忘记现实的肉体,获得精神之乐。魏晋士人还流行服五石散,五石散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配制而成,实则是一种毒药,何晏最先开始服五石散,他肤白貌美,大家都以为是服药之效用,便跟着服食。《言语》篇中何平叔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可以看出魏晋士人服五石散有多重理由,或以其治病,或修饰容貌,或令己“神明开朗”,也就是说,服药能使士人们直接感受到身体的愉悦。晋人喜肤白、形体纤美,敷粉和穿个性服饰也是魏晋士人修饰自己身体容貌的重要方式,《容止》篇中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怀疑他敷了粉,就让他吃汤面,结果吃完大汗淋漓,用袖子擦汗后脸更通透白润了,可见敷粉在当时已经屡见不鲜了;士人们身着奇装异服,脚踏木屐追求个性风韵也成为风尚,何宴喜欢穿妇人的衣服,《假谲》篇中描述谢玄年少的时候“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充分显示了魏晋士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对自身愉悦享受的关注及对姣好容貌的追求。此外,裸身也是士人追求自身愉悦享受的一种重要方式,《任诞》篇中记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㡓(裈)衣,诸君何为入我㡓中?’”裸身还通常与饮酒并行,谢鲲、毕卓等人闭门裸身饮酒,数日不出。关上门,裸身而饮,任门外世事如何纷争都一并抛却脑后,身体和心灵都处在一种最自然最享受的状态,这便最能产生对人生、世界、自我的思考,也最能接近本真的自我。表面上看,服药、饮酒、着奇服、裸身是士人对自身的放纵,实际上是他们为追求身体愉悦享受做出的种种尝试。他们从身体这一最基本的载体出发思考短暂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不是被纲常礼教束缚,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感受,不断获得身心的愉悦享受,所以裸身是士人们对身体形骸的放逐,是在一定意义上对肉体的扬弃,彰显的是对肉体的超越和对形而上自由之境的追求。
魏晋士人对身体美的追求还强调与世界相融,强调理想与现实的融合。身体并非一种孤立存在,它一定存在于世界当中,与周围的世界相联结,在世界中展现自身;身体是世界的缩影,它反映着世界,同时又受世界的制约,即身体总是由它所嵌套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所塑造。魏晋时期士人身体意识的觉醒,彰显着那个时代的变迁。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思想异常活跃,儒道佛三教合流,统治阶级将儒家的纲常礼法作为维系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们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因生命无常的感慨而想到设法逃避政治以保自身,服药、饮酒便是他们从自身之境出发,寻找到的安顿身心的合适路径。尤其借助于服药,一方面,士人们或通过治疗疾病提升自己的容貌,或借以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以求身体长存,一方面又可通过对身体的麻醉,躲避政事,逍遥沉醉于属于自我的精神世界之中,体会到哪怕是短暂却也真实的快乐与幸福。美,不正是身体在一系列的刺激下,经由各种器官感受或产生的诸如轻松、陶醉、快乐、舒服等主体感受吗?饮酒亦如是。士人想要生存就要立于世,立于世就要与周围的环境打交道,然而生存环境恶劣,该怎样才能首先保全身体生存下来而又不招惹祸事呢?魏晋士人发现了饮酒这一绝妙的手段:人们总是对醉酒之人多一些宽容,酒后大醉,可以装狂,以此为借口就可以免去尘事的纷扰,顺利地将自己置身事外,不参与朝廷政事,自然也就少了是非祸端的危险,保全自己的身体便成为可能。然身体是肉体和精神的合一,肉体徒存,倘无精神,亦乏快乐,何况人终有逝去之日,于是魏晋士人索性及时行乐,摆脱肉体的羁绊,将天地当作房屋,将房屋当作衣服,在闭门裸身饮酒这种最自然舒适的状态中逍遥沉浸。如是,则以饮酒、服药的效力麻醉身体,发散精神,从而超越身体,享受独特的身体愉悦是魏晋士人与世界和谐相处的一剂良方。当我们能看到魏晋士人一边身著个性服饰,脸敷白粉,格外追求形貌之美,又一边饮酒服药,裸身放纵,不顾形态,好似弃置身体不管不顾时,当知其并不矛盾,究其实则在于魏晋士人在追求形而上的精神理想境界时认识到肉体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中,追求自己的理想必然要先立足于社会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身体是作为灵与肉的结合体而存在的。
三、中西古今身体观对照
古今中外的文化各异,但人们的思想处处相通,这种相通,跨越民族、地域和时代,从未停止。关于身体及身体美的思考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由上可知,魏晋士人对于身体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然而,由于重视抬高身体的地位并从学理上对身体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是从近代西方开始的,故许多学者运用西方理论来指导阐释中国身体美的研究,这对于中国身体美学理论的发掘显然是不够的,从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语境出发来分析当时的身体美思想,再与西方近代的身体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身体美学思想。
细数历史,不难发现,在一千多年后的西方,尼采、梅洛-庞蒂、福柯等人对身体的讨论与魏晋时期士人的身体观念有诸多契合。魏晋时期,士人们“发现了身体”,重视自然之身体,并向内发现身体的价值,此时的身体不再是儒家用来承载纲常礼法的工具之身体和共性之身体,而是独属于自我的身体,我可以对它随意修饰,也可以用药和酒将它麻醉,无论我做什么,我的出发点都是我的身体。一千多年后,尼采强调身体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准,所以一切应当从身体出发,提出“要以肉体为准绳”的口号,认为人就是身体,身体是决定人的基础。尼采对身体的赞美:“还是来好好倾听一下健康身体的声音吧,因为那才是一种更正直更纯粹的声音”、“我整个儿都是肉体,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我的灵魂只是肉体上某一部分的名称”,他将一直处于理性、上帝、道德压制下的身体释放了出来。诚然,两者分别是在中西方开始重视身体价值的代表,都对身体重要性的发现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尼采过于鼓吹身体的价值,甚至认为灵魂是对身体的蔑视,这就与魏晋时期身心并重有所不同。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既不是作为客观生理性存在的“身体”本身,也不是主观的自我意识或心灵,而是在纯粹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一种存在,是身心不分、主客相融的统一体,这与魏晋士人的身体概念相近。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灵魂和身体的综合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一个是客体,另一个是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都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身体意味着一种结合,体现出身心的交织与互动。魏晋士人认识到身体就是灵与肉的结合体,生理性存在的身体或者说肉体只有和精神灵魂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所以他们不仅注重外在的容貌形体之美,更强调对精神气质的追求,寻求一种身心愉悦的身体体验。梅洛-庞蒂还认为身体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主体,而是扎根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存在着交往互动的关系;世界是身体得以实现自身的场域,身体是世界得以呈现的必要条件。在魏晋士人那里,身体与世界相互联结,身体需在世界中存活,世界需要身体来呈现,于是饮酒、服药、敷粉便成了士人们的身体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身体概念、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上,梅洛-庞蒂的观点与魏晋时期士人的身体观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
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礼教严格管控着人的身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严重制约了人的身体能动性,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更是将儒家的纲常礼法作为掩饰自己罪行的工具,用政治权力规定和限制人的身体欲望,干预人对身体的塑造。意识到这一点的魏晋士人试图摆脱礼法教条对身体的束缚,以获得个性解放,一大批人饮酒作乐,裸体服药,越名教而任自然,公然对抗儒家传统是其实现“身体美”的自觉选择。到了近代西方,福柯指出身体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有机体,还是社会历史的建构物。身体不仅在自然、社会、文化中不断被塑造和改造,它也展现着历史事件的冲突和对抗。这就导致了身体必然要受政治权力对它的影响和干预,比如对人的欲望加以规定和限制。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它可以通过一种话语或者一套法规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塑造、监管、规训和惩罚,将身体驯服为依其旨意行动的身体。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福柯的身体观是与权力产生强力联系的身体。因此他主张将身体从政治权力和传统文化的压抑之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更多直接而现实的身体愉悦享受。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有共同的观念:身体的能动性一旦被压抑,就会影响身心的塑造,摆脱权力对它的控制就是寻求解放。
舒斯特曼对梅洛-庞蒂、波伏娃、褔柯、维特根斯坦、詹姆斯和杜威六位哲学家的身体理论进行探讨并做出评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身体美学首次做出了定义,指出身体美学将身体“作为感性审美欣赏与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核心场所,并研究人的身体体验与身体应用”,以此为据,他指出了身体美学的三个基本维度,即分析、实用主义和实践的维度。他明确了身体的概念,认为它既包括主观意向性,也包括物质客观性,倡导通过身体训练的方式(比如瑜伽、太极、禅定等温和的练习)来培养我们的身体意识,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高雅,感觉和意识更加愉悦敏锐,最终达到身与心融合为和谐的一体、知行同一的境界,达到美的状态。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士人是在提高自己的身体意识,虽然并非以禅定、太极这类“优雅”的方式,而是饮酒、清谈、服药等这些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够优雅”的方式,然而还原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思考,我们发现,他们选择的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最恰当的方式,其目的也是达到身心融合为和谐一体的目的。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从古到今,人们从开始发现身体的价值起,就一直对身体进行思考:身体究竟是单纯的肉体还是身心合一的统一体?一直处于压抑中的身体应如何获得解放?身体与世界怎样才能和谐相处?怎样才能获得直接现实的身心愉悦?这些问题拉近了中国古人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距离,使其在美学史上留下了一方思考的空间,也使中国古代关于身体美的思考有了现实的延展。
身体美学的核心是身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身体,身体观又映射着对一切事物的思考。在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念的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于人生、世界和自我的思考,以及对于追求理想和回归现实的巧妙处理。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是当时种种思想危机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当身处环境动荡、遭遇生命短暂威胁的士人们发现,周围的一切都瞬息万变,唯一可以确切感受的是自身的身体时,他们便选择从身体出发构建有限的人生。在具体的操作中,他们没有将身体美的体验与展现局限于肉体,也没有过度升华为灵魂思想,而是视身段为身心合一的结合体,进而思考身体如何与世界相处,在不与当时社会环境生死相克的情况下,选择了饮酒、服药、裸身、敷粉、服妖、清谈这些方式,一方面与世界相互交融、保全自身,一方面追求内在身心愉悦的体验。
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固然有其独特的当代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士人们追求身心统一及身体与世界相处的过激方式——如大范围式的过量饮酒、服药、敷粉——不仅对其修身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理想,还会对后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它容易使人们夸大和轻信外在形体美的重要意义,而走向“身心相融”的身体美学思想的反面。舒斯特曼认为:“身体美学尽管也关心形体的外在之美以及其他一些外在的身体表现和标准,但是,它所探讨的主要是身体本身的内在感知与意识能力。”显然,魏晋时期身体美学的实现方式确有其一定的社会局限性,对它的意义的宽容理解也只适应于那个大动荡的时代。
舒斯特曼作为第一个系统提出身体美学理论的美学家,他不仅站在西方哲学家的肩膀上,也曾坦言自己的理论灵感部分源自中国的哲学思想。实际上,舒斯特曼及其所站的那些巨人的思想与魏晋时期士人的身体观有许多契合之处,换言之,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的研究不仅可以与现代西方身体美学的研究联系沟通,对于中国美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产日益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不断充沛的物质生活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精神带来预期的满足感,反而使人们的“身—心”走向了“异化”之途,分析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能够让我们在当前这个过度关注身体的消费社会中保持对身体的清醒思考,认识到身体是一种充满情感、生机而灵敏的身体,而不是缺乏感觉、单纯物质性的肉体,使身体能够帮助人们体验身体自身的魅力以及审美多样性,而不是仅使其成为一种获取超额利润的附庸物和消费品。因此,无论怎样装饰和美化身体,我们都应时刻记住身体的本质,处理好身与心的关系,让身体与世界和谐交融,去获得自然的身体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