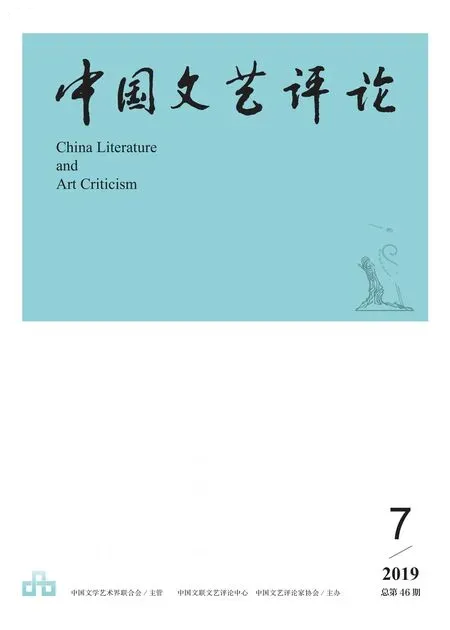道艺统一 褒优贬劣
——新中国70年文艺评论断想
仲呈祥
想起了恩师钟惦棐
《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约我对新中国文艺评论70年写篇纪念文章,这任务重要且光荣。吾生也晚,新中国诞生之时,乃三岁幼童,不晓世事。这令我想起了恩师钟惦棐先生。他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培养出来的文艺评论前辈。1979年当新中国诞辰30周年时,饱经风霜的他正届花甲之年,应新时期扛起文学评论界思想解放大旗的《文学评论》之约,写了篇享誉文坛的两万余言的长文《电影文学断想》,从被列宁当时称为“在所有的艺术中”“对我们是最重要的”电影入手,断而想,想而断,借用电影镜头语汇,从“光焰夺目的片头”到“人的焦点在变虚”,从“长镜头和短镜头”到“多声带混合录音”再到“空镜头”,从“和弦论”到“电影构思”再到“断想之余”……实际上通过解剖电影这个典型的“麻雀”,对整个文艺创作与评论中的“政治与艺术,源与流,放与收,香花与毒草,大题材与小题材,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诸般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刻的辨析和反思,至今仍闪耀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的思辨锋芒和智慧火花,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历史已经证明:40年前的这篇经典性范文,在新中国文艺评论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如今要对新中国70年来的文艺评论进行反思,当效法恩师,努力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枪法,尝试主要对近40年自己经历的文艺评论实践断想一番,虽不能达到恩师之高远境界,但心向往之却是真诚的。
在恩师之后“接着讲”
其实,吾生也有幸,逢盛世由蜀进京,求学立业已四十余载矣!自1978年起,而立之年后的我,紧随几位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军前辈陈荒煤、冯牧、钟惦棐、朱寨等身边,耳濡目染,受益匪浅。荒煤老师把自己当成提供精神能源的“煤”,无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扶掖新人的载物厚德和人格魅力;冯牧老师那锐敏的思想发现和审美感悟,以及他评论中显示出的独特的逻辑力和穿透力;惦棐老师“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总是以难能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把握大势,置身于民族审美思潮的前端,去导引大众攀登思想艺术的高峰的魅力;朱寨老师严谨治学,秉笔直书,力挺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谌容的《人到中年》,并确立其在新时期文坛重要地位的评论大家风范;以及谋面不多但给我教益甚深的王朝闻先生,总是置身于民族审美海洋的漩涡中心,以其健全而灵敏的审美神经去感人所未感、悟人所未悟,并以独特的审美发现去提升大众审美修养的功绩……所有这些前辈师长,都是引领我从事文艺评论的灯塔,令我终生难忘。可以无愧地说,我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亲历者、参与者、受益者和见证人之一。
新中国文艺评论的前30年,恩师钟惦棐先生的《电影文学断想》已从电影入手作出了精彩的断想,吾不能及,在此只能斗胆地承续师业,“接着讲”这后40年主要在文艺评论政策与标准上的断想和反思。
焦点之一:文艺与政治之关系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当然也是文艺评论的生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党的文艺政策,我以为主要进行了两次重要调整。
第一次,鉴于前30年、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极具胆识地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石破天惊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是因为,实践雄辩地证明:在抗日战争历史环境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再简单地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就弊多利少了。一种情况是:当政治错误时,如“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要求文艺从属之,便催生出如电影《反击》《春苗》《欢腾的小凉河》之类的“阴谋文艺”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服务,祸莫大焉;另一种情况是:即便政治正确时,也难免有人为了虚假政绩,不顾民心所向和民间疾苦,挪用有限资金建造豪华的文化广场,并强迫文艺去“写广场、唱广场、颂广场”,这就为炮制虚假政绩服务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提供了政策依据。有鉴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与时俱进地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二为”)取代了简单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这一重要政策性调整,极大地解放了创作与评论的思想,拓展了题材的风格样式,促进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现实主义文艺的复苏与繁荣。想当年,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有人要批,认为“谢惠敏形象”歪曲了教育界的现实,是恩师朱寨先生仗义执言,旗帜鲜明地以一篇四两拨千斤的文艺评论《从生活出发》,驳斥了这种把文艺简单地从属于政治的责难,充分肯定了这篇小说坚持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品格,吹响了现实主义文艺复苏和繁荣的进军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改革开放呐喊,也有人要批,说是丑化了党和现实,又是陈荒煤、冯牧在当时文联、作协的极简陋的沙滩的会议室里,召开作品研讨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发出了文艺评论的科学声音。之后,从“伤痕文艺”到“反思文艺”再到“寻根文艺”,文艺评论都紧随时代的脉博,为反映人民的心声发挥着开路先锋、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可见,党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这一政策性调整,确乎关系着文艺评论的生机与活力。
当然,作为大政治家和辩证法大师,邓小平在提出用“二为”方向取代简单的“从属于政治”时,又高瞻远瞩地提醒我们务必要防止长期制约和影响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或从“从属于政治”走向从属于“一己之悲欢,并以此为大世界”的自我表现和“为艺术而艺术”,或走向“从属于经济”搞“唯票房、唯收视、唯码洋、唯点击率”那一套。他再三精辟指出:不再提简单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丝亳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归根结底,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政治,文艺要以审美方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好务。这才是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法。
焦点之二:文艺与经济之关系
果然,不出邓小平所预料,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建立和逐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出现了有悖“二为”方向的倾向:或张扬“文艺表现自我”“为艺术而艺术”思潮,或鼓噪唯票房、唯收视、唯码洋、唯点击率的唯经济效益主张。针对这些倾向,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都反复强调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些文艺政策无疑是文艺评论必须遵循的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文艺创作与评论的实践出发,接着聚焦于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不断加大力度,又一次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两者都要抓好,不能重此轻彼。而文艺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必须高度重视。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又在肯定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存在着“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还利益的‘摇钱树’”的现象,存在着“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问题,并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特别强调:“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正视了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作品的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的严峻现实,并明确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准则。这正是坚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深刻揭示的真理。马克思指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不只是感性的物质动物,更是高级形态的理性的精神动物;人不能只以物质的方式即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人更需要以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如以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以经济的方式即资本生产的方式把握世界,其最高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以艺术的方式即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其最佳境界是超功利。在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到康德、黑格尔,在东方,从老子、孔子、庄子到陶渊明、王阳明,直到现代的朱光潜、宗白华,概莫能外,都作如是观,最通俗的说法便是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资本论》)。其实,近20年来中国电影的资本运作即市场化的实践,已经再次雄辩地印证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真理性。所以,2015年10月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绝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视察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时的讲话,直到2019年3月4日在同全国政协文艺界和社科界委员座谈时的讲话,都反复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坚持培根铸魂,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指明了发展路径。
焦点之三:文艺评论的标准
同党对文艺与政治、与经济关系上先后两次重要的政策性调整密切相关的,便是文艺评论的标准问题。标准的科学程度直接关系到文艺评论执行政策的精准度及其成败得失。
1985年,面对电影的票房,在对电影的评价标准上,有关部门在长期坚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标准之外,又加上了“观赏性”标准,变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简称“三性统一”。应当客观地说,这确实事出有因,面对市场,电影不能不考虑其观赏性,因为这直接攸关票房。但是,三十余年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这个政策性的标准效果是不好的,它在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好像艺术性不包含以其自身的历史内涵和美学品位所应有的吸引力、感染力去征服观众,还需要加上一种自立于艺术性之外的观赏性才行;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便是如今充斥于某些影片中的凶杀、床上戏、婚外情、多角恋、“小鲜肉”……电影界的那种以“视听生理奇观美感”冲淡乃至取代优秀影片理应给人带来思想启示和精神美感的伪美学主张,实质上便是为鼓噪这种“观赏性”张目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个流行了三十余年的“三性统一”标准,始于电影界,却普遍使用于整个文艺界,成为一个具有政策性权威性的文艺评论标准。音乐作品也要讲“三性统一”,试问音乐这种听觉艺术的声音、旋律与节奏何来“观赏性”?文学作品也要讲“三性统一”,试问,以语言为载体供人阅读的并无具象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何来“观赏性”?甚至连“五个一工程”评奖的标准也要求“三性统一”,那理论文章怎么讲“观赏性”?果如是,恐怕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优秀论文也并无什么“观赏性”了!
理论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反思“三性统一”与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创作出现的那股不可小视的庸俗、低俗、媚俗思潮之间有无内在联系,不难发现:当我们盲目地把本来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与本来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即把本来以作品自身的品格(内容与形式)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思想性、艺术性,与本来以观众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观赏性,置于同一范畴,作出“三性统一”的判断时,我们就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违背了逻辑学与范畴学的一个基本法则——“只有在同一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一定的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判断的科学性。”因此,说“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统一”,与说“男人、女人(以性别为逻辑起点)与农民(以职业为逻辑起点)统一”一样,都是违背逻辑学、范畴学基本法则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
再说,思想性、艺术性是客观存在于作品中的恒量,主要由作家艺术家决定;而观赏性则是弥漫于观众群体中的变量,是主要由观众不同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和社会提供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鉴赏环境来综合决定的。马克思有两句经典判断,一句是: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另一句是: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两句经典判断讲的正是这个真理。观赏性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对观赏的需求是不同的,如中小学生爱看《还珠格格》,我却认为太闹太浅),因时而迁(历史条件与时代语境不同对观赏的需求也不同,如老舍的《茶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被斥为“毒草”,而新时期以来成为久演不衰、一票难求的精品),因地而变(审美空间变了观赏效果也会变,如当评委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拿张碟带回家与亲友边聊天边喝茶边看,效果迥异)。所以,观赏性乃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主要是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决定观赏性的主要因素不是作家艺术家,而是观赏者的素养和观赏的文化环境,而这两条,都需党和政府依靠全社会齐心合力才能妥善解决。倘若把观赏性单一推给创作主体即作家艺术家解决,那么,面对着在“三俗”思潮影响下日益下滑的受众群体和良莠芜杂的鉴赏环境,缺乏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而又缺信仰、缺情怀、缺担当的创作者为了占领市场赢得票房,便势必会放弃引领,一味迎合市趣,愈迎合则愈败坏受众审美情趣;而审美情趣愈低下的受众则势必刺激这些创作者粗制滥造历史品位和美学格调更低下的伪劣产品;于是,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恶性循环之中。此种教训,极为深刻。
唯其如此,为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201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废弃了“三性统一”的提法,明确提出“优秀作品必须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时也强调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栏目都必须“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同年11月30日,他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强调要追求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翺翔俯视。”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重申了应当“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科学标准。之后,他又强调“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在2019年3月4日与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座谈时,他再次号召“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而精品之所以精,就精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所有这些重要论述,都廓清了不科学的文艺评论标准,激励作家艺术家倾情创作“三精”作品,指引评论家坚持培根铸魂,道艺统一,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为“三精”作品鼓与呼!
断想之余的几点思考
在关于政策、标准等关键问题断想之余,反思自己四十余年从事文艺评论实践的经验教训,确有些浅识,现实录于后,求教于方家。
首先,文艺评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的指引。哲学管总。哲学通,高屋建瓴,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左摇右摆,四处碰壁。为什么调整了简单化的“从属于政治”,又有人走向了笼统地“从属于经济”、抑或“从属于自我”?为什么纠正了“高大全”,又有人走向了“非英雄化”?为什么匡正了“题材决定论”,又有人祭起了“题材无差别论”?为什么弘扬了主旋律,有人又放弃了多样化?……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从哲学思维层面寻根溯源,盖因为长期影响和制约着文艺评论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不左就右、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在作怪。文艺评论应当以执其两端、把握中间、全面辩证、兼容整合的和谐思维去观照审美鉴赏对象,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思维层面的深刻变革,才能真正占领精神高地,获得独到的真知灼见和审美发现。
其次,文艺评论必须获取历史镜鉴的启迪。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过去,洞察今天,预见未来;历史又是一位智者,可以了解客观、反思主观,努力实现主客观的统一。为什么今天文艺评论中反复出现的问题,竟然是过去历史上有过的教训的重蹈覆辙?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中的表现都那么似曾相识?为什么文艺评论在五花八门的对革命历史和红色经典的肆意颠覆篡改现实前显得那么麻木迟钝、软弱无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文艺评论所操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枪法尚未娴熟!
再次,文艺评论必须更好地用中国文艺理论解读中国文艺实践。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16字经”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经验的精辟总结,当然也是中国文艺评论理应遵循的重要准则。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评论而言,各美其美,就是要立足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论艺论,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弘扬中华美育传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之美,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之美,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美。这是需要大培特培之根。在此基础上,以世界眼光和宏阔胸怀去美人之美,去学习、借鉴别的国家和民族创造的文明文化成果,特别是文艺理论批评成果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美美与共,就是要把上述两种“美”交流、互鉴、整合,创新出既富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著名的“四个讲清楚”,第一个便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据此,我们理应讲清楚中华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丰富多样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印论、戏论、园林论以及后来的话剧论、电影论、电视艺术论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评论经验,讲清楚文以载道、道艺统一的中华文论艺论的优秀历史传统,讲清楚中华美学精神在审美运思上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在审美表现上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在审美形态上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从而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评论道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4日在与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座谈时强调要“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他之前还告诫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人的审美”。这种极强的问题意识有现实针对性、有深意存焉!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文艺评论实践中,确实存在一股数典忘祖、盲目西化,以半生不熟的西方文论艺论误读中国文艺实践的错误思潮和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尖锐批评的:“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言之谆谆,语重心长。我们理应深入研究阐明中华文论艺论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论艺论是发展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滋养,阐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论艺论是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评论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必须,阐明面对新时代的当今中国文艺评论的科学体系必须在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艺评论经验成果的交流、互鉴、整合、创新中构建。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更好地用中国文艺理论解读好中国文艺实践,有力地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第四,反思自己四十余年来从事文艺评论的经验教训,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包括他在致光荣入党的83岁电影演员牛犇的信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殷殷厚望,在给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的回信中对文艺作品提出的要“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高标准,在给中央美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发出的“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深情号召……都对整个文艺工作包括文艺评论具有及时雨般的重要指导意义。吾距此要求,差之远矣!惶愧之余,总结出自己从事文艺评论的20字体会: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
以文化人。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以载道,道艺统一,以文育人,培根铸魂,这是中华文论艺论优秀的历史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时代,尤须坚持传承弘扬这一优秀的历史传统,与时俱进,着意久远,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以文艺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然后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学发展观;反过来,倘若急功近利地以文化钱,用经济思维误导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甚至以降低人的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为代价,那么,即便经济一时搞上去了,也难免终会被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吃光、花光、消费光,整个国家和民族还会垮下来的!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宗旨都在培人之根、铸人之魂、化人之境,这极为重要。
以艺养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文艺之美,贵在养心;评论之美,贵在提神。习近平总书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文艺作品当然要靠自身的史学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人感染人,但这种吸引力感染力是有引领性的,是把读者观众引领到作品的精神高地上来。而观赏性只讲适应与迎合,因人而异,因时而迁,因地而变,是没有引领性的。所以,我们在文艺评论中并不笼统反对作品养眼,而是反对一味养眼、止于养眼,尤其反对花眼乱心。止于养眼乃平庸之作,花眼乱心乃伪劣之作。须知,过度的视听快感是扰乱伤害人的心智的。优秀作品乃是通过养眼达于心灵,进而养心。文艺评论理应力倡以艺养心。
重在引领。文艺评论务必要把满足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是文艺创作与评论都须遵从的辩证法。只有重在引领,才能真正使文艺评论成为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既有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又有百余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影响,还有照搬苏联模式的影响,更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因此在今天广大受众的文化心理中,虽然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深情呼唤,但难免也残留着落后的消极的东西。一味迎合,势必强化受众群体中落后的消极的东西;被强化了的这种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又势必反过来刺激缺信仰、缺情怀、缺担当的创作者生产格调品位更低下的作品,从而使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而重在引领,就要秉笔直书,敢于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郑板桥先生这两句名诗,应当成为当今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座右铭。
贵在自觉。文化自觉是当今文艺评论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要以高度的自觉,认清文艺评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方向盘”的地位和作用。自觉的反面是盲目,要同盲目“西化”的倾向,同“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的庸俗现象,同“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的八面讨好态度,彻底划清界限。要真正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胜在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论胜败的关键所在。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充满自信,要对与时倶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充满自信,要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论、艺论和中华美学、美育精神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满自信,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艺、红色文艺充满自信,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充满自信,果如是,我们就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稳操胜券,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