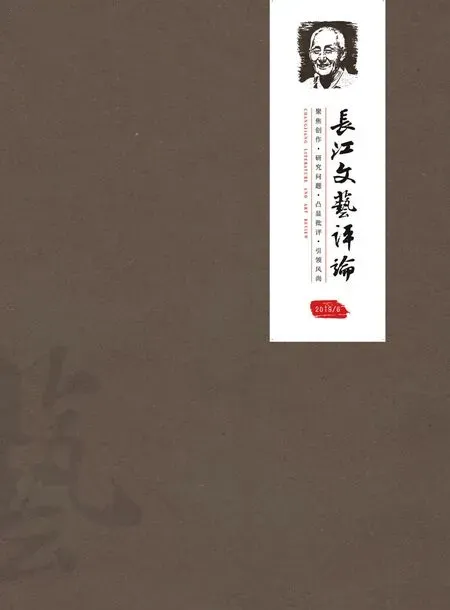叶与梅多小民说族的文民学族观性
◆贺绍俊
叶梅是一位土家族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既有鲜明的土家文化印记,也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研究叶梅创作的文章大多都会围绕这两点来论述。事实上,我对叶梅的小说研究得很不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对土家族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专门学习了一些土家族文化的文章,再来梳理叶梅的小说创作过程,就发现叶梅的民族性书写是建立在自己对民族性独特理解基础之上的,她对女性意识同样也具有自己新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则与土家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有关。
叶梅对小说的民族性有清晰的认识,她说过:“我的小说植根于长江三峡流域的民族地域生活,高山峡谷的三峡人对世界万物和人生的理解,体现了巴楚文化中从庄子到屈原浓烈的诗意美,对我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财富。我想表现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并试图诠释民族的文化母体,有力寻译民族文化的秘密,对土家人刚烈勇武、多情重义、豁达坦荡等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的展示,对西部山地少数民族地方与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来寻找救治现代文明之弊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资源。”在她的小说里,可以发现土家族的文化符码俯拾即是,龙船河、豌豆角、桡夫子、梯玛、女儿会、跳丧鼓等。但我觉得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者对这些文化符码的阐释。
叶梅自主的民族意识是逐步形成的。她最初开始写小说时还没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她最初写的小说基本上是以土家民族聚居的农村为背景,但小说并没有特别渲染其民族特色。小说中多半有一个工作队干部形象——“杜同志”,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而且是一个代表着公正、真理的政治角色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杜同志”基本上就是叶梅本人的化身。因此,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在叶梅早期的小说中占据了主流。但是,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基因深深埋在她的生命里,即使她是以一名工作队干部的身份来讲故事,其民族特性也会在不经意间地泄露出来,印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比如她的第一篇中篇小说《香池》,除了香池这个可爱可怜的姑娘是恩施的以外,作者基本上没有自觉考虑采用土家族的文化元素,但其中隐约也透露出一点点,比如天地嘴穿的服装:“一身崭新的蓝布裤褂,头上捆着昨天才买的黑丝帕子”。叶梅开始小说创作的初期,从1979年到1983年上下,她的土家族文化基因还没有完全进入小说思维之中。《谢了的花》这篇小说很有意思,小说写一个乡村姑娘因为贫穷而最终死亡的故事。叶梅给这个姑娘取名为“翠翠”,与沈从文的小说名篇《边城》中的女主人公同一个名字,而且两个翠翠也有相似的可爱和美丽。我不知道叶梅写这篇小说之前是否读过沈从文的《边城》,但叶梅曾在散文《从恩施开始写作》中说,她以前还不知道有一个大作家叫沈从文,因为写了第一篇小说,也开始知道了沈从文。叶梅将第一篇小说稿寄给《长江文艺》后,就被邀请去参加改稿学习班。有一天《长江文艺》的一位编辑问她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没有,并对她说:“我读了你的稿子,有点沈从文的味道。”叶梅在这篇散文中写道:“这话让当时的我受宠若惊,可惜不知道沈从文的分量。但从那以后,我有意去读了沈从文,果然湘西鄂西有许多共同的亲切,文学道上多了一个前行的灯。”叶梅写第一篇小说《香池》时还不知道沈从文,但她的这篇小说会让一位文学编辑感觉到有沈从文的味道,这也许就是共同的民族文化血缘在他们的叙述中起了作用吧,如果说从叶梅的《香池》中能够读出沈从文的味道来,这只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合。这种味道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水风情孕育出来的,自然在叶梅所写的龙船河这一具有土家族山水风情的河流中我们也能体味到。叶梅创作是否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至少从民族意识的确立来说,沈从文对于叶梅有一种引导的作用,沈从文是出生于湖南湘西的苗族,叶梅是土家族。苗族与土家族虽然是两个民族,但这两个民族在文化血缘上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文化习俗也基本上相同。我相信,叶梅读到沈从文的小说时,一定会有一种文化的亲切感,沈从文应该能够激活她生命中潜伏的土家族文化基因。叶梅的《谢了的花》是在《香池》之后不久发表的,也许她读到了沈从文的小说,也许还没有读过,但这篇小说的“沈从文的味道”更足了。
1984年写的《过了河,还有山》已经有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小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土家族文化符码,也仍然是“杜同志”的工作队干部视角,但叶梅的土家族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渗透进“杜同志”的意识中,因此尽管故事仍然是与农村的贫困以及日常生活有关,但她是要通过故事来诠释“大坪坝的土家人具有悍而直的气质,重义气,不反悔,任侠尚义……”老歪和宋珍儿这一对夫妇是因为贫穷而无奈凑合起来的婚姻,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但当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时,又能相互尊重,当然也免不了因为提防而耍点小心眼,比如老歪怕宋珍儿突然离去时把他为婚姻准备的八套新衣带走,就悄悄地用塑料包好埋到土里,又向大家宣布家里被盗了。最后他们好好地离了婚,离婚后仍是好朋友。像老歪和宋珍儿这样的相处方式,在汉族生活地区似乎是很难被公共的舆论所容纳,但通过叶梅的叙述,就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土家人重义气和不反悔的豪爽、真诚的品格凸显了出来。
1990年代,叶梅的民族意识进入自主阶段,土家文化元素在她的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土家文化意识也构成了她的小说的基本主题。这些以土家文化意识为主题的小说也使叶梅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写于1990年的《酉水少年》是一篇才一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但完全可以看作是叶梅的土家族宣言。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在土家的酉水河上,一条船载着一群从武汉来的贵客要出发了。突然一个少年飞身从岸上跳到了船上,他是老艄公的孙儿,爷爷答应他每次行船让他扳舵,但这次因为载的是贵客,老艄公不想让孙儿扳舵,但在大家的支持下,老艄公还是交给了孙儿来扳舵。小说描述了这位满脸带着稚气的少年如何从容地扳着舵驶过最险峻的鸡公滩,还纵身跃入水中捡回了一位老师不小心掉到河里的笔记本。这位酉水少年具有鲜明的土家族性格。长期研究土家族文化的学者周兴茂对土家族的文化性格是这样概括的:“刚柔相济,是土家族文化的基本性格特征。在武陵山区的高山大川之间和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土家族人民长期养成了一种以‘良心’(善良之心)为其价值观的根本出发点的人性本体,‘良心为本’,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崇力尚勇’的阳刚之气和‘淳朴憨直’的阴柔之美天然整合的基本民族性格和精神,或者说,土家族人民从‘良心’的人性本体出发,长期养成了‘劲勇’与‘淳朴’的民族天性的‘两翼’,并且,这两个方面形成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浑然一体,刚柔相济,最终形成为‘一体两翼’的人性格局,从而达到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高度统一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从酉水少年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土家人的“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对他言行的影响,他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后代。但更重要的是,叶梅不仅要写出酉水少年能够接好老艄公的班,他还有了比老艄公更远大的胸怀,他从土家的酉水河出发,要奔向辽阔的大海。当孙老师邀请少年去武汉时,酉水少年信心满满地回答:“我要去的。我自己驾船去,到了长江,再到海里去。”这其实是当代的土家族发出的宣言:要从自己的故乡武陵出发,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去。
进入民族意识自主阶段的叶梅,其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土家族文化符码,其基本主题则是重新认识并彰显土家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以199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为标志,她陆续创作了《花树花树》《黑蓼竹》《山上有个洞》《最后的土司》等一批中篇小说,集中讲述了土家人的故事。这些小说的风景描写非常突出,展现了土家族居住地神奇秀美而又雄浑险峻的自然风光,显然,在叶梅的民族意识中,土家族居住地的自然风光是与土家人的性格融为一体的,因此叶梅的风景描写也具有一种人格化的特点,与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构成互文关系。这些小说因为比较真实客观地书写了土家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品格,对土家族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文化世界作了准确的阐释,因而被研究者称其为“土家族文化小说”。
有许多批评家和学者对于叶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文章都准确地抓住了叶梅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但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叶梅民族意识的自主性。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的特征,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充分发挥自己民族文化的资源,是他们创作成功的一大途径,叶梅从这一点来说与众多少数民族作家是相同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叶梅在民族意识上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这使她在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上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她的关于多民族文学的思想,叶梅说:“今天在中国谈少数民族文学,更多的是应该放在多民族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一个维吾尔族作家,还是土家族作家,都与生俱来地带有不可抹煞的民族性。至于说在你的作品里如何去表现,那就要跟你的生活体验和表现的内涵,你希望达到的精神高度等有关系。”我非常欣赏“多民族文学”这个提法。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传统,这是我们观察汉语写作的重要前提。我以为,完全可以将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扩大到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汉语写作的文化本质的概括。也就是说,汉语写作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特征,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汉语的文化系统中,在汉语写作中或隐或现地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首先应该具备多民族文化的意识。叶梅从多民族文学的观念出发,也就不再是将土家族文化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对待了,土家族文化既融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溢出本民族的边界,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互动和化合作用。尽管多民族文学的观念是叶梅在21世纪之后正式提出来的,但我认为,当她20世纪90年代在小说创作中自觉确立了民族意识之后,就开始孕育起多民族文化的观念,这也与土家族文化特征有关。土家族文化,是世世代代聚居于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土家族人民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创立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黔中文化、夜郎文化等多种文化发生了密切交往的关系,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民族文化形态或区域文化形态。因此,土家族文化的成熟和定型过程就决定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叶梅对土家族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就具有一种开放性。在《撒忧的龙船河》中,覃老大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汉子,他有乐观潇洒的生命观,有敢担当的气魄,有一颗自由奔放的心。小说一开始就写覃老大告别世界的豪爽方式,“覃老大迸发出全部生命的力量,朝天大笑了三声,便戛然而止,一个结实的魂魄犹如一块巨石訇然落入漆黑的深潭。”覃老大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重情义恰是土家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在这种重情义中我们又能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覃老大与莲玉的关系变化犹如一波三折,在变化中唯有覃老大的情和义始终没变。他最初与莲玉在洞中发生了激情燃烧的浪漫之举,这似乎是年轻男女亲密接触后都难以避免的“自然”之举,是人的正常之情的宣泄。而后来他之所以放不下莲玉,既有爱的因素,也有义的考量,而这些“义”可以说是儒家的礼义伦理与土家族的以诚相待、恪守信誉的习俗交互融汇的结果。如他那一年冬天去县城本来是为了挣点钱让妻儿过一个快活的大年,但听到枪声不断,又看到县城里乱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便想起莲玉是否安危才决计去看个究竟。又如后来答应到县城当贫协委员,也是因为还抱着一丝能再见到莲玉的愿望,见到莲玉后才发现她对自己根本没有真情,因此哪怕面对裸身的她,他原来火热的情欲便顷刻间熄灭。在这些描写中,覃老大就像是一个土家豪爽汉子与儒家礼义君子的合体。而覃老大为儿子说亲事的方式则完全是土家族父亲的方式,他根本不与儿子商量,就让妻子给儿子说媳妇,“临到结亲的头一个月才把置办起的聘礼给儿子看了,叫儿子到女家报期。”尽管儿子大为震怒,覃老大也不计较,依旧计划行事,当然这样的结果是儿子婚礼的当天晚上就只身离家出走了。
多民族文化观念对于叶梅女性意识的构成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叶梅的女性意识充分吸收了土家族文化精神的积极面,并与现代女性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她的刚柔相济的女性观。
叶梅是一位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家,她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情女性的遭遇。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并不如人意,叶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她在小说中鲜明地批判了现实中对女性的不公,同时表达了她对一个公平、公正、幸福、和谐的女性理想社会的期许。在叶梅看来,这个美好的女性理想社会是等不来的,要靠女性去争取。她愿意以文学为武器,为女性的理想而呼喊,她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女人不要甘于做一个弱者,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站立着,勇敢地爱和被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因此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能够“勇敢地爱和被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是以土家族女性为楷模的。尽管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时代里,许多土家族女子始终也未能走出大山,她们在现实中的处境并不理想,她们的命运也很坎坷,不少女性甚至逃不出悲剧命运的结局。但叶梅特别强调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土家女子有着不甘的心境,有着敢于与现实抗争的意志。这类女性形象用叶梅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过河的女人”,叶梅小说中有不少“要过河的女人”。比如《花树花树》中的双胞胎姐妹昭女和瑛女,她们性格迥异,一个倔强,一个内秀,姐妹俩配在一起真是刚柔相济,但姐妹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都怀有强烈的“要过河”的愿望。昭女是大胆地去争取“过河”,她不把村长的恐吓放在眼里,直接找乡长。瑛女把“过河”藏在心里,缺少姐姐昭女的胆量,她告诉祖母,自己就是不知足,“别人有的我为什么不能有?”她还许诺有了好日子要把祖母也接去,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却戚戚的”。瑛女最终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昭女则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大山。
叶梅的“要过河的女人”意象来自土家族民歌《龙船调》,这首土家族民歌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土家文化的核心内涵。过去对土家族推行“汉不入峒,土不出境”的封闭政策,但是《龙船调》中的土家姑娘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性格,她活泼奔放,不仅主动跳上艄公的摆渡船,还大胆地招呼小伙子们来推船。叶梅由此演化出一个代表土家姑娘本质的“要过河的女人”,这一本质集中体现为:有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并且自信、乐观,这是叶梅为土家女子拍的标准照。叶梅又以土家女子的标准照来塑造小说中的女子形象,《花树花树》中的昭女和瑛女是这样,《五月飞娥》中的二妹,《青云衣》中的妲儿、秀娘,《黑蓼竹》中的竹女,《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李玉霞等都具有土家女子的共同品性。
叶梅强调了土家女子品性中的积极一面,是因为她希望土家族文化能够为现代女性争取自由解放提供精神武器。叶梅认为,在现实中每一个女人面前都横亘着一条男权主义的大河,而女性的理想则在大河的彼岸,追求理想的女性就要设法蹚过这条河。她曾将她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妹娃要过河》,她在这本小说集的后记中写道:“在河的彼岸,星空闪烁的彼岸,有着女人的希望,虽然河水深浅不一,有着不可知的风起云涌,但过河——是一件多么诱惑女人的事情。这些要过河的女人,闪动在我的小说里。对命运改变的期许,对渡过河流的心驰神往,浪漫与现实,温情与倔强,使她们在不同岁月里有着相似的梦想。”叶梅曾说过,现在的文明是让女人吃亏的文明,因此她在小说中塑造“要过河的女人”形象时,侧重于表现女人追求理想中的不服输和敢拼搏。土家女子形象成为叶梅女性观的最佳代言人,在叶梅的女性观念里,现代意识与土家族文化意识得到有机结合,这也是她的多民族文学观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