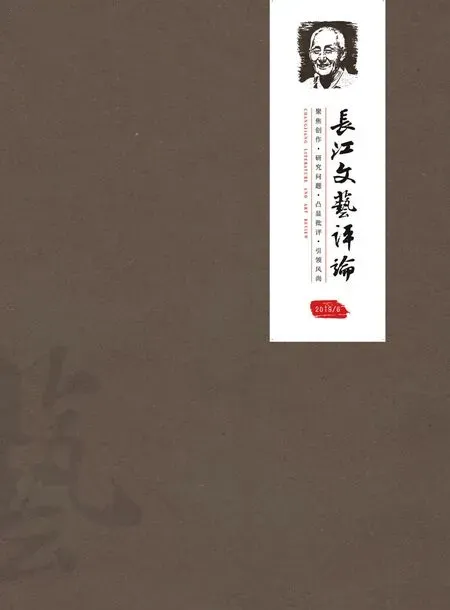穿透正史的浪漫书写
——读尔容长篇历史小说《伍子胥》
◆吴平安
作为文学大省的湖北,历史小说在其文学成绩单上无疑是高分科目,顺着姚雪垠的《李自成》、杨书案的《九月菊》、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映泉的《楚王》下来,可以排列一长串作家作品的名录。刘川鄂在言及这一现象时,有过一段精辟的总结:“厚重的文化底蕴氤氲了湖北作家的正史情。无论是人文正史还是革命史,湖北作家的历史书写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以确凿的历史事件为素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将艺术的想象和虚构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编织情节、刻画人物、表现人性,以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2011年,女作家尔容以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为辛亥百年献礼,加入到湖北这支历史小说家的队列,2018年,又以长篇小说《伍子胥》昭告她不会只是历史小说界的匆匆过客。对她在这条路上能行走多远,读者可以怀抱乐观的期许。
一、追慕荆楚先贤的功业和建树
“纪传体小说”是尔容给《伍子胥》的文体定位,这一定位表现了她尊正史、忌翻案、拒戏说的叙事立场,鲜明地印证了湖北作家的“正史情结”。这是一部“大历史(History)”即所谓“宏大叙事”,而非近年风行一时的,打捞被历史遮蔽的碎片,书写芸芸众生悲欢离合的“小历史(history)”。在纪传体的文体笼罩下,枢要人物的命运走向是已知的,重大事件的演变轨迹是预设的,如此留给作者放纵想象自由挥洒的空间便是有限的。就叙事策略而言,线性叙事便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有文字记载的3000年辉煌国史,给中国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源于《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等典籍记载的伍子胥其人其事,已成为一人物原型(archetype),敷演于历朝各代的历史叙事中,唐代有敦煌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宋代有话本《吴越春秋连像评话》,元代有杂剧《伍员吹箫》,明代有传奇《浣纱记》、冯梦龙小说《东周列国志》,晚清《吴越春秋说唱鼓词》,现代冯至小说《伍子胥》、曹禺话剧《胆剑篇》、萧军《吴越春秋史话》等等。那些不同时代、不同门类的“伍子胥”携带着各自时代的印痕,俯就着不同艺术的规范,或突出传奇性(讲唱文学),或展现悲剧性(传统戏曲),或聚焦勾践复国(《胆剑篇》),或着意于范蠡、西施爱情(《浣纱记》),有的上下500年(《东周列国志》),有的仅截取伍员出逃(《伍子胥——从城父到吴市》)。倘若再原其叙事立场,更是新旧杂陈,瑕瑜互见。一言以蔽之,留给后来者的空间并非没有,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了。
以此观之,作为后来人,又是在“纪传体”的严格限制下,区分度的有无及强弱,是作者面对的最严峻、最苛刻的挑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衡估作品得失的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尺度。
驱动作家历史书写的心理动因毕竟是多种多样的,国人治史,其立足点多为以古鉴今,使君王明治乱兴衰之理,“资治通鉴”四字,即可概括正史千年不变的主旋律。尔容写历史小说,却透露出“一个隐秘的原因”:“楚地望姓家族就是前吴相国伍子胥的后人”,而长江三峡一带则是其繁衍之地(尔容原名望见蓉,生于秭归茅坪)。正是认祖归宗的愿望使业已固化千载的纪传体内容出现了松动,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被置入以“生命密码”开篇,以“爷孙揭秘”收束的结构框架中,中间夹以“缘定终身”,在“伐楚入郢”时阵前认父,以及主人公伍子胥失意得意之时均心念妻儿的点醒之笔,虽属“草蛇灰线”,着墨不多,但却“伏脉千里”,间离效果生成了。正是认祖归宗的愿望,使充满了血雨腥风,暗藏着阴谋权变的春秋历史,有了情怀,有了温度,小说便不再是史家的客观敷衍,而是作者对先祖魂兮归来的呼唤,而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故事讲述与小说叙事,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就由此实现了整体性转换。
《诗·商颂·殷武》有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楚之先民发于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其以五十里荆山子爵之微,崛起而为春秋五霸之一的过程中,伍氏先祖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小说以伍氏曾祖伍参以谜语讽谏韬光养晦不理朝政却“性好隐语”(刘勰《文心雕龙》)的庄王奋发图强起笔,随即辅佐庄王与晋逐鹿中原,取得邲之战大胜,进而伐宋降宋,建问鼎中原的不世之功,继而写祖父伍举扶立楚灵王灭陈改县,开疆拓土,为此书的主人公伍子胥登台亮相,敲响了开台锣鼓。
二、传达古代战争的艺术和韬略
在我看来,决定一部历史小说成败的因素很多,而传达时代氛围、刻画历史人物,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衡估尺度,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的,分而叙之只是出于言说的方便。《伍子胥》的时代背景是春秋中后期,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缶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孟子》)的大动荡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并起,战乱频仍,烽火不息。据统计,春秋时期有记载的战争多达395次,故而传达时代氛围,首当其冲不可不写战争,而一场战役往往纵横千里,“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人们称历史是雄性的,说的就是历史前行的脚步,总是与暴力和血腥难舍难分的。
战乱频仍,斗智斗勇,必定会刺激军事谋略的成熟与发展,千古兵圣的孙子及其《孙子兵法》遂应运而生。《伍子胥》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春秋时期的战争艺术。当伍子胥登上历史舞台时,这场战争大戏的主战场已经由北方转向了南方,齐鲁之战、齐晋之战、秦晋之战相继鸣金收兵,旷日持久的吴楚之战、吴越之战,成为春秋落幕前的两出压轴大戏。三国间攻伐不断,此消彼长,战役有大小,历时有长短,叙述有详略,行文有疏密,但满纸风烟,金鼓杀伐之声可闻,对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而言,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试看鸡父之战和拔郢之战,这是吴楚之战中两场重大战役。鸡父是楚国在大别山以北的屯兵要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公元前519年,吴兴兵伐楚,吴王僚亲任统帅,楚挟七国之师,以逸待劳,吴则劳师袭远,孤军深入,未战胜负似已立判。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究其实,楚首先败在临阵换将,接任者难以掌控局面,犯了兵家大忌,吴则调度有方,在运动中进退穿插,将强敌截为数股,分而歼之,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终获完胜,鸡父之战,将战场推进到楚国北大门,这一举改变了吴楚对抗的战略态势,并成为上古战争中以弱胜强的案例。
拔郢之战更是纵横江淮流域、大别山区、江汉平原,横跨今之鄂豫皖三省区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任统帅,以伍子胥、孙武为左右手,以攻克楚国郢都为战略目标,分南北两路,水陆并进,挥师犯楚。楚国迎战的主将是左司马沈尹戍、令尹囊瓦。沈尹戍堪称将才,然而将帅不和,囊瓦贪功冒进,直接打乱了沈尹戍的战略部署,吴军则调度得法,主动后撤,诱敌深入,相机歼敌,三战而三捷,士气大振。吴军大将阖闾之弟夫概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不惜违抗君令而主动出击,不给败军以喘息机会,终将楚军击溃,直捣郢都,圆满完成战略目标。
我在阅读小说的战争叙事时,特意将手边著名军旅作家朱增泉将军所著《战争史笔记》的有关章节加以对照,以求在历史和小说之间寻找差异。总体印象是,《伍子胥》叙述的鸡父之战,脉络似乎尚不够清晰,比如一场战役发生的具体时间,作为“纪传体小说”理应清楚点明。比较起来,“伐楚入郢”这场重大战役,叙述到位,令人信服。朱增泉将军曾在其《战争史笔记》中,总结吴军战胜强楚的四条经验:一是战略思维清楚,二是战略步骤稳妥,三是作战方法灵活,四是作战指挥果断,战场感觉灵敏。尔容叙述这场战役的全过程,基本上吻合了朱增泉将军的军事专业性判断,亦属难能可贵。
三、塑造伍员性格的丰满与复杂
春秋乱世,人生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部《伍子胥》,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好几十,有的神龙一现,有的中途下台,有的则演完全场。作者将众多人物,纷繁事件,锁定一条主线,聚焦一个人物,即为伍子胥树碑立传。
《伍子胥》的最大成功之处,在我看来,就是在正史叙述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小说化的再叙述,通过低谷与巅峰,复仇与报恩,在人生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塑造了伍子胥这个兼有传奇性与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其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人物的鲜明性与独特性。时下小说由于受现代后现代影响,多不大在意人物塑造,更鲜有立得住的人物,而《伍子胥》无疑有积极意义。以主人公命名作品是需要几分底气的,因而在当代文学中十分罕见。
三代以降,能臣贤相,代不乏人,而像伍子胥这样,毕生功业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复仇之上的,却难有其二。复仇是中外文学一个重要母题,是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伍子胥的复仇,却不同于新旧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也不同于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复仇。封建时代的复仇只能借助于权力,这种原本属于个体间恩怨情仇的报复,一旦与吴国争霸中原的野心相重叠,就转变为一种国家行为,牵扯到若干诸侯国的国运兴衰乃至生死存亡了。从负罪亡命一夜白头,到行乞异邦吴市吹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不堕其志,见其逆境中的韬晦和隐忍;助公子光谋君篡位并剪除庆忌,见出其超人的心机和谋略;在手掌兵符号令三军的阵前交锋中,则尽显其勇武与豪侠,在助吴国兴利除弊建都姑苏的过程中,他的胸怀扩大了,精神升华了;在几经反复终于伐楚复仇,他轻财仗义,将吴王阖闾所赐金银珠宝悉数散尽济贫;他既有伯乐相马慧眼识才七荐孙武的眼光,也有蒙蔽于表象荐人失察的地方,“只谋事不谋人”的先祖基因,使其忘记了“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对“匹夫无罪,怀璧有罪”失去了警惕以至于招致杀身之祸;在功高震主之时,盖因因袭三代辅佐君王的历史包袱太重,远不如孙武头脑清醒功成身退而得以全身远祸……
如果说伍子胥的上述行迹在正史中已具备或隐或显的脉络,则其在漫长的复仇过程中,以及此后人生沉浮中的心路历程,便不仅成为后来人重新阐释的空白点,也成为作者悲悯情怀和人文情怀的寄托点。
纠结与矛盾,乃至于撕裂与痛苦,几乎是伍子胥终其一生的心理状态。立志复仇之初的决绝,在利用专诸、要离行刺,唆使公子光谋君篡位的血腥过程中,因心中善念不泯而时时受到良心叩问,又不得不寻找“尊王攘夷,替天行道”的堂皇借口安慰自己,以“顺天承运,应时而动”的理由求得心理平衡。这种痛苦在吴师攻破郢都时达到高潮,当吴王阖闾以下君臣士卒以胜利之师放浪形骸时,伍子胥却“神情沮丧,表情黯然”,以至于“大放悲声”。何以会如此这般?作者给我们预留了有待填充的空白。是仇人恩人都已不在,报仇报恩皆无着落?这显然比中外复仇文学中的大团圆式结局,更平添一份空虚与无奈:是士人面对王朝更迭世事无常心头油然而生的“黍离之悲”?这也是春秋时期时代情绪的一种。无怪乎伍子胥内心深处,还不时泛起放弃修齐治平,返身山野林泉,与妻儿“过朝看日出暮起炊烟总角晏晏其乐融融的日子”的念想了,他不但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危险,更看清楚了“天下的王位没有哪一个不是血迹斑斑”的残酷现实,但“既已上船,就没了退路”,只能让下一辈隐于草野民间,永不为官了,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士人心头萦绕千年的入世出世的心结。总而言之,这种反常而合道的心理状态,无疑加重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经由作者想象性的、阐释性的复制,经千百年间叙述的开放性的历史人物,被作者再次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特定的个体。
四、探究人心人性的清澈和浑浊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修史的民族,这给中国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若问,已有史籍浩瀚,堆叠如山于眼前,而由话本肇始的演义类历史小说却何以能一直长盛不衰呢?将文字艰深的史书普及化,以利于大众接受,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小说相对于历史,更是人类心灵史的记载吧。春秋时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但那又是一个自由奔放、生机勃勃的时代,《伍子胥》以宏大的格局,铺展了这个历史转型期的长轴画卷,礼赞了汉民族童年期充沛勃发的生命力。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忠奸之别,势同冰炭,对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奸臣的切齿痛恨,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如何既尊重又跳出这种阅读期待,既不作所谓翻案文章,又不被其狭隘性所拘囿,这又是一个亟待作者突破的地方。
《伍子胥》描写了费无忌、伯嚭等几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形象,努力用现代眼光观照古人,透过这些奸臣巧言令色、工于心计“共性”之外,解剖人性混沌幽暗的一面。
其一是嫉妒。费无忌与伍奢本同为楚平王身边近臣,虽胸无点墨,不学却有“术”,为了“抓牢今世的王,笼络未来的王”,争取到太子少师的官职,当看到太子建对太傅伍奢敬重亲热有加,自己难以争锋时,便妒火中烧,遂改弦更张,认准了“将全部心思用来取悦楚平王才是正道”,此后的翻云覆雨,阴谋诡计,一手酿成太子建和伍奢父子,乃至于楚国宗庙隳弃的悲剧。
无独有偶,伯嚭与伍子胥共事一主,每临一事,皆败其下,“他深知伍子胥的思想与才智都远在自己之上”,“心里酸酸的”,由此滋生的嫉妒之心,与费无忌不遑相让,而“要打败伍子胥唯一的七寸处”,一言以蔽之,就是其“不会来事”,伍子胥身死而吴国灭,不妨说就始于嫉妒的罪孽。
其二是贪婪。吴越争霸,子胥运筹帷幄于内,将士浴血奋战于外,终将越军困于固城,吴之灭越,已无悬念,当此生死存亡关头,越能起死回生,显然不在天意,而是越国谋臣文种瞅准了伯嚭的贪婪本性,贿以黄金白璧美女,许以“日后春秋朝贡未进王宫,也会先入宰府”,而获求和,此后勾践事吴三年,得以保全性命放还,也全仗越国对伯嚭不断的利益输送,可以说,吴与其说灭于越,不如说是灭于伯嚭的贪婪。
“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西方人在评价春秋时期中国人的国民性时,用了“清澈”一词。这种精神世界的清澈,庙堂中固然也有,比如朝中官人申包胥与县衙小卒伍子胥超越身份地位的真挚友谊,以及灭楚兴楚,各事其主的坦荡磊落,都见出清澈的人格,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孔子所言之“野”,即民间和江湖、乡土和市井间,这些草根民众精神世界的“清澈”,与肉食者的浑浊形成强烈的对照。尔容曾思索过一个问题:在伍子胥亡命天涯途中,楚国的通缉追杀,几为天罗地网,如何能顺利逃脱虎口呢?面对举报者的重金悬赏,藏匿者的杀身之祸,却有傅永慈的以身相许,皇甫讷的甘冒替身,老渔夫和浣纱女的舍命相助。而渔夫之子在吴国大军压境,郑国危在旦夕之际挺身而出,以伍子胥救命恩人之子的身份劝退吴师,且婉拒了荣华富贵的许诺,仍以艄公摆渡为业,其人品的冰清玉洁,足令人感佩。至于春秋时期两个著名刺客专诸和要离,其轻生重义,蹈死不顾的决绝,更将其侠肝义胆演绎得淋漓尽致。
相比于西方,中国哲学与文学对嫉妒这一人类“久远的罪恶”,还欠缺足够的关注度,明乎此,则《伍子胥》的涉猎,其价值便彰显出来。在我看来,作者对此主观上的认知还不一定很清醒,以致在叙述的突出与深刻上,与“贪婪”和“清澈”相比还不甚到位。这足以提示我们,对人性方方面面的探讨与开掘,正是历史小说价值的重要生成点,而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铺排与再现。姚雪垠先生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历史使命。”作为小说世界一角的历史小说,必须服从小说美学的总体要求,即力求超越具体题材的拘囿,由此岸到达彼岸,这是这位著名历史小说家对毕生写作经验的总结,其实也是任何一位小说家应有的追求。
注释:
[1]刘川鄂主编:《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朱增泉:《战争史笔记·上古——秦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3]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前言》,《姚雪垠研究专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