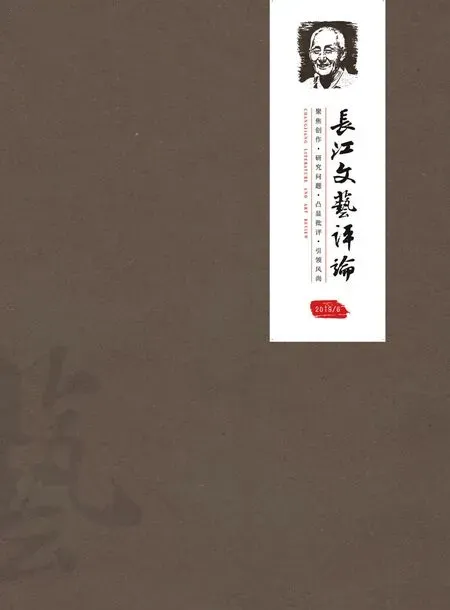讲述“中国”的故事
——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有感
◆叶立文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茅盾文学奖从来都是批评家进行历史叙述的一个切入点。每逢大奖揭晓,各种学术话语便汇聚于斯,或以得奖作品的经典化问题为契机,总结某一时段内的创作成就;又或以评奖机制、社会舆论和市场反应为推手,寄寓当前文学“往何处去”的价值期许。众声喧哗之下,茅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功能也一览无余。
但问题就在于,批评界的学术话语大多具有自洽性,那些基于先验批评理念的文本解读,往往在关注作品与理论契合度的同时,忽略了茅奖评审的具体标准。比如常见的“文学性”问题即为一例。由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让文学回到自身”的诉求始终强烈,故而有不少批评者就据此认为,《牵风记》《人世间》《北上》《主角》和《应物兄》这5部得奖作品,很难说在“文学性”上高于其它提名作品。毋庸讳言,这一判断当然可以成立,毕竟《北鸢》的温润典雅、《敦煌本纪》的疏朗壮烈,以及《祭语风中》的神性光辉等等,无不在美学维度上具有了“经典”的品格。但茅奖的特殊性就在于,“文学性”只是众多评审标准中的一个选项,若是从整体上来看,得奖作品当属实至名归。
为便于讨论,不妨将茅盾文学奖的评审标准照录如下:“茅盾文学奖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对于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标准既定,那么如何解读便是关键。作为本届茅奖评委,我认为上述标准里的关键词即“中国”二字。它既是一个恒定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随时间发展而不断扩容的文化政治概念。茅奖评审标准里所说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等等,就意味着中国作家不应再以早年的那种历史窥视态度,去书写“中国”社会的“原始”风貌。实际上,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如何借文化自信去保有我们的民族身份,业已成为了后“八五”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向。除此之外,茅奖作品的整体性问题也不应忽视。标准里所说的“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应是针对五部获奖作品的整体状况而言。因此如何排列组合,令五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去反映这种多样性,也就成了评委们的考量重点。
总体来看,此番得奖的五部作品,皆以讲述“中国故事”为己任,不仅追索革命历史的烽烟聚散,描摹人世生活的岁月沧桑,而且也勘察民族秘史的丰赡曲折,体味传统文化的流风余绪。更有甚者,又在写实之外,试图以社会寓言之形式,管窥一番国民众生的隐秘心史。由于五部作品赓续了当代文学的家国传统,交相辉映、踵事增华,因此它们充分代表了近四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二
五位获奖作家中,徐怀中最是令人敬重。论者多赞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比这种写作态度更为重要的,却是徐怀中对同类题材中“革命+恋爱”模式的超越。而评奖标准所说的“中国”精神、风格与气派亦由此可见一斑。
在新文学史上,2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少,“革命+恋爱”的情节模式也十分常见。只不过这种藉由革命运动去铺陈男女情爱的写法,却常因作家思想立场的暧昧和情欲本能的张扬,陷入到了一种首鼠两端的创作困境:以革命而言,由于人物大多青春热血,视革命为血色浪漫的祭坛,故而动辄盲进、无谓牺牲;以恋爱而言,则追求情欲自由、目无礼法。狭隘偏激处,遂使革命变成了一剂“疗救私人痛苦的良药”。从这个角度看,很多“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其实并不能够真实反映革命先贤的舍身取义。自此以后,虽然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曾将情欲话语逐出过文本体系,但80年代以个性解放为目标的同类作品,却又发扬了早年的“革命+恋爱”模式——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即为典型。问题就在于,这种游移于革命和爱情之间的情节模式,其实是在西方启蒙哲学影响下所形成的一套“现代性”叙事,隐含其中的民粹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情调,既远离了历史真实,也模糊了那些为国为民的革命者形象。而《牵风记》的出现,虽不至于完全扭转这一方式,但它对“革命+恋爱”模式的超越,却仍有其特别的文学史价值。
这种文学史价值,主要体现在《牵风记》对革命和恋爱关系的处理之上。男女主人公齐竞和汪可逾,因宋琴结缘,在烽火绵延的战争岁月里互生情愫。按“革命+恋爱”的情节模式,这两位具有艺术气质的人物,本应在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认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徐怀中的处理方法,却是以汪可逾的贞烈为叙述焦点,讲述了她因被俘而遭受齐竞怀疑后对于爱情的断然舍弃。当汪可逾斩断情丝之时,那些深植于人物内心的伦理意识,也焕发出了夺目的道德光芒。而齐竞的男权思想和汪可逾近乎偏执的贞烈观念,其实都是中国人固有的存在经验。从这个角度看,作家书写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常”与“变”问题——即使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身处历史大变局之下的中国人民,也依旧秉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操守。说到底,只有将《牵风记》放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序列里,它的“中国”气派才能尽显无疑。
至于梁晓声的《人世间》,则更是将茅奖评审标准里的“中国”精神阐释得淋漓尽致。遥想知青文学当年,梁晓声关注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等重大题材,凭借着“虽九死而不悔”的道德理想主义光芒,不知打动了多少国人。如今对比来看,较之他80年代启蒙文学的“宏大叙事”,《人世间》看似体量巨大、包罗万象,但它对普通民众命运沉浮的描写,却多以生活化的日常叙事展开。更准确地说,《人世间》其实是一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中国小说不乏世情小说的渊远文脉,它关注市井人生、世相百态,常于烟火缭绕的日常叙事中,一览国人绵延不绝的人生哲学与处世之道。从文化底蕴上说,不管此类的世情小说如何喧嚣扰攘,都真实地记录了独属于我们民族的中国经验。《人世间》正是这样的作品。作品中底层人民对于传统道德的践行感人肺腑,那些生活的激流、历史的巨变与人物的成长,无一不在梁晓声所讲述的中国故事里,彰显了我们无法忘却的民族记忆和道德理想。就此而言,《人世间》最终以文化自信的中国气派,捍卫了平民的尊严与荣光。
三
与前两位作家相比,徐则臣的获奖似乎更有讨论之必要。姑且不论作家的代际更迭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单就《北上》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也足以证明年轻作家的文化自觉是何等强烈。如果考虑到“八五”一代作家因急于融入“世界文学”而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的话,那么徐则臣所具有的文化立场,就反映了新时代语境下当代作家对于“中国”概念的全新理解。而作为后“八五”一代作家叙述“中国”的产物,《北上》最能反映当代作家对于“中国”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它所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为阐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八五”一代作家对于“中国”概念的理解,究竟造就了一个怎样的纸上中国?而徐则臣这样的年轻作家,又如何讲述了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故事?凡此种种,皆需从1985年前后中国文学的新变谈起。
众所周知,1985这个年份,早已因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运动而被载入了文学史册。彼时中国作家凭借着融入世界文学的渴望,在充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不仅打破了中国文坛独尊现实主义的创作局面,而且也令当代文学真正地走向了繁荣昌盛。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八五”一代作家笔下的“中国”其实并不真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东方主义文化想象下的中国形象。从理论渊源来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他者”的眼光,本身就发端于西方中心论,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原始风情的开掘,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东方主义者的文化猎奇心态和基于西方现代化危机之上的代偿性心理,终令“中国”形象遭遇了被污名化的命运。
更为吊诡的是,“八五”一代作家并非没有本土的文化立场,否则他们也不会有“影响的焦虑”。但东方主义的这种文化想象,因其叙事逻辑是建立在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事”之上的,故而“八五”一代作家就将反映中国形象的偏陋遥远和原始神秘,当成了是融入世界文学的必经之途。于是前述的种种文化乱象,便在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而《北上》的价值,恰在于对此类中国故事的“拨乱反正”。
从作品涉及的内容来看,《北上》里有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八国联军、义和团、土匪和革命者等各种极具东方风情的小说元素,故事时间更是始于20世纪初。与大运河的百年沧桑相对应,徐则臣书写了若干个家族的兴衰沉浮。如此繁复的书写对象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完全可以满足东方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历史窥视欲。但徐则臣的写法却别具一格,譬如故事主线之一,讲的是保罗·迪马克在大运河上的文化考察之旅,但作家的笔锋所指,却并不是要借这位外国冒险家的视角去展开一段有关大运河的东方主义想象。恰恰相反,由于迪马克的文化考察既是受到了同胞马可·波罗的感召,也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兄弟,因此他的运河之旅,就有了一种“反将他乡认故乡”的寻根意味——中国成了意大利人迪马克和马福德兄弟的精神故乡。需要说明的是,徐则臣如此处理外国人士的精神寻根,并不是一种“万国来朝”式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以大运河的历史积淀为媒介,希望超越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当迪马克病逝于大运河、马福德英勇牺牲之时,这两位意大利人也就和谢平遥、邵常来等中国人一样,变成了落叶归根的运河之子。换言之,大运河作为一个文学意象,不仅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天然界限,而且还在连接不同人物的命运轨迹中,成为了一个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这当然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文化自觉。从这个角度说,徐则臣的历史叙事,既不是东方主义的文化猎奇,也不是保守主义的兴亡喟叹,而是思接千载的精神寻根,是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如此强大的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性眼光和人类立场,自然反映了徐则臣对于“中国”概念新的理解和阐释。
同样,本届茅奖的另一部获奖作品《主角》也讲述了一个新的中国故事。这种新,主要体现在陈彦对秦腔这一“最中国”艺术的专业化书写上。当然,对读者来说,陈彦的这部作品难免会让人想起贾平凹的《秦腔》。两者同为陕西籍作家,同样写秦腔,又同获茅盾文学奖,陈彦的写法较之贾平凹,究竟又有怎样的不同?
其实在贾平凹笔下,秦腔艺术的工具论色彩要更为浓烈一些。他从秦腔戏曲演员白雪的人生故事,写到清风街白、夏两家的家族命运,那些大开大合的戏剧冲突和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无不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和国民的灵魂裂变。从文学谱系上看,《秦腔》依旧是80年代启蒙文学的回响。这是因为贾平凹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国民价值困境的书写,仍然是一种深具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与之相比,陈彦也写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剧人生,也同样借助这一人物的命运轨迹,真实再现了宏大历史的沧桑巨变。但与贾平凹不同的是,陈彦并不将秦腔视为一种叙述工具,他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从小到舞台化妆与表演程式,大到文化精神和人生哲学,几乎处处用笔、时时倾心。这种写作态度,虽说在价值上与贾平凹的工具论色彩并无高下之分,但陈彦以专业知识入文的做法,却同样具有特别的意味。
我们知道,知识与人情,从来都是小说叙事传统里的车之两轮:有的作家善于体察世相人心,描摹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有的作家则长于知识书写,勘察行业规则和文化谱系。虽说有关知识的陈述,有时会损害故事进程与人物塑造,但假如没有它,则作品的趣味、品格和价值便要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某些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少当代作家的知识修养都较为匮乏,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难以超越就事论事的狭小格局。近年来,当我们强调中国经验时,提到的工匠精神首先指的是叙述艺术本身,一个不打磨叙事技巧的作家,实际上很难创作出深入人心的艺术精品。除此之外,作家的工匠精神更应包括对专业知识的钻研,否则作品的思想容量和文化价值便难以深广。从这个角度看,陈彦写秦腔,不仅真实再现了人物的戏剧人生,而且还以专业的知识描写,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了基于传统艺术形式之上的中国经验。
四
本届茅奖的第五部获奖作品《应物兄》,恐怕是所有提名作品中最具话题性的一部。虽然评委无人否认它是2018年的现象级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当代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但因为此前围绕《应物兄》的各种学术研讨实在是过于热闹,所以也就让这部作品在阐释与过度阐释中变得愈发复杂。评委们对这部作品不仅抱有了更高的阅读期待,而且也会下意识地在显微镜下观察其思想或艺术上的各种瑕疵。当然,这并不是说评委们就对这部作品格外苛刻,而是说《应物兄》作为一部“可写性”文本,其主题的多义与叙述的多元,最终令其成为了本届茅奖评审中的争议对象。
从表面上看,由于《应物兄》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游走在讽刺与批判的边缘,对儒学的态度也暧昧不明,再加上李洱那套略显油滑的叙述“花腔”,种种因素累积起来,遂让评委们对如何指认这部作品的思想取向和美学价值出现了分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应物兄》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茅奖作品。远的不论,单与其它四部获奖作品相比,《应物兄》既无《牵风记》的英雄主义,也无《人世间》的道德理想,较之《北上》和《主角》,它又少了那么一份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积淀。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腔调,或戏谑调笑,或反讽厚黑,严肃的学术话题和轻薄的市井俚语随意切换,正经的道德文章与油滑的庸俗玩笑共冶一炉……总而言之,在素来以典雅周正、肃穆深沉见长的茅奖作品里,《应物兄》颇有些不合时宜的味道。
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应物兄》的那些“不合时宜”,恐怕是绝大多数评委肯定它的根本原因。更确切地说,“不合时宜”主要是指作品在思想取向和美学格调上的特异,而它的基本内容,仍是一种符合茅奖评审标准的、根植于我们民族记忆和生活经验里的“中国故事”。只不过在讲述“中国”的对象与方法上,李洱确如一些评论家所言的那样,“已经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
先来说对象问题。相信在很多读者看来,《应物兄》首先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作品里描写的众多学者形象和士林生活,尤其是纷繁芜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书写,更是坐实了这部作品就是“当代《围城》”的说法。但和《围城》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不同,李洱写应物兄、费鸣、乔木、姚鼐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其目的远非是讽刺与批判,而是以这些人物的活动交集为线索,将叙述进程导向了他心目中的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既是儒学复兴、重振传统文化的中国故事,也是经济发展、再造济州新城的中国故事,同时更是权力博弈、复造世情伦理的中国故事。三者兼而有之,经纬相交、彼此缠绕,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热热闹闹、生机勃勃的故事走向,也反映了李洱如何以描写浮世绘的用心,真实记录了充满着无限生机的当下中国。简言之,李洱脱离了当代文学里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中国故事的主流叙事话语,以一种反先验主义的思想预设,在多重的故事线索中,极力还原了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的探索与实验。由于这一书写对象实在是太过庞杂,任何单边主义的思想立场,都会损害李洱对这种社会探索和实验的反映,因此作家便不再偏安于一隅,他的价值立场,也由此表现出了一种暧昧游移的状态。不过从总体来看,由于《应物兄》这部作品仍是对我们如何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因此尽管李洱在书写不同的逐梦方式时,总是要在相应的知识谱系内上下求索,顺便还要给读者制造一番阅读障碍,但他的写作立场和书写对象,却与茅奖的评审标准基本符合,因为《应物兄》就是一部“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
接下来再简要说说方法论问题。由于李洱写《应物兄》,本身就不愿站在先验的单边立场上去倡导某种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因此在表现社会探索和实验这一书写对象时,他的叙事也就采用了一种随意赋形的方法。主人公的名字叫应物,典出“虚己应物,恕而后行”一语,本身就有顺应事物之意。因此这种顺应,就既是主人公的处世之道,也是李洱随意赋形这一叙事方法的理论基石。更具体地说,基于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李洱十分欣赏顺势而为的人生哲学。而顺应事物的本来状况,继而采取对应的处理方法,难道不正是一种务实的人生态度吗?更重要的是,这种顺势而为,还避免了以先验观念裁决现实困境的危险。具体到叙述方法上,李洱的顺势而为就变成了一种随意赋形。他既不会为了推进情节发展,在某一关键处舍弃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也不会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去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从叙事效果来看,这种写法难免会给人留下详略不分和松散随意的印象。但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一种随意赋形之法,背后并无一套道德理想主义或者是启蒙主义的先验观念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李洱实际上是以挑战我们阅读习惯的方式,将中国社会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复兴探索,直接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基于这一点考虑,《应物兄》也就如茅奖评审标准所说,在“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与“探索和创新”方面做出了特别的努力。
当然,以上所论,或是取诸怀抱借物言志,又或是因寄所托不及其余,故只能以“随感”之名教于方家。好在随着前述五部作品的获奖,相信本文所说的讲述中国故事,也必将成为推动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李洱《应物兄》的空间叙事
——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