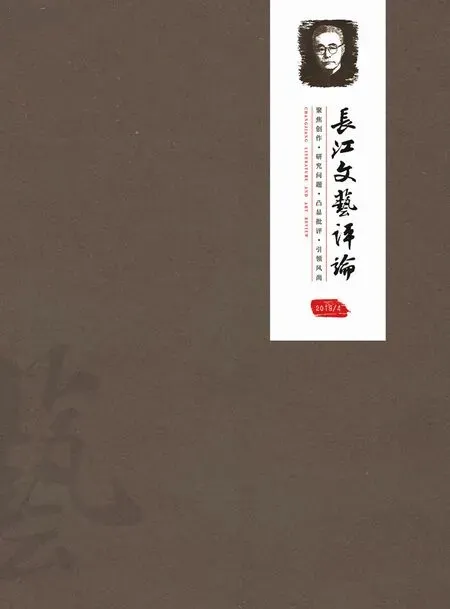学理性与历史理性的追求
——评《陈美兰文集》
◆汪树东
在论文《前沿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魅力所在》中,陈美兰教授曾说:“所谓前沿性,很大程度上是指精神价值的前沿性,作为研究者,更需要的是具有一种建立在历史透视基础上的超越性眼光,一种广涉于多元文化格局的大视野,一种紧贴文学演进行程所获得的敏锐感悟。当研究者具有这样的资质和素养时,我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才会真正焕发出它诱人的魅力。”这一段话不仅是陈美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美好前景的勾勒和憧憬,也是其毕生学术研究的自我总结。在撇开俗务,静下心来,再次细细展读这散发着油墨馨香、囊括了作者毕生心血的百余万字的三卷本《陈美兰文集》后,笔者认为陈美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抵达了学术前沿,她的现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体现了难能可贵的超越性眼光,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构建了一种多元文化格局的大视野,小说批评文章也紧贴文学演进行程。作为学术后辈,笔者在此不再逐一评述陈美兰的相关学术成果,而是整体归纳她的学术理路和学术品格,以期昭示后学,继承前辈的学术衣钵,勉力前行。
一、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意识和学理性追求
历史意识和学理性追求是陈美兰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鲜明的学术理路和学术品格之一。在当代长篇小说研究领域堪称经典的学术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中,陈美兰专门设置了第四章第二节谈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意识,陈美兰说:“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识,主要包含两重内容:一是指作家在观察和反映生活时能有意识地从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把握生活的流变,也就是以历史的发展眼光透视生活;二是指作家对历史生活形成发展的动因、态势以及所具有的意义作出的认识判断,体现出历史的识见。正是这种历史眼光和历史识见,使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所塑造的形象具有鲜明的历史感。”虽然在该节中,陈美兰只是对比研究了梁斌的《红旗谱》和张炜的《古船》这两部代表性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但是对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的关注其实一直贯穿于她的所有学术研究中,甚至可以说,历史意识是她用来衡量长篇小说的一个价值标杆。在她看来,优秀的长篇小说能够以历史的宏观眼光透视生活,能够在微观生活和宏观历史之间进行自如的切换,塑造出兼具生活感和历史感的人物形象,给人带来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深邃洞察。
对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的关注,其实是陈美兰的主体意识和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的一种外化。对于陈美兰这一代学者而言,他们受过较为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育,养成了较为宏阔的历史眼光,相信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和必然规律,倾向于在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理解人生目的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他们树立了较为明确的历史意识,偏重于把握文学现象的历史流变,擅长从宏观层面理解文学历史的走向,把反映历史意识的丰富性和新颖性当作考量文学作品的价值基准。
在陈美兰文学史研究中,寻觅新的“史识”和“史见”就是其历史意识的显著表现之一。陈美兰曾说:“所谓‘史识’‘史见’,无非就是对历史的存在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而要做到这点,对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掌握要尽量地广泛。”应该说,参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时,陈美兰便较好地发挥了大胆的“史识”和“史见”,她能够在不冒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掘出被遮蔽、遭误解的当代小说经典,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欧阳山的《三家巷》等,甚至有意识地寻找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点疏离的小说,如在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表现得“另类”的刘澍德的《甸海春秋》《归家》等作品。这部当代文学史初稿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叙述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格局。
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来把握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也是陈美兰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意识的主要表现之一。无论是《近百年中国长篇小说的现代演进》还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陈美兰以极为恢弘的历史眼光深刻透视了近百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概况、演变特征、形象世界、主题意蕴、文体意识等,体现了难能可贵的超越性的历史眼光。至于陈美兰的《“文学新时期”的意味》《创作主体的精神转换》《行走的斜线——论90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等著名论文,也无不是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审视独特的文学现象,洋溢着底蕴丰厚的历史意识。
学理性是陈美兰文学史研究的又一鲜明的特征。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学术追求多样,学术风格繁复,有的学者擅长作家作品论,有的学者专攻文学流派研究,有的学者执意于通史、门类史的撰写,有的偏重于实证性,有的偏好感悟性,有的追求学理性。陈美兰就是在文学史研究中自觉追求学理性的著名学者,无论是文学史撰写、文学思潮研究,还是展开长篇小说研究,抑或是作家作品论,陈美兰均有意追求眼光宏大、问题意识敏锐、富有逻辑性与系统性的学理性境界。她不愿意沉湎于单一的作家作品论,也无意于实证性资料的搜集与展示,她总试图在作家作品中去开掘有意味的、规律性的研究论题,在长篇小说、文学思潮研究中把握全局性的、能够透视历史规律的重要论题。陈美兰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的《引言:历史的潮汐》中说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这一研究主题,就是力图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四十年间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势作一整体透视。它的重点将不在于仅作某种表象性的全面描述,而是力图从它的发展动势去探视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由,从创作所呈现的若干重要侧面去考察内在的构成及形成这种艺术构成的驱使力量。也正是力图从纵向的线路和横向的侧面进发,以期获致对这一壮丽的文学景观及其审美价值、历史价值的切实认识。”这一段话,可以看作陈美兰文学史研究的一种理想目标,那就是对文学史做出透彻的、逻辑严谨的学理性研究。
陈美兰的论文《“文学新时期”的意味》一文堪称学理性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该文中,陈美兰站在更为高远的立场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多元格局、现实主义和价值基准等问题做了切中实质的论断。她认为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而从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到今天已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一元到多元的趋向。这个论断成为此后许多当代文学史家立论的基石之一。她针对那种潜在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垄断欲望,提出“文学的多元共存,实际上就是使文学获得一个从各方面充分体现自己本体特征的机会,从而为进行超越于前一历史阶段的新的整合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文学多元化发展时期,正是中国文学真正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阶段”。而针对有些论者所说的1985年之后没有什么像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她指出,虽然从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既要面临着现代主义,又要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但是正是这种挑战会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引向一片新的领地,为它创造一个有别于上一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中国作家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现实主义经典性作品。从随后十余年的文学史发展经验来看,这种论断的确是先见之明。而关于文学价值基准问题,她承认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固然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成果,但如果相应地忽略历史观的价值标尺,文学的思想根基终究会沦于空虚。整篇论文立足点高,能够透过历史的纷纭表象看取历史的真实脉动,层层深入,论理剖析,举重若轻,值得后学反复研读。
二、小说批评的职业追求和伦理操守
作为文学史家而言,陈美兰显示了超卓的历史意识和学理性,对近百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历史演进的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把脉和肌理疏通,均有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值得后学反复揣摩学习。作为小说批评家,陈美兰则显示了难能可贵的职业追求和伦理操守。她认真地细读每一部长篇小说,对其主题、人物、艺术构思、文体意识详加斟酌,逐一拆解小说的生成方式,慎重地选取评价标准,然后在宏阔的历史层面对其进行价值定位,以朴实严谨的逻辑对其核心问题进行学理性的阐发。她的《珞珈书简——就当今长篇小说创作致友人》《寻找症结——谈谈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突破问题》《对历史意义的追问与承担——从〈圣天门口〉的创作引发的思考》《力与美的升腾——读〈我是太阳〉引发的思考》等小说批评文章,均是体现了其作为小说批评家的职业追求的佳作。
对于陈美兰而言,小说批评就是小说批评,是对一部长篇小说的深入剖析,是对其潜在价值的精微发掘和对其思想艺术问题的直道批评,既不是廉价的赞美,也不是蛮横的棒喝。因此她批评某部长篇小说时,一般都能够充分肯定该小说的独有价值,在此基础上,又循循善诱地展示其内在的思想艺术症结。例如对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的评论,陈美兰认为《圣天门口》显示了刘醒龙在驾驭长篇小说时不仅具有非凡的实力,而且对历史的追问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勇气,是他创作的一次非常大的跨越;但是也指出该小说在处理历史的“寓言性”与“史实性”之间的关系时颇有不当之处,从而造成长篇小说的艺术内伤。这样的批评文章无疑是言之有据、葆有职业精神的,尤其是和当今文坛泛滥无度的那种赞美式的、不及物的小说批评文章相比,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美兰曾说:“坚持带着问题意识从具体创作实践出发,摸准问题的症结,再进行理论的提升,并敢于作出自己的理论归纳。”这是陈美兰小说批评的职业追求的准确表述。她总是全面细致地占有被评论作品,敏锐地聚焦于不同的问题症结,进而进行理论的提升。例如在《期待着更强的突破力》一文中,陈美兰就认为造成当时长篇小说没有塑造出较有艺术光彩的典型的原因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是作家的感受力与剖析力的不平衡,其二是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与所获得的艺术空间的不平衡。针对这个问题症结,她分析《两代风流》和《河魂》中的相关典型,令人豁然开朗。至于《寻找症结——谈谈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突破问题》就考察了个体化写作对长篇小说全局性视野的限制和寻求富有时代意味的哲理感悟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切入长篇小说创作中,批评的敏锐眼光令人尊敬。
在小说批评中,陈美兰也相当重视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这也是她的职业追求之一。例如,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中,她提出长篇小说中的“锁结”概念,对长篇小说的文体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在她看来,“所谓‘锁结’,是指对世界事物之间、人际之间的贯通点的锁合。在一部小说中,一种事态与另一种事态之间,一个人物或人物与另一个人物或人群之间,此一局部生活层面与另一局部生活层面之间,人物命运或生活流程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实际上都会隐蔽地存有贯通点。此外,在精神意象之间,在生活实体通向精神意象之间,同样有贯通点的存在。可是,当这个贯通点尚未显现或尚未相贯的时候,它就只能是个暗而未明、贯而未通的‘锁结’。一部长篇小说蕴含的这些‘锁结’越丰富,遍布越广,存在越经久,在欣赏者心灵上激起的解结情绪就越强烈。当人们阅读长篇小说时,随着那些‘锁结’的逐一贯通,可以获得对世间人情的不仅是一次性的而是接连性的感悟,对世间事理的不仅是单层面的而是多层面的释通,这自然会感到比阅读中、短篇小说获得更大的满足,长篇小说的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获得的。”应该说,“锁结”概念切中长篇小说文体的关键,值得继续发扬光大。此外,陈美兰还破除了人们对长篇小说的史诗性的迷信,“今天的长篇小说既可以像《地球的红飘带》《皖南事变》那样,实实在在地谱写伟大的历史事件,以此为基础重建令过来人和后来者都感到震惊的独特经验世界,也可像《活动变人形》《洗澡》那样,全力楔进生活的某个狭缝,窥探某种心态,着意于强化摧人心魄的精神氛围和强烈的情绪化世界。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方面显示了自身的美的价值。”针对当时有些长篇小说疏忽于情节的建构,陈美兰指出:“建立基本的情节,是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素质。一部长篇缺乏情节骨架的支撑,所有的生活场面、所有的心态、世态都会失去依附而难以构成完整的宏篇。”至于悬念问题,陈美兰也认为不能一味地排除悬念,否则读者阅读长篇小说的兴趣必然会大减。
正是基于对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意识,陈美兰才特别关注现代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并概括出以巴金的《家》为代表的“伞网式”的结构方式、以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枝桠式”的结构方式和以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为代表的“漫反射”的结构方式;还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折射生活的艺术途径概括为三种:以家庭为纽带的折射方式,以人物命运为线索的折射方式和以事件为轴心的折射方式。在对姚雪垠的《李自成》进行研究时,陈美兰还提出长篇小说美学问题:追求整体开阔美,追求艺术色泽的丰富美,追求形式建构的均衡美。陈美兰认为姚雪垠的这种追求尽管还保留某些传统艺术思维的惯性,但主要方面已经触及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趋势,对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确立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些概括都是她在丰富的长篇小说阅读经验中做出来的,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普适性。
除了难能可贵的职业追求之外,陈美兰小说批评的伦理操守也值得关注。对于像《创业史》《红旗谱》《艳阳天》等红极一时的经典性长篇小说,她敢于指出其中的艺术症结,绝无为尊者讳的矫饰;对于当时的当红小说家,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铁凝、莫言、余华等,她照样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长篇小说存在的思想艺术问题,绝没有丁点趋势而为的聒噪和吹捧;即使对于湖北本省的知名作家,如鄢国培、方方、刘醒龙、邓一光、熊召政等,她的小说批评文章也是热情而又冷静地分析他们创作的特点和局限,有一说一,不护私也不夸耀。陈美兰的小说批评文章和研究论著绝不是依附于作家作品的应时而为的宣传品,而是具有学者个人独立品格的精神产品,也是个人创造性的结晶体。在《珍惜作家精神劳动的成功——答〈文艺报〉记者问》一文,陈美兰曾说:“文学批评不是从属于文学创作而存在的,更不是依附着作家而存在的,它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曾经有一位台湾诗人好心劝导我:‘你应该多写些著名作家的评论,这样你也出名了。’我听了淡然一笑,他对文学批评理解得太肤浅了。他不知道文学批评是推进文学发展的有骨有肉的‘一翼’,而不是纸糊的点缀性的‘一翼’。一个文艺批评家他也有对人类、对世界、对生活独立的观察力、理解力,具有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洞察力,由此而生长出他作为生命主体的一套思想理念,他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正是他这种能力和理念对象化的结果。”的确,正是出于对文学批评的这种独立理解,陈美兰在小说批评中才呈现出独立不羁的批判精神。她还曾说:“对于单部作品的评论,我也尽量坚守学理性的原则,不因与作家关系的亲疏或作家成就的高低而放弃应有的评论品格。”这就是陈美兰小说批评的伦理操守,对于当今文学批评底线屡屡失守的悲哀现实,简直是一针见血的犀利针砭。
当然,对于那些文坛名家、大家名作,陈美兰体现出小说批评家更为严肃的一面;但是对于那些刚出道的、尚处于发展中的小说家,她就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呵护。她曾说:“在文艺评论的操作过程中,也还有一个从评论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问题。我常遇到这样的场合,在讨论一些刚涉足文坛、或一些来自基层的业余作者的创作时,我们有些专业的批评家常会拿出‘专业’的口吻,以高蹈的标准来证明这些作品的不足,这种姿态我以为是不妥的。一个批评家,应该能体会到作者发现他的优势和潜力,再从他的基础出发提出一些切合实际并可能达到的要求,这样的批评也许会更见效。对一些刚从事文学创作经验不足的青年作者,我们的批评更应该采取认真细致的态度。正在成长中的作家,是最容易受批评舆论所左右的,所以批评家的发言要更加慎重。”笔者认为,陈美兰的这种批评态度恰恰遵奉了老子所说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的天之道,而当今文学批评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肆赞美著名作家,对那些需要批评鼓励的年轻作家、新进作家则或不闻不问,或横加棒喝。陈美兰对湖南作家向本贵的《凤凰台》、湖北基层作家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的批评就是典型例证,她没有把小说批评视为砍伐的刀子,而是认真细致地发掘其潜在的思想艺术价值,指出其可能的完成之路。2002年,陈美兰还针对当时一批文学批评家对一些湖北本地作家的苛刻评价说:“就目前对湖北作家创作的研究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更应该持一种理解的宽容,这倒不是说不应该苛求,我说的理解和宽容主要是指理解和允许作家保留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不要用一个单一的尺度去左右他们各自的创作追求。……我们搞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人对于创立文学多元化格局的意义,曾经谈过千条百条道理,那么,我们在进行创作批评时是否需要注意保持一种允许多元存在的气度和心态呢?”好一个“理解的宽容”,这就是陈美兰小说批评值得尊敬的伦理境界!
三、历史理性、启蒙情怀和乐观主义
如前所述,陈美兰这一代人受过较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很容易形成一种较为宏阔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但是更为鲜明的乃是他们的历史理性立场。这种历史理性,相信历史是客观的,是有规律的,是进步的,相信历史发展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即使是暂时遭遇什么挫折,终究会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重新找到正道,找到出路。一旦建立起了这种历史理性观,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往往较为独到。例如在评价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时,陈美兰针对该小说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暴力化的过度演绎,就如此评说道:“二十世纪无疑是一个战争恐怖的世纪,暴力横行的世纪,但不能忽略,中国的二十世纪也是人民大众反抗反动暴力,抵制野蛮侵略,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世纪;也是人的理性逐渐觉醒、从挫折走向成熟的世纪。”也许像刘醒龙这样的作家感性意识较为发达,想象力丰富,对历史中的血腥暴力极为敏感,会强化人性的丑恶和历史的诡谲,但是陈美兰在评述该小说时,却站在历史理性的立场上,把暴力、野蛮等历史负面因素组织进了宏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下子超越了作家的感性直观,展示出了历史理性的乐观主义面貌。
可以说,正是历史理性立场的确立,使得陈美兰对许多当代长篇小说的判断发人深省。例如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中,她认为张炜的《古船》对赵氏农民家族的彻底否定和对隋氏家族的着力冀望中,表现了一种偏颇的历史识见,这种判断自然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性立场有关。她在谈到《古船》对历史动因的迷惘时,曾引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的话,肯定历史的进步,“一百多年前这位德国的哲学大师就能领悟到历史进步的辩证法,看到历史正是通过无数的矛盾、无数的正义同非正义的冲突,由较高阶段代替较低阶段,由较高文明代替较低文明的过程。而如今我国一些当代小说家为所经历的灾难的情感所裹挟,却无法用冷静的眼光去对历史前进的动因作出客观的判断,这在创作上不能不是重大的遗憾。”这就是典型的历史理性立场。对于像张炜、莫言、陈忠实、刘醒龙、王安忆、刘震云、余华这样的作家而言,历史理性是无法接受的立场,历史理性毫无疑问地会造成对个体命运的遮蔽,他们也很难接受历史是进步的理性观念,但是对于像陈美兰这样的学者而言,历史理性却是基本的立论立场,离开了历史理性,许多学术判断就无法生成。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之间的精神张力于焉滋生,彼此互相矫正。
启蒙理性是陈美兰文学史研究和小说批评的另一基本立场。陈美兰也是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学者,她对鲁迅等“五四”精神发扬者始终都秉承着崇敬之情。她憧憬现代文明,视现代意识为一种价值导向,她曾说:“现代意识,不是一个空洞、时髦的字眼,它是社会发展最新阶段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最高自觉,是当今社会的主人站在历史阶梯的最高层次上,对社会历史发展、政治经济模式、各种人际关系、精神道德伦理等等所获得的最新认识,形成的最新观念。”应该说,她对现代意识的正面表述就是启蒙理性的典型立场。启蒙理性在她的学术研究之路还会沉淀为一种价值关怀意识,一种朴素的人文情怀。她曾说:“价值是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的最高依据。与人类精神直接联系的文学,没有了价值基石,就等于是失去了血脉的生命躯壳。”的确,陈美兰在文学史研究和长篇小说批评中是非常关注其中的价值问题的,她在对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主体的精神转换和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精神探索的相对落后的深入分析中,也是在探讨中国作家价值重建的艰难历程。
历史理性和启蒙理性之间虽然共享着一些价值基设,例如都相信历史进步观,都是乐观主义的,都相信人的理性力量,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历史理性很容易导向一种集体主义而启蒙理性倾向于个人主义,历史理性倾向于一元化而启蒙理性倾向于多元化,历史理性强调历史目的论而启蒙理性偏重于人本主义价值观。这种差异往往难以调和,有些时候甚至形成冲突。那么对于陈美兰而言,她更倾向于以历史理性来统领启蒙理性。例如她的论文《“文学新时期”的意味》中,历史理性和启蒙理性的博弈是以历史理性的获胜为终结的。陈美兰说道:“一些作品所持的价值准则,如摒弃了崇高感、强化人的生命欲求的现代人道主义,如视世界为荒诞存在、视人的本质的自由选择,等等。诚然,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成果,但今天如果我们据此而摒弃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的价值标尺,那恐怕不能说是‘新进’而是文学思想根基的‘虚脱’。”虽然谈的是价值问题,陈美兰明显偏向于历史理性的集体本位立场和历史目的论。她的论文《创作主体的精神性转换》也是历史理性和启蒙理性的对舞,无论是对个体独立意识的首肯,还是对文化守成的剖析,抑或是对后现代的批判,最终都是回归到对人类社会未来的信心,对全方位现代化的期望。启蒙理性孕育出的个体化写作,在陈美兰的判断中最终也价值有限,必须向历史理性所中意的价值转向,“个体化写作,并不像有人所阐释的‘不必关注公共利益,每个人只关注自己’,仅具有‘私人性、自闭性、非功利性、自我娱乐性’就行了,恰恰相反,个体化写作更要求作家具有独立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与时代沟通的能力,具有独立熔铸人类历史经验、吸纳人类文化精神积累的能力,具有独立冲向时代潮头、对新的生活现象作出科学审察和特有感悟的能力。”这样的立论无疑是中肯的。
整体看来,陈美兰的文学史研究和长篇小说批评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是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的。她确立了较为鲜明的历史理性和启蒙理性立场,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在文学史研究中弘扬历史意识和学理性,在长篇小说批评中具有难能可贵的职业追求和伦理操守。对于后学而言,陈美兰的学术理路和学术品格至今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注释:
[1][3][5][10][11][13][15][16][17][18]陈美兰:《陈美兰文集》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37页,273页,277页,273页,532页,425页,400页,325页,322页,413页。
[2][4][6][7][8][14]陈美兰:《陈美兰文集》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页,15页,43页,42页,45页,139页。
[9][12]陈美兰:《陈美兰文集》第3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17页,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