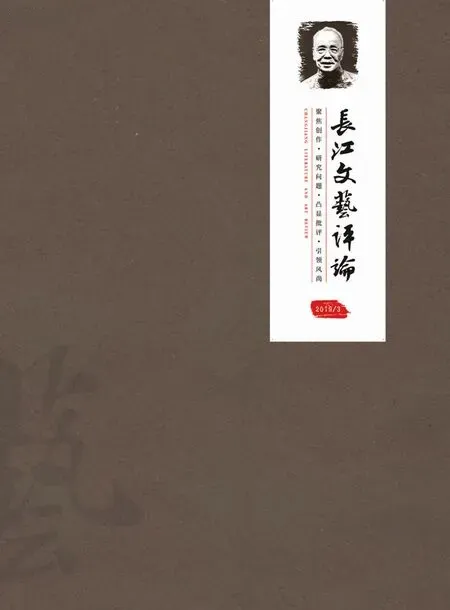生命的“终极悖论”
——张翎近期小说的哲学解读
◆倪学礼 张 琪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阐明,在‘终极悖论’的前提下,所有的存在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世界在根本层面是一个充满意义又无限荒谬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终极悖论”。伟大的小说家应以小说特有的方式揭示出在意义与荒谬间浮沉的人之存在的不同状态,这是有关人生永恒命题的体悟,也是对存在之根本意义的思考。张翎作为北美华文文学的扛鼎作家,不论是《雁过藻溪》中的人性扭曲与世事悲凉,还是《余震》中的满目疮痍与心灵救赎,抑或是《金山》中的沧桑历史与款款温情,都给人印象深刻,她的小说有着超越“地域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广阔的叙事视角和丰厚的思想深度。张翎近期的中篇小说《死着》、长篇小说《流年物语》《劳燕》更是以独特的文学形象和叙述视角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生命“终极悖论”的深刻思考。
一、真实还是虚假
真实与虚假是一组永恒纠缠的“悖论式”命题。从个体的人降世之日起,便在其纠缠之中浮浮沉沉。就漫长的人类史而言,不论是西方所追寻的向外进取的“真实”,还是中国所要求的反身内求的“真诚”,都是对“真”的一种探索。对“真”的探寻似乎是人之本能。
张翎的中篇小说《死着》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眼见之实”的不可靠性,塑造了“茶妹”这一别具意味的盲人形象。故事围绕主人公路思铨的死展开,并分别从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王中队长、主治医生刘主任以及路思铨公司副总廖总的视角层层剥离展开,最终呈现出整个死亡事件的全貌。
盲人茶妹则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谜题的唯一知情人。“茶妹”既是从小生在农村、从未进过城的现代社会的“他者”;又是患有失明、与纷繁虚假的“视觉世界”永久隔离的“他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未见识过城市世界之真实面貌、甚至不被城市人当作“人”,而是当作一种消费产品、赚钱工具来看待的形象,却是整部小说中离真相最近的存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具有深刻的隐喻意味:茶妹就好像是独立于当下社会之外的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面真实的镜子,无情地揭示了视觉世界漂浮着的虚假。因为失明,所以茶妹的听觉与嗅觉系统异常发达,她通过声音和气味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并能敏锐地分辨出许多依靠视觉官能无法分辨的细节。或者说,上帝在为她关上一扇世俗世界的感官之门的同时,为她开启了一扇通往真实世界的心灵之窗。
茶妹就在嗅觉世界中闻出了掩藏在视觉世界之下的种种真相:她闻出了王队长的疲于奔命,闻出了廖总的焦虑与怨念,闻出了刘主任在坚守医德与医院施加给他的压力之间、在心灵世界与功利世界之间的挣扎与彷徨,闻出了路太太泪水中的复杂成分——对丈夫离去的不舍、对路思铨手机中那个神秘的Q的嫉恨以及对出现在车祸现场的那个古驰手袋的怨念……茶妹闻出了路太太复杂情绪的来源,并且深知路思铨的死已无法挽回,而对于还要活下去的路太太来说,事实的真相也许并不重要了,与其让自己带着恨的决绝麻木地苟活,不如保留住丈夫路思铨在路太太心底的温情与回忆。于是茶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一瞬间,那堵横在路太太与路思铨之间的墙轰然倒塌,路太太几天来积攒的情绪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这对于生者和死者来说或许都是一种解脱。
茶妹不但能闻得出每一个现世之人的虚假,甚至还闻到了主人公路思铨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让我走吧”。那是一生干净整洁的路思铨对自己行将就木时肉体的腐烂及其所散发出的气味之嫌恶,在公司、医院、交警大队三方各自心怀鬼胎的博弈中,路思铨是他们手中用来维持自身利益的工具,显然无法决定自己的死期。茶妹听到了路思铨灵魂深处对肉体死亡的渴望,最终帮助路思铨结束了他的生命。
可以说,茶妹是整篇小说在真实与虚假之间沉浮的人中唯一一位清醒者,她是当下社会种种牢不可破的规则的一剂解毒剂,她成全了生者的灵魂,揭示了“有序世界”的崩塌。或许世界的本质就是失明的茶妹眼中的那一片黑暗、那一抹混沌。而真实与虚假正是交织在其中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混沌体。
长篇小说《流年物语》也是一部在假象与真相之间寻找出口的作品。作者采用物的全知视角作为叙事手法,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开辟了一片可以自由游走的广阔空间;同时这一叙述方式也是作者在假象与真相模糊的交界处(如果有的话)为自己撑开的小小出口。如果说真实与虚假本就是一个没有边界、融为一体的圆圈,那么人将注定永远在这个牢固的圈套中沉浮,而能跳出此窠臼一窥究竟的,大概除了上帝,就是“物”吧。唯有以“物”这种没有主观情感之远近亲疏的视角,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于是,作者大胆地赋予了“物”以上帝的视角和人类的情感,从而将被生活的迷雾包裹着的个体的情感谜团层层剥开。
小说中全家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其不同物象的选取也贴合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及不同的命运走向,具有深刻的象征隐喻意味。与全崇武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那块为了伟大的航海事业而生、却终生未曾见过大海的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作为首长送给全崇武的礼物,这块手表承载着首长对全崇武即将开启的崭新生活的鼓励和忠告——“命犯桃花,别在女人身上栽跟头”。然而,正如那块手表自身的荒诞悲剧式命运一样,全崇武在女人身上栽的第一个跟头,也是让他一生永远无法在心里真正站起来的跟头,正是因这块手表而起:由于精密仪器专业的学历背景,叶知秋在被下放到全崇武所在工厂的当天,一眼就认出了这块手表,也正是在这块手表被扔进水盆里的一刹那,全崇武爱上了叶知秋,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个体的情感命运就这样牵系到了一起。
与叶知秋相比,朱静芬是一个吃苦耐劳、老实本分,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性格特征的女人,她是首长介绍给全崇武的、适合娶回家做老婆的“好料子”。当全崇武与叶知秋的婚外恋情暴露时,朱静芬以极为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强大的包容心解救了自己的丈夫。作者在此处选取了一只在除“四害”中幸运地被朱静芬解救的麻雀的视角完成故事的叙述。在屠格涅夫的笔下,麻雀是一个敢于同猎狗斗争、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子女的伟大的“母亲形象”。而朱静芬恰恰有着如麻雀一般的人格形象——平庸凡俗、无法高飞,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家人。
叶知秋就像那块心怀大海却不幸落入凡尘的沛纳海名表,从她爱上全崇武那一刻起,她就做好了与他共赴刀山火海的准备。然而在爱情面前,全崇武无疑是个懦夫,他终于没能抵住流言的压力,躲进了婚姻的保护伞下。叶知秋的骨子里毕竟流淌着高贵的血液,一个人有再大的勇气也承担不了爱人的自私和背叛,她选择用自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这个女人也终于成为全崇武心中那块秘密之地上的一道永远无法消褪的血痂。
老鼠和苍鹰是刘年性格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面对恩人的女儿全力,刘年是一穷二白谦恭卑微的穷小子;面对情人尚招娣,刘年又是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的施恩者。因此,在妻子面前如老鼠般自卑压抑的刘年,在情人面前却能展现出苍鹰般的自信和勇猛。如同全力的秘密一样,情人尚招娣、儿子刘欧仁、童年时期的偶像和精神支柱——《国际歌》的作词者欧仁·鲍狄埃、法国、药瓶……都是横在他与妻子全力之间的秘密。
与其在清醒中痛苦,何不在无知中快活?无知是一张最好的保鲜膜,无知把真相裹住了,真相的毒汁就无法渗入到神经。没有人真正需要真相,除了上帝。
真相无疑是残忍的,它似一阵粗砺的风,裹挟着人类感知的毛孔;也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割着我们情感的神经。因而小说中直面真相的人都是痛苦的:全知一出生,名字中就裹藏着父亲的秘密——叶知秋,也许是名字的寓意、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她眉心中间多了一只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天眼。这双眼睛非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便利,反倒让她终生不得安宁,最终走上了精神分裂的道路,并带着自己十六岁的爱情秘密神秘地消失了。
全力与刘年的女儿刘思源也是一个在真相的海洋中孤独挣扎的逆流者。她过早地窥破了父母之间的幽秘怨恨。真相带给她的不是平静与释然,而是孤僻的性情和乖张的叛逆。真相没有让她在生活面前变得理智与清醒,反而永远地给她加上了一层偏光镜——她或许永远无法消除对父母的怨恨与芥蒂、永远不会毫无保留地爱与生活。
小说用河流这一物象统摄了全篇:生活就像是一条滚滚向前、奔腾不息的大河,无论个体的是非荣辱、生死祸福曾在时代的洪流中激起多么绚烂夺目的浪花,都会像那个象征着忠诚、爱情与友情的“三位一体”的高贵的卡迪亚金钻戒一样坠入冰冷静默的河底,一切是非真假终将在生活的河流中归于平静、难寻其迹,而时间却依旧兀自向前……
二、活着还是死着
生死问题不但是永恒的哲学命题,也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死亡展现了肉身的腐朽性和可消灭性,让人意识到人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同时,死亡又是人类一切的根本起点:时间通过死亡让人感知到时间的存在,也通过死亡赋予人生以意义。没有死亡,人不过是没有差异的时间刻度,没有这一秒与下一秒的区别,没有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人们也就不需要为“下一阶段”的生活努力付出,因为每一个时间刻度的意义都是全然相等的。有了生死意识,每一个存活于现世的人才会在生与死的夹缝中寻找意义;而每一个寻找意义的个体又是整个人类“无限追求”链条上的一环。
《劳燕》是一部以三个已故亡灵的视角进行叙事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作者有意将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美国人和几个中国人抛在月湖那个狭小致密的时空环境中,让他们的命运相互牵连、自发地产生一系列情感的化学反应。于是,在战争的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和平年代无法看到的许多人性的真实面貌。小说着力展现了一个叫姚归燕的女人和三个不同男人之间的人生遭际和情感纠葛,也以“劳燕”暗示了其偶然式的命运邂逅和终将向着不同方向离去的命运走向。
主人公姚归燕在三个不同男人的世界中有不同的名字。第一个与她的人生产生关联的是自小和她青梅竹马、一起在四十一步村长大的哥哥刘兆虎。在刘兆虎的世界里,姚归燕的名字是“阿燕”。刘兆虎为了逃兵役,与阿燕签下一纸婚约。不久,阿燕就遭到了日军残忍的强暴……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女性的贞洁历来被视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在少女阿燕还不太懂得什么是“贞洁”的年纪,战争就无情地夺去了她的童贞。日本人的强暴无疑给阿燕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然而在牧师比利的救助下,阿燕并没有全然丧失生活的勇气和希望,真正在精神上击垮她的是回乡后乡邻们的集体唾弃和癞痢头的第二次强暴。日军的强暴更大程度上是一次肉体的侵犯活动,如果阿燕的乡亲们能像牧师比利一样怀有善意的同情并给予她更多精神上的安慰,阿燕会更快地从羞耻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战争的阴霾的笼罩下,每个脆弱的个体生命都有可能成为苦难的受害者。面对日军惨绝人寰的卑劣行径,无知的人们不懂得反思,甚至也不会抱团取暖,人性在战争面前堕落成一种“弱肉强食”的生物性存在:阿燕成为乡民们可以肆意作恶、妄加践踏的合理化理由——反正她已经脏了。就连曾经受到过阿燕极大帮助、自小与阿燕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且接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刘兆虎也无法摆脱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与愚昧的乡民们无异,刘兆虎在心理上认定了阿燕无可挽回的肮脏,他的胆小怯懦、犹豫逃避将他潜意识里的卑龊想法暴露得一览无余——他不但再也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这样的阿燕,甚至极力躲避阿燕可能给他带来的一切拖累与牵连。在流言的压力、所谓的“面子”面前,曾经的个人情感、共同的家仇国恨脆弱得犹如空气中的一粒灰尘,风一吹便踪迹全无。
牧师比利是整部小说中思想内涵丰富的一个人物,也体现了张翎的思考深度和对作品的架构能力。中国文化一直缺少西方的忏悔意识和拯救意识。西方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的基础是人的原罪意识,即人人生而有罪。中国人不是把自己的罪过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看作与自己的意志和“本心”相违背的结果,并认为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本心去行动,必然就会有德性。这种带有自欺性质的忏悔其实是在推卸人的自由意志对自身行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人历来缺少直面人之卑劣天性的勇气以及触及本心的反思意识。作为有着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海外华人作家,张翎深知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以及民族精神的缺陷,故而引入具有基督教传教士背景的牧师比利来帮助阿燕完成自我拯救。
“斯塔拉(Stella)”是牧师比利为姚归燕取的名字,在英文里是“星星”的意思。“星星”这一意象象征着光明与希望。本质上,死亡带给人的恐惧是一种终将被世界离弃的恐惧。对于斯塔拉来说,战争虽然没有剥夺她的生命,但却让她经历了比肉体死亡更加残酷的精神死亡:日本兵的残忍施暴在她的生理上造成了一种被离弃感;乡民们的恶意侮辱与排挤在不断刺戳着日本人留下的伤口的同时,又给她造成了心理上的被离弃感,这种比肉体上的凌辱更加寒冷逼仄的精神离弃最终将她推入绝望的深渊。她处在生与死之间的真空地带——比苟生更孤绝,比惨死更荒秽!
牧师比利一路见证了斯塔拉悲苦的人生遭遇。他以一名医者的职业精神为她医治身体上的伤口;同时也以一种超越了种族、文化、性别的基督教情怀教她习医治病的生存能力,让她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拯救自己。比利在斯塔拉坠入恶与绝望的谷底时用他人性中的善在斯塔拉心中种下了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当一次偶然的意外,中国学员鼻涕虫因为受到其他学员的侮辱与调侃而自尊心受挫,在河边对斯塔拉心生歹念、无礼欺辱时,斯塔拉没有选择沉默与逃避,而是毅然决然地站起来与人性中的邪恶力量做斗争,她亲手把自己的伤疤撕开给众人看,这无疑是异质文化给予她的力量。在与人性中的至恶面以及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屈辱的对视过程中,斯塔拉学会了自尊,自尊又给了她站起来的力量和活下去的勇气。牧师比利无疑是斯塔拉在生活的分岔口迷失时照亮她前进道路、给予她希望之光的那颗“星星”;而在斯塔拉身上,牧师比利看到了生命的韧性与灵魂的高贵,最终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上帝赐予他的这颗独一无二的“星星”。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比利与斯塔拉就是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两颗相互拯救、彼此照亮的“星星”。
在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一等军械师伊恩·弗格森的世界中,姚归燕的名字叫“温德(W ind)”,英文“风”之意。风是与时间同行的物体,它无时无刻不在奔跑,一旦停止奔跑,“风”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因而“风”是当下与自由的象征。与伊恩相比,牧师比利给予温德的爱是永远关乎“过去”与“将来”的,他更像一位智慧的长者,不断帮助温德从过去的痛苦中走出,又不断为她扫除未来道路上的阴霾。而伊恩的爱则是时时刻刻关乎当下的,在伊恩面前,温德没有不堪回首的过往,也没有艰辛沉重的未来,只有如风一般轻盈和自由的当下。
姚归燕的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与刘兆虎的感情始于少年的懵懂,终于中年的陪伴;与牧师比利的感情是一种推心置腹的托付与信任;而与伊恩的感情是真真切切的爱情与自由。在刘兆虎的离弃与背叛中,阿燕坠入生活的谷底;在比利的关爱与呵护下,斯塔拉重拾了光芒与希望;唯有在与伊恩的爱情中,温德最终完成了自我拯救,获得了灵魂的自由。
基督教的最高德行是爱,是对一切的普遍的爱——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爱那些恨我们的人。爱是温德得救的原因,也是温德得救的结果。温德最终在与伊恩的个体的爱情中,获得了爱世界的能力。即使在战争结束后,面对三个男人的同时离弃,温德依然拥有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这份力量来自她心灵深处的爱。她终于在战争带来的这场劫难中完成了自我拯救,她的灵魂是独立自由、不需要依附的。她独自生下与伊恩的女儿阿美,抚养她长大,又以圣母般的博爱情怀宽恕了曾经背弃和伤害过她的人。并在四十一步村开了一家小诊所,用自己的力量拯救和关爱更多的生命。
斯塔拉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真正皈依基督,可是我总觉得她离上帝比我更近。她有一双天眼,总能跳过一切文字和概念制造的阻隔,直接进入信仰的核心。
面对生活、面对上帝,她不屈服、也不亵渎;不邀宠、也不谄媚,而是以理性的光芒和至善的力量来守护人性的尊严和心灵的自由,因而她比那些形式上的皈依者更接近上帝、接近信仰。
战争把人性撕扯成碎片:有的人心如死灰,有的人形容枯槁,有的人堕落成禽兽,有的人麻木如荒草……而姚归燕则真真正正活成了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大写的人”——即使肉身被百般凌辱,但她的精神没有被击垮,她通过理性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中那“至善”的一面,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结语
文学归根到底是对人之生存境遇的关切。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而言,人既在“世界”中存在,也在“大地”上存在。“世界”意指具有某种意义规定的有序的“生活世界”;大地本质上是自行锁闭者,是不可道说、混沌暧昧的“原初世界”。人生在世就是在这种澄明的意义世界与永恒遮蔽的大地间浮浮沉沉。张翎敏锐地意识到世间所谓“真理”的自相矛盾以及生命中那些永恒纠缠、不可解的“终极悖论”。从视觉世界纷繁交错的层层假象到“盲人茶妹”清澈通透的心灵深处,从现实社会诡秘莫测的人情世故到物语空间中一览无余的事实真相,从生死存亡之外的苍凉底色再到生死夹缝之中的人性光芒……张翎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对历史命运的整体把握还是对细微人性的深刻洞察,都俨然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母题而上升到普遍人性的思想高度,并不断在“世界”与“大地”间探寻人生在世的根本意义。
注释:
[1]【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2]张翎:《流年物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3]邓晓芒:《灵之舞》,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4]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页。
[5]【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