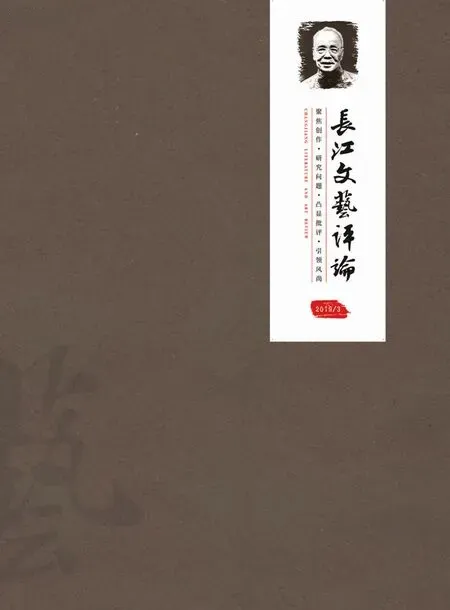先锋文学的回顾与猜想
◆东 西
“先锋文学”在我这里是一个成长的概念。但它在中国文坛却是专指,专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批具有先锋姿态的文学作品。我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先锋文学在中国如日中天。我注意它,主要是注意它的姿态,也就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方法。那些眼花缭乱的写作方法,对一直接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训练的我来说,确实具有吸引力,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只在乎方法而不重视内容,甚至某些作品的写作动机,仅仅就是因为想到了一个方法,至于主题、人物塑造、对话的生动等等都暂时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在文学品种单一的事实面前,年轻人极其渴望新的写作方法,渴望打破一些写作规矩。非常奇怪,我们这一代怎么会自带“文体意识”?想想,和当时的“改革开放”大环境不无关系。
我不知道马原、余华、苏童和格非等等作家的先锋小说写作,是偶然或是必然?是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小说文体意识,抑或是社会变革的带动?这需要他们来细心确认。但是,我知道在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的时候,即便像我这样的初学写作者也面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型。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先锋文学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的合力,而不仅仅是作家文体意识的觉醒。当然,我们今天总结先锋文学,基本上就是在总结它的“文体意识的觉醒”。但我们在总结“文体意识的觉醒”时,是不是忽略了这种“觉醒”也许是因为内容的“倒逼”?仿佛,当下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写作选择。30年前,先锋作家们成功地从“写什么”逃离到“怎么写”,并用“怎么写”来证明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多么渴望写作的创新,多么需要对单一的写作方法进行恶补。我们在欢呼“怎么写”的时候,原谅了对“写什么”的逃避。这一问题,大部分先锋作家很快就意识到了,并进行了写作调整。
“先锋文学”更多地是指向技术,甚至就是一个技术术语。但是,当中国的作家们把外国的各种文学流派都演练过一遍后,才发觉内容的重要,至少我在使用先锋文学技巧的同时,从来不敢对内容有丝毫的怠慢。我相信作品内容永远是读者阅读时产生化学反应的第一要素。现在回头检视自己的作品,发现还是“内容为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先锋文学”带来的撞击,即创新理念的撞击,这种撞击让深受先锋文学影响的作家们留下了值得骄傲的“内伤”,即对平庸文学的反抗,对文学创新的本能追求。正是这一群体捍卫了文学的底线。如果没有先锋文学对技术的唤醒,我不会逼出《没有语言的生活》的构思,也不会用那样一种方式创作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是先锋文学助长了我的想象,掩盖了我的幼稚,包庇了我的不讲逻辑。如果不是因为“先锋文学”这块“虎皮”,我是不敢在《耳光响亮》一开头就写牛翠柏倒着行走,也写不出“杨春光为牛红梅堕胎的胎儿召开追悼会”这样荒诞的情节。即便是今天,我也仍然在大胆地享受先锋文学的遗产,比如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我用呼噜声的消失来描写村庄的害怕。小说的最后,我写汪长尺的灵魂在全村人的呼喊声中飞起来,在村头的大枫树上停了停,然后恋恋不舍地飞向城市。余华在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不久,曾经跟我说这个小说貌似不先锋了,其实还是先锋的,比如许玉兰在生小孩子时喊疼,但她喊着喊着,时间就跨越了好多年。余华用作品中人物的喊声来过渡时间,这当然是先锋文学的伎俩。先锋文学不是停滞的,它被有心的作家隐蔽地带入后来貌似传统写法的作品里,直到现在还在作家们的手里变异。这是一种先进技术,会使用者悄悄受益。当然这些技术不再为技术服务,而是服务于内容。只有服务于内容,技术才获得存在感。只有在内容里酝酿出先进思想的作品,才会被人们继续称之为先锋文学。而那些只有技巧没有思想创新的作家,渐渐地变成了传统作家,或者格式化作家。大多数读者对那些内容苍白的纯技术作品越来越不“感冒”。
先锋文学的成长既指向未来也指向过去。未来,那就是作家们的崭新思考以及对写作技巧的不断拓展。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先锋文学,那些思想冲在前面、技术不断升级的作品都应该是先锋文学。至于指向过去,那是因为阅读顺序造成的。许多读者或者作家是因为读了中国先锋小说家的作品之后,才去阅读他们西方导师们的作品。随着阅读的扩宽,你会发现先锋作品越来越多,先锋作家队伍越来越壮大,就连托尔斯泰也堪称先锋作家。千万别把他当成过时的老头,只要重读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你就会改变看法。一百四十多年前,他竟然写得那么好,真不知道是他太厉害或是我们没进步?当看到《安娜·卡列尼娜》第七部第29、30节时,托翁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心理描写彻底把我征服,那简直就是心理描写最绚烂的篇章。今天的作家们如果写不出这样的篇章,就必须承认托尔斯泰才是真正的先锋。
因此,先锋文学不仅往前冲,还要朝后看。在创作技巧开发几乎罄尽之时,先锋文学得以继续的惟一办法,就是致力于内容的深度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