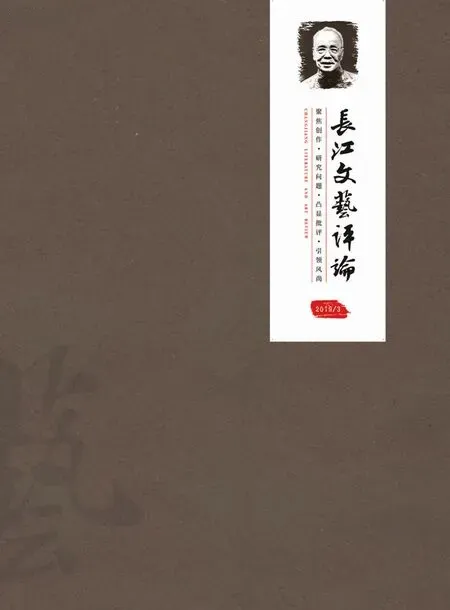闲中着色,无事生非
——浅议游移叙述的形式价值
◆叶立文
1984年,随着马原的短篇小说《拉萨河女神》的发表,一个形式试验的潘多拉魔盒也就此打开:那些致力于文学革新的先锋作家,无不跃跃欲试,凭借着意识流、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等各种理论武器,一再涤荡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成规。然而,如此“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形式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却仍可存疑。因为若是以上述诸家后来写成的文学批评为据,当可发现马原、余华和格非等人,其实都在反思早年的形式试验中,注意到了以人情小说为主的文学传统。虽然不能说他们的创作就已经回到了这一传统内,但余华的《兄弟》、马原的《黄棠一家》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作,确也有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传统韵味。
那么,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缘何经历了这样一场历史的轮回?如果回归传统方为创作正途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此前形式试验的失败?实际上,当下先锋小说的新变,与其说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和国学热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倒毋宁说是其内部叙事话语自我演进的结果。为阐明这一问题,兹以先锋小说的游移叙述为例,来勘察一番先锋话语的嬗变历程。
一
一般而言,一部小说的叙述话语往往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紧贴情节本事的主线叙述,其二是围绕情节本事所衍生出来的描写和议论等支线叙述,其三则是分离于情节本事之外,以离题为表征的游移叙述。在这当中,主线叙述掌控全局,支线叙述丰富细节,两者经纬交织,共同推进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相较之下,游移叙述则是小说的离心力,它离题万里,冲破了小说固有的叙述网络,或可谓之“闲笔”也。从叙述功能上来说,游移叙述既能闲中着色,也可无事生非。所谓“闲中着色”,意指游移叙述与情节本事分离后,虽然暂时中止了叙述的进度,但它却能以优裕从容的闲笔之法,为作品平添几分韵味精神。由此可见,闲中着色的游移叙述,乃是承载作家美学意图的工具,它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实属寻常。至于“无事生非”,则多见于先锋小说,意指游移叙述在偏离情节本事后,通过制造一些无关宏旨的情节及意义,为小说的情节走向横生枝节。它们和情节本事无甚关联,也用不着完善统一,但无事生非处,却陡然让游移叙述和主线叙述之间,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叙述张力。而这一叙述张力对文本中心的反抗,不仅会为作品带来一种自相矛盾与支离破碎的现代性审美意蕴,而且还能在表达先锋作家颠覆历史理性的启蒙诉求的同时,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有趣的是,游移叙述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其实是先锋小说所有形式试验的元叙述话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起点,即为了打破现实主义文学合目的性的历史理性主义,它不相信外在于人自身的历史规律,以为物理性的时空观、因果律的情节观,都体现了历史理性对人物的压制与异化。因此为了颠覆历史理性、救赎异化之在,先锋作家就热衷于以形式试验的方式去表达这种启蒙诉求。从这个角度看,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从来都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形式主义,而是一种以形式试验为手段,在历史批判中抒发家国情怀与存在之思的启蒙文学。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为什么会以游移叙述为元叙述话语。这是因为游移叙述偏离情节本事的基本特质,最能实现先锋作家的创作意图。
比如意识流手法。严格来说,意识流本身就是一种游移叙述,因为它无中心无逻辑,自由散漫、随机而动。像残雪和莫言就十分擅长于这一叙述方法。在《山上的小屋》中,残雪对主人公受迫害妄想症的叙述,经常会被一些意识流叙述所打断。而《红高粱》里当莫言在讲述伏击场景时,“我父亲”的意识流动,也经常溢出了抗战故事的宏大主题。换言之,意识流承担起了无事生非的叙述功能,它打破的不仅是伦理悲剧和战争故事的叙述进程,而且更是以含混暧昧的意识流动,拆解了情节本事的自足与有序。在残雪和莫言笔下,因袭了传统伦理及家国大义的芸芸众生,其实都是因为游移叙述的存在,方才更多地体现出了人性的诡谲,由是也就有助于作家深入描写人物的异化,继而为他们的启蒙救赎奠定逻辑基础。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先锋作家乐于在形式试验中拆解因果律。这是因为历史理性主义的权力意志,尤其反映在因果律的森然秩序中。有鉴于此,像余华这样的先锋作家便习惯以游移叙述为主导,去讲述一些有因无果或是有果无因的故事。比如《四月三日事件》这部作品,余华通过讲述少年的日常生活,极力延宕了“四月三日”阴谋事件的发生。而这种偏离了情节主线的游移叙述,也让事件本身因叙述逻辑的中断而无枝可依。及至作品结尾处“四月三日”仍未到来的时候,事件也就变成了一个妄想的阴谋。如此有因无果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深思,显然有赖于游移叙述对情节本事的不断分离与冲击。同样,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我”被人绑架的情节主线,也经常会受到“我”的遐想此类游移叙述的干扰,以至于绑架事件的起因被完全遮蔽。就此而言,余华的游移叙述在情节本事的“无事”处,凭空生出了一种叙述的话语力量,它对主线故事的反复离题,最终造成了这一有果无因的故事的成型。
上述几部作品,虽然游移叙述较为明显,但至少还存在着一个情节主线。相较之下,更为激进的形式试验也同样出自余华。比如《古典爱情》这部作品,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爱情故事,饥荒引起的人吃人惨剧,完全背离了小说的命名。而这种名实两乖的写作方式,其实就是把游移叙述的自由度发挥到了极致——余华以离题万里的游移叙述,最终呈现了历史的混乱与无序。因此《古典爱情》实则是一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作品,那些耸人听闻的人伦悲剧,完全得益于游移叙述的无事生非——余华不因题释义的游移笔法,不仅造就了这部小说的荒诞传奇,而且蕴藉其中的历史批判和存在之思,也体现了叙述本身的话语力量。
二
以上所述,皆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里游移叙述的叙述功能问题。而这一叙述话语的“无事生非”,颇能反映出彼时先锋作家的形式意识。对他们来说,写小说一定要有叙事的自觉,正所谓“一笔不肯苟且,一处不肯放松”。唯有排斥闲笔,时时关注叙述话语的功能指向,小说才会变成一门技艺。然而,这种技艺为王的文学观念,却在九十年代开始发生了变化。
按中国文学的传统,小说从来都不止于叙事,它还要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之外“熏浸刺提”:或以道德伦理教化众生,或以世情百态熏染人心。这就要求作者在叙事之外,更须将宇宙之大和苍蝇之微移入笔端——古典名著如《红楼梦》和《水浒传》,哪一个不是如此地海纳百川?有此文学传统在先,再加上九十年代文学语境的整体转向,早年致力于形式试验的先锋作家,也就逐步倾向于从传统小说里去汲取新的艺术经验了。譬如格非研习《金瓶梅》、毕飞宇细读《红楼梦》和《水浒传》等等,都属于比较典型的例证。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既然很多先锋作家开始从西方现代主义转向传统小说,那么他们最擅长使用的游移叙述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与早年相比,余华、格非和马原等先锋作家,都愈发丰富了游移叙述的使用。他们不仅会通过游移叙述去制造主题的多义性,而且也凭借这一叙述方法给小说增添了韵味与精神。换言之,此前所谓的闲中着色和无事生非这两大叙述功能开始出现了融合的迹象。这种融合,既反映了先锋小说向现实主义回归,继而开始重视小说美学的趋势,同时也体现了先锋作家在形式试验上的新变。比如游移叙述可不只是为小说增添了美学意蕴,而且还涉及了叙述的速度和节奏等更为专业的形式问题。更准确地说,虽然受传统小说美学思想的影响,这些作家都开始重视小说的韵味与精神问题,但骨子里的叙述自觉意识,却也让他们不断深化了游移叙述的叙述功能。如果说以前的无事生非,主要是为了制造游移于主线之外的情节和意义,继而通过分离主线叙述的恒定主题去制造小说多义性的话,那么后先锋时期的游移叙述,则在融合两大叙述功能的基础上,更多了几分和叙述民主有关的创作意图。在这方面,余华的长篇小说最为典型。
三
作为一部转型之作,《活着》显然增添了很多现实主义的文学元素。但这部作品对游移叙述的使用,却颇可见出余华如何在传统小说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左右逢源。按小说的游移叙述,主要指的是那些和主线叙述无甚关联的情节与意义,因此作品开篇处有关民间歌谣采风者“我”的叙述,就是一种典型的游移叙述。原因很简单,主人公徐福贵的故事,其实主要来自于人物的自述,而“我”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换句话说,若无“我”这一人物的存在,主线叙述也完全可以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我”的游移叙述就可有可无。那么,余华究竟是如何在这一部分的游移叙述里,闲中着色、无事生非地掀起了叙述波澜?
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民间歌谣的采风者,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是打着哈欠,“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这显然是一种自发的生命形态,因为从存在状态来看,“我”仅仅是“活着”而已。直至遇见了徐福贵,从倾听他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开始,“我”的生命意识才逐渐被唤醒。到了小说结尾“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之际,“我”已经焕然一新,重新认识到了生命的价值。从这一点来看,徐福贵的生命故事感动并且召唤了“我”,因此小说的主线叙述就与这一部分游移叙述,共同构成了一个讲述和倾听的叙事模式。
如果单从叙述功能来看,有关“我”的这一部分游移叙述同时具备了两大功能:其一自然是闲中着色。我们知道,徐福贵的生命故事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那些亲人的陆续离世,不仅令小说的主线叙述一直紧绷,而且也让读者近乎窒息。不过在这一切开始之前,余华尚有余裕闲中着色一番。那段有关阳光和知了的描写,显然是作家进行叙述冲刺之前的漫步。从审美效果来看,余华以前很少做这般叙述上的迂回,他通常是直入主题,以细密粘连的节奏描摹异化,用写实滞重的笔法勘察人性。如此闲中着色,自然会为小说平添几分牧歌情调。可别小看这一美学追求,它其实象征了余华的创作转型。这是因为当余华倾力于乡野闲情时,先锋小说常见的憎恨美学也开始悄然瓦解:之前出于对历史权力的反抗,先锋作家要么慷慨激昂,要么暴躁凌厉,总是以愤怒的主体情绪去面对历史权力。即便是以隐匿主观情感而著称的余华,其实也习惯于用暴力叙述去表达那份念兹在兹的启蒙诉求。而到了写作《活着》的时候,与生活达成了和解的余华,终于告别了那种现代性意义上的憎恨美学,开始注重起了对小说韵味的营造。这种东方美学,也悄然预示了先锋小说向人情小说传统的靠拢。就此而言,作品中与“我”有关的游移叙述,正是凭借着闲中着色的叙述功能,在为主线叙述做好铺垫的同时,营造了一份乡土叙事独有的闲情与野性。
其二是无事生非的叙述功能。与早期的形式试验相比,余华在《活着》里的游移叙述,明显弱化了对主线叙述的横生枝节。他讲述采风者“我”的故事,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试图开辟新的情节走向,而是涉及到了小说的叙述速度和节奏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追求一种叙述的民主。如何理解这一判断?我们注意到,小说中与“我”有关的游移叙述并不止一处,每当主线叙述推进到徐福贵的亲人之死后,“我”这个倾听者都会出现。按主线叙述的情节本事,虽然扣人心弦、高潮迭起,但至少在这一叙述进程中,作家的讲述逻辑自足、严丝合缝。若是余华心无旁骛,就此一直去讲述主线故事的话,那么整部小说的叙述便会持续推进。可是一旦“我”出现,那么主线叙述就会于“无事”处多了一些其它的叙述声音。这种无事生非,带来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小说叙述节奏的变化:此前风驰电掣的叙述速度会突然刹车,整体节奏也会骤然放缓。这种变化中断了人物的悲剧故事,不管是徐福贵还是读者,均可在惊魂未定之余得以稍加喘息,并由此将注意力从悲剧中暂时解救出来。因此可以说,游移叙述缓解了人物和读者内心的紧张,成为了一种足以表达作家叙事关怀的艺术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余华的这种游移叙述其实还是一种叙述的民主。因为在此之前,余华早就习惯了以心理描写的方式去勘察人物的精神世界,但叙述者怎能轻易洞察每个人物的内心呢?因此余华小说里的很多限制叙事,其实都是一种上帝式的全知叙事——此即为叙述的暴政。显而易见,这一叙述的暴政反映的正是先锋作家一种启蒙的霸权。他们看似悲天悯人,不断唏嘘感慨于国人的异化境地,但隐含其后的精英意识,却始终让先锋作家有些高高在上。直至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语境的世俗化,先锋作家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启蒙神话的幻灭。这种思想转变就体现在叙述的民主上。比如余华,当他在《活着》里建立起一个讲述与倾听的叙述结构,继而以叙述节奏的变化去缓释焦虑后,以往的启蒙说教也就此转化成了一种叙述的民主:读者再也用不着去聆听教诲,而是凭借着阅读的代入感,以己度人,深切感知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余华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描摹世相、熏染人心的叙述民主,而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也由此转向了传统的人情小说。
四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人情小说历史悠久:“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人情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一大转折,此前多依附历史,好言神魔,到《金瓶梅》却转向‘世情’,着重描写社会人生,人欲人性,至《红楼梦》达到长篇艺术的高峰,在‘话本’之后,自成一个文人独创的系统。”人情小说因要写世相人心,故其内容往往是包罗万象。在此前提下,情节本事的主线叙述和强化主题的支线叙述构成了小说主体,而除此之外大量的叙述空间,则由游移叙述来填充:举凡和情节主线无关的风土人情与世道民俗,以及宗法伦理等等,均在游移叙述的闲中着色里一一呈现。至于那些旁逸斜出的情节走向和野史秘闻,也大多由游移叙述于主线叙述的无事处生发开来。由是观之,人情小说对人际关系与社会风貌的摹写,最终决定了游移叙述的丰富和驳杂。
对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作家来说,人情小说的游移叙述意义非凡:这是因为当他们将汲取艺术经验的眼光从西方现代主义转向传统文学后,竟发现自己主张的叙述自觉也同样赫然在列。因此借鉴人情小说的叙述传统,在游移叙述上大做文章,就成了九十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一代作家对人情小说的游移叙述进行创造性转化时,也就开始在某些创作观念上发生了分化。而这种分化,主要体现于游移叙述的细节描写上。
我们知道,由于游移叙述偏离了主线叙述,因此每当游移叙述专注于自身的细节描写时,主线叙述就会被延宕与搁置。从这个角度看,细节描写决定了小说整体性的叙述方向:是省略细节描写,让叙述从游移部分回归主线;还是强化细节描写,在不断充实游移叙述的同时另辟新线,业已成为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前者讲究小说叙述的逻辑分寸,而后者则更看重叙述美学的闲情与野性。这其实也反映了先锋作家对待技术和审美的不同态度。
比如余华就偏于技术路线,他在《活着》里的游移叙述,已经尽可能地省略了细节描写。因为只有如此,方能保证徐福贵这条主线叙述的逻辑完整。就算是到了写作《兄弟》的时候,余华仍然视游移叙述为主线叙述的和声。且看他在表现李兰母子的人生悲剧时,便特意将叙述从这对母子的午夜流浪中游移出去,以寥寥数笔,书写了一番“月光下原野的壮丽”。这一游移叙述当然是作家对人物悲惨境遇的中断,是缓解李兰内心忧伤的神来之笔。但如果余华展开细节描写的话,那么这段游移叙述就会发展壮大,继而影响到主线叙述的推进。从这个角度看,余华的游移叙述大多篇幅不长,它始终受控于主线叙述的推进速度。当然,以细节描写见长的余华,绝不会在主线叙述内有丝毫吝啬,他对细节的掌控,最终决定了小说整体的叙述速度。
如果说余华的游移叙述,主要是为了发挥其辅助主线叙述的叙述功能,从而属于“一笔不肯苟且,一处不肯放松”的技术立场的话,那么马原和格非,就时常在游移叙述上大费周章,他们或以必要性细节描写去完善作为独立叙述单元的游移叙述,又或以非必要性细节描写去表现叙述的闲情与野性。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余华的叙述方式。那么,细节描写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又所指为何?在这两位先锋作家的笔下,游移叙述如何体现了叙述的闲情与野性?
由于“小说的内容越是进入细节,便越是调慢了叙述的时钟,甚至使之趋近静止。换言之:细节是调整小说叙述速度的枢纽”。因此在游移叙述中,如何使用细节描写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将游移叙述视为一个独立的叙述单元的话,那么其中的细节描写又可分为必要性细节与非必要性细节。前者是为了推进和充实游移叙述,而后者则有“为文而造情”之意:当作者将叙述从主线之中游移出来以后,由于不想或者说不知该如何推进这一部分的叙述进程时,就会在一些细节上盘桓良久。此种盘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让游移叙述具有了某些“闲笔”的意味,所谓叙述的闲情与野性亦于焉而起。考虑到必要性细节对游移叙述的充实和完善,其实质与主线叙述内的细节描写并无二致,因此关注这两位作家笔下游移叙述的非必要性细节,或可见出他们对于小说美学的特殊追求。
五
作为和余华齐名的两位先锋作家,马原与格非也在九十年代以后实现了创作的转型。虽然《黄棠一家》和“江南三部曲”这些作品,依旧葆有形式试验的创新精神,但和余华的技术路线相比,这两位作家显然更接近人情小说的文学传统:不论是马原对欲望人心的摹写,还是格非对男女离合的叙述,均可见出世相人心的波诡云谲。而他们对游移叙述的运用,尤其是对非必要性细节描写的拓展,也令其创作展现出了更多的闲情与野性。
先来看看马原的《黄棠一家》。作为表现当代社会的一部人情小说,马原以主人公黄棠一家的人生故事为叙述主线,辅之以商场与官场的诸多支线故事,喧嚣扰攘、纷繁杂沓地书写了一幅当代中国的浮世绘。毫不意外的是,作为一位热衷于插入式叙述的先锋作家,马原在这部作品里也广泛运用了游移叙述。其中大量的非必要性细节颇可观瞻。然而,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马原的这种叙述方式显然是不成功的,因为那些非必要性细节不仅“冲淡了长篇小说的叙事浓度与虚构魅力”,而且还“把读者的耐心逼到了极限”。问题就在于,深谙叙述之道的马原,难道不懂得细节在小说叙述中的枢纽作用吗?在这个讲求文化快餐的时代,他怎会不知道沉湎于细节描写之后所造成的叙述速度的丧失?事实上,马原对游移叙述里非必要性细节的耽溺,恰是一种闲中着色,营造小说美学的艺术手段。
比如作品中有一处关于手袋的细节。在描写黄棠的“戴安娜同款手袋”时,马原不仅详述其外形和质地,而且就连价格问题也不肯放过:“细密润泽的质感让她觉得它柔软到了极致。黄棠一直不喜欢金光闪闪的物件,但是她对它浅金色的金属配饰与如软缎一般柔韧的小皮革相衬在一起的视觉效果钦佩得五体投地,它们构成了那样一种无可言说的和谐,透着极致的高贵与奢靡之气。那张照片成了她的最爱,她不止十次不止一百次地对着照片发呆。现在画面上最吸引她的居然不是戴安娜的笑靥,而是她身前的手袋了。”这个手袋“到了中国的柜台上价格在三万到四万人民币左右”,拍卖场上更是以“八万元”成交。
单从叙述功能上来说,手袋显然是一个非必要性细节,因为可以证明黄棠奢华生活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既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非必要性细节,那么马原为何还要在此盘桓良久?如果非要强作解人,毋宁可说此一细节以不厌其烦的描写,处处反衬了人物的蓬勃欲念。以小见大处,自是批判了当代中国的拜金主义和价值盲从。只是这种解读显然以指认手袋之叙述功能的同时,否定了其细节的“非必要性”属性。然而,“强行为美学手段和叙述功能寻绎出它们和小说寓意之间的联系,反而是在诬陷小说作者刻意经营意义结构手段之低劣,同时炫示了评者冗赘的巧辩和机智而已”。对于马原来说,这款手袋只是叙述进程中的一次游移,是叙述的闲情与野性,让手袋偏离了主线与支线所构成的叙述网络。可以这样理解,当马原在描写黄棠一家的奢靡生活时,偶尔也会耽溺于物质本身。这种耽溺,并不是说作家与人物一样都有占有物品的执念,而是说手袋的形状、色泽与质地,甚至包括价格,暗自构成了某种独立的叙述场域。在此场域中,马原可以暂时遗忘小说的寓意所指,也无妨放下针对现实的批判者身份,转而以详尽的细节描写,来欣赏和把玩一番这些稀罕之物。毫无疑问,马原的这一叙述立场无关物欲,实乃闲情所致也。与此同时,当作家“为文而造情”的闲情一起,则小说的叙述也就变得野性十足了起来。因此可以说,像手袋这种非必要性细节性描写,显然以对物的耽溺,贴近了用人物姓名所暗示的这个“荒唐”年代。除此之外,马原对商业运作模式的详解,对官场人情世故的体察,其实都是一些叙述的闲情与野性。它们可能无助于主线叙述的推进,但游移停滞之处,却处处可见作家的美学追求。
与马原相比,另一位先锋作家格非同样看重人情小说的文学传统。在写作“江南三部曲”的时候,他不仅醉心于研究《红楼梦》,而且也自承受到了这一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比如《山河入梦》就明显借鉴了《红楼梦》。这部作品以谭功达和姚佩佩这对男女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叙述,重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世相人心。其中有一处细节颇可玩味。主人公谭功达遭受排挤,下放到了花家舍人民公社。在得知姚佩佩为避开警察的抓捕而开始了逃亡生涯后,他不禁忧心如焚,整天面对着地图,不断想象着姚佩佩的逃亡路线。这段细节描写是典型的重复叙述,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指向了谭功达对爱人的牵挂。若是以此来表现谭功达对爱情的忠贞似乎大可不必,按说作品的叙述本该是以姚佩佩的逃亡为主线的,但格非偏偏要舍易求难,不去叙述姚佩佩亡命天涯的惊魂之旅,反倒是好整以暇,将叙述目光聚焦在了相对安宁的谭功达身上。从这个角度看,格非描写谭功达查看地图,整天胡思乱想的情节,其实就是一种非必要性的细节描写,它游移于姚佩佩逃亡的主线叙述之外,以谭功达静默无言的意识流动,中断或者说悬置了让人屏息的惊险情节。
和余华不同的是,格非的这段细节描写并没有穿插在人物的悲剧进程之中,而是单独游移了出来,因此它就不是作家为了缓解人物和读者的紧张而特意安排的叙述关怀。相反,它既是谭功达荒凉内心的死水微澜,也是他没有被花家舍这一伪乌托邦世界所规训的明证。换句话说,花家舍所制造的繁荣假象,并未真正感化和改造谭功达,反倒是因为姚佩佩的逃亡,让谭功达在接受政治规训之余,生出了一段爱意缠绵的闲情别趣。而格非的小说美学,同样也因如此闲情造就了一份叙述的野性。这般格调,怎会配不上姚佩佩对于权力机器的绝命抗争?因此可以说,格非对于谭功达的这段非必要性细节描写,正是一种闲中着色,营造小说美学的艺术手段。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相对次要的叙述话语,游移叙述虽然不如主线叙述和支线叙述那样支撑起了作品的叙述骨架,但凭借着闲中着色与无事生非的叙述功能,却也圆满和完善了小说的叙述血肉。在此过程中,游移叙述的功能变化,不仅反映了先锋作家自觉的形式意识和创新精神,而且也见证了先锋小说对于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注释:
[1]马原:《拉萨河女神》,《西藏文学》,1984年第 8期。
[2]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许多先锋作家都转向了文学批评领域,他们对于文学经典的解读,其实也是对自己早年创作的一种反思。参见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5]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6]於可训:《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论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
[7][8][11]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166页,202页。
[9]段晓琳:《先锋之后:马原近作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10]黄桂元:《“华丽转身”的背后——读马原长篇小说〈纠缠〉〈荒唐〉的一种观感》,《文学报》2014年4月10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