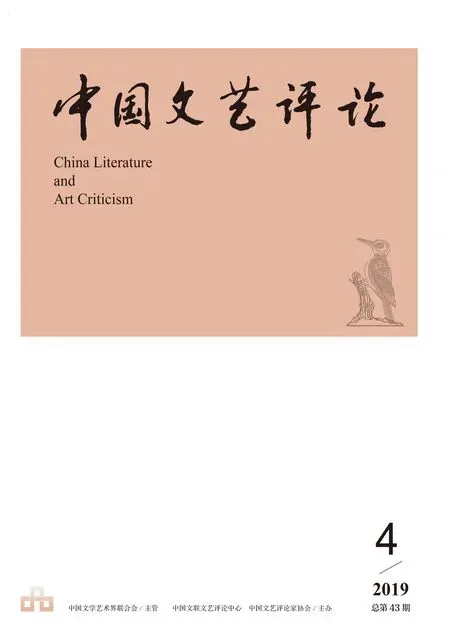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农村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反思
薛晋文
近年来,以《十八洞村》《出山记》《最后一公里》为代表的脱贫攻坚电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批农村电影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大众对乡土文化的回望、对农村生活的审视、对贫困和反贫困斗争的思考,一度成为了全社会的热门问题和焦点话题。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反思和探究新时期以来农村电影创作的得失和出路,无论是在社会价值层面,还是在学术价值层面,均具有非凡的意义。纵观新时期中国农村电影从1978年至2018年约四十年的发展史,大体而言呈现出V型反转的变化轨迹。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存方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乡土中国的变迁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电影艺术创作者积极反映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依托农村生活去反映“文革”带来的创伤和教训。农村电影不仅数量直线上升,而且诞生了一批经得住时空检验的精品力作,尤其是一些农村电影走出了国门,不仅提升了民族文化软实力,担当了先遣队和排头兵的重任,像《黄土地》《红高粱》这样的作品,试图在寻找跨文化对话的可能空间,促进了中国农村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和全球性传播,可以说,新时期农村电影的起点很高,作出了应有的独特时代贡献。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建立,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突飞猛进,农村逐渐失去了改革的优势地位和试验田作用,都市文化的崛起让乡村显得有些冷清。于是,农村题材电影在1990年代前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骤然下降,在影视画面中都市生活成为时代宠儿,乡村生活变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农村电影的发展举步维艰,观众大量流失,投资比较匮乏,创作热情有些低迷,此时的农村电影创作一度陷入了低谷。步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改革重心的倾斜,“三农”政策的强力落地生根,以及都市文化发展的困境和价值观的迷惘,反映农村和关注农村的热情再次出现,依托乡土文明重建价值观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别是农村电影《冈仁波齐》《山河故人》《百鸟朝凤》的热映,唤起了人们对农村电影久违的热情和激情,农村电影在创作数量和质量方面明显回暖,但艺术品质总体而言难以和改革初期的作品比肩。就此而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之下,探究农村电影美学构建的问题显得十分必要,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村电影的健康发展。
一、现实主义美学的游离与回归
在现实主义美学范畴中,题材是构成农村电影艺术的基础,也是传达农村电影思想的基础,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碰撞交融的艺术结晶体。新时期农村电影之所以呈现出宽幅震荡的发展态势,固然有种种内外交困的复杂原因,也与农村电影自身的问题紧密相关,而创作题材的褊狭以及创作视野的固化可能是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将农村电影的困境全部归因于题材方面出了问题,显然有失公允,甚至会滑向“题材决定论”的窠臼。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不在于选择了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题材蕴含着什么样的内容,负载着什么样的思想内涵。题材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可以说,题材是血肉之躯,主题才是它的灵魂。
现实主义的要害问题是“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之间的问题。前者一般是指继承和借鉴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是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创作规律的形象化表述;后者是指席勒创作中从观念出发的概念化、抽象化的主观倾向,即以主观观念的演绎代替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写,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实际上,创作的出发点应是现实,而不是观念,应当严格地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再现现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言艺术的目的是“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与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这一理论基础应该是研究新时期中国农村电影的逻辑起点。
严格意义上讲,包括农村题材电影在内的艺术作品,作品中的“个人”不等于“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不能简单地将电影艺术当作思想的机械解说者和阐释者,更不能抹杀人们的时代意识与时代精神的现实内容,不应该离开基层农民这一特定的阶层去随意发挥和想象,从而忽视了农民这一群体特殊的属性。我们需要回归到现实中选取有血有肉的人物,而非任意剪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此可见,农村电影艺术创作应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社会生活,正确处理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特定环境中现实人物的真实描写,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内涵,即在典型环境中显示出社会与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能够彰显一个时代的社会本质特征。当然,在农村电影创作中,我们不能忽视艺术思维的形象性、隐喻性的特点,人物塑造的个性和共性统一的特点,以及视听语言的本体属性。艺术家若离开剧情的合理发展,热衷于概念化的说教和符号化的赞颂,可能会流于空洞的赞美和虚假的迎合,那么,电影艺术的感召力弱化是早晚的事情。
具体而言,农村电影应迅速及时反映我国农村社会的重大变化,以及新政策对农民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这是中国农村电影的一种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农村电影中也不例外。实事求是地讲,在普及农村政策的同时,诞生了一批以《喜盈门》系列以及《乡音》系列为代表的“农村电影三部曲”,应该说赵焕章和胡炳榴创作的这些农村电影比较独特,以虔诚的创作姿态反映了农村现实的变迁,同时敏锐捕捉和契合了农民最熟悉的审美期待,在当时获得了既叫好又叫座的社会效应。但是,我们深入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农村电影多有配合农村政策宣传的痕迹,而且携带着“文革”时期文艺图解时代政策的惯性痕迹,特别是《喜盈门》中面对传统大家庭能否坚持传统的时代问题,作品通过民众对大媳妇强英的舆论谴责,以及二媳妇水莲对她的精神感化,实现了想象中的伦理道德对现实生产关系变革的缝合,于是,出现了无视现实的大团圆结局,可见,电影对现实问题的“艺术把握”被冲淡了。今天我们去品评这些电影作品,感觉从艺术的角度解读还不够深入和深刻。
纵观新时期电影,一些农村电影对共同富裕题材的反映陷入了概念化的窠臼。比如,农村电影《咱们的退伍兵》就有这样的痕迹,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现实矛盾,创作者没有以艺术的忧患精神为未来提供解决之道。可能为了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以未来的共同富裕神话去回避现实矛盾的做法。后来的农村电影创作一遇到类似的现实尴尬,就效仿前人概念化的惯性图解表现手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出现偏差和误判。如果艺术没有解剖现实矛盾,这样的电影通常是聋哑性的作品。倘若没有艺术对历史错误和现实困境的整饬,那么,个体生命就可能在曲折的社会险滩中继续徘徊,难以找到通往希望的出口,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失职和错误。一般而言,在大的历史转型期,个体生命的创伤、迷惘和困惑,需要艺术去抚慰和引领,帮助他们走出历史的泥淖。可见,电影艺术创作不能玩忽职守,人们期待艺术的力量去矫正社会历史的错误,盼望艺术的光芒去照亮个体前行的道路,这是艺术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所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对共同富裕矛盾的掩盖,还是对农村现实问题的回避,艺术家确实缺乏一种将悲剧毁灭了给人看的艺术胆识。也许从艺术给人以光明慰藉的角度看去有合理之处,但是,配合宣传的惯性思维,遮蔽了当时农村社会遭遇的真实矛盾和危机,使得一些农村电影没有充分反映出具有历史本质规律的社会关系。这种对题材的过度应景性把握和迎合性宣传,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农村电影艺术应有的担当和作为,没有让艺术的使命和功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敞亮,弱化了农村电影应有的思想穿透力和批判性。正如农村电影《天狗》的制片人指出的那样,“没有《天狗》这种作品,你的银幕是空白的银幕,你的民族是没有思考的民族。可见,以《天狗》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小成本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梳理新时期农村电影创作会发现,多数作品将镜头对准了党的基层组织领路人,他们带领农民开拓进取的故事题材占据了银幕的主要位置。应该说勤劳致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迁的主基调,农村电影创作聚焦于这一题材本身并没有错。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一批不容忽视的现实题材并没有获得深刻表现。诸如守土和离土矛盾的加剧,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一些农村基层政权的微腐败,农村社会贫富悬殊的拉大,以及脱贫攻坚中出现的新问题,创作者面对这些现实题材似乎没有积极作为,显然在重大的历史现场有所缺位,在题材选择方面有些避重就轻。当然,这里面有艺术家规避现实风险的考量,但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性艺术类型,倘若没有挑战现实问题的气概,不敢和坚硬的现实较真碰硬,那么,我们就会缺乏可以检索时代本质的扛鼎之作,这无疑会成为一个时代艺术殿堂的缺憾。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村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类似于《天狗》《盲山》这样的良心之作毕竟十分有限,题材的固化无疑是农村电影滑坡的重要问题之一。也许有人说,这样的批判对于当时的电影创作者有些苛刻和为难,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艺术的使命和初衷,不应该忘记艺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倘若电影在现实生活面前亦步亦趋,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绵羊,而不敢充当现实生活的啄木鸟,不敢和农村现实中的现象问题认真过招,而是选择随波逐流和打闹嬉戏,那么,电影艺术就会失去本分和节操,艺术就会丧失改变生活的力度和力量,农村电影艺术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威望会随之走低。正如席勒所说“艺术是理想的表现,而不是消遣或说教等等”,农村电影艺术若没有了现实主义美学的情怀,就会陷入自娱自乐的孤独境地。
二、现实主义深广度的缺失与深入
农村电影创作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而不是某一种抽象的观念,应按照农村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现实,这是考察农村电影现实主义美学构建的核心问题。比如,以吴天明为代表的第四代农村电影导演,依托农村电影《人生》和《老井》实现了对乡土中国变迁的追问和反思,应该说这两部电影是当代农村电影的优秀作品。然而,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不是真正的“农民自己的农村电影”,而是“知识分子的农村电影”。作品所聚焦的两位主人公高加林和孙旺泉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属于被先进文化启蒙后率先觉悟的新青年。就此而言,两部作品主要是在探讨农村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非纯粹意义上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创作者试图以“知识分子”的反思去代替对农民自身的反思,作品的深度和力度难免会受到影响,农民群体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失语者,创作者信奉的价值尺度可能会与农民自身的价值取向错位,农民的情感期待和价值期待会不同程度地落空,这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显得有点无奈和凄凉。一定程度上,创作者预设的价值尺度削弱了作品应有的美学深度。艺术家大量使用长镜头、隐喻蒙太奇去传达他们对乡村形而上的思考,使得作品本身的意蕴与农民遭遇后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引爆和共鸣。它们在电影学者和都市人眼中获得了很高评价,但远不如赵焕章的农村电影更受农民群众的认可和欢迎。在这方面,伊朗农村电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电影的接受和传播几乎做到了妇孺皆知,根本原因在于导演没有将自己凌驾于农民个体之上,具有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习惯于以一种静观的姿态去平等讲述平民的故事,不刻意追求高深莫测的视听语言美学,以一种简单的曲折故事,冷峻平实的叙事姿态,简练而深刻的人性呈现去和民众对话,帮助他们畅想困境中的美好,携手赞美坚忍不拔的生命力,在促膝而坐的谈心谈话中,讲述着生与死缠绕而成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然而,这里的平凡和平易不代表不深刻,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伊朗农村电影“淡淡的抒情意味中寄予着创作者对本土生存的深沉爱意,以内敛的表意策略彰显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和跨文化的人文诉求”等因素是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主要奥秘。
客观而言,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农村电影导演,依托《黄土地》《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在新时期农村电影殿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回望历史,这些作品曾经让农村电影又一次找回了春天,而且让农村电影成群结队走出了国门,成为了传播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支生力军。然而,这类作品在“新历史主义思维”主导下,将社会历史生活推向了后台,而将创作者自己的历史观、乡土观和情感观推向了前台,变成了农村的人与事搭台布景,创作者尽情吟唱着自己的另类农村独角戏。这种多凭自身对农村的印象和直觉,借助主观艺术想象和民俗创造手法,去完成对乡村的个性化演绎和叙述的创作理念,颇有印象主义的遗风,我们不妨称之为“印象派农村电影”,其优点和缺失同样十分明显。尤为遗憾的是,在一些作品中乡村成为了一个“欲望场”,对乡村女性人物的欲望化展示和奇观化兜售,也许无意中迎合了异域人的东方想象,同时加剧了乡土子民的“他者化”形象,使得原本朴素憨厚、重情守义、古道热肠的华夏子孙,在西方人的眼里变成了一个个欲望化的客体存在,甚至是充满野蛮和情欲的东方形象符号。农村电影《菊豆》中菊豆乱伦的场景,以及农村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老爷妻妾成群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中华子民的形象,无形中稀释了作品应有的思想高度和美学浓度,改写了民族美学的价值模式,反倒迎合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只是农村少数人的生活情趣,不是大多数普通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样态,他们的欲望动机难以代表乡村社会大多数的情感态度,而且与乡村生活的伦理生态和历史潮流多少有些脱节。这些变形和扭曲的个体欲望,能否代表乡土中国的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能否彰显一代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能否给当代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带来许多启迪性的正能量?这些创作初衷和传播效果恐怕都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农村电影导演和新生代农村电影导演,他们依托《小武》《站台》《三峡好人》,以及《Hello!树先生》《路边野餐》《嘉年华》等农村题材电影,实现了新一代农村电影人对乡土中国的静观和审视,他们对农村的反映和审视不同于吴天明和张艺谋的电影,前者更加注重以小视角承担大格局,去倾情观照游走在城乡接壤地带的边缘群体,对处于小农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夹缝中的农民/农民工,对孤独无助的农民群体,给予了真诚的情感慰藉和人性关怀,将资本对人性的挤兑和异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索。然而,一些新生代农村电影人个体性叙事的痕迹太重,普遍弥漫着一种个体化的忧伤和迷惘,没有深入到一种时代情绪和社会情绪的核心漩涡之中,尚未对一个特殊时代的命运共同体进行普遍性的深入揭示,没有将造成小武、树先生、韩三明悲剧命运的社会矛盾揭示出来。比如,隐藏在这些矛盾深处的经济结构问题、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甚至现代化与传统遭遇后的共存共融矛盾,特别是农民工阶层背后裹挟的制度体系和社会治理问题尤为复杂。从艺术责任的角度讲,此类问题都应该进行深入的艺术发掘和美学表现。倘若说要求一部电影做到这些显然有点强人所难,然而,如果新生代农村电影人的一系列作品都不能深入表现这些现实问题,那么这样的农村电影多少会给历史留下遗憾。因为,后人能从一个时代最优质的作品中,读出这个时代的优越性和局限性是什么。事实上,通过电影作品,去审视一个时代的阶层本质,是一流农村电影理应回答的美学命题。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新生代电影人的作品有些冷清,似乎并没有引起农民群体的广泛共鸣。他们过分专注于对边缘群体的哲学性思考和个体化叙事,缺少一种现实主义美学的自信和自觉,与农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期待存在一定隔膜,致使这些电影的思想内涵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创作者的艺术理想与农民的情感渴望似乎有些脱节,那么,依托电影艺术去干预现实、影响生活的深度和力度,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方面,新生代的农村电影人,还真应该向农民作家赵树理学习。这位前辈毕生致力于做农民文化上的真实代言人,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始终与农民的情感同频共振,直到今天,他的作品都没有过时,“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建立在农民真实生存、存在境况基础上的农民的价值观念、情感渴求、生命愿望,这一价值观念、情感渴求、生命愿望,随着农民生存、存在境况的改变而不断有所改变”。再往深处说,马克思的文艺美学中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论述非常深刻,明确指出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在于揭示阶级和阶层的真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否写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揭示这个环境中真实的阶级关系,在整体上符合历史真实,是判断历史剧是否达到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可见,我们的一些农村电影,由于对典型环境中真实的阶层关系反映和表现不够,尚未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关系揭露出来,没有通过阶层关系去充分审视社会体系中存在的弊病,更缺乏对这种弊病的艺术警示和艺术引领。这样的艺术,恐怕在时代的变革和前行中难当历史的重任。当然,我们反对农村电影和农村社会的发展亦步亦趋,农村电影应在整体上符合农村社会的历史真实,允许进行适度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就农村电影美学构建的出路而言,问题不在于创作者能否想象和虚构,而在于能否通过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出农村社会历史的本质面貌,表现出农民阶层的整体困境和理想诉求,从而揭示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和可能趋势,这应该是一流的农村电影艺术的最高美学追求。总之,社会历史的真实应该是电影艺术真实的基础,电影艺术真实是社会历史真实的升华。一些脱离农村现实的理想化艺术反映,无疑是违背现实主义农村电影美学的不良做法。
三、现实主义审美理想的式微与重建
无论在传统和现代社会,留给农民掌握自己话语权的空间都比较狭小,多数的话语空间往往是掌握在权力机构和精英阶层中间。农民自己想说的话语因为文化教育的局限,常常是能想出来却难以表达出来。尤其在都市文化强势崛起、农耕文化式微的大环境下,农民自身的精神诉求更显出了“弦断有谁听”的凄凉。基于这样的困境,农村电影创作、生产和传播,应该最大限度地呼应农民自身的精神诉求,最大限度地抚慰农民群体的社会创伤和时代忧伤,从而拿出艺术的良心和真诚去温暖农民的精神家园。
有一些优秀农村电影做得比较好,比如,中法合拍的农村电影《夜莺》就是典范之一。电影中来自农村的爷爷很早就失去了老伴,夜莺就成为了他余生中唯一的伴侣。鸟笼中的夜莺其实就是爷爷生存困境的隐喻,象征着现代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烦恼,隐喻着他们精神家园的荒芜现状。笼罩在爷爷心头的精神孤独和生存忧伤不是个案,而是一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命运处境,是今天谁都不可否认的时代问题和社会忧伤。整部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审美理想。再如,农村电影《十八洞村》极具代表性,影片不仅反映了精准扶贫思想带来的山乡巨变,而且从物质脱贫延伸到精神脱贫,打通了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新唤醒了农民之于土地的敬畏之情,激活了农民之于乡土文化的深厚情感,找回了农民之于自身的生命重心和精神家园,彰显了富含责任和使命的现实主义审美理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影片为现实主义农村电影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深度挖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农民和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又如,农村电影《出山记》也不容小觑,它虽然是一部纪实性的脱贫攻坚电影,但在骨子里透视的却是几千年来农村社会的人性问题,而且将人性问题和思想问题,置放到都市文化和现代性的大背景下进行追问和审视,使得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具有了时代性和社会历史价值。就此而言,这部影片是我们这个时代纪录乡土社会的民族日记,也是后人检索和回望这一特殊时代的极好文本,具有鲁迅小说和杂文一般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给我们认识当下农村和农民带来了震撼性的欣赏效应。这种深入特定阶层群体、借助小视角承担大格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内蕴着深邃宏大的现实主义审美理想,反映了创作者博大的艺术抱负和虔诚的使命担当。
然而,一些农村电影创作在这方面多有欠缺,部分作品的审美理想缺乏普遍性和引领性,存在着审美理想和乡村现实错位的问题。这些农村电影审美理想的真实性和社会历史性经不住检验,电影对农民群体认识生活、改善实践的力度就会削弱。有的作品将农民的精神诉求简化为物质财富的满足,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条件的改善,去代替对农民精神诉求的探寻,以消费文化提倡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试图去颠覆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将农村电影当做商业大片去创作,迫不及待地在影像中炫富和炫耀,以现代化的物质繁荣刺激农民的神经。于是,在巨大的落差对比之下,影像中反复出现了农民们的茫然与迷失,比如,农村电影《叶落归根》中老赵识破工地老板给的假钞抚恤金后,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无底线人格羞辱;再如,农村电影《花腰新娘》中依玛涂抹口红后,被姐妹们称赞“不愧是去过城里的人”的虚荣感;又如,农村电影《一个勺子》中主人公拉条子拼命追赶汽车,央求城里人三哥打听儿子下落的奴颜婢膝。在物质的挤兑和金钱的奴役之下,一批民族审美理想中推崇的典型人物,一些传统乡土社会中脊梁式的人物,在农村电影中却投降和屈服了,成为没有骨气和血性的软体动物,失去了起码的人格自信和个体尊严。这样的审美理想令人困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创作者审美理想的不自信,体现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自卑心理。倘若对农村社会的生活经验稍多一些,你会发现转型期农民的精神苦痛远不止这些,诸如农村养老的问题、传统伦理坍塌的问题以及留守妇女情感残缺的问题,失地之后或离土之后灵魂无所依附的问题同样揪心,这些精神的疾苦和灵魂的破碎构成了当代农民主要的痛苦。由此看去,今后艺术家们应该直面农民灵与肉的真实处境,从而帮助他们挣脱存在的痛苦和羁绊,增强改变现实处境的信念和勇气,努力抵达充满希望的彼岸,这是农村电影艺术审美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这样的问题隐忧,农村电影应该重建现实主义的审美理想,引导农民群体清醒看待自己的现实处境,正确处理他们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新的生活中形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力量,这应该是农村电影的本分和使命,因为“审美理想在人的意识中产生,但是它引导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时,表现在人的活动和行为中,而在艺术创作中审美理想最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可见,艺术的审美理想凝聚和反映着艺术家的价值观,农村电影是艺术家对乡村社会的物化反映载体,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艺术的信仰和对社会的使命良知。艺术家应承担起这个时代的艺术应当承担的责任,主动介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场域,从而以艺术的名义积极作为,而非将农民的幸福生活简单地理解为对高楼大厦的满足,或者现代化的高档消费品的拥有,这样无法全面而深刻地呈现改革开放时代乡土中国的本质特征。实际上,这些“物欲性”的农村变革故事,往往掩盖了“精神性”的苦痛和情感的焦虑。物欲的农村不等于精神的农村。这样的创作思维会将农民的精神诉求拒之门外,使得他们在艺术作品中“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这些困境都需要农村电影艺术去敞亮和还原。农村电影艺术本应依托农民熟悉的故事,秉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以一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使命意识回应社会矛盾,奋力为农民的精神世界代言,真正与农民同悲戚和共欢乐,用形象生动和直观易懂的画面语言传达农民群体的喜怒哀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参与自己的精神家园构建,从而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重心和归宿,以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惟其如此,农民群体才有可能借助艺术的力量去对抗生活的不幸与苦难,在生活的河流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坐标体系,找到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获得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艺术形式的喜闻乐见以及审美理想的静水深流在这里同样重要。
由是观之,中国农村电影审美理想的重建任重而道远,一些创作者并未做到全面、客观地观照农村世界,一些作品没有深刻反映和解剖农民的精神世界,没有为疗救农民群体的精神病痛开出时代药方,更没有很好地坚守电影艺术的本分和职责,这不能不说是当下农村电影创作的最大隐忧。所以,关注“精神的农村”应是农村电影再创作的主要发力点,也是农村电影不辱艺术使命、构建现实主义美学大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