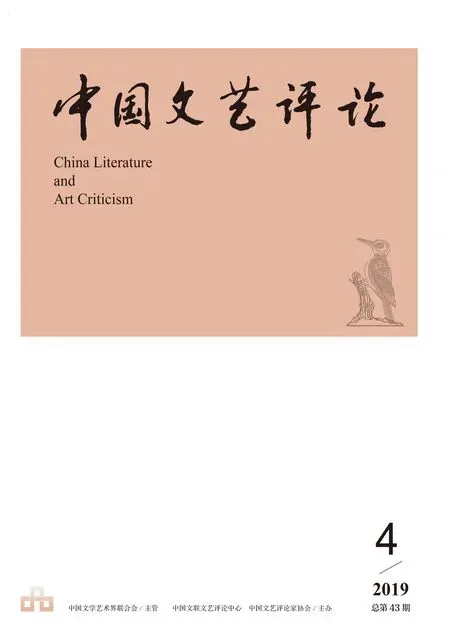诗人的心路历程与时代的精神图谱
王雪瑛
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复杂对当代诗歌创作提出了重大挑战,也对怀有青云之志的诗人敞开了广阔空间:在学习中建立文化自信,在探索中积累诗艺学养,形成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新鲜诗意的能力与善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用诗歌捕捉自我心灵的颤动,呈现时代的精神图谱,用经过艺术提炼的语言、饱含真情的诗句,传递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情感,以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呼应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的新时代,创造出诗歌的新华章。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早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涌流着淙淙清泉,灌溉着几千年文明的演进,滋养着华夏世代的心灵,塑造着中华美学的精神,这正是诗歌与心灵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形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传统。
时光之河奔流不息,我们从新时代的岸边眺望文学,我们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在互联网全媒体的现实中,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真正的诗人是民族的触角,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诗歌往往是时代演进的先声。新时代、新征程、新经验,诗人何为?诗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如何认识我们的诗歌传统,认识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经验,理解我们时代的前进方向,倾听砥砺前行中的人民心声,这是值得当代诗人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也是努力践行的伟大使命。
诗言志的美学本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典诗歌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生发,生成了丰厚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和美学资源,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跨越时空的经典诗句生动地注解着诗歌的生命力、诗歌与教化、诗歌与现实、诗人与时代、自我与人民。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给千年之后的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诗经》是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开端,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诗经》以反复咏唱的旋律、礼仪规范的约束、潜移默化的熏陶,以“诗教”化人,养成社会的伦理秩序。
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诗”是“言”的基础,可见孔子对诗歌的推崇,诗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儒家经典中,首推《诗经》。在中国古代,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诗教”,《礼记•经解》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次,“诗教”也是一种修养,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他人时曰:“可与言诗也。”
孔子暮年,自卫国返回鲁国,他潜心编订《诗经》。《诗经》是中国诗歌源流中最具民间性的诗篇,鲜活地书写着黎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亲情和伦理,但三百多首诗歌的作者佚名,已经无法考证,而诗人的盛名与诗集一起流芳千古的是《楚辞》。楚辞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之后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如果要与人言诗,在我少年时代就驻留心间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自屈原《离骚》的不朽诗句千百年来回响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从此将真理的探索者、理想的追求者的诗人形象永恒地定格在中国历史上,《离骚》《九歌》《九章》《天问》闪耀着楚辞的光芒,也形塑着心系苍生、兼济天下的“大我”,树立了一个为国运忧心伤神的诗人形象。他内心的困顿与忧愤是时代的困境,而他的坚韧不拔是超越时代的,他以一生写就的“楚辞”生动地注解了中国诗歌“诗言志”的本质特征。
屈原的《离骚》蕴含着诗歌源头处“诗言志”的精神内核,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则是他对“诗言志”具体化的理解和生发,也体现着历代诗家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集中提炼:融入当下社会,回应时代命题,为现实而作。诗歌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从《诗经》就开启的中国诗歌传统,这也是诗人关心民生与道义、自我与国运的责任和情怀。
白居易不仅在散文《与元九书》中自陈每逢披阅史书,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才更体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还将这样的理念运用在他的抒写中,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关乎世道人心,体察民间疾苦,诗歌语言平易晓畅很接地气,代表诗作《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流传广泛,《卖炭翁》《琵琶行》等是诗人自我的人生体验与民间生活的结合,将新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新的高度。
诗立言的诗学谱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些千年流传的诗句,出自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是他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所书,字里行间真切地记录着当时的社会现状,流露着他内心的喜忧苦乐,期望着国家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杜甫的喜忧来自于真实的自我体验,来自于嬗变的时代风云和家国命运,这是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和忧患意识。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 “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传颂千古影响深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皆成笔底波澜,为时代画像,为历史立传,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史”之称,“诗圣”之谓。这和他贴近人民的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杜甫以“即事名篇”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留下了诗人与黎民同忧、与时代同行的心路历程,形成了他意境高远、沉郁顿挫的诗风。
杜甫将律诗写得纵横恣肆,合律而去声律之束,工整而无对仗之痕,蕴含着感时忧国、仁政爱民的儒家精神。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仙,他的诗歌挥洒着自由旷达、浪漫飘逸的才情,流露着道教的精神气质。韩愈将杜甫与李白并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诗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典范。
不朽的诗篇产生于壮阔的社会实践,五万首全唐诗中有代表性的还有边塞诗,抒发着守疆护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流露着为国利民的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边塞诗绘就了明月天山、苍茫云海、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般雄浑辽阔的意象,热血边关的画卷,传颂着边陲将领有志之士的琴心剑胆和共同心声,回荡在千年历史的崖壁上余音不绝……我想起了清代诗人龚自珍创作的七言绝句《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时无力的清朝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家面临着被侵略,民族面临着被奴役的危机,要拯救暴风雨中飘摇之舟,须有各方英才,所以诗人力劝天公,大降人才,共挽即倒之狂澜,将倾之大厦。诗中选用了“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些恢弘壮伟的主观意象,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前瞻的眼光、战略的设想,留下了别开生面、气势不凡的诗风,蕴含着呼唤变革、期待未来的深刻寓意。
这首诗为《己亥杂诗》中脍炙人口的名作,是龚自珍罢官南归,路过镇江时所写,既是诗人内心真实的思想,也是天下士子的心声,直击了清朝的痼疾、社会的黑暗,还超越了时代,诗意历久弥新发人深省。
《己亥杂诗》315首内蕴丰厚,是诗人的心路历程,也是时代的精神图谱,有对社会现实政治的剖析,也有对民族命运前程的思考,有传统中国的儒道思想,也有民间文化的吉光片羽。他的诗作赓续了近代到现代的中国诗史,对于诗人诗派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诗界革命诸君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及南社诗人高旭、陈去病、柳亚子,还有鲁迅等,他的诗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环节,构成一个自先秦而晚清的中国人文主义诗学谱系。
百年新诗感应时代
中国文学的发展交织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五四新文学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化。从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新诗开始,到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全国各地陆续举办过多种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研讨会、论坛及诗歌活动。“百年新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诗寄予厚望: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旧体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新诗也成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领衔创作白话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文学革命,他认为白话诗可以自由表达,注入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五四新文学以解放诗体、解构格律来成就新诗、感应时代、贴近民众、启迪民智。“在郭沫若、冰心、胡适、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诗人艾青的代表作《我爱这土地》,也是中国新诗的扛鼎之作。诗歌写于抗战后的1938年11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大地。诗人和文艺界人士一同撤出武汉,汇集于桂林。对战火蔓延的祖国的忧患,对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深情,让诗人拿起笔,写下这和着血泪的诗行。
土地是博大的意象,鸟儿是灵动的意象,艾青以写实和象征交织的手法,展开了苍凉而辽阔的画面,“鸟儿、土地、河流、风、黎明、泪水” 有动有静的审美意象提升和强化了诗人的情感表现力,对血沃中华大地,诗人爱得执著,爱得坚贞:嘶哑的喉咙也要为民族、为土地而歌唱。诗人真挚的情感凝聚在诗行里, 跨越了时空。从诞生之日起,就回响在几代读者的心里,精悍的篇幅蕴含着沉重的忧思和深厚的情感,每一句都从诗人不屈的心头流出,带着诗人血液的温度,直击读者的心灵,成为我们对祖国与大地,时代与人民,新诗与自我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中诞生的新诗已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们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昂扬向上的抒情主义一度占据诗歌创作的主流,成为新中国诗歌的审美风范。艾青、何其芳、贺敬之、邵燕祥、李瑛、公刘等诗人书写着新生的土地、祖国的发展、人民的豪迈。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食指的《相信未来》则记录了时代疼痛和历史转折中,诗人的忧思和向往,诗人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大潮正在蓄势涌动中……坚冰深处春水生,他们的诗句感应着时代的伤痛与渴望,犹如料峭寒风中的迎春花,呼唤着春天的到来。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地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诗句以信心和勇气穿越动乱年代的阴霾和黑暗,以思想的力度、情感的温度,慰藉着一代人的心灵,向沦陷在迷惘和苦难中的同时代人真诚地宣告: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重启诗歌探索之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历史重大转折,中国社会时移世易,中国文学迎来了冬去春来的新时期,诗歌重启现代探索之路:挣脱极左的思想桎梏,追求真实的自我表达,荡涤虚假的空洞语言,呼唤人性的回归,弘扬真善美,以个体的心灵倾听时代的大潮,以深入的思考、开放的心态书写着中国诗歌的新篇章。一批语言清新且思考有力的诗作应运而生,评论家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先后发表了三篇重要的诗歌评论,当代文学史上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以真诚的自我,触摸时代的脉搏,给诗歌注入生命力,从提炼自我的心灵体验,呈现一代人的思想情感,成为同时代人的共同记忆。这批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诗作,穿越近四十年岁月的长河,在纪念改革开放中,被引用最广的就有其中的两首: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这首诗是梁小斌的代表作,是诗人自我曲折的心路历程,也是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代青年特殊的思想历程,表达了全国上下的热切渴望。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变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文引用了这首发表于1980年的诗作,并作了新时代的解读:“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找到那把钥匙,重新启动历史前进的时间,打开融入时代潮流的大门。”
“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新华社评论员在《向着更加壮阔的航程——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一文中引用了舒婷的诗作《一代人的呼声》。诗人以真理的光亮,探寻民族的未来,以承担时代的使命,体现自我的价值。诗人独立的思索中,充盈着对祖国和民族的深爱,全诗在哲思中饱含着激情和信心。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对诗歌审美作用的深刻认识与社会教化作用的高度概括。兴,朱熹注为:感发意志。诗是用比兴的手法抒发感情。的确,诗歌的魅力是以情动人。诗人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抒写华夏子孙的内心愿望,诗人以自我的拳拳之心抒发对祖国的真情实感。余光中的《乡愁》是以自我最深切的乡愁呈现最真切的家国情怀的经典之作,几十年来被广泛传颂,余光中也被称为以乡愁之诗感动心灵的诗人。
《乡愁》是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中的一首,全诗选用了“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生活中常见的意象,寄寓其情感和思想的内涵,将常见的主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诗人按时间顺序和不同的人生阶段,从“幼儿恋母”到“青年相思”,到成年后的“生死之隔”,再到对祖国大陆的感情,不断发展的情感逐渐升华,凝聚了诗人整个人生历程中的情思。乡愁的对象,从具体的“乡”到抽象的民族之“乡”,从地域之乡到历史之乡和文化之乡,诗人最真切的“乡愁”、最深厚的情感,层层递进积淀成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诗歌以“小小”“窄窄”“矮矮”“浅浅”等叠音词来修饰中心意象,语言纯净清雅、浅白真率而又蕴藉唯美、意味隽永,透出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汉语之美、文化之韵。
余光中一生漂泊,他自称是“蒲公英的岁月”。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在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度过晚年。“童年的天空啊,看不见风筝,看到的是轰炸机”。战火中一路逃难的童年,诗句中呈现的是诗人对战争的记忆,是童心对民族伤痛的敏感。青年时代他在美国留学,之后又去讲学访问,美国文学与文化对他影响愈深,乡愁在他心中愈是滋长。对乡愁的生命体验和艺术表达贯穿了余光中的诗文创作,也是他日渐深入认识诗歌和自我、艺术生命不断成熟的过程。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余光中曾经主张西化,有脱离现实的倾向,他自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经过在西方世界的人生历练,他开始回归东方,他在文中礼赞中国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他想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因为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诗人吉狄马加的近作《大河——献给黄河》以诚挚的敬意,倾听了千万年奔流不息的大河,以恢弘的气势和对民族未来的憧憬,回溯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以不凡的构思,以三百余行的长诗,汇成献给黄河母亲的赞歌。海子的《河流》《亚洲铜》以丰富的意向,深沉的情感,书写着河流与大地的谣曲。他们的诗歌创作触及了世界华人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中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恋。
创造诗歌的新时代
新诗百年诞辰刚过,21世纪诗歌也将近二十年,有理想的诗人在重新梳理我们的诗歌传统、汲取百年新诗的美学资源的同时,要全面认识当下诗歌创作的真实状况,思索诗歌创作与时代的联系。当代诗歌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时代经验,诗人如何捕捉创新灵感:从自我情感抒发中,表达人民的心声,从自我生命历程中,呈现时代的发展,在价值多元中,坚守诗歌的审美品质,在过剩的资讯包围中,创造有生命力的诗歌。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以强大的功能辐射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诗歌传阅上,自媒体、微信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上首发的诗歌产量(包括旧体诗词)在一年内已接近一亿首。“睡前读诗”“为你读诗”等公众号让诗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快捷推送让诗歌的写作人数、传播速度、接受广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变,使得带有“新闻话题”“娱乐效应”的诗人借着现代传媒高效的传播力而一夜成名。
诗歌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密切关联,现代社会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诗可以“群”。但是低门槛、快传播、无标准,导致诗歌创作量多优少,价值多元中标准迷失,诗体驳杂中审美失范,广泛传播后记忆中留不下诗句,缺乏让人怦然心动的诗歌。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对诗人的如此调侃:会用回车键就会写诗……
我们要总结诗歌创作中的得失,思索新诗与传统、诗歌与时代、理想与现实,要找到诗人的情感认同,诗歌为谁立言,不能忘记诗歌中蕴含着的民族的精气神,不能忘记诗人与时代同行的使命:诗歌是对丰富心灵世界的生动呈现,也是对时代发展、社会主潮的有力揭示。评论家谢冕凝心聚力历时十年撰写完成的《中国新诗史略》是研究新诗的代表性著作。《诗刊》《扬子江》《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专业期刊也推出相关的新诗评论文章。
时代呼唤着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引领时代风尚的诗人,读者需要心灵相通真挚动人的诗歌。成为卓越的诗人,创作出脍炙人口的诗歌,这对诗人的思想深度和想象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当然离不开天赋,而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更是不可或缺。要在学习中建立文化自信,在探索中积累诗艺学养,形成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新鲜诗意的能力,也要有善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
诗人的价值不在于经过训练之后就能写出分行排列的文字,而是用诗歌捕捉自我心灵的颤动,呈现时代的精神图谱,用经过艺术提炼的语言、饱含真情的诗句,传递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情感。诗歌是充满创造性地表达时代与自我的语言艺术,是书写者与阅读者的心灵相通,是人与人情感交流跨越时空的“空间站”,也是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艺术形式。
屈原的“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谭嗣同的“留取肝胆两昆仑”,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诗句,携着生命的温度、时代的风雷、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激荡在读者的心里,是中国诗歌的金声玉振,是中国文学血脉绵延的民族记忆,也是中国历史大浪淘沙后的精神财富。
不同时代的经典都安慰着我们的心灵,人生的不同境遇都召唤着诗歌,而奋进的时代更是呼唤着宏伟的史诗,奋斗的人生更应该涌现壮丽的诗篇。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复杂对当代诗歌创作提出了重大挑战,也对怀有青云之志的诗人敞开了广阔空间。只有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流出的诗句,传递出人民的心声,描绘出时代的画卷,才能满足他们的艺术雄心:以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呼应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的新时代,创造出诗歌的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