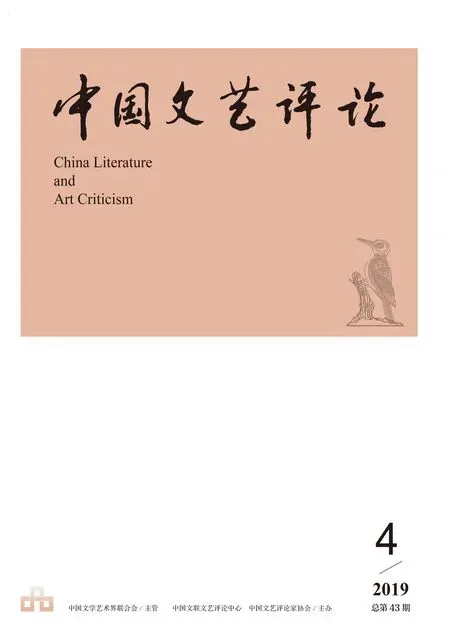现实题材话剧的整体性艺术构思和唯美表达
——评话剧《小镇琴声》
景俊美
题材选择向来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标尺。历史、现实和未来是艺术创作绕不开的重要维度。在话剧创作中,现实题材在三类题材中占比一直偏高。反观话剧从引进到当下,其艺术品质与题材表达从来不具有完全的正比例关系。相反,凡是有艺术突破、思想厚重和深刻的作品,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主流与实验都可以是其自由驰骋的天地。具体到现实题材,不仅是时间段落的一维表达,也不仅是简单呈现现实生活和社会变革中的人与事,更是强烈的时代诉求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集中释放,是观照和书写人和人性的重要舞台艺术样式之一。原创话剧《小镇琴声》达到了现实题材戏剧的较高水平,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与演出实况的探讨,讨论其得失,总结当下艺术创作中一些普遍性问题。
敢于面对、善于选择的厚重主题
如果参照影视剧分类,《小镇琴声》应该属于典型的年代剧。它主要讲述了一群农民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开厂办企,实现生活、事业与情感梦的故事。因为时间跨度较大,该剧采取了闪回的方式展现不同时代的不同面貌和主题故事。一号人物男主角阿德和其兄弟水根分别由老年和青年两位演员扮演,闪回与穿插的叙述方式以冰糖葫芦的样式贯穿全剧,使舞台效果有了变化:正在经历和回望观看这两种视角交替进行让观众看到了别样的生命慨叹。贝克在《戏剧技巧》中说:“选择和压缩是一切戏剧艺术的基础。”笔者相信“小镇”的故事一定很多,但是小镇里飘扬着琴声的故事,则是高度压缩和提炼后独特的“这一个”。而它,正是中国“农村”“农民”最好的写照。一如编剧李宝群所阐述的那样:中国农村是神奇的所在,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多彩;中国农民是独特的族群,他们很平凡,却又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若给他们光,他们会着火,火着起来了会越着越大……
从故事文本看,该剧有高远的立意,涉及农民的梦想、底层的生存以及情感的错位与生命的意义等。木匠身份的阿德恋着青梅竹马的越剧名旦文莺,然而文莺为追逐梦想却选择了钢琴家,婚后又因家庭需要远走他乡。和阿德一起玩耍长大的荷花一直恋着阿德,为他默默流泪、付出,并选择了成也好、败也罢的相随相伴。在这三位小镇青年的爱情与事业的故事里,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青春的活力与执拗,为了心中的梦想,他们都在追梦,并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圆梦。所以木匠阿德做了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疯狂的事——造钢琴。
农民的“朴素”与造钢琴的“高雅”,就一般人的观念看不只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甚至是异想天开般的绝对不可能。正是这种巨大的对比所引起的“身份”与“梦想”之间的错位,才塑造出阿德、荷花、旺财叔、水根、刘一手、郑大锤、三剪子等不同人物真实而鲜明的性格,并高扬起那个时代看似疯狂实则艰辛与毅力并存的光亮。而这种种“光亮”,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整个社会需要的精神内核,是需要我们传承和呵护的民族命脉。编剧通过剧中人“八级半”的话,讲出了农民造钢琴的意义:“造钢琴就是天大的事,就是换活法。它不光能挣钱,还能让人把腰杆子挺直了活。”伴随着造钢琴、而且是造最好的钢琴这一高难度梦想,剧情铺陈了请工程师、留工程师的桥段,面对问题如何解决、遇到挫折怎么面对等人生难题也扑面而来。整个剧一波三折,故事相当引人入胜。这是戏剧最大的张力,也是该剧最吸引人的所在。
不过笔者相信,有趣并不是编剧的全部用意。《小镇琴声》真正要传递的还是有思想的内容。正如剧中人“阿德”所说:“人家说的没错,余英镇太小了,我阿德更小,小的像一粒土一滴水。农民祖祖辈辈刨土坷垃,渔民一年到头水里来水里去,我们就是土就是水,那又怎么了?土和水比什么都金贵。土多了能堆成山,水多了能汇成河……”类似这样的朴素语言,是农民的语言、农民的心声。农民的世界虽然平凡,但是代表了大多数,代表了千万老百姓,他们风风雨雨的故事、酸甜苦辣的人生,汇集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并最终奔向远方……这,正是这部戏厚重的所在。
充满喜感、善于调度的二度创作
相较于一度文本的厚重,二度创作的最鲜明特征是“喜剧”色彩的凸显。导演傅勇凡在借鉴与化用、舞台与受众、故事和人物、视听效果与文本内容之间统筹考量,打造出了一部深具“浪漫喜感”戏剧效果的舞台艺术作品。王朝闻曾说:“综合艺术是戏剧的重要特征……由于各种艺术的综合性质,戏剧艺术要遵循极为复杂的、互相制约的许多艺术部门的特征,它本身具备着多方面的审美价值。”该剧的“喜剧”调度为舞台注入了青春昂扬的活力。与之形成有效互动的,是观众的反应。正所谓“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之于戏剧的意义是毋庸讳言的。笔者在剧场中观察观众的反应,发现观演效果十分融洽。一部农民与农村题材的年代剧,竟令剧场中的小观众也笑声迭起,而在笑声之余,人们又体会到了历史的沧桑、命运的无常以及人性集复杂与质朴于一体的矛盾……剧中所触及的“活着”“做人”“尊严”“底线”等问题,实际上又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的。真正的好剧,正是来自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探讨。当老年阿德和水根既相互照拂安慰又互相掐逗时、当青年阿德痛失梦中爱人时、当荷花站在角落默默抽泣时……剧场中激荡起与故事主人一起欢笑、一起悲泣、一起默默流泪的情感共鸣。
从“喜剧”角度看,剧中的笑声主要是因为导演在人物塑造方面添加了更加个性化、剧情化与小品化的语言动作。比如旺财叔的贪财、刘一手的娘气、郑大锤的憨直、三剪子的精明等,编导通过三言两语或看似简单实则千锤百炼后的动作细节,迅速立定了一个个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这样的创作手法营造了一种特别的气场,也是喜剧在众多现实题材戏剧中最能吸引人的地方。特别是国营钢琴厂工程师欧阳被阿德请来之后,笑点更是层出不穷。他有技术、遇到难题敢于和勇于克服,但是他又有些虚荣和贪财。这些优点与缺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既能看出人物的复杂与多面,又能看到戏剧的张力与节奏。所以欧阳的出场演讲、村民为留人才促使他被迫东躲西藏、第一架成熟钢琴的弹奏以及欧阳与阿德之妹阿清的恋爱关系等,都充满浓浓的喜剧味儿。
激荡人心的地方更在于老年阿德和水根的对话以及青年阿德与文莺、荷花的错位爱情。阿德与水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知根知底知心声。他们的对话里有回忆、感慨,更有自我认知与人生百味。当他们以对话方式回望自己的青春时,一是得意于自己的闯劲,二是感叹于命运的无常。通过回望,展现了普通人“生如蝼蚁”的人生。不过,即便低到尘埃,也不能没有梦想。他们可以像滴水之于大海,却不能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做梦、奔梦、圆梦,是每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必备的人生阶段。最终,阿德以及小镇村民活出了自己,活得像白鹭那样尽情展翅飞翔,即使这飞翔有时带着伤痛、病痛甚至付出很大代价之后才得到和拥有的,也一样具有重要的价值。阿德与文莺、荷花的错位爱情,一个是梦想的开始和想象中的完美,一个是梦想的终结与现实中的守护。梦开始的地方是甜蜜,破灭的地方是痛苦;追梦的过程是付出,守护的结果是圆满。这正是人与人之间最微妙的情感本质,也是这个故事最坚实的内在逻辑。
唯美诗意的舞台呈现
话剧作为综合的舞台艺术,舞台美术的好坏是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当下,包括舞美、灯光、道具、服装、化妆、音响、装置等在内的大舞美引起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关注。别林斯基指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话剧之舞台美术的发展,一样需要评论者的关注,而且其批评的第一标准,便是“美学的标准”。具体来说,从舞台实现看,导演的调度和节奏,需要舞美的技术与艺术支撑;从观演关系看,观众的审美期待不再仅局限于故事内容,而是建构在内容之上的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的舞台整体,是“人人看得见的演出形式”的整体。
话剧《小镇琴声》的舞美设计别具一格。这“一格”的主调在于“小镇”所凝聚的类似“乡愁”与“故乡”的灵魂寄托。剧一开始,最抓人的便是舞美与灯光共同营造的“审美场域”。我们看到,舞台右侧前端的芦苇与小船,左侧前端的芦苇与钢琴,从右侧前段延伸出的弯曲的小路,又从左侧前段延伸出来的笔直的栈桥,远处是繁星满天的天穹。随着灯光变化,晨曦微显,四周的芦苇一簇簇、一丛丛涌现,白鹭从路与桥交叉处的湖岸边醒来,抖动翅膀,随之翩翩起舞……好一幅江南“小镇”的田园盛景图!与视觉震撼相伴相生的是听觉的飨慰。作曲石松原创的钢琴曲缓缓流淌,随着灯光的起、亮、转、染、聚,音乐在抑扬顿挫间激荡起来的正是观者的情绪和审美。这种唯美诗意的场域,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随之,观众随着主人公的情绪迅速进入了剧情之中。
而随着剧情的展开,《小镇琴声》的舞美变化又是多样而丰富的。文莺唱越剧时的块状结构,像幕布又似天空的蓝色,给人一种空灵感;为留住人才,接风酒席从阿德家转战荷花餐馆、道路旁边,时空转换迅速,转台的启用、架状结构的切割,很好地实现了在短时间内隔离出不同空间的艺术效果;阿德与荷花的情感转折点,主要集中在前台右侧的小船边:送饭、吃饭、喂饭,是情感转化的载体,也是把握人生命运的契机;老年阿德和水根的对话,主要集中在前端台口的两端;欢迎两位造钢琴的工程师、旺财叔以次充好犯事后的“审判会”等主干故事的表演主要集中在舞台的中间区域……整体来说,《小镇琴声》的舞美设计呈现出“主体结构不变,时空变幻鲜明”的特点。舞台上场面灵活、气氛紧张,互相穿插、动作鲜明。这是架状结构的理想构造,也是该剧舞美设计的一大亮点。
结语
一切艺术作品总有一句创作者最想要说的话。评论者的第一任务就是找到这句话对于受众的影响,第二任务才是分析这句话怎样作用于受众,即艺术技巧问题。从文本、导演、演员、舞美等具体艺术细节去评论一个剧目的好坏,是艺术批评必须做的功课和绕不开的话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作品的好与坏、高与低还在于如果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否一样有足够的分量担当得起被评论的任务。惟其如此,这个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才能超越个案分析的局限,达到其启迪同类题材艺术创作和演出的新高度。
当下,现实题材话剧创作与演出蔚然成风。这和我们提倡关注现实以及话剧自身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类题材并不必然具有艺术审美的豁免权。相反,越是写当下生活、表达主旋律的作品,反而越容易招致诟病,这不得不引起话剧从业者的警醒。众所周知,话剧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国外传入,进入中国便担负起救亡与启蒙的大任。随着历史的发展,话剧的创作类型与演出样式日渐多样化,但现实题材一直是其重头戏。正因如此,现实题材话剧创作与演出的得失总结尤为重要。
《小镇琴声》突破了同类题材的“泛”,采取更加聚焦、更加提炼的“小镇”故事,而具有了恩格斯所说的“典型”性,实现了对社会生活本质属性的反映和较高审美价值的舞台表达。该剧真诚地道出了人之为人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问题:一是物质方面的生存问题,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二是精神方面的追求问题,即“为什么活下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相伴相生,进而触碰到社会变革、农民生存、小人物命运和有关尊严与梦想的书写等等。因为敢于触碰、善于选择,这样的现实何其“真”,“真”到人物故事仿佛就在观众身边;何其“痛”,痛到观众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相似的经历。唯其“真”与“痛”,作品才脱去概念表达进入到共鸣层面,对观众的吸引力也便自然而然和水到渠成。我们也因此得以透过剧中人的人格镜像看到真实的人生和人性,进而获得了精神的洗礼。这样的剧目主题厚重,感染力强,能够收获深刻之心理效果,是真正的从题材“现实”到表达“现实”的现实主义。
作为艺术作品,《小镇琴声》较好地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从文本到舞台的整体表达。编导将该剧定位在现实题材轻喜剧,苦难之“苦”便不再一味地“苦”,而是夹杂着甜蜜、温馨甚至戏谑。观众在欣赏时,也会在笑声中意识到以往没有意识到的另一种现实。换句话说,它开拓了现实题材话剧的深度和广度,这正是戏剧所要收获的效果:传奇、跌宕、真实而又动人。对艺术创作规律的遵循与重视则为该剧赢得了口碑。《小镇琴声》在国家话剧院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探寻出了一条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道路:通过对主题的选择、风格的定位、舞美渲染和观演关系的观照,最终塑造了众多立体而丰满的人物。话剧虽然是讲故事的艺术,但又是在时间、地点和空间上受限制的艺术,它的内核与小说、散文、影视剧等其他艺术样式不同,它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创作者必须遵循的艺术规律。人物是话剧艺术的根本,无人物就无艺术内核。当人物在舞台上立定、在观众心中扎根时,也正是一个作品能够立定和扎根之际。
近年来,随着现实题材戏剧的扎堆呈现,现实题材及其创作手法受到质疑。《小镇琴声》的多面表达实现了题材的突破,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观照人,从文化内涵上挖掘艺术的深度,从更深远的空间探索舞台与表演的关系,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又拥有艺术的共性。剧中对越剧等传统文化的认知、对农民语言和心声的探索,为现实题材话剧创作与演出探索提供了新的思维逻辑和创作手法,我将之总结为从时间的“实写”到时间与题材的“特写”的整体性艺术构思。整体性的艺术有利于观众形成对话剧艺术新的文化期待,也有利于话剧艺术的总体提升。
但是,该剧也有提升的空间。水根和阿德一直在一起,却很少有自己的想法,也似乎没有自己的家庭,这样的设置令人疑惑——他的人生呢?他的性格呢?他的梦想与困惑呢?该剧的轻喜剧风格很能吸引观众,但与此同时又似乎与剧作者最初的构思有所背离,那种关于青春、青涩与青年的激情、高扬与欢快的气息,与深邃主题、回望结构也有出入,舞台上时而历史、时而当下的闪回,有时候闪着无限的光亮,有时候又显得有些出戏。而在表演方面,李梦男饰演的老年阿德、褚栓忠饰演的老年水根以及闾汉彪饰演的旺财叔很好地诠释了人物的身份、性格与艺术的质感,但是年轻演员的表演还有稚嫩之处,需要舞台的磨练和编导的引导。另外,该剧的舞美设计的复杂结构相对限制了表演区,以至有些调度显得有些雷同。当然,瑕不掩瑜,经过进一步打磨和完善,话剧《小镇琴声》应该能成为舞台艺术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