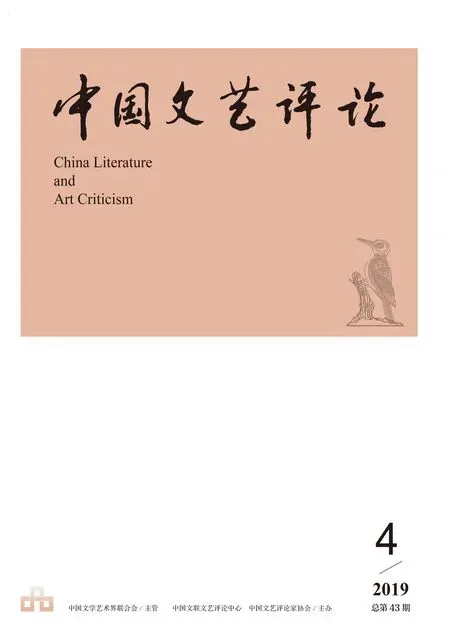百年新诗中的北岛与昌耀
李少君
百年新诗成就如何,争议甚大。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入手,百年新诗其实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相互关联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如何理解百年新诗,其实也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但新诗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
中国现代性问题发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但真正开始探求比较全面的解决之道却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反省和检讨中国文化与文明。新文化运动万事开头难,其真正突破恰在于新诗革命。
旧体诗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核心,那么,对传统采取激烈否定的态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要从新诗革命开始。新诗,充当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带头创作白话诗。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文学革命,声称要用“活文学”取代“死文学”,认为只有白话诗才是自由的,才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
这些年,关于“五四”的争论也很多,肯定的认为其代表时代进步思潮;否定的认为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带来了激进主义思潮,导致伦理丧失道德崩溃虚无主义泛滥。我认为,学者张旭东的观点比较公允。他指出在“五四”之前,人们常常把中国经验等同于落后的经验,而将西方经验目之为进步的象征,由此就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陷入了“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五四”将“中西对立”转换为“古今对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五四”成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从此可以“既中国又现代”。
关于百年新诗的争论同样如此。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15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的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甚至有些尖锐地说:“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而鲁迅在留日时期写过《摩罗诗力说》,对诗曾寄予很高的期许:“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甚至以写新诗而著名的流沙河,也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是中国文化再次复兴的一个征兆。
关于百年新诗的激烈争论,何尝不正是中国现代性之复杂的显现?这些问题何尝有过共识?这种复杂的现代性也体现在一些新诗的代表性人物身上,或许结合他们来作分析,会看得比较清楚。在这里,我试以北岛和昌耀作为分析对象,来探讨此一问题。
北岛被认为是朦胧诗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启蒙精神和批判性,北岛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对旧有的虚假空洞意识形态表示怀疑,他质疑:“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他更进一步公开喊出:“我不相信”:“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二是对个人的权利的申张,北岛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显示了对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回归。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也得到了部分评论家的肯定,其中尤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其确定追求人性人情人权的准则,从而为其提供合法性正当性证明。但批评朦胧诗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后来被广泛接受的“朦胧诗”命名,开始本是批评性说法和意见。“朦胧诗”一词来自评论家章明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认为一些青年诗人的诗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章明贬称:“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
北岛及其所代表的朦胧诗一开始就遭遇的争议,不能简单地视为新与旧、开放与保守之争,背后所折射的,可能是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难。恰如前面所说,原本是批评概念的“朦胧诗”命名后来居然成为北岛们的诗歌新潮的公认代名词,本身就说明问题,说明对朦胧诗的批评有一定的公众认可度。当然,这样的批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朦胧诗由于要表达一种新的时代情绪和精神,老一辈可能觉得不好理解,故产生隔膜,看不懂;二则可能这种探索因为是新的,表达方式是此前所未有的,因而必然是不成熟的,再加上要表达新的感受经验,中国传统中又缺乏同类资源,只好从翻译诗中去寻找资源,而翻译诗本身因为转化误读等就存在不通畅的问题,受其影响的诗歌自然也就有不畅达的问题,故而扭曲变异,所以“朦胧”,让人一时难以理解接受。
具体到北岛的诗歌,争议也很大。比如有一种看法就认为,北岛其实与其所批评的对象是一体两面,这正是北岛的吊诡之处,虽然他声称反对此前的革命浪漫主义,但其所选择的题材乃至思维方式某些方面很接近其所反对者,只是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所以,他们这一代又被称为“喝狼奶长大的”。他们实质是郭小川、贺敬之们的现代版本加上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且这种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也是二手的。诗歌界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没有灰皮书就没有朦胧诗。已有人考证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其实是翻译诗。而被公认为朦胧诗起源的灰皮书,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高干高知可以阅读的、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西方图书,其中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早期的朦胧诗人们正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得到启蒙和启迪,从此开始他们的现代诗歌模仿和探索之路。
确实,关于北岛诗歌的争论从未中断。即使其诗歌历史地位已经奠定的今天,对其诗歌艺术及成就的批评仍不绝于耳。撇开成见和个人意气,有些批评还是有其道理的。还在北岛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宇文所安就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以北岛为例分析,批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们的“世界诗歌”幻象时,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在塑造“世界诗歌”方面,尤其在第三世界诗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诺贝尔奖的光环有时可以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并且让原本受到很少关注的地方文学暂时成为全球注意力的中心。……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宇文所安还批评某些在西方受欢迎的中国诗人的热衷创作适合翻译的诗作,但缺乏“中国性”,他们的诗歌,遮去国籍,可以看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诗人的诗作,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
确实,朦胧诗本身存在着某种受制于时代约束的难题,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与形式,但因受制于时代和翻译体的影响,再加上表达因时代限制而导致的曲折艰涩,及对所谓“世界文学”的有意识的模仿和追求,诗艺上难免存在欠缺,诗歌表达方式和技巧难免粗浅和简单化。
在朦胧诗抱团以集体面目出现时,昌耀却独自一人屹立在中国的西北角,在青海高原上。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预兆。历史地看,昌耀确实高过了包括很多朦胧诗人在内的许多诗人。朦胧诗有时代意义,这不容否认,但其意义也更多地限于时代,现在重新阅读朦胧诗,隔膜越来越多。读昌耀则不会,昌耀是那种越读越觉得博大深厚的诗人,他的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背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交融共处的地域,有52个民族居住,他的独自一人孤独隔绝的存在背景——高原上的蛮荒与艰苦,还有他在湖湘文化影响下的儒家精神,一种担当感、进取心与建功立业的冲动,和在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昌耀远比一些只是受了一点西方现代主义和革命抒情主义影响的朦胧诗人更耐咀嚼。
昌耀在艺术上也显现了相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无论创作的题材还是诗歌手法都与众不同,比如在《青海的高车》里,他将西北常见的一种普通家庭农用交通工具,赋予特别的形象、价值和象征意义,使之成为了一件美的艺术品,“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是青海的高车呀”,这与凡高笔下的《农鞋》何其相似,揭示出大地的神秘性、存在感、意义和深渊一样的吸引力。昌耀的这种现代感显然是具有天才色彩的,一种天生的艺术敏感和自然的深刻感受力。还有在《良宵》中,“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这新嫁忍受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不,今夜没有月光,没有花朵,也没有天鹅,/我的手指染着细雨和青草气息”,诗人将一个苦难中的平常日子渲染得如此隆重典雅,因其心中有深情的爱和辉煌的美的照耀,还因其贫瘠艰苦的岁月,这寻常的恋情和念想尤其显得富丽堂皇,一个清寒的普通夜晚被描绘成了让人无比留恋珍惜的难忘时刻,散发出无限的艺术魅力。还有《斯人》中那种宇宙意识和孤独感,“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这种空间的孤独感,堪与陈子昂的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间孤独感媲美。而这是在全球化概念还没普及的封闭年代里,昌耀就已敏锐地感受到的。昌耀也不是一味地高冷孤绝,远离人间烟火,他身上还有一种笨拙的试图紧贴时代的追赶欲望,和对人世的热爱,比如他的《划啊,划啊,父亲们》,就很典型,“从大海划向内河,划向洲陆……/从洲陆划向大海,划向穹隆……/……从所有的器物我听见逝去的流水/我听见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我们会有自己的里程碑,/我们应有自己的里程碑”,这样的诗歌里,又可贵地显现出某种时代气象,一个上升时代抗争拼搏的积极景象,被昌耀敏感地捕捉到了,虽然他本人后来被排斥在外,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昌耀显然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的一个方向,那就是一种大地性。而且这种大地性如此有吸引力,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子,比如海子、西川、骆一禾等,他们专程去青海拜望昌耀。在当代诗歌中,朦胧诗更多地代表一种时代意识、批判意识及对西方现代性的追随模仿和学习,也是一种诗歌的方向。但较之昌耀代表的大地性诗歌方向,朦胧诗似乎已随时代而去。昌耀的这种大地性诗歌的方向,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比如对自然和大地的关注,对传统的继承,对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的尊重和吸收,对地域的强调和弘扬,尤其是对神性的维护和膜拜,对民族价值的坚持和捍卫,这些都曾被朦胧诗及随后的后现代思潮等解构掉了,而在昌耀这里得到了恢复和重建,还有其“草根性”,一种立足扎根于大地的写作,一种真正的自由、自然、自觉的个体创造,昌耀堪称新诗百年以来最具草根性的诗人。
昌耀早期,一直在主流叙述之外,他的思想资源应该主要是1980年代以来主流叙事中忽略的民间和边缘文化,这些,却最终将昌耀滋养成一棵大树,这恰恰提醒我们对所谓我们习惯地认为不言自明的诗歌现代知识、现代叙述和现代资源的反省。我们曾完全笼罩在西方现代性的阴影之下,那真的是唯一的途径吗?当然,从另一角度,如果没有现代性的背景,没有对现代性越来越深入全面的认识,昌耀这样的孤绝者也很难被接受和理解。
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昌耀无疑远逊于北岛,但在诗歌界内部,昌耀是公认的大诗人,昌耀显示的诗歌现代性的多种维度,启迪了当代中国诗歌。昌耀的意义,在于对此前单一的现代性认识的一个修正。在1980年代单一现代性的叙事逻辑里,昌耀是不可能获得更高声誉的。比如那时对诗歌的最高评价是“洋气”,要“写得比外国诗歌还像外国诗歌”(芒克语)。与之相比,昌耀肯定是有些“土气”的,是有些沉重笨拙质朴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并不只有以西方为标准的那种现代性,还可能有一种立足自身传统的具有主体性同时兼具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美学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我们自身可以本能地判断的,具有亲切感、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的,而这,也许才是真正的中国诗歌的现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