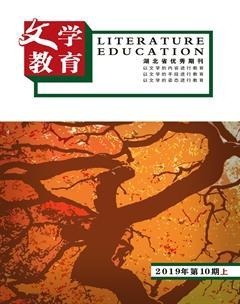荒凉的呼告与“被动孤独感”
在于是的《被动时态》中,出现了早已渗透于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鲜被表现的题材:被“虚化”的书写场域或说被“虚化”的关系。它在一个期刊编辑“我”及其作者“小黑”之间展开,长达二十年。
对于编辑来说,小黑是最理想的合作者:她召之即来,來之能写;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她既可以嬉笑怒骂,也可以通俗时尚。二十年来,“我”和“小黑”之间延续着平稳的编写关系,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以至于“我”从没去查证过小黑是谁。
这一次,引发“我”认真追索小黑信息的是她的稿费被退回来了。“我”决定根据小黑的地址去寻找她。当“我”开着破车抵达小黑所在的城市时,她却了然无痕,再也联系不上了。在她的小区里,“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垃圾站,它装饰着繁多的花卉和绿植,有真有假,一看这就是被当作长期居所多年经营的结果。捡垃圾的人告诉了“我”小黑的地址,但那是一个空荡荡的烂尾楼,无人居住。垃圾站和烂尾楼,这是现代城市典型的空间意象。由此,“我”寻找的小黑的终点成为了一个废墟,一个不存在。
这种“虚化”、“虚无”是现代城市的产物。也可以说,由于现代生活的快速、粗陋、易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全面地改变了。我们看似生活在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里,实则游荡于无法稳固的空间场域,人际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不可靠、不可信。想想吧,在前工业时代的乡土中国,在那个“熟人社会”里,人们之间互相熟知上下三代的人与事,聊起“村庄”的事就像自己的家事,人际关系是恒定不变的。当现代性进程冲击并改变了乡土中国的人伦形态,让大地上的人们纷纷成为都市里一个个孤立的“原子”时,以往那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彻底地被解构了。当人际关系表面上那一小块“熟悉度”被蹭掉之后,裸露出来的灰白、隔绝、恍惚、荒凉才是城市生活的真实质地,这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
作者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城市洁净便利、炫目富有的一面,也看到了现代性承诺所包含的对“人”的全面淡化和降维。在这样一个互不认识、互不关注的世界里,“人”的实有不再重要,只有名字和符号能够带来短暂的安稳。《被动时态》充满了多元的张力和多层肌理,它来自于巧妙的叙事策略。比如小说里那个“小黑”的多重能指。它既指向被“我”寻找的“小黑”,也指向守卫着价值千万的珠宝的保安“小黑”,还有住在垃圾站那一家人养的小狗“小黑”。他们共用着一个能指符号,看似有着截然不同的所指,可又通过与“我”的各种纤细微弱的联系,同样讲述着都市生活的孤独和荒谬。在小说最后,当“我”即将告别垃圾站和烂尾楼时,小狗小黑斜靠着虞美人的花盆,出神地凝视着“我”。它的姿态和眼神俨如“我”寻找的小黑的头像图片,“相似度高到令我持续恐慌。”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小黑”只是烂尾楼里的虚妄存在,那么二十年来,一直与“我”通信、写稿、交流的那个人,“她”到底是谁?又如何解释“她”留下的废墟地址曾经有效地传送着杂志和稿费?或许在作者看来,答案并不重要。其实早在去寻找“小黑”之前,“我”已经对“她”有过一个判断:“她是那么可靠,又几乎不存在;那么像机器人,又似乎最有人性。”这个含糊其辞的结论预告了这场“寻找”将以无解而告终,并且展示着一个荒诞的事实:在现代都市生活里,“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等不确定性才是唯一可以被确定的。
《被动时态》是《花城》的“花城关注”栏目刊发的小说之一。在与专栏主持者何平的访谈中,作者于是提到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BBS开始了文学起步,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在那里获得了书写的自由和自由的书写。令人感慨的是,时过境迁,许多人和被遗忘的BBS一样早已随风而逝,不留痕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动时态”的含义可能更接近于“被动状态”。就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假如“我”通过微信将稿费转给小黑,24小时后,“没有被接收的2013.50元被退回了我的账户。两个‘被字的主语是不同的,但都不是我。”在一个被微信、网络等虚拟空间主宰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存在、“被”生活、“被”修改的。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抗拒。
这是一个荒凉的呼告。它提醒我们,在当下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已经被虚无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此微弱,彼此之间隐约可见,但不可触碰,不可沟通。孤独的人不再是“可耻”的,因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一种都市人的必然属性。用作者于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被动孤独感”。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