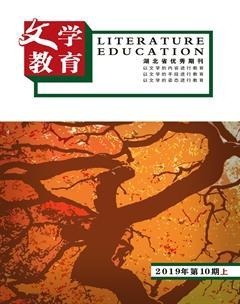被动时态
于是
想起那块移动硬盘后,我又去了杂志社。我幻想着人去楼空的场景,很有主观能动性地为我工作了十五年的大楼覆上了蛛网,推倒了文件柜,还用红色弄污了编辑室的玻璃门,在门内张牙舞爪的僵尸应该就是我本人。
硬盘是用来下载美剧的,这个习惯是我在报社做国际版夜班的时候养成的,那时候家里下载太慢,报社的不用钱,还快,我做完版了,剧也下完了,一集不长,催眠正好,回家看几眼就能睡了。后来报社倒闭了,我跳槽到这家杂志社,做遍了各种栏目,大概从第十一年开始,平媒兵败如山倒,我以为杂志社随时都会关张,没想到靠着两三个土豪客户,这本刊物竟然又撑了三年。现在要下载的东西很少,美剧在线看,所以那块储藏了两千三百部非法下载影视剧的移动硬盘被塞到了抽屉的最里面,最后一天收拾东西走人时,我完全忘了它。
我开锁进门,直奔自己的办公桌,从抽屉的最里面掏出了那块硬盘,感觉像是抓到了自己存在于世的唯一物证,莫名叹了口长气。当即返回,出去锁门。等到电梯开门后,有个穿西装的魁梧男子迎面走出来,我让了一下,突然意识到我认识他——
他总是坐在珠宝盘的旁边,穿一身怎么看都是制服的西服,表情永远介于饥饿和困乏之间。黑丝绒盘里摆满了钻石项链、手链、戒指、胸针……最昂贵的单品会有单独的方盒,比如钻石手表。公关、编辑、化妆师、摄影师、明星经纪人助理会接替出现,挑中某件单品,拿去给明星戴上。一组又一组的照片和视频拍完前,他得保证没有闲杂人等靠近这方价值千万的桌面,还要保证收工时黑丝绒盘上颗粒未少。除非品牌公关来顶班,否则他连厕所都不能去,少说五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
现在的他枉然地按了按门铃,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我告诉他,杂志社已经关门了。他露出诧异的表情。我又说,我知道他是某某品牌公关常用的保安,他又露出诧异的表情。我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是你们主编说,如果我失业了,可以来这里应聘。我思索了一下可能有的各种语境,在珠宝盘周边的各种状况,认定主编不过是开了个玩笑。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小黑。
我笑了,说,我也有个朋友叫小黑。走吧,这里没人了,也不会有新工作。主编都回香港了。
他又问,是主编自己想找保镖吗?我想摇头,但忍住了,又点点头说,有可能,她以前是个挺有名的模特,還拍过电影。
一起等电梯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比他矮二十公分,大概轻二十公斤。我们都是失业的中年男人,但根据我的气场,绝不会有人以为他是我的保镖。我下意识地往前蹭了一步。
他以为我按了一楼,结果跟着我到了地库。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兴趣,就建议捎他一段到地铁站。他再次露出诧异的表情,跟着我上了车。
根据车上的短暂聊天,我在心中描摹出保镖这种职业的侧像。说出来没人信:他从来没有触摸过那些近在眼前的珠宝,哪怕戴着白手套也没有资格。来自农村的他以前从没想过,照片要拍那么久,化妆要那么久。他在心里骗自己:就当是坐传说中的长途洲际航班,舷窗外星空点点,月亮都比地面上看到的更亮。他听哥们说过,在飞机上看闪电特刺激。比珠宝刺激。珠宝都好小,小到贵得离谱,小到让他这样的彪形大汉死守十一小时实在荒唐。
他有个哥们去给明星本人当保镖了,戴着耳麦跟前跟后,戛纳金马,机场酒店,最大的本事是一条手臂挡住一百个粉丝。哥们比他赚得多。哥们保护的是会行走的珠宝。对比下来,他像农夫,守着一块既不属于自己,也不会长出庄稼的田;而哥们像猎人。他像机器人,被设定好了固定动作;而哥们是最高级的机器人,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做出不同的高难度动作。他的工作只是待命,坐在黑丝绒珠宝盘边,让人看到就会想:抢劫珠宝应该很容易吧;而哥们工作时横冲直撞,待命时分腿站立,虽然时常戴墨镜,但总是虎目圆睁,耳听八方,让人看到就会想:应该和这种人保持至少一条腿长的距离。
小黑在地铁站下车时带着憧憬和自嘲混合后的笑容,而不是谋职失败后的落寞。也许是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了。
就是那天傍晚,我接到财务的电话,说有一笔稿费退回来了,是我的作者,需要我跟对方解释一下,再想办法把钱给她。我一看,竟然是小黑的。邮编、地址、收件人名字都没错,从我进这家杂志社开始,小黑就一直用这个地址收稿费和杂志。
对编辑来说,作者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小黑就是我的资源库里最宝贵的源头活水。宝贵到我不忍心将她视为资源的程度。我用“她”这个人称,也许是错的。收件人叫“李德雅”,是个男女皆可的名字。财务有扣税用的身份证号码,但我没问过。我叫她“小黑”,只是因为我们最早在BBS上认识时她就用这个ID。我们从未见过面。
小黑用过很多笔名。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克尔凯郭尔也曾这样,竟然很为她喟叹。在我心目中,若是时光倒转,小黑或许能成为十九世纪的勃朗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甚至古希腊的萨福,但她把这些才华和智慧都用于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媒体,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们是最早混迹于BBS的那拨文青网友,就在不断发帖、日夜回复、时常掐架的那些年里,我基本看清了自己,软弱,无能,没有抱负,终于在某个百无聊赖、穷到交不起网费的日子里,愤然决定去找工作。而小黑不一样,她是那个BBS,不,确切地说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可怕的作者。她似乎不用睡觉,不用工作,又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时候她喜欢写诗和小说,主人公大都是乡野里的年轻人,感官发达,诗意来自动植物、梦境和学识。我在报社做副刊时就开始向她约稿,最放心的就是她。渐渐地,约过稿的网友们都散了,只有小黑坚持到现在,成为我的御用文人。做杂志时,天南海北的旅游稿她能写得极其精彩,让人身临其境;时尚餐饮的稿子她也能写好,好像很懂;我把采访明星的录音发给她,她就能写出一篇比我的采访更高级的专访;新书新电影她更不在话下,观点犀利,风格幽默;尤其是需要观点和论证的大专题,她写得最漂亮,对生活和时代的见解令人拍案叫绝,每一句话都挠到了主编和读者的痒痒。她的文风多变,可冷可热,姿态多变,可雅可俗,知识丰富,不管是掉她自己的书袋,还是擅用网络资源,总之毫无破绽,什么话题和文体她都能驾驭。早年杂志上还有情爱微型小说,她特别会写白领的七情六欲。我观察过她文中的细节,感觉她应该是摩登都市中上层生活的拥有者,就算不是亲身处在时尚圈和富人阶层,至少也耳濡目染,深谙游戏规则。如此二十年,她没有一次拖稿,没有一次被毙稿,还有无数次被我当作救火队员,帮那些拖稿到令人发指的恶劣作者临时补稿,免除我的版面开天窗的尴尬。最可怕的一次是杂志社刚启动那会儿,没有足够的编辑和作者,大概有半本杂志的稿件都是她用不同笔名来写的。
如今是读图时代,大部分人的脑神经只与视神经相连,像我这样偏重文字的编辑越来越少了——要不是那个摄影师转行来当编辑的姑娘嫌工资太低,她铁定抢走我的饭碗,而我就可能沦为自由撰稿,和小黑这样的选手在同一片文字海洋里沉浮,而我必然是最先沉没的那一个,要不然,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选择当编辑呢。话说回来,小黑写得那么好,但除了我,大概也没有更多认真读她作品的人。说是作品,也很勉强,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用“沦为”这个词呢?
现在回想起来,真正最可怕的是:我竟然没有见过她。在所有人从QQ、MSN转场到微信后,我发现,她的微信号没有开朋友圈,头像是一只黑猫,名字是小黑。不论黎明还是子夜,她总会在一天之内回复我工作上的事。我跟她说过,现在不用跑邮局了,可以转账,但她坚持说她喜欢去邮局,可以给她正当理由去外面走走。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退回来的汇款单上的地址读了几遍,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手机导航目的地栏。她距离我528公里,在不堵车的情况下预计行驶6小时10分钟。手机地图上出现一根毫无美感的绿色粗曲线,意味着冒昧、犹疑、隔阂,以及迟到的关注。
我先去车行,这辆车跟了我十年,是离婚时唯一留给我的财产,活像一匹苟延残喘的驴。修车工里里外外地检修时,我抽着烟,心里盘算扣除今年的房贷、保险、给父母的生活费、给前妻和儿子的生活费,还有多少积蓄能让我闲多久。无论如何,总能负担得起闲两三天,跑个一千公里。更何况,是为了小黑。自从保安小黑出现后,小黑的形象好像突然扩容了、具象了,这个名字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犹如我存在于世仅存的人证。
出发前,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说我会“路过”她的城市,可以“顺便”把退回的稿费带给她。没有回复。我们上一次沟通是我通知她杂志关张了,她留下的最后一个符号是小刘鸭说好吧。
导航让我走一条启用不久的高速公路。有一次我们的旅游版做的是拉斯维加斯,小黑写的是:那是全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快到每个月都需要新地图。我加了“据说”二字,因为我懒得去查证,也没必要。就像将近二十年来我都没去查证小黑是谁。
有一部分原因比较堂皇:如果我喜欢一本书,就尽量不去认识作者本人,离得越远越好。我既不是太史公,慨叹高山仰止,便“想见其为人”;也没有迷妹体质,与偶像共呼吸同室空气不会让我心跳加快,相反,只会觉得双方都将死得更快。这是我在做报纸时得到的结论,那阵子我采访了一些当红作家、得奖作家、外国作家,我发现自己对不喜欢的书的作者特别宽容,他们的笨拙会让我觉得亲切,他们的狂妄会让我开心,他们的腼腆会让我怜惜那些我不喜欢的书;但如果是我喜欢的书,作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毁掉我之前阅读时的欣喜、崇拜或遐想。这比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你讨厌的演员毁掉你喜欢的角色,更残酷。
还有一部分原因比较实际:每天每月连轴转,要出差,要应付和维护各种人际关系,要和时下热点保持同步……还要腾出时间恋爱、结婚、生子、婚外恋、离婚,不可能像当年逛BBS那样每天都有时间和精力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仅仅是好奇心,有没有建树都无所谓。所以,我对小黑的好奇在前几年里逐渐走高,但当我们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合作方式后,又逐渐下降——原因参见上一段。
截至目前,我所有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小黑是被我保护得最好、维持得最长久的一个人。一开始我会把她推荐给别的编辑,后来就不了,坚定地让她成为我的私有。我问过她,有没有别的杂志找你写稿?如果稿费更高,你会不会就不要我了?她在Q上回答,当然有,但当然不会。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网聊也涉及过一些私人问题,例如生病、养猫、过年之类的,但都点到为止。要保持亲密友好但不越界的分寸是很难把握的,但我恪守了原则。越是需要她,越是在意她,越要不冷不热,美其名曰:专业。
很多往事突然浮现出来,像一群冒着泡儿的锦鲤,听到了我内心的响动而凑过来,等待投喂。我想起有一次夜里催稿,她竟在同一分同一秒交稿。我想起离婚前去日本度假,看老婆给闺密买了些小礼物,就要了一份打算寄给她做新年礼物,回国后却觉得很矫情,随手送给了同事,结果搞出了婚外情。我想起有一次写大稿,我坚持讲电话才能讲清细节,她拖延了很久,最终我還是用打字的方式说完了,所以我们也没有打过电话。她对我的工作了如指掌,清楚每个月什么日子交什么稿,尤其和我们这个鬼行当一样,习惯了提前两三个月的思维——国庆时做圣诞的稿,圣诞时做春节的稿,永远假装活得超前。她默默地、无意识地收纳了我大部分的自私,却近乎无私地回报我。
想到这里,我降低了一点车速,好像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省力——将人拖曳的滞坠感。进入邻近省份后,我在服务区上了厕所,吃了简餐,抽了烟,买了水,继续开。我很久没开长途了,眼前的景色似乎没有变化,新是很新,却只是新的荒芜感。在这个格式化、再被量化的世界里,我以110公里的时速向她靠近,似乎同时在清理内存。
油门踩久了,有种不是自己在开车的错觉。我突然想要一辆可以定速自动驾驶的新车。在最后一次进入服务区时,我突然想到,也许小黑就是个定速自动书写的机器人,而我突发奇想要去找她,就是因为需要发生基因转化,把自己也变成机器人。事实上,我早就在变成机器人了。虽然供职于媒体,但我对世事的厌倦与日俱增,越是娴熟于无休止的敷衍,越是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恐怖。对世人也是如此,只有像珠宝盘旁的小黑那样宛如无影人般的陌生人类才能引发我稀少的好奇心。小黑也宛如无影人,但唯有她确凿地烙印在我的时光里。也许是因为现在的时光喑哑下来,别的物事连同影子全部消失,她的烙印才突然让我的视野有了焦点。
她是那么可靠,又几乎不存在;那么像机器人,又似乎最有人性。
离开高速后,顺畅地进入市区,因为走的是高架路,对这个城市的地面景致毫无概念。导航让我下高架后右转三百米进入小区。门口有保安,但没有拦我。根据那个地址,我把车停在两分钟后。
露天停车场在楼间的空地上,树很旺盛,听得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她一直住在这里,想必这些树也跟着她一起成长。我下车活动腿脚,抬头盯着树影间灰蒙蒙的天空看了很久,树不置可否,对我的进退两难,树莫衷一是。
唐突也罢,诚恳也罢,我关掉导航,看了看微信,依然没有回复。就在我即将离开树的荫庇时,叶间滴下一颗雨,打中了我的前额。我再走几步,雨滴的密度便开始加大。我再走几步,像是为了测试雨的大小,其实是为了离车远一点,迫使自己往她所在之处更近一点。雨水啪嗒啪嗒打在外套上,我又走了一会儿,直到脸上的雨水汇聚成滴,滴落在领口。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个垃圾站。
任何小区里都会有的垃圾站,但这个异常美丽,因为主人在门头、门框两旁、屋檐上下摆满了花卉,植株高低不同,花盆大小不一,再仔细看就会发现花有真有假,真花细弱摇曳,假花冷艳高挺,仙人掌开花,文竹层叠,绿萝从屋顶垂到地面,姹紫嫣红,虚实互补,摆放得也错落有致,显然是主人多年搜集且经营的成果。我脱离自己,幻想有一个镜头摄入全景和我的背影,跨页彩图,标题刚好可以压在一排花盆下用米黄色马赛克铺的屋檐上。然后呢?当你的眼睛适应了满地脏水和艳丽花卉的对比,就会注意到黑漆漆、空洞式的内景里堆满了一袋又一袋打包好的垃圾,一捆又一捆扎好的废纸,冲洗好的垃圾箱一只接一只排立在门口,站外的建筑垃圾堆成小山,最上面横卧着一只肚子被捣烂的一人高的大熊公仔……因为是平面媒体,你不会闻到任何气味,但雨中的我清楚地闻到了馊水、汗臭、霉菌、砖土和花香。
但连我也没发现阴影中的人。主人。她穿着油布围裙和雨靴走出来的时候,我才好像意识到这是某种现实。从上到下,她的每一寸颜色都是不单纯、不饱和的。她让我觉得视线找不到焦点,甚至无法在灰白棕黑的乱发间、混着污浊和岁月的深浅褶皱间捕捉到她眼神中的确切含义。我开口说,你好。她弯下腰,翻捡一只垃圾袋里的东西,扔出了一节五号电池,落在左边。我又说,请问!她又扔出一截鱼骨头和一团沾了酱油和米饭的纸巾,落在右边。我问,95号往哪边走?她扔出一本杂志。我们的杂志。最后一期。啪一声,落在了她身后的阴影里。主人举起右手指了指。我盯着那本杂志看了几秒钟,转身离开,幻想那片阴影里囤积着有史以来的一切书籍报纸和杂志。
雨越下越大,我从20号走到40号,外套和长裤已湿透,从50号走到70号,眼睛里都进了雨水,我不得不低下头,加快脚步。脚下越来越泥泞,树木和花草似乎已远离了我。狼狈敦促我不要再拖拉,唐突也罢,诚恳也罢,我们已经走过了终点,被啪的一声扔进了阴影,还有什么可畏缩的呢。从80号到90号,我一路小跑,一部分是因为雨,一部分是因为困惑。我似乎已离开了那个整饬良好的小区,进了一个尚未完工的工地。95号在小区的最深处,其所在的那排楼灰扑扑的,外立面只是裸露的水泥,洞开的窗户没有框也没有玻璃,从敞开的大门口可以直接望见水泥楼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滂沱的阵雨戛然而止。我想我是傻站了一会儿,因为非但雨停了,连太阳都出来了,把我的影子照在门阶上,曲折成了三段平行的黑影。我和财务核对了一遍地址,没有错。又问小黑,你到底在哪里。等了几支烟,都没有回复。
往回走的路变得很长。我开始放肆地猜测。小黑用这个地址已整整十五年乃至更长时间,那杂志和稿费究竟去了哪里?从泥泞走回绿草坪和车道、人行道的过程里,我想起于斯曼写的那位逆天的独居者,疲倦的享乐主义者,德泽森特公爵,他定义了隐居者的高雅配色,重新定义了花卉的格调,还在乌龟的背上堆满宝石,直至它无法动弹而死去。在小说里闭门不出的人,除了公爵,就只有病人、死人、囚犯和宇航员。所以,小黑在哪里?她要隐瞒什么吗?我曾以为她是追剧成瘾的宅女,或是每天购物煮饭洗衣打扫育儿的家庭主妇,在厨房里写文章,有时像阿连德,有时像门罗;也曾想过她应该是个懂得发挥才智的富二代,所以从不计较稿费多少;最大胆的猜测是她是专攻人类文字学的外星人……但此刻的我被剥离了所有装饰——而非尚未建成——的钢筋水泥板楼格式化了,突然转变了思路,怀疑她是不是有肢体残疾?过气的明星?被毁容了?
我回到姹紫嫣红的垃圾站,主人还在翻捡垃圾。我直接跨进以绿萝为标志的边界,跨进那片阴影里。主人微微转身,看了看我,但我找不到她逆光的眼神中的確切含义。我已在高高低低的一堆废纸板和破报纸中了,用脚尖拨开一沓超市免费目录,在几张社区报下面看到杂志的一角,把它抽取出来。我问,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主人反问我,你去那边干吗?谁不知道那一片烂尾楼空了十多年了。
我拂去沾在杂志上的食物残渣。我注意到封面明星戴的钻石手表。我想起校对订正的一处错误。我看到小黑写的大专题标题压在明星的胸部。
主人又问我,你不住在这里吧?我没见过你。
我注意到她总是自问自答。我把杂志夹在胳肢窝下,掏出烟来点上,也递给她一根,再把火机凑过去帮她点上。火光照亮了她上唇的浓重汗毛。我们安静了一支烟的时间。把烟用力掐灭在垃圾箱边沿的时候,她又说起话来,而那些烂尾楼的故事是如此千篇一律,都有一两个欠债跑路的老板,总有维权的弱势群体,我听了几分钟就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便扯开了话题。
她又开始说自己和烂尾楼平行发展的这些年。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出工,骑着三轮车把装满的垃圾箱拉回来,换上清理好的空箱,下午五六点再来一圈。余下的时间都在翻捡、分类,除了可食用的现成食品,别的日用品都可以捡到八成新的,被淘汰的锅碗瓢盆、衣服和铺盖可以让她的一家人一年四季不停地换。儿子把孙子接过来后,从幼儿图书到硕士参考资料一应俱全,根本看不完。儿媳妇啥也不干,只管做饭,打游戏。这时候,从我们眼前驶过了快递的三轮车,车斗半满,在主人眼里全是能换钱的纸板箱。废纸涨价了!
我看了看手机,惊讶地发现她把全家的事都讲了一遍,但这个世界只过去了十分钟。没有回复。临走前我问她,邮局在哪里?物业呢?她抬起左手指了指,出大门左拐再右拐,但现在都关门了。
我走出那片阴影时,胳肢窝里依然夹着最后一期杂志。我把车开出来,再次经过垃圾站的时候,看到从阴影里接二连三走出主人的老公、儿子、儿媳、孙子,还有一只硕大的黑猫。儿媳手中有只锅。孙子手中有本彩绘书。我看着真假花卉框定的这幅全家福,如同观赏平行世界里自己的一生。我在后视镜里看到黑猫跟着车跑了几步,还听到儿媳大声喊:小黑,回来!
邮局关门了。对面的火锅店都开始做晚餐的生意了,热气羊肉摆在户外的案板上,刀起刀落。现在我有理由怀疑被斩的那只羊也叫小黑。在这个所有景物都让我无法产生叙事渴望的城市一隅,我第一次想到,小黑也许只能做我的作者。她写了那么多文字给我,但在那些文字由生到灭的整个过程里,她和我都不存在。存在的是这条街,这座城,这个兼具大规模和无意义的世界。
我开车在这条街上跑了个来回,看到所有店面的照片都是灰底色、统一字体,因而提醒自己这是一个监管力度不小的城市,所以,千万不要乱停车。我决定把车停在千篇一律的连锁酒店的停车场里,办完入住再步行去千篇一律的饭馆。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即兴决定的生活了。多年来,每一次出差都入住有客户关系的新兴酒店,有至少体面但未必美味的三餐和酒会,习惯了在酒店大堂和别的杂志社同行热络交谈,习惯了临走时带上资料包、礼品包和现金红包。这家廉价酒店的房间散发着潮湿的霉味,没有散尽的烟味吸附在所有布料上。我像主人一样自问自答,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像样的酒店住下?因为我累了,因为这里离线索最近,因为这是小黑的地盘,因为我需要回到某种根本就属于我的世界。
热气羊肉膻味很重。晚上睡得倒很好。但我醒来后,苟延残喘的车就再也发动不起来了。我步行去邮局时是正常营业时间,里面坐满了各式各样的老人。有的坐着轮椅来,大多数都戴绒线帽,尽管已经快夏天了。穿着制服的保安很热情地指导我取号后,更热情地劝我放弃等待,因为附近小区的老人都会挤在这两天来领退休工资,我看了看号码牌上的数字:在此之前等待人数56人。其实我不用拿号码,但我还是找了个空位坐下来,仔细打量每一位老人家,继而感受到自己对世间的好奇心在端详集体面目的考验中像阳痿般偃旗息鼓。直到听完一位老太太详细问询了如何用积分换取食用油后,我终于忍受不了老年的逼近感,起身到柜台询问,能否与负责那个小区的邮递员面谈。说明来意后,我只能继续等待,等到老人家都快走光了,等到保安已经不对我热情微笑了,才见一位女经理从玻璃封闭的柜台里走出来。她流畅地回答我——
负责那个小区的邮递员三个月前因病离职。根据查到的记录,95号503室李德雅的所有邮件和稿费都是由家人代领的,手续证件一应俱全,除了两个月前发出的这期汇款共计2013.50元,新邮递员发现那是个无法投递的地址,遂在第一时间退回发件人。本邮局没有任何可指摘之处。若有失踪人口或诈骗嫌疑请立刻拨打110。
我当然没有去警察局,但在警察局门口徘徊时,我决定再等几天。也许去物业可以找到业主,大不了最后用微信给小黑转账。我说过,我是个软弱的人。
后来的几天里,我对自己和所有人说,逗留在那儿是因为车坏了,第一个车行的人说发动机完蛋了,没法修;第二个车行的人说可以修,但把车拖去后,整整五天都没有修好,后来,老板索性叫我把车卖给他。他说,都开了三十五万公里了,好歹换点钱,你总得回去吧。
后来的几天里,我用文字问小黑:在我回去之前,还有机会见一面不?人生有几个二十年?人生有几个同甘共苦的知音,能一起目睹一个时代的结束?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煽情的话,但最终都消失在删除键下。被掩埋的,必须是我所能自控的多情和怀旧。转账后24小时,没有被接收的2013.50元被退回了我的账户。两个“被”字的主语是不同的,但都不是我。
处在被动时态的那天,我在小饭馆点了一盘水饺,边吃边听后面一桌的聊天,大嗓门女人对小嗓门女人说:你别以为那是爱,有时候人分不清什么是爱,什么是安慰,有时候人狠命去做一件事,只是因为他做得到,但不说明他爱做……
那阵子,我每天都步行去那个小区,只奉献脚步和沉默,不求答案。我开始习惯那片惨淡的烂尾景致,甚至有点喜欢走进那些恍如末日世界的楼内,声音被奇怪地放大,沙砾在鞋底的摩擦显得忍辱负重,咳嗽的回音听来意犹未尽,抽烟时的呼气显得暧昧。是因为独占,所以有了近似安全的归宿感吗?文学史上的畸零人都会喜欢这里,粗糙的隐世变得诱人,只是,让那位公爵情何以堪啊。
我以顺时针的方向,命名了95号5楼的第三户为小黑的家。房型不错,客厅、卧室和书房都朝正南,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确认过。我用意念布置了书房,把曾经在家具城看中但买不起的那套美式胡桃木转角书架搬过来,尺寸都不用量。我认为小黑应该不会使用苹果电脑。我实在无法猜测她喜欢什么样的卧室寝具,只能让那个房间空着。厨房就好办了,她配得上最好的烤箱、蒸锅、炒锅和漂亮的餐具。事实上,每次进那个房间,我都会联想到不同国家的美食,摩洛哥鸡肉塔吉锅,日式寿喜锅,美式烤牛肉汉堡,法式牛尾汤,西班牙火腿冷盘……我并不是贪吃的公爵,只是坚定地认为,优良餐饮有益于写作者的工作。然后,我才会让小黑在书房里写出属于她的杰作,今天是部电影剧本,明天是本传记小说,后天也许是一摞留白很多的诗集。臆想丰足后,我就会离开那套空屋,在下楼时幻想一下和她的情人擦身而过,那人会比我高二十公分,重二十公斤。是的,她必须做爱。是的,她需要给自己布置一个让想象力、认知力和生命力共同生息的环境,以便供养文字,还有我这样的编辑。是的,她和我之间的沉默关联还将继续保持,如同这空楼在世间的短暂存在,灵魂深处有泥泞但仍是干净的……想到这个地步,我就自嘲地敦促自己快点滚蛋,带着微笑,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烂尾楼。意义在无意义中得到歌颂,想象在无法想象中得到满足。
我既没有去物业,也沒有去居委会,但每次都会经过姹紫嫣红的垃圾站,和主人打声招呼。她总是在重复那些翻捡、冲刷、捆扎、堆叠的动作,俨如下凡的西西弗斯。根据所有侦探小说的逻辑,主人应该是最了解这个小区的人,因为垃圾包含了所有真相。只有主人和生活是零距离的。但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向她打探,她倒着急地先来问我:听说你的车坏了?咋不卖给我们家呢?我就笑了。
没了车,我觉得人生在世很虚弱。每天都不出这个小区所在的街坊,竟然会走十几公里的路。我在菜市场外的衣帽摊上给自己买了新内裤和新跑鞋,挺舒服。我每天都要经过邮局、饭店、水果摊,最初东张西望,后来却眼盯脚底,因为总有人叼着烟、斜着眼、或冷笑或呆呆地望着我,似乎从保安到经理,甚至到那些戴着绒线帽的老太太都知道我在寻找小黑,而小黑根本不想被我找到,甚至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落在我身上的这种目光是有黏性的。这么多年来,在自我感觉优越的主编、目不斜视的明星、日理万机的高管和所有领先于时尚市场的采访对象面前,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好像马上就能打破某种安全边界,所以,威胁就从四面八方而来,像警示,像威胁,也像嘲笑。而这种感觉最终延伸到了无人之境。可笑的是,我至今仍以为那是无人之境。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95号5楼,走上楼梯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白色泡沫粒子散落在地。但没有一颗粒子抵达6楼。我们都止于5楼。我开始怀疑有人在楼里,身上感觉有如蛛网蒙住,轻微的黏坠。我喊了几声,没有人应。我走进意念中的书房,猛然看到地面上摆满了杂志,每年十二本,依次摆放成一列,一共十五列,一百八十张明星脸在水泥地板上反出冷光,还有很多泡沫粒子滚落在周边,或被静电吸附在铜版纸利刃般的页缘,颤颤巍巍暗示着这些古董曾被尘封在何处。最后一期也在。被惊吓到的我心跳加快,胸腔里如同溺水般憋闷,充斥了难以言喻的各种情绪,不明白自己是恶作剧的对象,还是被回复的提问者。也许是我的好奇让谁高兴了。我很仓皇地离开了那栋楼。
最后一次经过垃圾站时,我看到主人和儿媳在给孙子洗澡。小黑斜靠虞美人的花盆,出神地凝视渐渐走近的我,那种姿态和眼神俨如小黑的头像图片,相似度高到令我持续恐慌。由远而近,我看到她们在白铁桶里倒上热水,再把孙子放进桶里,只露出惊悚浮现在白茫茫水汽中的小脑袋。远远看去,她们好像在煮小孩。
(选自《花城》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