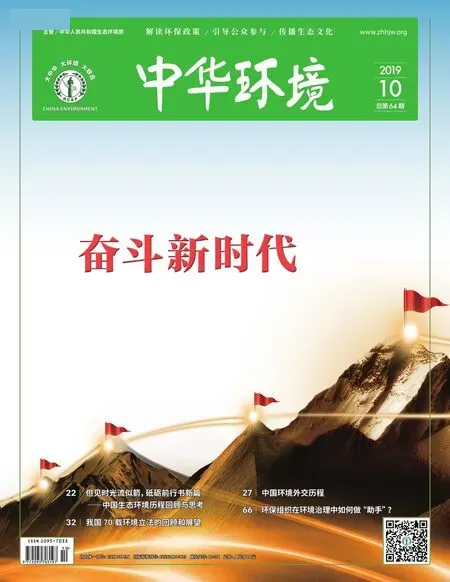论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保护
文 马明飞 马佳楷
对于如何处理水下文化遗产,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可能的建议。第一是创立区域协议;第二是创立一个新的公约;第三是增加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将分别基于港口国管辖、国籍管辖、船旗国管辖和领土管辖。
从古至今,浩瀚的海底,有难以计数的宝贵人类遗产,这些遗产沉没在近海或公海海底。在处理这些水下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可能需要与别国进行沟通、磋商甚至谈判,在确保给予该水下文化遗产最合适的保护的前提下,保障包括文化来源国、历史和考古来源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一国因属地原则对在其水域范围内的水下文化遗产享有管辖权,但这并非意味着排斥其他国家享有的合法权利。因此,讨论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边协议中的国际合作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第149条和303条。水下文化遗产(以下简称UCH)问题最初被提起时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中只有两条与其有关,即149条和303条。第149条位于《海洋法公约》的第11部分,隶属于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是专门解决在国际海底区域内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保存和处置问题的。相比之下,第303条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第303条位于《海洋法公约》的第16部分,并标题为“总则条款”。因此,除了第2款只适用于毗连区之外,其他条款对整个公约适用,并且没有地理限制。这也就是说,第303条第1款的保护义务和国际合作责任,适用于所有海域。
《海洋法公约》中的国际合作责任。如上所述,《海洋法公约》只有两条与UCH有关。为达成一致,这两条采用了很多模糊手法,许多关键问题没有给予清晰的描述和规定,留下许多遗憾。
一是国际合作责任的范围。
在保护对象方面,由于对于考古和历史文物的外延和内涵各国有不同的态度,因此,为尽可能达成一致,公约文本对考古和历史文物没有进行统一定义。
要对考古和历史文物进行定义,关键在三个因素:时间、考古和历史特性、保护的形式。首先,关于时间因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聚焦于考古和历史文物的年龄,即只保护超过100年的人工制品;另一种强调文化价值而不论年龄长短。其次是关于考古和历史特性,有些国家提倡一揽子保护,而其他国家想只保护有重要价值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一揽子保护虽然会使成员国承担较重的财政负担,但能够确保给予文物更全面的保护,而且不必对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进行研究鉴定以确定价值。最后,关于保护的形式,《海洋法公约》第149条和第303条提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似乎并不包括遗址。在公约的准备文件中表明,考古和历史文物是指,“在海洋中发现的各类沉船和相关考古和历史文物。”

5月17日,由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大海道—“南海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展览亮相广东省博物馆,共有400余件“南海I号”沉船文物及馆藏相关南宋时期文物现场展出。图为“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
在适用水域方面。第303条第1款规定国际合作责任适用于所有海洋水域,但是,这不能推论出沿海国有权管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内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第303条的谈判过程可以得出,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不享有类似领海甚至是毗连区内的管辖权,只需承担国际合作、保护考古和历史文物的义务。
二是国际合作责任的内容。合作责任在整个海域内缺乏统一的标准,但本质上它和各国在该海域的管辖权紧密联系。
内水、领海和群岛水域。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其内水和领海及海床和底土均属于沿海国的主权范围。沿海国对该范围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享有管辖权,同时有义务与其他国家合作保护该区域的考古和历史文物。
毗连区。毗连区的合作责任一直不太明确,因为该水域的考古和历史文物的法律地位本身具有较大争议。总的来说,在毗连区,对考古和历史文物的最终决定权属于沿海国。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均不享有主权。沿海国虽然对大陆架上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但这一权利并不包括保护考古和历史文物。
公海。第303条第1款难以确认成员国在公海的保护考古和历史文物的国际合作责任。公海自由的范围包括考古调查,而《海洋法公约》第303条第1款对此没有进行限制,各国均有权在公海上开展考古活动。
国际海底区域。第303条第1款同样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但第149条的规定在这方面属于特别法,应优先适用。在第303条的指导下理解第149条,我们可以推论,对位于国际海底区域的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所有国家都应该合作保护。
综上所述,虽然《海洋法公约》以教诲的方式规定了为保护考古和历史文物的一个总的合作责任,但仅通过该规定,难以将其转化为更加具体的义务和各国的行动标准。
2001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2001年通过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水遗公约》)与《海洋法公约》不同,它是关于UCH保护的专门公约,对UCH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因此对于国际合作问题,《水遗公约》有更详尽的规定。
《水遗公约》国际合作责任的范围。《水遗公约》的条款适用于所有水域,包括内水。与《海洋法公约》相反,《水遗公约》对UCH下了一个非常丰满的定义,其确立了100年的时间标准,接受一揽子保护方式而排除了任何重要性标准。它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文物,还包括与其一同存在的考古环境和自然环境,并强调就地保护。
《水遗公约》国际合作责任的内容。一是领海。《水遗公约》第7条第1款和第3款可以理解为,缔约国对内水、群岛水域和领海内的所有UCH享有专属管辖权;对可辨认的国家船只和飞行器的发现,沿海国应通知船旗国或其他可证实确有联系的国家,特别是有文化、历史或考古联系的国家。二是毗连区。《水遗公约》对毗连区UCH的规定,主要在第8条:在不违背第9、10两条的情况下,并在此两条之外,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303条第2款的规定,缔约国可管理和批准在毗连区内发掘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此时,缔约国应要求遵守《规章》的各项规定。对于没有正式宣布毗连区的国家,适用处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第9、10条。三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的公约草案规定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UCH,享有的管辖权范围较大。《水遗公约》中的第9、10条这种替代的合作系统以通知、磋商和临时措施为基础。但是,该体系并没有明确谁和谁合作。任何能够确认联系,特别是与UCH具有一种文化、历史或考古联系的国家,都能够要求参与到合作进程中来。四是国际海底区域。关于在国际海底区域发现的UCH,《水遗公约》在第11和12条规定了与前文类似的通知、磋商和采取临时措施的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领域制度的两个不同点在于,协调国不是沿海国,而是根据第11条第4款确有联系的国家磋商之后任命一个协调国。同时,国际海底管理局需要被通知,并参与磋商。
双边协议中的国际合作
除了《水遗公约》之外,各国也通过双边协议达到保护UCH的目的。双边协议解决具体的水下文化遗址和文物,它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在一国领海发现的UCH的协议;一类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水域发现的UCH的协议。
在一国领海发现的UCH的协议
澳大利亚和荷兰对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四艘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案件的处理就是双边合作协议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和荷兰之间的有关1972年的老荷兰沉船的协议,规定了荷兰对沉船所享有的名义上的权利和利益予以转让,并且规定文物在荷兰、澳大利亚之间分享。英国、法国和埃及就阿布基尔湾的一艘拿破仑战争沉船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从海底打捞上来的财宝将被运往埃及的物主,但其他发现需要在另外两个国家之间分配。
有些协议也涉及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历史沉船,例如加拿大和英国关于HMS Erebus和HMS Terror的协议。另外两个协议必须被提及:HMS Spartan协议,涉及一艘二战时期的巡洋舰;HMS Estonia 协议,涉及一艘班轮沉船。虽然这两艘沉船都在其沉没之后很快被确认,并且这两艘沉船被作为海底公墓而不是UCH遗址,但它们强化了一种国际合作的倾向。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水域发现的UCH的协议
最著名的例子非泰坦尼克号协议莫属,该协议也是《海洋法公约》第303条第1款和《水遗公约》中有关合作的典型展望。在该协议中,合作责任扩展到了大陆架上。这种相对有限的国家实践,特别是在领海之外,形成了关于习惯法早期形成的讨论。
合作保护责任的问题和前景
关于UCH合作保护责任,主要有三个问题:《海洋法公约》对合作责任模棱两可的规划;《水遗公约》的争议性阻碍了它被广泛接受;双边协议较为稀有。
《海洋法公约》:一个抽象的、模棱两可的制度
《海洋法公约》明确承认各国有义务为保护海洋中的UCH承担合作责任,该公约被164个国家和欧盟批准,对UCH保护来说,具有象征性意义。实际上,虽然UCH保护是海洋法的目标之一,但《海洋法公约》第303条似乎逐渐削弱了这一目标。因为该条款所涉及的内容规定太少,太不清晰。由于它的含糊措辞,有人认为它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标准”。批准了《海洋法公约》的荷兰宣称,“关于UCH保护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国际法可能需要更多的发展”,这正说明《海洋法公约》条款的不完善。因为与具体UCH有联系的国家难以确认,因此,并不清楚哪些国家之间将要合作。
《水遗公约》:一个充满争议的机制

《水遗公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它和《海洋法公约》的关系争议,《海洋法公约》第303条第4款允许达成专门条约,不过第311条禁止成员国通过达成新条约降低公约标准的严格程度,来实现修改或延缓《海洋法公约》的执行的目的。
第二个争议涉及《水遗公约》第9、10条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合作方式的规定。这是该公约谈判期间争议最大的问题,并且第9条和第10条已经遭到了批评。
双边协议:一个破碎的网络
《海洋法公约》和《水遗公约》均鼓励其成员国对具体的UCH保护问题达成双边协议。《水遗公约》要求这些双边协议必须完全符合它的规定,不得削弱其普遍性,但如果协议是在《水遗公约》出台之前达成,就不受此约束。双边协议也被认为是《海洋法公约》第303条第4款明确允许的协议,因此从《海洋法公约》第311条设置的严格要求中豁免。现有合作责任的法律制度的关键问题在于:《海洋法公约》是抽象的、纲领性的,并且没有推行具体的合作义务;《水遗公约》只有55个国家批准,并且它不能约束第三国,而对UCH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却不是成员国;双边协议虽然有用,但它相对来说较为罕见,并且不能整体管理UCH。
可能的解决办法
对于这一复杂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可能的建议。第一是创立区域协议;第二是创立一个新的公约;第三是增加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将分别基于港口国管辖、国籍管辖、船旗国管辖和领土管辖。
区域协议
在地中海,一个区域性的解决UCH问题的协议一直在起草中。2001年《锡拉库扎宣言》强调通过一个区域公约、双边和多边协议地促进来创建地中海博物馆网络等方式开展合作。基于2001年宣言,意大利2003年提出了一个保护UCH的区域公约草案,试图克服一些地中海国家对普遍适用的公约的担忧。
新公约
新公约可以以船旗国管辖为基础,规定检查沿海国管辖权以外的区域内的非法古物交易。用这样一种方式丰富合作责任能够通过法律被清晰体现,并且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广泛接受。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新公约的谈判以及最终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虽然一个新的专门公约能够解决关于UCH的一些棘手问题,但是并不能保证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更多双边协议
增加双边协议的数量是另一种加强合作保护UCH的办法。双边协议能够在对更有意义的遗址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往前推论,从长远来看,双边协议可能导致习惯规则的创立。但它们不应该超出已经建立的法律制度,也不能提出将会导致“管辖权扩张”的主张。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域的或者是双边的协议,均不是万应灵药。它们不能在一夕之间创造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法律制度,因为它们所包括的合作义务只能约束成员国。另外,由于没有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它们会在不同的标准下被适用,除了那些被《水遗公约》附件所囊括的内容,而这些技术标准只约束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