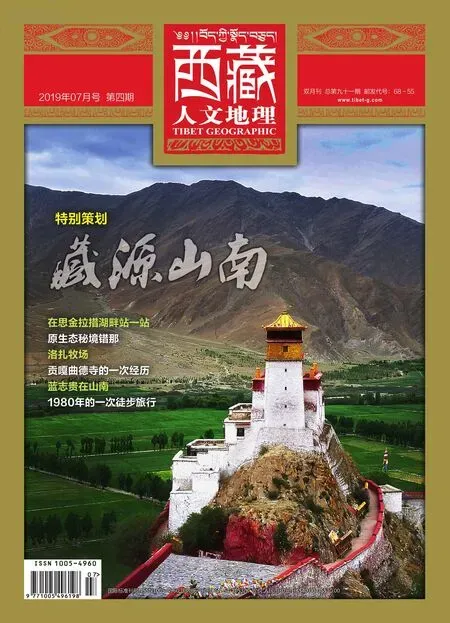牧民曲扎
撰文吴雨初
人跟人真的是有缘分的。很多人问我,你在拉萨怎么会认识加查的牧民曲扎并且成为好朋友的呢?
那是2012年,我们组织筹备办工作人员下去做牦牛文化田野调查,其实一共只有四个人,去了四个地方。次旦卓嘎就去了她的老家——山南市加查县。
听说有一个叫曲扎的牧民特别喜爱牦牛。次旦卓嘎就去找他,先坐汽车到加查县,再搭拖拉机到村里,可曲扎在一个高山牧场上,还有几十里地,次旦卓嘎只好搭上一个牧民的摩托车,到半道上一条小河,过不去了。那边正好一个人要过来,就问她要去哪儿,次旦卓嘎说,她是去找牧民曲扎的,那人恰好就是曲扎。
曲扎就把她接到牧场上去,问起她的来意,次旦卓嘎就把牦牛博物馆的创意设想给曲扎描绘了一番。曲扎特别惊讶,说,怎么这个人跟我想的一样啊?曲扎就跟卓嘎讲起牦牛来,说,牦牛跟我们藏族人生死相依几千年,我们藏族人要是没有牦牛,就跟其他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了。
曲扎养了两百多头牦牛,别人家放弃了的病牛残牛,他也收过来放到高山牧场上去。他说,能想到做牦牛博物馆的这个人不简单啊,我要是有他的照片,就要放到佛堂里供起来,等等。次旦卓嘎回到拉萨汇报时,就专门讲了曲扎这个人。我对此特别关注,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人。
直到第二年,我去加查县,才见到曲扎本人。他的家离县城不远,就在加查县著名的千年核桃树下。我与曲扎虽然素昧平生,可一见如故。他说,通过次旦卓嘎,因为牦牛,我结识了吴老师,您做牦牛博物馆,这是大功德啊,我要尊您一声大哥!
然后,他就从藏族历史、藏族文化、藏人生活,谈起牦牛。牦牛就是藏族的伙伴,就是我们的家人,要是将来牦牛消失了,我们藏族可能也就消失了。
我很惊讶一个牧民能有如此之高的思想境界。听说曲扎不仅是个牧民,也还是农民,不仅做木匠,还会绘画,我就要去看看。他们村的小寺庙,房子是曲扎盖的,壁画是曲扎画的。我马上就问,你会画牦牛吗?他说会啊。我立刻想到,一定要让曲扎在牦牛博物馆留下他的作品,让牧民到牦牛博物馆画牦牛,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014年4月,曲扎真的来到拉萨,我们借鉴寺庙护法殿的风格,在“感恩牦牛”展厅特别设计了一个空间。曲扎问我怎么画?我说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当时博物馆还只是一个工地,堆满了钢筋木料水泥,曲扎带着一个表弟当助手,自己搭起脚手架,就画开了。他只有三天时间,因为他们村到了挖虫草的时节,必须赶回去。
曲扎的画儿画得真好,后来很多前来参观的职业艺术家都感叹不已。他在右边画了牧区的场景,左边画了农区的场景,正面居然无师自通地画了一幅抽象画。——他把牦牛的双角,想象成两座雪山;双角之间的颈峰,想象成太阳;牦牛额头的鬈毛,想象成河流,流淌的河水中还隐藏着藏文的“牦牛”。把牦牛的两只眼睛想象成湖泊,把牦牛的颊骨,想象成崖石立本;从这具牦牛头两侧,铺展开辽阔的原野。

曲扎和他绘制的壁画(吴雨初/摄)
曲扎画画儿没有底稿,就用指甲勾勒一下,但正面这幅抽象画,是他从工地上捡的一张水泥袋的包装纸,打了一个草稿。我请他把这张稿纸留下来。临行前,他在我的住处吃饭,走时匆忙忘记留下了,我赶紧给他电话,他已经坐上长途班车了。后来托返回的班车司机带回来,背面还写了一封信。我让司机米玛翻译,信中写道:“作为一个养牦牛的牧人,我要向牦牛博物馆的吴老师和全体工作人员致敬,你们办牦牛博物馆,就是在传承和弘扬西藏民族民间文化,我们都热爱西藏文化,我们是兄弟,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读着这封信,我忍不住流下泪来。
曲扎走的时候,邀请我到他的高山牧场去看看,我说,好的,一定去。曲扎说,吴老师答应了,我想一定会去的。他的这番话把我架在那儿了,不去不行了。
2015年,我带着北京电视台《牦牛宫殿》摄制组,驱车几百公里,翻越高山峻岭,终于来到曲扎的牧场。曲扎见到我特别高兴,他跟我行贴面礼,很是亲切。
曲扎的牧场海拔很高,只一间石屋,条件特别简陋,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就坐在外面聊天。他说,他现在有三百多头牦牛了,但一头也不杀,只取牦牛的奶、绒,这个牧场上的牦牛会越来越多的。
曲扎那时还用着一部旧式手机,不能拍照片,我去看他时,给他带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曲扎则把他当天挖到的三十根虫草送给我,我坚辞不受,这可是牧民是重要的收入啊,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县城换现金的,但他一定要送给我。他说,他明天还可以挖到更多的虫草。
曲扎还向我透露,他要在加查县也办一个牦牛博物馆,已经买了一万平方米土地,可以让游客来参观,还可以经营最生态的牦牛制品。这个博物馆要请吴老师您当顾问。真的让我彻底晕了!我觉得,这个牧民曲扎真是个天才。如果他在寺,会是一个高僧;如果他绘画,会是一个名画家;如果他经商,会是一个大老板;如果他做学问,会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钟情于牦牛,始终是一个牧民。
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建成开馆后,曲扎一直没能来过。去年终于来了。曲扎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参观,我们很庄重地给他献上了哈达。曲扎看完后,在我们的留言簿上写道:“到寺庙,可以拿到加持过的甘露丸,到牦牛博物馆,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像到了家一样。”我觉得,这是对牦牛博物馆的最高评价和奖赏了。
这一次,曲扎是自己开着私家车来拉萨的。我请他来家吃饭,曲扎一般比较严肃,言语不多,但说起一件事来,连他自己都笑起来了。——曲扎与他哥是双胞胎,他哥是出家的僧人,他们长相极似,如果他哥不穿僧装,一般人是分辨不出他俩的。最逗的是,这双胞胎各有各的身份证,但可以共用一个驾驶证。这个驾驶证是曲扎去考的,兄弟两人谁用车就谁带这个驾驶证,交警绝对搞不清他俩谁是谁。曲扎能听懂一些汉语,但不太会说,这回他用汉语说:“这个,他们,不知道的……”

曲扎和本文作者(吴雨初/供图)
桑旦拉卓读后感
熟悉牦牛博物馆的人,对曲扎这个名字可能并不陌生。
是的,他的确是一个天才牧民,绘画、木匠、畜牧都很拿手,但更让我们震撼的是,据同事姐次旦卓嘎介绍,当牧民曲扎见到一个陌生人,到自己面前,谈论起牦牛文化、谈论起要建立一个关于牦牛文化的博物馆时,他对此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不仅选择了相信她的话,而且很热情地说道“你觉得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以后放在博物馆里展览”。
现在这个充满猜测的社会里能有一颗如此单纯的心是多么的宝贵啊!
这句话让我的同事次旦卓嘎至今难忘,让我们也至今很感慨、感动!立时鼓舞了我们筹备办的工作人员建立牦牛博物馆的信念。
因为曲扎的单纯,他自己也收获了一份可贵的友谊,牦牛博物馆建立了不解之缘。
我们在北京举办展览时,邀请了曲扎,曲扎是一个寡言之人,但是每次谈到牦牛文化、藏族民俗俗文化、他的眼里会放着光,并滔滔不绝的说上好几个小时,嘴角也会漏出难得的笑容,他是那么的热爱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公元十三世纪,拉加里王族为便于地方统治,又将王宫由色吾迁至今天日果曲德寺台地所在的曲松村。(卡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