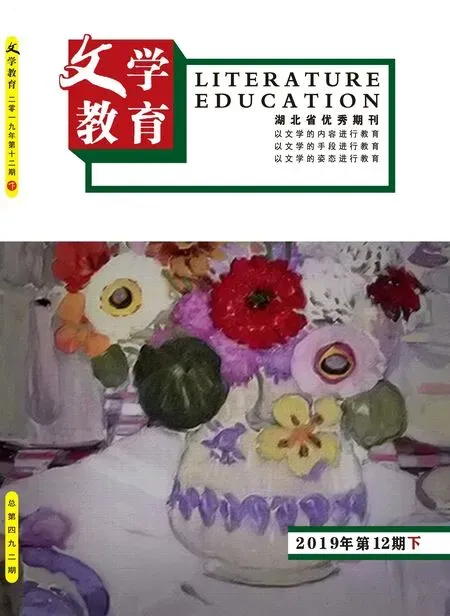畸人意象与庄子创作
谢晓莉
《庄子》一书中存在着大量意象,最为人熟知的无非是大木意象、再有动物意象如鲲鹏、鱼、蝴蝶等,除此之外,还有别开生面的畸形人物意象(下文简称“畸人”)。这些畸人意象体现了庄子以“立象以尽意”为旨归的创作实践,更独立于大木、鲲鹏、神人等意象之外。
一.畸人意象的研究梳理和重新分类
此前已有研究者对庄子笔下的畸人意象做过一些探究,主要是归类和分析等工作,如雷江红的《庄子〈德充符〉中畸人意象探析》和郭晓宁的《〈庄子〉畸人意象的思想内蕴》。孙艳平的《〈庄子〉畸人略论》也大概如此,不过在“畸人”的定义上加入了“心理上的畸形,如精神病类的疯人”,因此在该文中出现了一类新的畸人——“心理上变形的疯子、强盗(也是疯子的一种)、社会越轨者。”1。此外,外部因素也有学者关注。不少人提到了庄子的神巫文化思想与战国诸侯争霸的背景,如乔守春的《〈庄子〉畸人形象论析》、刘成纪的《〈庄子〉畸人四论》等,郭树伟的《论〈庄子〉中畸人形象的地域文化内涵》从历史近、中、长时段三个角度详论了河洛商宋文化对畸人意象之产生起到的影响以及边陲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学者从跨学科角度解析畸人意象的审美意义,如邓心强的《〈庄子〉畸人形象的人学意蕴》,谈到了其对现代人的价值;黄琳斌的《〈庄子〉畸人意象二题》中提到这种意象对后世的文学、绘画等有所启迪,包括形神论的发展和审丑风气的张扬。还有一些硕博论文也曾提到畸人意象,如袁云霄的《〈庄子〉畸人之德》。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对畸人意象重新分类和梳理,探析畸人作为意象时在文本结构中起到的功能。
上文提到孙艳平“精神病患者”也算畸人,这一点往往不为其他学者所采用。本文在分类时则吸纳了该作者的观点。基于此,本文拟将畸人意象分为以下几类:
2.残缺型:右师、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闉跂支离无脤
3.极端型:支离疏、哀骀它、子舆
4.精神型:接舆、盗跖
二.畸人哲学
1.生存——从畸人到健全人
将畸态概括为病症,而非通过章节,抑或是通过外部体征来分类,是因为本文认为庄子进行了意象的“嵌套”,在这种嵌套下,体现了庄子立“畸人”之象以尽意的第一个目的:阐述一种生存哲学、生命哲学,不为艺术而为人的哲学。
书中的其他意象如鲲鹏、大木等都已在神话传说中出现过,甚至成为了植根于人们心中的记忆。而“畸人”这一意象却有其社会基因,代表了庄子的“有意而为”。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已经成为阶级的新兴地主阶级以及与它血肉相连的大商贾和说客游士推动大领主们为建立地主政权而展开剧战”2,这种牵扯众多利益关切方的战争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儒家学说也因此有了立足之地。再结合《庄子·胠箧》中所言,“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3、“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子百家的学说——尤其是儒家,往往被用来维护“违天之性”的政权。侵害他人的行为得到“合法性”,受害者数量急剧增加。《人间世》中的接舆说道:“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知之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甚至孟子也曾言:“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4,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缺一只脚的畸人最多,他们也恰恰是最具现实意味的一类人——“道德社会”的受害人,《韩非子·和氏》中有言:“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因此,庄子着意选择了这类人,组成了上述的“残缺型”畸人,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阐述如何在这个“道德社会”生存的哲学。
纵观这些含有畸人意象的篇目,似乎很多话语都是通过孔子之口说出的,还有蘧伯玉和扁庆子也都是贤人。正因为庄子需要借助孔子等在世俗意义上的“圣人”面目来讲述在世俗社会的全生避祸之道。《人间世》中颜回和仲尼、叶公子高和仲尼、还有颜阖和蘧伯玉之间的对话,其前提都是颜回、叶公子高和颜阖欲“有为”,对于这样的人生追求,庄子借仲尼和蘧伯玉的口说出了“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都是在以孔子这类人为主流的语境下进行讨论的,虽然与庄子的最高主张有些不符,但正应和了文中仲尼所说的“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相比这些人,缺了脚的畸人是被忽视的集体,他们与“形全”的平民共同构成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的第一要务不是“有为”,而是“生存”,这就是他们的“不得已”,庄子书写下与他们相适应的生存方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得已”。
面对畸人的生存状态,庄子再三谈到他们与世俗的来往和肉体上的需求。王骀的“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虽然未必是他主动,但他还是默认了师生关系,否则之后不会提到“立不教,坐不议”,如果王骀无心,何来“教”与“议”的说法?再如闉跂支离和瓮大瘿,游说卫灵公和齐桓公并得到了他们的喜爱;支离叔的目标是“挫针治繲,足以糊口……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对此,《达生》中讲得更明确,“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养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不厌其天,不忽于人,民几乎以其真”,虽要抛开心中之累才能使形体、精神得到休息,但生存资料不能缺少。这和庄子笔下已得道的神人是不一样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可是这些畸人的生存状态已是俗世中人在求道和“道德”社会中所能取得的最佳平衡。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畸人的生存状态?在此庄子进行了意象的“嵌套”,从而赋予了看似只适于畸人的方法以普遍可行性。“心斋”、“坐忘”、“守真”,它们在文中被反复提及,具体而言就是“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是可以从畸人身上得到的经验。但畸人毕竟“畸于人而侔于天”,对于“形全”,即看似无所缺损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是“异己”的。然而通过意象的嵌套,能增强畸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叙述逻辑从“畸人虽形残但德全,健全人虽没有‘形残’这个触发条件却依然可以向他们学习”变成了“无论形是否完整,健全人完全可以学习畸人处于得或失状态下的保身之道”。这样一来,很多畸人之“畸”就被虚化了。《德充符》中哀公问:“何为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中行也”,这里仲尼所提到的世事变幻,几乎可以和畸人身上的“增殖”或“缺失”对应,即无论他们身上是多了瘤还是缺了腿,其本身的实在意义消失,而变成了人们经历过或即将经历的各种得失体验。就像《大宗师》中的子桑思索为何自己处于穷困绝境之中,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面对这种境地,“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德充符》)、“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如此维护命运的本真,才叫“得天之性”。《大宗师》中,子舆生病了,身体发生了如支离叔一样的畸变,于是他大加感慨:“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正是对此的诠释。
2.对“道德”——从妥协到反抗
如果说,庄子为那些处在“道德”之世的人提供的生存方案算是一种对儒家的妥协,那么他也同样通过“畸人”作出了反抗。这体现在畸人意象的纵向深入上——从身体的畸形迈向心理的“扭曲”。对肉体畸变的人的书写,尚处在客观描写的状态。但“楚狂”接舆和“横行天下”的盗跖,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符合“道德”之世的标准,而被看作异类。像叔山无趾,虽因触犯所谓“法律”而被砍去脚趾,然单因形体上的残缺便被边缘化了。盖因他们仍处于一个被人为改造过的社会之中,这也是为何畸人还是畸人,尚未成为神人。《养生主》中说,野鸡若在樊笼之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在之后的文本中隐晦说明了“樊笼”到底为何。《人间世》中颜回和仲尼谈话,仲尼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是皆求名实者也……犹师心者也”,欲有为于世、欲求名实,会造成道德的沦丧,而它们恰好都是儒家追求的目标。当畸人意象发展到接舆和盗跖,则更加直白:接舆直言孔子去到衰败的楚国,彰显自己的德行,不知无用之用,最终只会招揽祸患;至于盗跖对孔子长篇大论的唾骂,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不仅如此,建立在儒家学说上的国家也应该被抛弃,鲁哀公将国家托付给哀骀它,而哀骀它却在不久后就离开了他。《人间世》中谈到支离疏时说:“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所言之“德”,恐怕就是经过人为改造和制定标准的“德”,“其之所以要被‘支离’的内在因素在于此‘德’是被强加于人之性命之情上的”5,《骈拇》中提到“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不是“道德之正”,已经很明显了。庄子刻意在初提到接舆和盗跖之时采用世俗社会对他们下的断论,又通过他们之口表达反抗,鲜明的前后差异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与其他畸人相比,其背后的“意”不再那么隐晦,象与意的黏连度更高,甚至于“盗跖”变成了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名词。
3.畸人——天人之间的道之代表
以上的生存哲学仍属较低层次,是一种“方法”,但哲学家最感兴趣的永远是“本源”、是“根本”,庄子也怀抱着这样的“野心”。道之难言,在书中已被反复提及。自古言意之辨就是饱经讨论的话题。“夫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人间世》),语言不被信任,同时道也难以表达:“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大宗师》)。南伯子葵向女媀问道,女媀说她的学道路径是:疑始→参寥→玄冥→於讴→需役→聂许→瞻明→洛诵之孙→副墨之子,副墨之子(文字)是她的老师,她的“道”和原始且不可推测之“道”隔了七个层次,可见道虽可学、可言、可记,也只是较低层次的道。庄子便怀抱着这种意图——尽可能地用文字表现大道至理,让道的追随者意识到道之本体的存在,也让他们亲近“可学之道”,进而达到畸人那种“近道”的状态,所谓“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庚桑楚》)。畸人意象,就成为了“道”的实体形态。《达生》中的扁子对弟子说孙休是个寡识少闻的人,不应告之以“至人之德”,那样非但不会对他有所启迪,反而会惊吓到他。很多健全人恰是如此,幸运在形体完好,不幸在远离大道,于是庄子树立起“畸人”之意象,来体现道之性——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这种无周正规则之形的道貌,实具有丑的性质,和畸人之形有趋同性”6,来作为普通人和大道之间的桥梁。当然,除开这种有意之外,还有某种无意:传承在宋人庄子记忆中的神巫文化,让他将畸人塑造为沟通天人的媒介,就如古代的巫师:“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7,道—畸人—人与天—巫师—人,堪堪对应。
作为“道”的体现,阮忠认为:“实际上,畸形人物的畸形是庄子有意识设置的中介,……而庄子对正常者的表现是以畸形者的畸形为镜子的,映现出正常者的内心世界”8。庄子以畸人为道之景、人之镜,实际上他们身上有着“静态”的属性。《达生》中的单豹和张毅,一个远离尘世、一个闻名乡里,却都意外死亡,因为“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道不远人、也不近人,或静或动。《德充符》中言:“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然而水是很难停止流动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代表着“道之动”,在《老子》中水也多以流动的面貌呈现——临水自照,在暗涌之中发现凝滞的永恒;以心观物,于脉搏之间保持如一的静谧。而畸人则作为“道之静”出现,《达生》中纪渻子驯养斗鸡,最后达到“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这和畸人是一样的,子产、鲁哀公等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缺乏道性的事实。当然,在评判畸人作为意象时的功能的同时,便已体验了“得意忘象”的过程,不仅畸人忘记了自己的“畸”,读者也将逐渐遗忘畸人之存在。
《系辞上》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9“意象”一词,虽然等到《文心雕龙·神思》中才出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但很显然在此之前的庄子已经拥有了“意象”之意识。他将现实中的畸人摄入脑中,进行改造后再流泻笔端,以至真之人喻自然之道,在道不可言说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建立意象以表达多重含义,对后世的诗论和文论产生之影响不可忽视,甚至使得“意象”从一种在创作中起辅助作用的手段成为众多作家讨论的中心,诸如《诗格》中提到的“意境”、《河岳英灵集》中提到的“兴象”、严羽提出的“兴趣”说,都在寻求意象之外那深远又绵延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