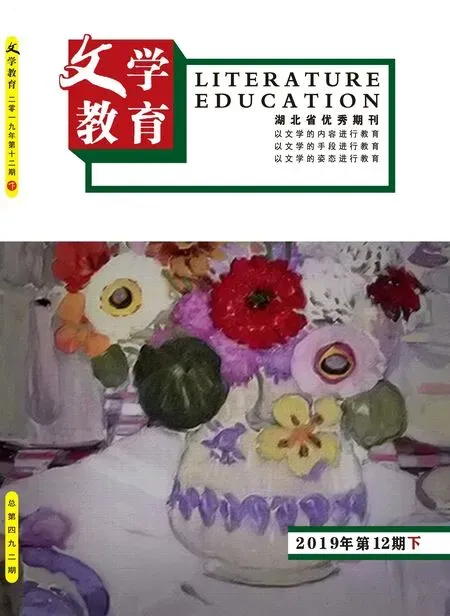以《眼中沙》为例看泰戈尔情味论与印度传统
陈 璐
《眼中沙》是泰戈尔1903年出版的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印度妇女尤其是印度寡妇的生活遭遇。维诺蒂妮刚结婚不久,丈夫因病去世,她不幸成为寡妇,住在偏僻荒凉的村庄中。寡妇拉洁勒克希米是维诺蒂妮母亲儿时的玩伴,她因为试探新婚燕尔的儿子莫汉德尔,回到儿时住过的村庄,在这里她感到很不方便,维诺蒂妮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她非常喜欢维诺蒂妮,暗自心里与媳妇阿霞作对比。莫汉德尔当初不肯娶维诺蒂妮而与阿霞结婚,婚后二人过着甜蜜的两人世界,拉洁瞧不上自己的媳妇阿霞,有时也会为难她。阿霞的姑母安娜布尔娜也是一位寡妇,她不想卷入家庭纷争,自己一个人到圣城敬拜神。拉洁把维诺蒂妮带回家以后,维诺蒂妮故意接近阿霞,与她成为知心密友,两人亲昵地称呼对方为“小沙子”,在阿霞的说服下,莫汉德尔终于答应和维诺蒂妮正面接触。维诺蒂妮心里认为正是因为莫汉德尔没有娶她,她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所以她带着报复的心理勾引莫汉德尔,让他爱上自己。果然,莫汉德尔深深地为维诺蒂妮着迷,准备抛弃阿霞带着她私奔。维诺蒂妮真正喜欢的人是莫汉德尔的好友毕哈利,她向毕哈利倾吐心意,毕哈利也同意娶她,可是宗教不允许寡妇嫁人,维诺蒂妮断然拒绝了毕哈利的求婚,最后与安娜布尔娜一道去贝拿勒斯城,以拜神度过一生。小说成功塑造了维诺蒂妮这个年轻寡妇形象,细致地描绘了她的心灵发展过程,刻画了她敢于反抗的性格,同时批判了印度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作用。
一.情味创作
味论是印度重要的诗学理论,味的内容丰富,最初是指植物的汁液,后来经历了医学味、宗教味和文学味三个阶段的发展。到底什么是味呢?它是一个开放性范畴,随着印度社会环境和文学实践的变化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讲,味是一种审美本质,涵盖了所有的美感,包含着对各种感情的体验和品味,它与情密不可分。婆罗多在戏剧著作《舞论》中写到:“味产生与别情、随情、不定情的结合。”比起味难以概括的特点,情就显得容易理解的多,它一方面指的是指诗意、诗人心中的情以及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别情、随情和不定情,另一方面具有传染和表达的审美意味。由此可见味产生于情,在经过普遍诗意或诗人情感的传达之后产生,同时情作为传达的手段,在激发诗人心中的情并使之大众化后得到的美的感受,那种品尝、欣赏、揣摩美的剩余即是味。
泰戈尔作为浪漫主义作家,他多次谈到情味论,他说:“我一直坚持探索情味文学的秘密”、“艺术的主要目的不是表现美,而是对情味的表达”。1在继承传统味论的基础上,泰戈尔进一步发展了味论。他将味比作情感的汁液,从创作角度分析了味的生成过程,基本体现为以下模式:“外界世界的情感汁液——诗人通过自己情感摄取外界汁液——引起反应变成自己的情感世界——借助优美形式把这个情感世界表现在艺术文本之中”。2他认为味是人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真实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审美关系,外在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态,它作为感情素材,一旦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心灵世界结合,当味的感觉无比强烈的时候,它就要溢出来,这时便产生了创作。《眼中沙》写于1903年,正值泰戈尔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时期的作品因为他在西莱达与下层人民的接触而变得有血有肉,加上国内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他深入地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印度妇女社会地位地下,寡妇的处境尤其艰难,她们被认为是不幸和灾祸的根源,萨蒂制就是对她们的戕害。泰戈尔一直反对赞美寡妇守节和萨蒂制,主张寡妇再嫁,由此他创作了《眼中沙》,思考印度妇女和寡妇的命运。
泰戈尔发展的情味论体现在其创作实践中,它不是外在世界自发地引起人们心中的感触,也不是作者自己的个人感情,它是外在世界结合作者世界反映出来并得到普遍化的感情。维诺蒂妮与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塑造的寡妇形象不同,她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大胆与命运抗争,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女性形象。她将莫汉德尔当初没有娶她作为自己变成寡妇的原因,她要报复。在拉洁勒克希米面前表现出媳妇的持家本事,与心思单纯的阿莎亲近,争取到和莫汉德尔相处的机会,欲擒故纵地勾引他,维诺蒂妮的畸形心理和卑鄙手段令人厌恶。毕哈利是维诺蒂妮真正爱的人,她勇敢地对毕哈利表达爱意。但她明白自己的身份,为了不损害毕哈利的名声,她没有接受毕哈利的求婚,这样的她又是令人同情的。在维诺蒂妮形象的塑造上,投射了泰戈尔对寡妇追求幸福的寄托,但是又残存社会现实无法挣脱的束缚,维诺蒂妮身上体现了真实性和复杂性,是作者塑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
二.情味追求
泰戈尔认为味是人创造的本质体现,人通过情味和形象创造感受着自己的本性,并且不断观察着自己,味具有认识自我的作用。泰戈尔所说的认识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其中之一是“我们通过感情,认识自己,那时客观物质作为次要认识目标与那个‘自己’结合在一起”。3《眼中沙》中的人物都被感情牵引,拉洁勒克希米嫉妒儿子与儿媳整天腻在一起,故意刁难儿媳,她也嫉妒儿子与安娜布尔娜亲近,对安娜布尔娜冷嘲热讽,她的身体每况愈下,阿莎把家务料理妥当,对她照顾有加,此时拉洁勒克希米认识到自己对阿莎太严苛了。维诺蒂妮怀着报复心理接近莫汉德尔,得到他之后并不开心,她发现自己爱的人竟然是毕哈利,为破坏阿莎的婚姻而感到愧疚。阿莎迷恋丈夫莫汉德尔,在他身边委曲求全,这样故意讨好并没能换来丈夫的疼爱,阿莎认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性。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感情丰富但不尽相同,他们随感情的发展变化从中发现和认识了自己。
泰戈尔晚年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更加注重情味的作用,在论述情味的审美特征时,他说:“情味具有永恒性。在转轮王时代,人们所享受的情味,今天也没有被抛弃”。4正是因为情味的永恒存在,才促使我们不断认识自己。文学表现充满情味的内容,情味使诗人的感情得以升华,外部世界得到情感的延伸,透过文学幻想的世界,人凭借感性经验认识自己、定位自己。小说中的莫汉德尔是小资产阶级青年,他整日无事可做,结婚后与阿霞厮混在一起,懒散度日,接触维诺蒂妮后深深为之着迷,为追求她作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伤害了阿霞的心,最后他看到阿霞的善良温柔一直包容着他,于是他悔过自新,不再游手好闲,与阿霞一起到毕哈利开办的为穷苦人治疗疗养的花园工作。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有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莫汉德尔克服身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选择服务劳苦大众净化自我的情感。
《奥义书》中写到:“我即是梵”,我与梵是和谐统一的,要想得到梵的亲证,就需要通过禅定并践行达摩之道,认识内在的我,达到梵我合一。受此影响,在泰戈尔的认识中,梵是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精神本体,是存在的最高理念或是最高真实。而我是有限的我和无限的我的结合,只有无限的我才能与梵统一,因此在认识中我要摆脱有限的我的局限,完善有限的我达到无限,从而接近梵与梵合一。味具有认识自我的作用,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与梵统一,在反映最高真实情况下,泰戈尔对味的论述超越了具体的艺术问题,上升到人存在的本质问题,使味论得以深化,烙上宗教的色彩。《眼中沙》的结局维诺蒂妮去圣城贝拿勒斯修行,与泰戈尔的个人经历分不开,1902年他的妻子去世,转年他的女儿和好友也相继病逝,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意识到人在宇宙中是渺小的,唯有神是永恒的存在和光明的向导,给人以无穷力量。虽然他宣扬妇女解放,但他并不认为男女是完全平等的,面对维诺蒂妮与神同在还是追求幸福的两难抉择时,泰戈尔选择超脱俗世的牵绊,回到宗教中才是最终的归宿。
三.情味超越
印度古典味论主要有八种味,它们分别是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惧、厌恶和奇异,后来优婆咜增加了一个宁静味,但大部分诗学家都认可八种味的分类。泰戈尔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味”,指的是与历史结合的一种特殊味,它在历史背景下表现永恒的人类感情,具有历史情味的艺术作品所描写的真实是永恒的、本质的,体现历史味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最初,历史味是泰戈尔用来分析史诗性作品的标准,后来他将历史味的内涵范围扩大,认为历史味不仅是对历史小说和历史诗歌的思考,“事实上,历史味通盘思考的是美或真理如何穿越时空形成历史积淀,并能不假理性思考和逻辑判断直接为人所接受的问题”,5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并流传下来,为我们所颂扬的作品都具有历史味。
小说《眼中沙》中有鲜明的历史味。就文学题材来说,它表现了印度封建宗教婚姻的弊病。童婚制摧残女性的身心发展,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很早就结婚了,跟随丈夫的意志生活,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阿霞甘心做丈夫的小鸟,莫汉德尔开心她就开心,她生活的中心全部围绕着莫汉德尔。印度寡妇的命运更惨,她们不被社会接受,整日素面朝天苦修以洗清身上的罪孽,安娜布尔娜结婚后八岁开始守寡,她早已把神与丈夫视为一体,凭借修行度日。就文学内容来说,小说成功塑造了寡妇维诺蒂妮形象,她不接受命运的捉弄,努力为自己争取获得幸福的权力,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她的心理发展过程,分析她的不甘心和报复心理,心理描写增加了人物的纵深感和立体感,维诺蒂妮变得有血有肉,集矛盾和复杂于一体,增加了人物的内涵。就文学效果来看,小说结尾维诺蒂妮去圣城贝拿勒斯修行拜神的结尾,加深了作品的悲悯味,读者对维诺蒂妮的结局感到惋惜,印度寡妇守节的礼教问题依旧严峻,作品起到了发人深省的作用。
四.结语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味论的发展者之一,情味是他一直谈论的内容,泰戈尔对味论做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历史味”的概念,将它的范围从史诗性作品扩大到普通作品,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实践着情味理论,《眼中沙》便是一个创作实例,表现了情感支配人物的行为,人物在情感中认识自我的过程。泰戈尔的情味论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中,与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梵我合一”相融通,实现了对情味论的超越。
注 释
1.泰戈尔.《诗人的追述》前言[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13.
2.倪培耕.《印度味论诗学》[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212.
3.倪培耕.《泰戈尔论文学·序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69.
4.倪培耕.《泰戈尔论文学·现实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76.
5.郁龙余.《中国印度诗学比较》[I].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517.
——并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