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的诗意探寻
王东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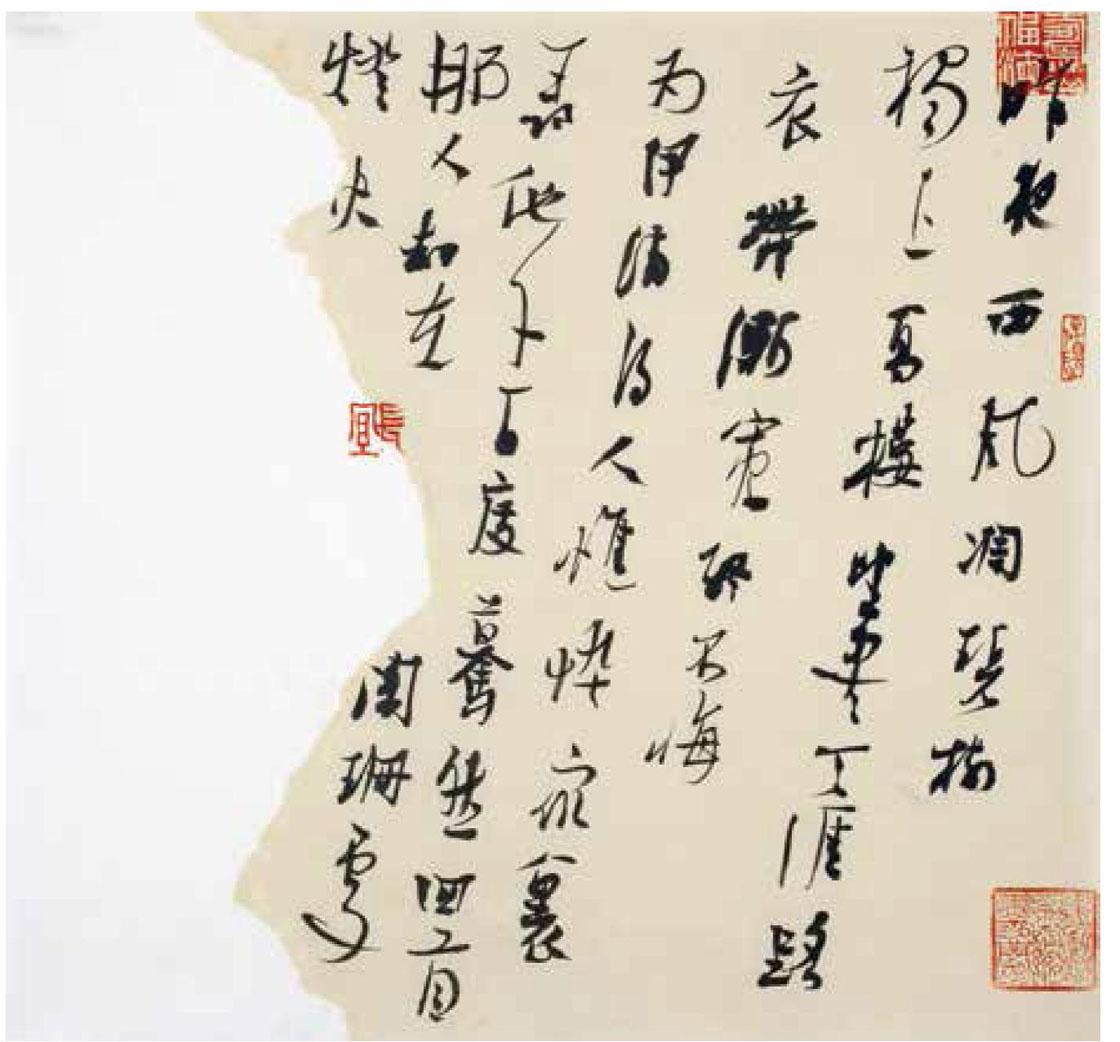
读诗,总是需要某种尺度,以辨识/阐述一首分行作品,是否具有诗的元素,而可称之为诗,或纯只是散文散句,借分行之列,鱼目混珠假冒为诗;或以跳跃语意,断裂词汇,通过晦涩风格,敷衍诗义的玄奥,以致令人炫惑于诗艺的展现,而莫知其乃诗或非诗。因此,常听到有人询问,何谓是诗?
何谓是诗?似乎是存之于新诗伊始的谜语。如五四时期胡适所强调的,新诗必须“明白如话”,也提及“需用具体而避抽象”的写法与“音节自然”功效,以呈现出诗的韵味来。由此可以窥见,胡适在提倡新诗之时,已经注意到了新诗的形成,脱离不了“语言”、“意象”和“节奏”的诗意空间展现。虽然,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置放在提倡白话文的基础上开展出来的一套初浅作诗理念,但大致上,新诗的创发,却一直以来离不开这三大元素组成。不论后来闻一多和新月诗派所倡导和实践的“新格律诗”,或新格律诗倡导者们试图回复古典诗歌那份因语言蕴藉、精炼和含蓄所获得的独特美感,以反拨胡适“明白如话”的语言表现,并突出了音乐性和语言构成的诗意表现,都是在这面向上为新诗寻求一个诗质的提升。
即使后来一些诗人对新格律的修正,强调语言和谐自然下,音律内化的节奏感,更能撼动人心,而非形成外在格套式音节所能比拟。如王独清的作诗公式法:“(情/力)+(音/色)=诗”,以此阐明诗人内在性向和情感认知所形成的音律和语言是难以割分,不论以口语为中心,或言文一致,诗人的精神气质和情感向度,还是往往决定了其诗中语言音色的表现。易言之,新诗自是无法回到古典诗那样以格律作为体系的形式呈显,而只能在自由体中,以诗人的情感和生命气度,形成诗歌语言的内在节奏,并由此组构出诗的诗性空间来。
同样的,新诗语言的追求,从“话怎么说便怎么写”,到徐志摩等诗人“语言欧化”的变化,或文白的交杂淬练,口语化写作的呼求等等,都是诗歌言说的种种试探;在此,新诗语言的迁更,几乎可以视为新诗史重要的进程。然而综观所得,新诗每遇到进入浅白外露的表现时,就会被要求含蓄蕴藉,可是一旦过于含蓄而深至艰涩难懂时,则又会要求改成浅显明朗,而在这方面,诗语言往往是被要求改造的首要元素,由此,可以窥探出其间诗歌语言更递角力的演绎,是如何的政治性。而口语的当下(鲜活)性和书面语的固定(典雅)化,两相交错,无疑征示着诗歌语言的相互对峙,以求通过艺术表现手法的加工,让诗意能从中敞开。
但在这里却必须面对一个提问,诗歌的节奏和语言形式,就能彰显诗意的特质了吗?以及一首诗有没有诗意,是由谁来确定?或换另一句话说,诗意是否有其特有的判定标准?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必须从一般定义上来看,何谓诗意?若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说,诗意是:“诗的内容和意境”,以及“通过诗的方式呈现,让人产生美感的意境”。由这两项解说,可以窥探出“诗意”是与“意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惟“意境”之说,诚属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具有道家意识的艺术思维,强调情景相融,意象浑然的瞬间之感。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提出的“意与境浑”说,即强调物我和谐统一,主客泯化的状态,由此而成其为“无我之境”论。这样的“意境”美学,还是要归入虚静之心,才能展现出来。就像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所云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在此,物各其性,使得万物都能纳入自然之中而成为自然,这样才能达到“意无穷”的境界。当然,就某方面而言,这样的诗境,对古人来说,实是一种写诗的理想。
然而,自有新诗以来,“意境”很少会被涉及,毕竟现代的传意,不若古典的情境,生活状态,也不似古代那般具有可以常与自然融合无间的文化空间,或神思灵动,即可进入事事无碍,万物自得的生命世界。新诗,尤其现代诗,在当下的现代语言里,需要去面对一个全新的景观、生活经验和存在情景。故自有其历史和时代语境,不论思维、感觉和表达方式,全然与古代迥异,因此“意境”在现代诗里,早已被转化成为“现代意象”的呈现,如三十年代施蛰存在《现代》所陈述的,指出现代诗是一种“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故它的诗意获得,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形式,而是“现代意象/精神”背后,所含蕴的现代意识之深层结构。最好的例子,其實可见于五十年代末,那群被放逐于台湾岛上外省诗人群里,如洛夫的诗作:
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那风声、蝉声
(洛夫《石室之死亡》)
那被强加锯断和隔离的苦梨(以梨之谐音喻指离),呈现了禁锢岁月中的伤痛、苦闷和孤绝,不论肉体或精神的流放,都表现出了诗人存在处境的一份顿挫。诗中的意象,不论是苦梨、年轮、风声或蝉声,都蕴涵了历史记忆和创伤的悲痛,此一情绪,无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性空间。而这样的诗,只有被置于那个特殊时代,才能凸显出其之意义和感染力来。
同样的,商禽以散文形式所呈现的诗作《长颈鹿》,即透过人物心理扭曲和变形的存在状态,展示了生命在禁锢中无可逃避和逃脱的悲凉处境:“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颈鹿栏下,去逡寻,去守候”在此,“监狱”、“动物园”隐喻了国家,“长颈鹿”和“狱卒”成了国家体制下所压抑和互相折磨的人,加上岁月所链结的容颜、籍贯和行踪等等意象,在超写实手法的处理中,展示了此诗在意/境表现上的独特性。是以,在这一代诗人的创作里,诗意的呈现,不再是重复那份饱满自足,或宁静致远的自得之境,反而是形成一种颠覆、断裂、陌异化,以及对生命真相揭显的可能。
所以在现代诗里,诗人能更自由的选择诗意的开展,并因应着各自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以各种技艺和修辞手法,去展现诗作中诗意的想象和生成。例如,对强调文字简洁和情感含蓄的意象派而言,意象的本体,乃属诗意的蕴发,其之情感和内容思维的形象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像庞德的名作《地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