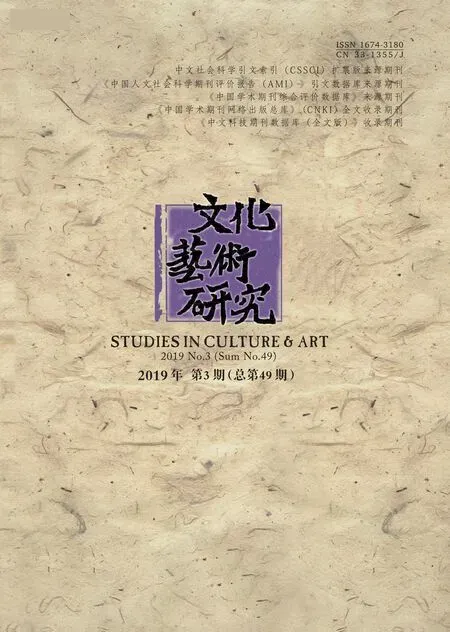从《缀白裘》看清代散出水浒戏的“俗化”趋向与流变态势*
陈秋婷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所谓“散出水浒戏”,指以水浒人事为题材进行表演的单出、单折戏目,是明清戏曲选本重要的择取对象。明清时期经由戏曲编选观念的变迁,水浒戏在书坊刻印传播与民间演出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贴合舞台表演与民间风尚的“趋俗”特征,其文本形态主要保存于《缀白裘》中。现今通行的散出戏曲选集《缀白裘》,乃清代乾隆年间钱德苍编辑而成。该书据玩花主人旧编本增删改订a关于清代钱德苍编选的《缀白裘》是否据玩花主人旧编本增删改订,见乾隆二十九年李克明《缀白裘新集序》,又参见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季永嘉程大衡《缀白裘合集序》云:“玩花主人向集《缀白裘》,钱子德苍搜采复增辑,一而二,二而三,今则广为十二。”只是,此序署庚寅,系用旧序稍改内容而成。又二集《李宸序》亦云:“玩花主人编《缀白裘集》,汇已往之传奇,悦世人之心目。”另有一说,认为钱编本为独立完成,其编目与玩花主人之旧编无关。由于玩花主人编本已失传,难定孰是孰非,本文沿用旧之说法,清之选本乃以明之旧本为依据。,所选剧目以昆曲为主,每剧所选出目多寡不等,又保存了一些花部诸腔的剧本,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所以,以《缀白裘》为考察中心,提取选本体系中散出水浒戏的出目变换、内容取向与编演特性,不仅有助于梳理水浒戏如何被花部诸腔演绎,以及如何在伶人技艺的打磨下形成经典折子戏目与成熟的脚色体制,而且能进一步了解水浒戏在“趋俗”风尚中的衍变轨迹与生存处境。
一、《缀白裘》中散出水浒戏的收录情况
若要考察《缀白裘》中水浒戏的收录情况与文本形态,首要需了解《缀白裘》的演变概况。据颖陶《谈〈缀白裘〉》、吴新雷《舞台演出本选集〈缀白裘〉的来龙去脉》、吴敢《〈缀白裘〉叙考》等文可知,名为“缀白裘”的戏曲选,主要有以下五种版本b参见颖陶:《谈〈缀白裘〉》,《剧学月刊》1934年第3期;参考文献[2],第218—219页;吴敢:《〈缀白裘〉叙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明代后期玩花主人编的醒斋刊本,书题“白裘”,可简称为“明刻本”(此本已佚)c关于玩花主人考论,可参见马晓霓:《吴门玩花主人与其编撰考论》,《戏曲研究》2013年第2期。;
(2)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金陵翼圣堂刊本,书题“新镌缀白裘合选”,秦淮舟子审音,郁冈樵隐辑古,积金山人采新,四卷八册,计选元明传奇、杂剧四十种,约八十五出,乃目前能见到的最早以“缀白裘”命名的折子戏选集,可简称为“康熙本”(不涉水浒戏);
(3)乾隆四年(1739)玩玉楼主人所编本,可简称为“乾隆四年本”;
(4)乾隆二十九年(1764)宝仁堂第一次刊出《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初编》,编者钱德苍。此本历时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编合刊行世,可简称为“通行本”或“钱编本”;
(5)清光绪年间刻本,萧山寅半生钟骏文编刊,模仿钱德苍编本的出书方式,企图选录清代后期新出的戏曲名著,可简称为“新编本”(此书选了二十四折,出自五种剧本,未录有水浒戏);
上述版本中,第一种“明刻本”已失传,第二种与第五种不涉水浒戏,余下的第三种“乾隆四年本”与第四种“钱编本”,此二者收录的水浒戏选出如下:
(1)乾隆四年本(见表1)
此本见路工家藏《新刻校正点板昆腔杂剧缀白裘全集》,题“慈水陈二球参订、玩玉楼主人重辑”,分元、亨、利、贞四集,自《西厢记》至《邯郸梦》凡三十六种,计一百二十折。此本卷首有陈二球序,道出忠孝节义的选取旨意,“不惟有益于身心,抑且有关于风化”,并评介剧中仁人义士虽流离颠沛,但“成忠孝节义至名者,正天地间之大文章也”。a转引自参考文献[2],第206页。其中,涉及《义侠》一剧,则定为“录其义”,可见此本取义之正。
(2)钱编本
编者钱德苍,乃乾隆年间江苏长洲人,于苏州开设宝仁堂书坊。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金阊宝仁堂出版的《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初编》卷首可知,钱德苍据旧本“删繁补漏,循其旧而复缀其新,欲证当世之知音者”。b乾隆二十九年,金阊宝仁堂出版《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初编》,标明“金阊宝仁堂梓行”,卷首有李克明写于宝仁书屋的序文《缀白裘新集序》,此序后刻各本均不载。见参考文献[2]。颖陶:《谈缀白裘》,《剧学月刊》1934年第3期。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缀白裘》十二集编辑而成。《缀白裘》出版后,在翻刻与改辑的过程中形成复杂的选本系统,据台湾学者黄婉仪《钱德苍编〈缀白裘〉与翻刻、改辑本系谱析论》一文考析,钱编本《缀白裘》版本甚多,简而分之,则有六类:金阊宝仁堂系统、武林鸿文堂翻刻系统、四教堂与集古堂共赏斋改辑系统、金阊学耕堂改辑系统、合缀本系统、重组本系统。[1]虽说《缀白裘》版本系统庞杂,但其基本体系仅两种:一为宝仁堂本,二为四教堂本。宝仁堂本先于四教堂本,“如果要考察乾隆时雅部与花部流行剧目的情况,宝仁堂本是比四教堂本更富有参考价值的”[2]209,所以比对两种版本有助于了解水浒戏目的变动特点,试简列如下:
1.乾隆二十九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陆续出版五编,分为阳春白雪、坐花醉月、妙舞清歌、共乐升平。c此处仅列前四编集名,第五编集名惜未见。参见颖陶:《谈缀白裘》,《剧学月刊》1934年第3期。
2.乾隆三十四年(1769),钱氏将之前五编改编增删,名为《新订时调昆腔缀白裘》,第六编名为《新订时兴文武双班缀白裘六编》,共分为风调雨顺、海晏河澄、祥麟献瑞、彩凤和鸣、清歌妙舞、共乐升平。此两种收录的水浒戏目如表2所示:

表2 “宝仁堂”本收录“水浒戏”
3.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编合刊本出版,前六编与乾隆三十四年同,新增后四编为民安物阜、五谷丰登、含哺击壤、遍地欢声。此四编与今通行本同,不录。
4.乾隆三十九年(1774),增入《缀白裘梆子腔十一集外编》与《缀白裘时尚昆腔补编十二集》,分为万方同庆、千古长春,内容与今通行本同,前后同共十二编,合刊行世。
5.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教堂翻刻宝仁堂本在调整次序与整编增删的基础上,取名为《重订缀白裘全编》,共十二编,标明“乾隆四十二年新镌”,此本遂成为后来的通行定本。水浒戏目如表3所示:

表3 “四教堂”本《重订缀白裘全编》收录《水浒戏》
《缀白裘》专门收录歌场流行剧目,是清代戏曲舞台的“活脚本”,借其不同版本系统中的水浒戏目增删变动,可察观清代水浒戏的活跃情况与关注点所在。简而概之,康乾年间,以《缀白裘》为代表的戏曲选本的选录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不收录水浒戏到收录。“康熙本”不涉录水浒戏,至乾隆时期不同版本的《缀白裘》皆收录水浒戏,且戏目呈增长趋势。二是从收录雅部昆曲为主到包罗花部诸腔。“康熙本”与“乾隆四年本”选录的都是“明末清初流行的昆腔戏,皆是元人杂剧和明清传奇的散出,还没有牵涉到花部乱弹戏”[2]208,至“钱编本”则增设花部戏目,如梆子腔等,多择取选录脍炙人口的水浒戏目。需交代的是,本文论及的《缀白裘》,指的便是乾隆年间昆腔和乱弹并存的演出本选集。
二、散出水浒戏的“俗化”特征
《缀白裘》甄择水浒戏,汇辑成编,取彼舍此的背后是一种观念的传达,亦是一种话语形式。这种编选行为,“不仅是将个人褒贬自觉不自觉地蕴涵其中了,而且也悄然透露出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艺思潮,乃至一个时代审美趋势的变迁与形成”[3]。可见,借由《缀白裘》探究水浒戏在明清戏曲选本发展体系中的文本样貌,有助于了解清代水浒戏的审美取向、演出实况与流变形态。总体而言,清代水浒戏在声腔戏目、文本内容、舞台样式等方面表现出的“俗化”倾向,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增录花部水浒戏。地方戏在《缀白裘》中占据极大的篇幅,尤以十一集为甚,“一改以往十集将花部剧目作为昆腔剧目附庸的习惯”[4],完全以花部剧目为选目。全集收录的花部水浒戏含梆子腔、西秦腔及时调杂出等,较之于昆剧戏目,更具民间生活气息,如梆子腔《落店》《偷鸡》二折,非执意于展示水浒人物的侠义形象,而是掺杂诙谐笑料,带有粗朴通俗的意味。这是民间梆子戏对水浒人物的借用,意欲在民间的“俗趣”空间中戏谑演绎水浒故事。
关注与选录花部诸腔,始自明末。明代戏曲选本如《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新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等,收有除昆曲外的其他时行腔调,主要以弋阳腔与青阳调为主。然而,这类选本仅为曲调摘录,并非完整的单折、单出择取,但它们说明了明末已然显露的其他声腔曲调与昆曲争胜的迹象。至清代乾隆年间的《缀白裘》选集,贴近剧坛声腔实况,在昆曲为重的戏曲选本体系中兼及民间审美情趣,囊括花部诸腔,为后世保留了早期花部戏目的剧本面貌,体现了《缀白裘》适时调整的编选视角与兼及花雅的收录准则。
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年间,桃坞叶宗宝题并书《缀白裘六集·序》,引醉吕山樵之语:“否否。词之可以演剧者:一以勉世,一以娱情,不必拘泥于精粗雅俗间也”,指出六集之编,“宜于文人学士有之,宜于庸夫愚妇亦有之”。[5]《缀白裘》之不拘雅俗的编选视角由此可见,兼顾文人学士与庸夫愚妇的视听取向;此外,更是有意识地向民间审美取向靠拢。《缀白裘》编者明确意识到昆腔与地方诸腔的差别,尤其在情节截取与词曲达意上,花部诸腔明显更胜一筹。《十一集·序》指出,昆腔本为世之所好,“率以搬演故实为事,其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奸谗佞恶,悲欢欣戚,无一不备”[6]1,但在表现民间俗趣方面,却不如地方诸腔,“若夫弋阳、梆子、秧腔则不然:事不必皆有征,人不必尽可考。有时以鄙俚之俗情,入当场之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6]1。这是《缀白裘》兼采民间审美习惯的体现,不想独出手眼,而是在尊重民间“鄙俚俗情”的同时,以观众的好恶为依归。[7]
二是偏倚“情事”演绎。明清水浒戏随着《水浒传》小说的传播与民间小说评点的流传,在主题与内涵上出现了多方位流变。一方面它延续旧有水浒故事的“侠义”情怀,成为依托文人士大夫精神品行的创作典范;另一方面,在民间“俗情”与“俗趣”的演绎下,“情事”逐渐成了主要渲染对象。《水浒记》与《义侠记》是明清戏曲选本的重点收录对象,原剧虽涉及“偷情”事件,但水浒英雄仍是侠义主题的承载者。然而,于戏曲选本中,“情事”演绎大有虎踞龙盘之势,掩盖了既有的水浒精神。《缀白裘》二集录许自昌《水浒记》之《杀惜》与《活捉》二折,《活捉》本为《冥感》,“活捉”为其俗名;一集《借茶》《刘唐》与三集《前诱》《后诱》,亦分别为原本的《邂逅》《发难》《渔色》《野合》。《缀白裘》选录的《水浒记》出目皆为阎婆惜与张文远暗中偷情的情节,于此表象下,原有劫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宋江上山、梁山小聚义等剧情却不为人悉,集中突显的是宋江、阎婆惜和张文远之间的情感纠葛。
《义侠记》与《翠屏山》亦是如此。《义侠记》的主轴剧情本为武松打虎、杀潘金莲、醉打蒋门神、投奔梁山,间以其他好汉梁山泊结盟,后被朝廷招安事。但在明代收录《义侠记》散出的戏曲选本中,已有偏尚“情事”的迹象。《珊珊集》收《调叔》,《歌林拾翠》收《武松打虎》《金莲诱叔》《挑帘遇庆》《王婆巧媾》,《玄雪谱》收《调叔》与《说风情》,仅胡文焕之《万壑清音》收《武松打虎》事,其余皆是以潘金莲诱叔与偷情的事迹为主要选目对象。清代《缀白裘》承袭这一指向,总十二集所收的《义侠记》出目分别为《戏叔》《别兄》《挑帘》《做衣》《捉奸》《服毒》《打虎》。《打虎》一出虽并列其中,但水浒英雄的活动主线被剔除,远不及潘金莲的“奸情”戏份。至于《翠屏山》选出中,潘巧云“情事”的关注度亦是高于石秀本人的英雄事迹。明显可以看出,女性的奸情事迹凌驾于水浒英雄的主干剧情之上,这固然是契合民间观剧需求所引申“俗情”演化,但事实上和官方政令、社会时局等亦有关联。
清代水浒戏的生存处境颇为尴尬。由于水浒故事涉及“诲盗”主题,尤为官方忌惮。早在明末崇祯年间水浒故事便遭到严酷打压,入清之后官方更是颁布政令强行摧毁水浒书板,波及水浒戏,致其被认为“教诱犯法”,禁止搬演。如此时局下,水浒戏只能寻求另类的变通方式:屏蔽政令所禁止的敏感内容,转而偏倚“情事”冲突。由此,最初的水浒侠义精神遭遇阻滞,取而代之的是,涉奸女性成为主要的描摹对象,而水浒英雄则演变为“偷情”事件的点缀式人物。不过,水浒戏的“情事”戏目虽然是躲避官方政令的手段,但更多展示出《缀白裘》趋步于民间情感诉求的收编标准。如此一来,不仅可顾及民众好尚,而且能避免抵触官方禁令。
三是虑及舞台调度。《缀白裘》选录的曲文与说白以戏班的演出本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早期民间演剧的面貌,乃乾嘉时期戏曲舞台演出实况的珍贵资料。基于对舞台演出的尊重,《缀白裘》甚为强调表演因素。胡适指出《缀白裘》所收的戏曲,“都是当时戏台上通行的本子,都是排演和演唱的内行修改过的本子”[8](《〈缀白裘〉序》),由此,为了增强舞台的演出效果,《缀白裘》在对话、角色分派、剧情上多有改动,与原本存有差异。[9]其中,《水浒记》《前诱》《后诱》中,张文远的说白全部改为方言,这是应对特定观众群体的改动方式。而在曲白增删上,《缀白裘》不似原本般累积成段唱词,而是穿插说白,加强对话性。四集中《戏叔》一折,来源于沈璟《义侠记》第八出《叱邪》,与之相比,《戏叔》一折曲牌有所减少。a明代《义侠记》第八出《叱邪》的曲牌为【缕缕金】【菊花新】【古轮台】【前腔】【扑灯蛾】【前腔】【尾声】【五更转】【前腔】,而《缀白裘》之《戏叔》曲牌为【缕缕金】【古轮台】【前腔】【扑灯蛾】【前腔】【尾】【五更转】【前腔】,可以看出,后者曲牌明显少于前者。明代《义侠记》的曲牌提取,见毛晋编:《六十种曲》( 第10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实际上,这是舞台戏目的常规调整,考虑到音韵谐畅、脚色劳逸等问题,以演出为旨归的戏曲选本无意于还原原本,而更多注意舞台的搬演效果。
基于对舞台经验与表演范式的考量,水浒经典戏目的变化亦是清代戏曲演出实况的一种另类反映。此中最为特别的是《宝剑记》,与明代戏曲选本相比,清代《缀白裘》中的《宝剑记》趋于匿迹。明选本中,《宝剑记》的《夜奔梁山》为常见出目b《宝剑记》一剧在明代戏曲选本中的收录情况为:《尧天乐》(《计赚林冲》)、《乐府红珊》(《林冲看剑励志》《张贞娘对景思夫》)、《珊珊集》(《夜奔梁山》)、《月露音》(《夜奔》)、《怡春锦》(《夜奔》)、《群音类选》(《神堂相会》《公孙弃职》《逃难遇义》)、《万壑清音》(《夜奔梁山》)、《万家合锦》(《夜奔梁山》)。详见参考文献[4];尹丽丽:《明代水浒戏散出综论》,《四川戏剧》,2016年第8期;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且多在编目上归类主题,如《乐府红珊》卷五设有“激励类”,收李开先《宝剑记》之《林冲看剑励志》;卷七“思忆类”收《宝剑记》之《张贞娘对景思夫》。据其序文可知,此选本的编选立场主要为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倾向于选取受曲词界欣赏的忠臣孝子与义夫贞妇的故事:
况乎辞人骚客之谭,有足以供清玩者,何取于连篇累牍为哉?以故忠臣孝子,义夫贞妇,多为词坛所取赏,而间有一二足为传奇者,所取节片辞,自可以知大概矣。[10]
又如《珊珊集》,明来虹阁主人辑,长洲周之标增订。全本分文、行、忠、信四卷,文、行卷选录散曲,忠、信卷选录了传奇名剧的折子戏唱段。卷三“忠集”收《义侠记》之【古轮台】(《调叔》),以及《宝剑记》之【点绛唇】(《夜奔梁山》),意欲渲染林冲的忠义秉性,树立“义夫贞妇”的典范。此类选本皆将水浒戏放置于选本的主题框架下,进行重新定位与意义阐释。
然而,《缀白裘》仅宝仁堂本的月集收《宝剑记》之《夜奔》一出,其他版本皆不涉此剧,这是十分奇特的现象。有研究指出,钱德苍更换戏目的原因之一在于避免官方的疑虑,在皇权高张、文网缜密的时代,这是戏班演出避开官方敏感情节的手段。[1]从明代将《宝剑记》编排进具有教化性质的选本体制中,如《珊珊集》与《月露音》分别将《夜奔梁山》剧情归为《忠集》与《愤集》,极度推崇此剧;到清代以《缀白裘》为代表的戏曲选集的逐渐淡化与匿迹,显示出《宝剑记》在清代戏曲舞台的冷落趋势。这也说明《缀白裘》不以固有戏目为基准,而是根据清代舞台的实际情况加以收编,由此更契合戏班搬演,被梨园奉为指南。
三、 清中后期散出水浒戏的流变
(一)两种分化路向
清代散出水浒戏的“俗化”趋向,实际上归结为两个层面的演变:一是从文人化到民间化,二是从文学性到舞台性。在此过程中,文人趣味滑落,而以民间审美为载体的地方戏地位日渐彰显,从边缘境地一跃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焦点,由此形成“诸腔竞奏、流派纷呈”的演剧局面。
事实上,清代散出水浒戏目的筛选与形成,受到明代戏曲选本的影响。明代戏曲选本已单出、单折抽取水浒戏目,不仅奠定了明清社会的水浒戏的传播与观众基础,如《八能奏锦》《尧天乐》《时调青昆》《乐府红珊》《珊珊集》《月露音》《词林逸响》《怡春锦》《歌林拾翠》《群音类选》《万壑清音》《玄雪谱》《醉怡情》等选本,皆在不同程度上选录水浒戏,且成为清代选本筛选重点出目的参照对象,亦是戏曲创作的示范与标榜。此后,在文人戏曲家、书坊主与民间艺人等不同群体的交替参与下,清代戏曲选本一方面延续旧有昆腔为盛的选本体制,注重散出昆剧水浒戏的选录;另一方面,在地方戏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中,选本形态适时调整,将民间需求与审美习惯纳入水浒戏发展的自觉追求。于此情势下,昆腔选本趋于衰变,而花部诸腔选本逐步崛起。由此,伴随着花雅变势中的戏目流传与舞台演出,散出水浒戏逐渐分化出不同路向。
一种是依托于雅部昆腔与花部诸腔的势力交锋中,花部戏目成为水浒戏的主要形态与发展路径。从明代仅关注昆腔水浒戏到清代选录大量的花部水浒戏,《缀白裘》选录取向的转变,实际上暗含着清中后期花雅变势的潜在轨迹。据陈建平《元明清水浒戏的舞台传播探略》一文统计,清代花部中的水浒戏,于《春台剧目》《春台戏班目》《庆升平班戏目》《花天尘梦录》《高腔戏目录》《花部剧目》《永禁淫戏目单》《今乐考证》《灵台小补》等记载,多达四十多种。[11]在选本传播与舞台演出的交互作用下,水浒戏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接受群体,更由此被不同声腔传唱。尤其是乾嘉之后,伶人多兼昆曲与乱弹。如《消寒新咏》载集秀扬部贴旦李福龄官,乱兼昆,尝演《调叔》。又如《日下看花记》载三庆部伶人双喜擅演《打店》;春台部伶人升官工乱弹兼演雅部,尝演《擂台》《打店》。又如《听春新咏》记载以秦腔为主的戏班演员擅长剧目,有伶人才林工乱兼昆,擅演《戏叔》《前诱》;大顺宁的小四喜则尝演《戏叔》。可以看出,不论是戏班的剧目记载还是文人的观剧著述,都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即清中后期花部水浒戏成为戏班演出的常见戏目,显现出繁盛之况,同时印证着昆部衰微的余势。事实上,这一转变倾向是水浒戏走向民间的生存方式,更是以《缀白裘》为代表的明清戏曲选本的转型依据,意味着文人文化层的退场与民间审美趣味登场的趋势。a朱崇志将中国古代戏曲选本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元代至明隆庆时期为萌生期,明代万历时期至清代康熙、雍正时期为成熟期,清代乾隆时期至宣统三年(1911)为转型期。其中,转型期的选本特征为:文人文化层的退场、昆腔选本的衰变、花部诸腔选本的崛起。见参考文献[4],第8—28页。
另一种则是随着民间戏曲班社于场上表演的精细打磨,水浒戏“脚色”技艺臻于成熟,并进一步演化为经典折子戏目。与之相伴的是,在偏倚“情事”的戏目推演下,水浒戏屈从于民间“俗情”,“旦色”好尚蔚然成风。据《观剧日记》和《消寒新咏》记载,戏班往往利用“旦脚”演出水浒“情色”戏,如庆宁部小旦徐才官演《反诳》《戏叔》,万和部贴旦毛二官演《挑帘》,小旦金福寿官演《杀惜》,乐善部小旦李玉龄官演《戏叔》等。由此,在“旦脚”与水浒情戏的互动配合中,水浒淫戏风行一时。而这与观剧场上的好“旦”之风不无关系,舒仲山《批本随园诗话》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京的戏班中,“各班小旦不下百人,大半见诸士大夫歌咏”[12]。随着民间戏班的兴盛,对“旦脚”的偏重使“旦色”成为“奸情”戏码的承载媒介,不仅迎合了“观众观剧专重旦色的好尚”[13],而且重视脚色的场上技能,如三庆班每演《杀奸》《杀嫂》等戏,皆让贴旦苏小三一人出台,因其技能精湛。由此可见,戏班精于琢磨与频繁搬演备受青睐的水浒折子戏目,一方面顾及民众的喜好,另一方面使得水浒戏的脚色行当体制与表演技能进一步完善。
(二)抑制与繁荣并行
清代水浒戏目随着声腔的发展而形态各异,然亦遭遇着多股势力的交错制衡,总体而言,散出水浒戏表现出勃兴与管禁并行的演变态势。乾隆后期,由于京腔和秦腔的盛行,淫戏戏目擅演一时,引起清廷的干涉管制。乾隆五十年(1785)禁止秦腔演出,令秦腔艺人改唱昆弋两腔;至嘉庆三年(1798),清廷颁布禁饬乱弹诸腔的谕令。丁汝芹于《清代内廷演戏史话》一书指出,禁演秦腔乃是由于戏坛淫佚污秽,“粉戏”“淫戏”炽盛,多为靡靡之音。[14]然而,即使有官方禁令钳制,道光年间的民间演戏酬神,依旧点演《挑帘裁衣》《卖胭脂》等戏。《得一录》中收录了各种乡约示谕,其中提及,“特近世习俗移人,每逢观剧,往往喜点风流淫戏,以相取乐,不知淫戏一演,戏台下有数千百老少男女环睹群听,其中之煽动迷惑者,何可胜数”[15]797,认为禁演淫戏实为第一要务。只是,禁俗腔淫戏以挽回恶俗的举措未能杜绝淫戏风靡之势。同治、光绪年间,据《菊部群英》等书记载,《后诱》《挑帘裁衣》等依旧是戏班的常演戏目,如四喜部与三庆部,且有意突出旦色技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一书更是记载了多处有关色情戏演出的信息,可见清后期淫戏盛行难挽的局面。
至于水浒戏,被不同声腔剧种搬上舞台,尤为秦腔、京腔等垂青,促进了水浒折子戏目的传播,但也加剧它们成为官方政令的禁止对象,被视为“诲淫诲盗”,有害人心。花部声腔依托于水浒“淫盗戏”,不惜以男女猥亵讨好观众,导致水浒戏于清末备受指摘。如余治《得一录·翼化堂条约》明文禁止演出“水浒戏”,认为《打店杀僧》《打渔杀家》《血溅鸳鸯楼》等戏,皆有悖于王法,甚至拟出《永禁淫戏目单》,含《翠屏山》《借茶》《挑帘裁衣》《卖饼》等戏目,将它们定性为“诲淫戏文”[15]803。金连凯更是于《梨园粗论》中提及观“水浒”剧之害:“《水浒传》下诱强梁,实起祸之端倪,招邪之领袖,其害曷胜言哉?”[16]甚至新式学人在倡言戏剧改良主张时亦以此为靶,指出水浒戏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1905年,陈三爱《论戏曲》指出:《武松杀嫂》《翠屏山》等剧应列入淫戏一类,“伤风败俗,莫此为甚”[17];远公《论戏曲》亦道《翠屏山》等剧乃“淫声秽色”[18]。不过,这类“淫盗”戏目虽遭受非议,被勒令禁演,却依然“触处皆是”,屡禁不绝。
同治、光绪年间,报刊大量刊载有关“禁止淫戏”、批评淫戏横行的文章,水浒戏每涉其中,如《道宪查禁淫戏》列出奉禁戏目《挑帘裁衣》《翠屏山》[19];而基于革除恶俗、整顿风俗的禁止淫戏演出的手段,在民间戏班与戏园演剧中失去了绝对的效力,一度出现“禁者自禁、演者自演、观者自观”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不仅是官方权威的失效,更是社会商业化进程中招徕观众的手段,如上海戏园园主“每恐看客不多,无以获利,特演一二出淫荡之戏以招徕生意”[20]。此外,戏园更是作为“民间之戏馆而民间看之”,尤为“商人所往来娱目赏心之处也”。[21]正因如此,困囿于戏园的戏曲活动不得不趋从于民间好尚,于趋利中整合淫戏戏目,变换各种演出策略,或是在遵从官方劝演善戏的要求下夹杂淫戏演出,又或是更改淫戏名目躲避排查。
除此之外,自雍正以来的废除乐籍、禁止蓄养家班与声伎,导致文人观剧的主体地位的衰落,而转移至平民阶层。[22]这是官方管辖与禁演“诲淫诲盗”戏目的同时,对文人士大夫做出的限定与干预,“至本朝雍正间禁止乐籍,不许士夫蓄声伎,宫谱丧缺,而移风易俗之柄,转操于村优里倡之手”[23]。由此,随着士大夫群体参与度的下降,昆剧的观众阶层被迫停留于底层民众的观演层次。在“昆曲即废,俗声旋兴”的演化趋势中,戏曲活动为了迎合民间观演风尚,则不得不加入放荡庸俗的表演因素与低级戏谑的桥段,形成“无惑乎所演者非淫即杀”[23]的局面。1908年,天僇生《剧场之教育》亦论析此中缘由,由于官方以演剧为戒,士夫不得自蓄声伎,导致移风易俗之权沦于“里妪村优”之手;于此审美风尚的转变下,民间演剧多为淫亵劫杀、神仙鬼怪等,而“与人心世道有关者,百无一二焉”。[24]
概而论之,清末水浒戏蒙受着官方监禁与公共舆论的双重抑制局面,其流于“淫戏”戏目的状况,是探寻生存出路的一种折中路径。在此过程中,水浒戏始终围绕着如何与民间接轨、如何展示民间风尚以及如何在脱离上层文化的掌控中谋得生存空间。只是,这一单向地与民间文化交错演进的态势,也潜藏着难以忽视的痼疾,即不复昔日雅致,导致“淫戏”肆行的困扰。
结 语
花部诸腔戏虽然流行于清初戏曲舞台,但少有剧本刻印流传,导致后人无法探测其原貌。然而,有赖于《缀白裘》对民间花部舞台本的暂时记录,不仅使当时的演出曲文有据可循[25],而且为清代散出水浒戏的存在风貌与分化状态提供了一个真实侧写。简而概之,清代散出水浒戏从文人欣赏品味到民间观剧趣味的转变,表现出取悦民间审美与遵从舞台表演的流变趋势。一方面,水浒戏于选本体系中对“演剧”因素的强调,蕴含着一个潜在信息,即清代戏曲选本开始注重演剧规范与舞台经验,如《审音鉴古录》具有表演范本的性质,《缀白裘》则看重“场上搬演”,皆具有舞台指向。由此,在民间戏班与伶人技艺的琢磨中,水浒戏的舞台脚色技艺进一步精湛,而这实际上是戏曲背离案头的过程。另一方面,水浒戏的“俗化”态势不仅预示着昆剧渐趋消歇的迹象,而且在花部诸腔的衍化下,“淫戏”戏目大行其道,虽有管禁,却愈演愈烈,成为戏班与名角的必演剧目。
综合说来,清代散出水浒戏于《缀白裘》中表现出的“俗化”趋向,在民间戏班演出、民间风尚引导与官方政令制衡下,走出了一条“离雅就俗”的道路,并于地方戏中保留了经典戏目,更具有民间生命力。不过,水浒戏在顺从民间“俗情”与“俗趣”的同时,亦流失了最初的水浒精神价值与表演形式,不可避免地沦为清末淫戏演出活动的“营利”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