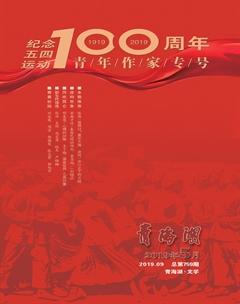心搏的间隙(随笔)
祁发慧
山巫:
把自己放在那里,在安静的时候想起来:最后见你是我做的一个梦,“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那些不明就里的失落,琐碎着这个世界的沉浮。只要能看到自己,每一天都像过节,却也是同样的遥远!
影子覆盖着路,我数我捧着的时间
手机铃声在午夜响起,没有惊扰的意思,一个声音从大山深处传来,伴随着浑厚肃穆的诵经声,想必酥油灯肯定随着电话那头的声波摇曳在初冬的山风中,它所照见的皆是摇晃与模糊。说是想念,如出一辙的重复被认定为新鲜,暂且把话安放在新鲜中体味那份真诚或甜蜜,明理的放弃让故事成为空壳,或许有本能迟疑的成分。然后继续自己最擅长的事,关闭语言和想象的绝杀之技,只留意表象的复杂便能得到熟悉,成为独立的或退却的零都不重要。
所有的本子都有撕扯的痕迹,还好能看到痕迹的整齐,这是专门裁剪过的;所有的文件夹都显示某个统一的时间,它们都被修改清理过。等她想起来的时候,发现早已删除清空了那些或重或轻的文字,记忆当然也不在线。忍不住后悔的同时猜测过去的某些瞬间,还是不太清楚和了解每一次撕扯和清空时的心境,对待自己就像对待别人一样。怅然若失之外略感悲戚和残忍,这都是自己制造的故意操作,也是多年来上瘾般的惯性行为。把忧伤、焦灼、苦闷释放在文字间,待情绪的大浪退去便将记录丢掉,只留下问号般的痕迹,用暴力的浪费给自己最绝的路——这是她给自己无可挑剔的说法。
总有个别被遗漏,有些时候也确实能够串联记忆的片断。比如,在需要受到疼爱的年龄依然独自行走,熄灭灯吹灭香,安静聚散的瞬间想着不着边际的丰盈与贫瘠,迷糊睡去,编织一段浪漫作为单调生活的补偿。再或者,平静地醒来,打开已被撕掉的完整本子,试着给自己讲一个别人已经讲过的故事,抓一把时间扔到眼前的路上,质问不可否认的情节,等待人物之间相互嘲弄,然后想起一些切实的事,数着他们看着自己,否认任何的熟悉就像接受任何的陌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也曾试图将一个故事写好并且为之努力过,可是始终无法接受现实与想象之间的鸿沟,放弃是临近终点的美,坚持未必一切光明。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反应过来嚎叫般对骂之后的转身有何不妥,也依然坚持跳出普遍去看待已经发生的永恒。是的,她不努力抓住什么,却在意一个短暂念头的成型,哪怕是断裂之后的一次想象或者回忆。
深夜驾驶的宽流挂着潮湿的雾
落座时看到茶几上的黄玫瑰已有枯萎的迹象,在她看见之前,它的绚烂应该包含着一段怦然心动和情不自禁。黑底金边的包装纸裸露的美在这一刻之前应该是盛极,它翻腾了某些柔和与平静,更多的应该是热情和迷恋,在她的猜想中。双眼下垂的凝视有些出神,最初的判断开始应验,故事套着故事,有时候一秒钟长如星光之路,可怜的火和心酸的美杂糅在一些不明确中。你看,沉香飘逸茶色渐浓,略靠后并排坐着,措辞精确,夜尾随在未被察觉的分离之中。
梦的回音越气海而来,探出地面进行模棱两可的谈话——“我送你吧!”像没听懂话一样盯着眼看着回答:“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内心的极端言说已被自己湮灭:我送你出去,给你展翅的房顶和天空,等待光线抬头,复制一个自我现实交付给那个拼装的完整。她嘟囔着只有自己能听懂的话走在楼道,处处熠闪着的灯光像是白白空留的光阴,有头有尾的音乐终究还是细碎跳荡,滑过各自生命的防区,却也是纠缠不清的气氛。
3月到元月是一场焚烧的火,新鲜者的抚摸与雕刻者的老练同在。细节透露的真实落实着刻意回避和答非所问,谎言不需要识别也不需要得到确认和辩解,知晓或者明白均是直感的天然。这并不是震惊的事,也不是她的结局,意识做了最完美的回答:如果有怨,请提醒那些闪耀着美好和刀子般的话语;如果有恨,请完整那些未能说出的话和未能完成的承诺;如果还有一种可能,请不要寄任何希望于她——一个不可能对自己的心一无所知的人。
她的晦涩成为尖厉,自制的长剑直抵心室,谈不上以暴摧之,相比较卑劣空洞一个血肉之躯并没有什么。她的世界彻底醒悟在喧闹的街头,醒悟即是绝望,那个时刻一切外部的努力都会构成伤害,精妙的语言还不如闭口不说,默默。只有三天,她的等待长于任何时间计算,她知道它与生活走样离心,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隐喻和象征!密闭之墙无法忍受爆裂,赶紧草草收场,不然连自己都会不屑。可是,匆匆的人群像是小说中自己的投影。夜的手指编织的长发在黎明来临之前松散,起身关门再自然不过。当然,还有客套的嘱咐和关心。
解释给自己听之后便没有了煎熬,跳出普遍的理解并非自我阐释,所有的言说都可能缺席,可是,这又算什么呢?就像一颗心:它能懂什么?可是安顿它的路那么难走!短暂的未明如突奔之火,或许全部都是短暂的孤零零,堆放在如临崩朽的拥挤深夜。对于夜,从来只有迷恋和欣赏。“你这个不怕黑又不怕高的女子啊!”这句话是带有定义的,她在此刻才意识到自己在极端处的诉说。
她寫满纸片上的空白,仿佛活埋了那个粘连肉与血的模糊人形,仰起头,略显疲倦的双眼和灯光一样柔和。她最终的坦白:你不说,我便不问!
光线诱惑的顺流而动越过杂音
发着抖的文字在昏暗处闹腾,它们早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轻飘或沉重,尝试把手放进刚刚飘落的雪中,生活在这里就应该有一个飘雪的标记,并把它传回给自己。雪变成唇上的阳光流入口中,冰甜醒神而后独自享受自我的独白:
我不负自己
却被你们基本判断
这该死的大多数啊——
仅止于日复一日的煎熬
她看到不祥的图语,梦到的艰难路给予最好的提醒和警示,对着自己不依不饶,将所有的坚硬朝向自己,惯用的手法自然而然甚至成为某种无意识而存在。青春流逝成为父母的担忧,人的自我异化是成长的代价,个人也必须要承担这个代价,这样的道理她从来都是懂得的,只是顶着一颗比心还挑剔的脑袋,谁还会相信她没有把黑说成白?谁还会承认她颠倒日夜所做的努力?就凭她那种风度和措辞!
她憧憬用新的能耐抵御老道理和世故,想着柔情渐生,可面面都是过去的街景风物,美的子弹锁在了美的期待中。镜子跌落摔碎,已然不可能拼装成完整的世界,精确复制更是天方夜谭。流动的自我固定取景的点,变换可以成为局部景象,其结果是修辞组装的内心,这是文字给她的荡漾和轻松。情绪极致的体验是一抹分裂的蓝,失语的口喊出:
重建或者不要
不要,以便再次焚烧
我走远——更远
回来之前就应该把希望放在路上,在枯萎成荒芜之前克制所有的繁华。可是,到了这里就得陷落于所谓的生活,她从未想到这里的温甜会毒杀仅有的沉默。大概没有人会相信她从未把切实的发生当真,却为未能说出的话失声痛哭,尾随着夜的悲伤对着自己说晚安。每一个善意的提醒都是明亮和美好,从最初的以礼相待到后来的触点反驳,她开始明白只要表达自我就会变得刻薄,对待自己不需迎接也无需遮蔽,除非突然叫停告诉自己坐错了车,那也得面对一个现在的自己。不是吗?高手过招也无非你看我平静如水,我看你波澜不惊,也曾一言一语地说着口舌无味或用力过猛,可到了这里就烦透了似是而非的饶有兴趣和能力超群。
曾孜孜不倦地为一个虚无奔命,它像一束持续闪亮的光迎接着她的努力和天真。这个被师父称为巫婆的女子不善于煽情和表演,那些不明朗可以被一个温暖的词语清洗,那些拥堵的心塞也可以被纯真和活泼冷静。
“孩子,你不温不火,不冷不热,不卑不亢,过分老练了。”
“这里用沙石铺就的路我只能独自走过,荒诞被事实说出的时候,荒废已然成为一种可能,我只记得那句十年在田!”
数着眼下的灰头土脸,她从一团糟糕中爬出来,感到福佑像神异降临,终生受益或者受损,不能断言渴望及时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