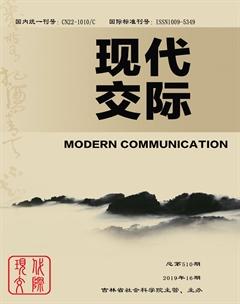《帕梅拉》中的身体政治
陈栩
摘要:塞缪尔·理查森在《帕梅拉》中通过建构服饰、空间与身体的谱系关系寄寓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愿景。小说中,帕梅拉的身体先后从自我坚守过渡到权力协商,最后蜕变为男性霸权话语下的臣服客体,身体的多重面相暗合了现代性初期人们对家庭伦理秩序的探索和想象。
关键词:《帕梅拉》服饰 身体 伦理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6-0241-02
塞缪尔·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创作于1740年,正值英国道德改良的高漲时期。学界对该小说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女性美德层面,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也关注到了小说中的身体话语,比如斯班克斯指出,小说“聚焦身体而非精神”[1]86;巴彻勒阐释了主人公的身体与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2]19。然而,学界对身体在小说中的嬗变轨迹关注不够。本文将以服饰与空间作为切入点,揭示小说身体政治的文化内涵。
一、服饰表征的身体主权
小说一开始就将帕梅拉的着装问题和盘托出。B先生在母亲去世后将她用过的衣物送给侍女帕梅拉,这些衣物在帕梅拉的家信中被展示出来:“一套衣服、六件汗衫、六条精致的围巾、三条麻纱白葛围裙”。[3]9B先生的慷慨馈赠让帕梅拉心生欢喜,这却引起了父亲的极大不满:“你受到的待遇大大超越了你的身份”。[3]4那么,作为赠品的服饰在帕梅拉和B先生的交往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莫斯认为,“在给与别人礼物的同时,也就是把自己给了别人。”[4]81-82莫斯关于礼物的深刻洞见为我们解读服饰的文化意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小说语境中,B先生向帕梅拉赠送衣物并非出于尊敬,而是肇因于自己蓄谋已久的征服计划。如果说服饰是关于身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是一个凝结了各种异质力量的综合场域,那么帕梅拉的新衣则明白无误地映照出赠送者的个人欲望,即将她的身体据为己有的险恶企图。位于礼物链条的另外一方的帕梅拉既然没有多少“财物”,那就应当以她的贞操回馈给对方。恰恰在这个环节,帕梅拉身体的归属问题在她与父亲和B先生之间形成了充满矛盾张力的三角关系,服饰的象征意味空前凸显。
斯通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时指出,“女性如今在公开的婚姻市场上相互竞争,制胜的关键不在于嫁妆,而在于身体和个人素质。”[5]261对于未婚女性,最重要的身体特质就是保持贞洁,而所谓的“个人素质”毫无疑问地指向贞淑娴静的女性气质。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帕梅拉对自身社会身份的选择往往与其对性的态度紧密相关,这将直接影响到她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声誉,因此父亲提出的忠告就显得合情合理:“我们担心——你会太感激他了,因此会用你的贞洁这个无价之宝来报答他。”[3]5父亲充当了旁观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其书信却充当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大讯唤。
对于父亲的谆谆教诲,身处威胁中的帕梅拉自然心领神会,她深知要在社会象征秩序中占据主体位置,需要父亲的加持和指导,她向父亲保证,“我能够甘心乐意穿着破衣烂衫”而“决不会丧失我的良好名声”。[3]6破衣烂衫有别于B先生赠送的高档衣物,成为帕梅拉钟情的着装模式,她对服饰的选择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区隔,换言之,“一个人对化妆品、服装或者房屋装饰的客观或主观的美学立场,可以用来确认此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6]57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帕梅拉对B先生赠衣背后物物交换的逻辑思维难以认同,她在服饰馈赠所形成的交换关系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维护身体主权的道德立场。帕梅拉表现出蔑视权贵的勇气。在服饰所引出的善与恶、强与弱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中,帕梅拉已然将身体的所有权问题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激烈交锋。
二、身体的权力协商
帕梅拉在发现主人的险恶用心后屡次请求辞职回家。当她获得B先生的准许后,却又陷入了对方布置的另外一个陷阱。B先生暗中将帕梅拉劫持到他的乡下别墅,交由女佣朱克丝太太监管。小说通过空间圈禁和信件偷窥呈现了帕梅拉与B先生就身体展开的权力协商。
首先是B先生对帕梅拉的空间圈禁。小说中的空间权力外化为令帕梅拉毛骨悚然的房屋意象:“宅第四周有高大的榆树与松树,树皮是褐色的,树枝像点头似地摇摇摆摆,气氛阴森可怖。”[3]125-126空间圈禁的目的在于生产驯服的身体。B先生命令朱克丝太太行使监督权,有必要指出的是,朱克丝太太作为B先生的替身被赋予了男性特质,这不仅反映在她男人般的身材和凶悍的长相上,更体现在她与男性凝视毫无二致的监视中。尽管帕梅拉形似囚徒,但她在权力的夹缝中努力通过精神自省来对抗身体圈禁,“也许万能的上帝只不过是让这些苦难来考验我是否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3]208
其次是书信窥视。在权力无孔不入的郊外别墅,帕梅拉暗中从事写作,塑造了一个无辜的落难女子形象。帕梅拉将这些信件巧妙地隐藏起来,“我把迄今为止所写的信全都缝在亚麻布裙子下面的衬裙里面。”[3]153书信、服饰与身体合而为一,书信成为帕梅拉身体的隐喻。然而,这些信件在随后的邮寄过程中被朱克丝太太暗中截获并上交给了B先生。如果说书信是帕梅拉身体的象征,代表了她的第二自我,那么B先生对书信的偷窥无疑意味着他以一种极富象征意味的方式占有了写信人的身体,并在阅读的快感中满足被压抑的力比多欲望。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将B先生包围的视觉快感暗含了某种改造力量,他在帕梅拉建构的文字镜像中看到了一个他者化的自我,由此激发了他的身份想象和认同机制。B先生的态度转变契合了伊瑟对读者反应的理论阐发,他认为阅读调节着文本和读者间的相互影响,这种调节“是通过阅读行为中实际产生的过程,这是改变观点的过程。”[7]271-272帕梅拉的书信让B先生感觉到了“有罪的内心骚动”,微妙的心理变化源于帕梅拉的高尚心灵和对诱惑的坚决抵制。囚禁帕梅拉的郊外别墅以及书信构建的文本空间被悄然引渡为一个彼此身份和身体协商的动态空间。一方面,帕梅拉以贞洁作为武器应对B先生的图谋不轨,她在写作过程中萌生的改造对方的想法使双方关系出现转机;另一方面,作为偷窥者的B先生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感化,他对帕梅拉的态度逐渐由荒淫浪荡转向了倾心爱慕。有学者指出,在小说着力再现的权力协商机制中,“女性书写和两性谈判的出现本身改绘了社会政治势力地图。”[8]137身份协商的结果是帕梅拉与B先生最终达成和解,二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最终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三、服饰凝视下的驯顺身体
婚后的帕梅拉生活优裕,成为小镇艳羡的对象。事实上,帕梅拉这一灰姑娘式的传奇经历也是评论界历来诟病的地方,她的贞洁自持在同时代作家亨利·菲尔丁的笔下被戏仿为投机钻营,而她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铜臭气息。尽管小说情节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理查森营造的童话氛围也暗含了异化的规训力量,这集中体现在帕梅拉婚后的着装实践中。
在小说中,服饰成为交织着各种矛盾关系的物质文本,它将帕梅拉的躯体包裹,成为父权社会制造驯顺身体的规训手段。首先是帕梅拉充满性别意识的穿衣理念。出身卑微的帕梅拉深知,要在B府及上流社会站稳脚跟,穿衣打扮是头等要事。作为新晋女主人,她的着装品味无疑成为她巩固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本,这可从她衣柜中的花色缎带、蝴蝶结、白纱长袜和紧身褡等各色时髦服饰中略见一斑。在18世紀英国的服饰时尚中,女性的衣着总是遵从性别、性感和阶级区分的界限,女性要在更多方面经受着来自社会道德的约束。服饰在增强女性气质的同时,也成为限制身体自由、改变身体形象的工具。反观小说,帕梅拉借助服装的美学组合化身为纯洁的天使形象和崇高的道德榜样,她的职责是忠实践行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做一个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
其次是B先生的角色召唤。在一家之主B先生看来,美丽的女性都要光鲜亮丽,她们的衣着模式反映了其对婚姻的态度,他甚至对衣着不整的已婚女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在结了婚以后的人们当中常常看到做妻子的对自己的服装愈来愈马马虎虎、毫不在意,我觉得她仿佛不想尽力设法来保持她所已取得的爱情。”[3]422细查之下,B先生对服饰表现出近乎偏执的迷恋,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恋物主义的典型症候。恋物主义可用来表达一种特殊的性态度和性关系,它是社会中受压抑的或有进取心的个人或少数群体用来吸引注意力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B先生的审美价值折射出他在家庭中的权威和欲望,这种权力以帕梅拉放弃女性主体性为代价得以执行,帕梅拉对此心知肚明,为了维护体面的声誉,她不得不与这种霸权话语达成共谋。表面上看,帕梅拉风光无限,但在意识深处,身体焦虑却时时刻刻操控者她,她坦言自己“只不过是一块外表涂了华丽颜色的可怜泥土。”[3]566由此可见,看似有利的婚姻已经变成束缚身体和思想的牢笼,帕梅拉婚后的唯一选择是在服饰的支配之下继续其身份操演,小心翼翼地呵护她的淑女神话。
综上所述,理查森在《帕梅拉》中通过建构身体与服饰和空间的谱系关系,寄寓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愿景。小说中,帕梅拉的身体先后从自我坚守过渡到权力协商,最后蜕变为男性霸权话语下的臣服客体。身体的多重面相暗合了现代性初期人们对家庭伦理秩序的探索和想象,小说通过美德有报的主题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之后英国小说女性描写的话语模式。
参考文献:
[1]Spacks,P.Novel Beginnings:Experi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M].New Haven:Yale UP,2006.
[2]Batchelor,J.Dress,Distress,and Desire:Clothing and the Female Bod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3]塞缪尔·理查森.帕梅拉[M].吴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马塞尔·莫斯.礼物[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M].刁筱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Bourdieu,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Cambridge:Harvard UP,1984.
[7]沃夫冈·伊瑟.阅读行为[M].金惠敏,张云鹏,易晓明,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8]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责任编辑: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