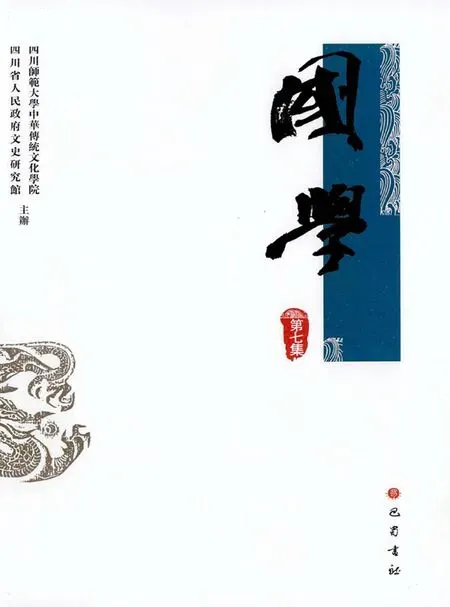魏了翁對《詩經》的闡釋及其理學思想
唐 婷
魏了翁,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 人,二十一歲登進士第。一生著述頗豐,著有《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説》《古今考》《經外雜抄》《鶴山詩集》《鶴山集》《師友雅言》①[元]脱脱:《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971 頁。等。魏了翁是南宋理學的關鍵人物之一,嘉定三年,魏了翁在蒲江白鶴崗創辦鶴山書院,“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争負笈從之,由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②同上,第12966 頁。,為理學在蜀中的傳播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魏了翁的理學思想集周敦頤、二程、朱子之精要,被稱為“私淑朱、張之學者”。魏了翁將理學作為規範社會意識形態、指導社會發展、革除各種弊端的主要思想,褒揚程朱對於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地位,對理學由“偽學”到被確立為官方正統哲學起到了推動作用。魏了翁的理學思想繼承程朱理學,又有與時俱進的發展。他折衷朱子理學與陸九淵的心學③蔡方鹿:《魏了翁評傳》,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164 頁。,“民心之所同,則天理”,將心學的“簡易工夫”融合義理的修身治國,規避了理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繁蕪浮泛的弊病,也為程朱理學熔鑄了新的思想。尊重傳統學術權威,也敢於對古注舊疏提出異議,主張回歸經典本身,這樣的懷疑精神是魏了翁突破理學發展既定規律的基礎。在對《詩經》的解釋中,我們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魏了翁不同於其他理學大家的觀點,即透露出魏了翁理學思想的特質與文化意義。
一、“淫詩説”的形成
《詩經》中到底有無“淫詩”,歷來學者們各執一詞。反對“淫詩説”者,多以春秋大夫燕享賦詩,不以淫詩相待;季札觀樂,不及淫字;孔子以“思無邪”論三百篇①如朱朝瑛《讀詩略記·卷首》云:“魯秉周禮,采之列國以為樂者,其淫辭淫聲不待夫子删正,久已斥去而不用,故季札歷觀列國之樂而不及一聞也。其所存之辭皆正辭,所存之聲皆正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 册,第340 頁);姚際恒《詩經通論·論旨》云:“春秋諸大夫燕享,賦詩贈答,多《集傳》所目為淫詩者,受者善之,不聞不樂,豈其甘居於淫佚也”(《續修四庫全書》第62 册,第11 頁);毛奇齡《毛詩稽古編》卷五云:“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 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册,第399 頁) 等。等證據説明《詩經》中無“淫詩”。主張“淫詩説”者,則以《論語》云“鄭聲淫”,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鄭、衛多淫奔之辭等為由堅持認為《詩經》中的確有“淫詩”。之後經歷古史辨派極力宣導還原《詩經》的文學原貌,這類頗有争議的詩又被定義為“愛情詩”得到全新的解釋。當代研究多沿着古史辯派的論調産生了大量研究成果,涉及探討“愛情詩”的詩歌意象、藝術美學、抒情模式;分析“愛情詩”反映的周代禮制、社會風俗,及其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等多個方面。這類詩佔《詩經》的絶大篇幅,如“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②[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蒹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69 册,第370 頁。(以下凡引《毛傳》《鄭箋》《孔疏》均出此書,不再另注。),是對期盼中的女子最動情的描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是心中情愫已難以抑制的可愛狀態;“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是願托飛鴻寄相思的綿綿情意。還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正值盛年,有“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絶代佳人,也有“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的始亂終棄……這些大膽熱烈的意象表達,坦誠直言的情感獨白,貌似與《詩經》“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政教功能不符,自然這類詩便成為《詩經》研究的熱點之一。
漢代經學家秉持先秦儒家詩學的傳統,認為《詩經》是先王用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經典著作,且聖人有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説關關和鳴的雎鳩鳥,感情真摯而有别,就像后妃有不嫉妒、不專寵的美德;“静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説懌女美”是説后妃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詳細記載后妃按禮法伺候君主之事;“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是説蘆葦要等到白露成霜時成熟,喻示着秦襄公需用周禮而後國治。諸如此類,所有迸發的感情都要套上政治教化的外殼,這類詩承擔着風化天下、移風易俗的歷史責任,被作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教科書。秦漢經學家構建《詩經》的政教大廈,給予了這類詩歌很重要的分量。男女乃人倫之大防,所謂“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禮記昏義》),衹有把“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的思念都解釋成為“求賢女而不得,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纔能脱離“飲食男女”,成為道德教化的模範。唐代孔穎達奉詔編纂《五經正義》,在《毛詩正義序》中説道:“夫詩者,論功頌徳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静於中,百物蕩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詩的定位是頌德,是規誡,要實現“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政治教化功能,在經學家的評判體系中容不下那些純粹抒發男女愛情的情歌,而孔子删詩卻没有删去這些篇什。因此,經學家們便根據舊説,將這些本來淺顯易懂的情歌講成后妃美德,講成諷刺時事,講成學校不興等等,最終都要指嚮“正得失”的終極目的。
雖漢代經學家也將《桑中》《溱洧》等詩指證為“男女相奔”“淫風大行”,但與朱子提出的“淫奔之詩”“淫亂之詩”不同。漢代經學家是從政治倫理出發,因男女有别而後君臣有正,當詩歌内容完全是男女對感情的大膽追求,無法借比興講做其他時,便根據《詩序》“刺時也”“刺亂也”大做文章,重點解釋導致男女無視禮法的現象是因君王昏庸、時代亂離,以此來委婉地諷勸執政者厘正風俗,最終都是以“三百篇”當諫書,落實在政治文化上。至宋代“淫奔”數次出現在《詩經》學著作中,歐陽修《詩本義》出現7 次,蘇轍《詩集傳》出現1 次,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出現8 次,范處義《詩補傳》出現13 次,《毛詩李黄集解》出現53 次,等等,以上提到的“淫奔”語義指嚮仍然是在漢代經學家的政教範疇内,是從政治倫理的角度對不合禮法、違背倫常的行為諷刺勸誡,最終將癥結歸為政治文化的敗壞。但朱子所論“淫詩”與此不同。
朱子認為《詩經》“淫詩”多集中在鄭、衛兩《風》。如《蝃蝀》篇,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毛傳》云:“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鄭箋》云:“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毛、鄭根據《詩序》認為“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從政治教化層面把這首詩解釋為國人對淫奔之女的鄙夷指責,認為“夫婦過禮”違背“適人之道”,强調的是維繫整個社會政治有序運作的禮法。朱子云: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倐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①[宋]朱熹集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49 頁。(下文凡引《詩集傳》皆出此書,不再另注。)。
朱子明確將這首詩定義為“淫奔之詩”,非《詩序》“止奔”之説。虹乃日雨相交,象徵“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喻示男女不倫之事。朱子云:
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從“天理人欲”的角度來評判,他認為婚姻是男女本能的欲望,淫奔是不守貞信之節、違背天理,如果人聽任欲望支配就與禽獸無别,於是提出“以道制欲”。人欲要有所節制,漢代經學家也提節制,云“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先王的教化、以既定的禮法約束不當行為,而朱子提出要以“道”、以“天理”節制欲望,重點不在“政治”“禮法”上,而是在“存天理、滅人欲”上反覆致意。其云:“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悦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朱子提道,一則“男悦女之辭”“女惑男之語”都是淫奔之詩;二則“鄭聲淫”,且無羞愧悔悟之心,鄭聲之淫甚於衛;三則“詩可以觀”,通過鄭、衛詩可見兩地民風。朱子云:“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②[宋]朱熹:《詩序辨説》,見《詩集傳》。朱子提到《詩經》中留存淫詩是為規誡,這些直白裸露的情感表達是違背了天理、違背了人道,應順聖人之意從天理人道的角度大加批判纔是解釋《詩經》的正途。有理學系統醇熟的理論為基礎,朱子從“存天理、滅人欲”角度來闡釋《詩經》,從此“淫詩説”便正式確立。
朱子之後,王柏、輔廣、嚴粲、季本、劉瑾等延續朱子的觀點,贊同“淫詩説”,王柏云:“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删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攛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①[宋]王柏:《詩疑》卷一,《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王柏認為“淫詩”源於漢儒求全,《詩經》經秦火後應無全本,夫子所删之詩在民間有所流傳,漢儒為求全便將閭巷淫俚之歌混雜其中以湊數。季本也提到“秦火之後,詩篇錯亂,多失故序,而又雜以里巷狎邪之言,則其義始不明矣。……及觀《左氏》載諸大夫賦詩之事,有斷章取義而理可通者,有可不通者,有舉里巷狎邪之言賦於燕饗之正會者,此則鄭聲之亂雅樂,士大夫習而不知者也”。②[明]季本:《詩説解頤·總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9 册,第7 頁。季本認為《詩》之雜亂在孔子之前,士大夫賦詩時就已經混入了里巷狎邪之歌,也是從發生根源為“淫詩説”找邏輯依據。輔廣於“發乎情止乎禮義”云:“ 《小序》以諸淫奔之詩為刺奔者,皆緣泥此節而失之,故先生以為此言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於禮義者,固已多矣。其説可謂公平正大,可以一洗千載之固矣。”輔廣認為朱子提出“淫詩説”革漢儒論詩必講美刺之弊端,此舉功不可没。“淫詩説”經朱子正式確立後,歷經明清兩朝不斷有學者强調“淫詩説”的合理性,自然也有非議。如楊慎即云:“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③[明]楊慎撰,王大淳箋證:《丹鉛總録箋證·訂訛篇·淫聲》,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77 頁。之後反對“淫詩説”者,多就此做文章,如朱朝瑛、毛奇齡、姚際恒等。實則,在南宋的理學家中也有並不贊成“淫詩説”者,以魏了翁為代表,也反映了魏了翁對於理學經典命題“天理”與“人欲”的獨特詮釋。
二、魏了翁對“淫詩”的闡釋
朱子認為《詩經》中“淫詩”約有22 篇④此22 篇是以朱子闡説中明顯提到“淫”“淫奔”等關鍵字為主要依據進行梳理統計而得,具體篇目如下:《邶風》有《匏有苦葉》《静女》2 篇;《鄘風》有《桑中》《螮蝀》2 篇;《衛風》有《氓》《木瓜》2 篇;《王風》有《采薇》《大車》《丘中有麻》3 篇;《鄭風》有《將仲子》《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褰裳》《野有蔓草》《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12 篇;《陳風》有《株林》1 篇。,限於篇幅我們以其中明確提到“淫奔”的11 篇為例,從魏了翁對這些篇目的闡釋中見其對“淫詩”的態度。
這11 篇分别為:《静女》《螮蝀》《氓》《采葛》《大車》《將仲子》《有女同車》《風雨》《子衿》《出其東門》《溱洧》,以下表做一對比分析:

① 《毛詩要義》分條目摘録《毛傳》《鄭箋》《正義》的内容,如《采葛》篇,《要義》云:“三月、三秋、三歲各從韻,不由事大憂深。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表中每篇所引衹取其所摘録的要點(即作為條目之首句) 以見其詩學主張。(《毛詩要義》,《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 册,第410 頁。下文凡引《要義》不再另注,請參見此處。)

序號 篇 名 《詩序》《詩集傳》《毛詩要義》6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鄭莊公處叔段於大都,使驕而作亂。箋所引祭仲諫語乃公子吕。古名甲後世名鎧。《箋》云服馬猶乘馬,非夾轅馬。7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鄭忽兩辭昏,《鄭志》問答止言文姜。忽已娶於陳而齊猶請,皆無文以明之。他女不當言孟姜,《疏》云何必實賢實長。與女同車謂親迎婿御婦車。舜一名木槿,都者美好閑習之言。8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風雨雞鳴興君子不改度。9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子,男 子 也。衿,領 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箋》以鄭謂學為校,疏引公孫弘難之。父母在,故青衿無則素衿。《傳》以不嗣音為不習音聲,鄭為音問。士佩瓀瑉而青組綬,與今《禮記》不同。在城闕非人君宫門。

序號 篇 名 《詩序》《詩集傳》《毛詩要義》10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争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 皆 有 之”,豈 不信哉!忽初立以太子故唯數後無争。《傳》以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為夫婦。《箋》以縞衣、綦巾作詩者之妻服。毛謂詩人出曲城門台,鄭謂國人出城出都。荼謂茅秀,非《邶風》苦菜、《周頌》荼蓼。11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採蘭水上,以拔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 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 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芍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蕳即蘭,漢池苑皆種,可辟蠹。
以上數篇朱子直接以“淫奔”二字概括主題,個别篇章《詩序》也提到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等字眼,但《詩序》首句無不是以美刺功能為主,如言“刺亂”“閔亂”“刺時”“止奔”等,務在將詩歌主題指嚮社會政治、風俗教化。與朱子重在批判人欲相比,《詩序》認為《詩經》不應局限在男女倫理上,而是由此生發到社會政教層面。男女相奔、無視禮法是社會風俗敗壞、上層統治失去約束規範的突出反映。毛詩學派主張《詩經》承擔着“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重要作用,則所有篇章自然不應衹停留在人倫大防上,要深刻剖析造成這些現象的社會原因,這纔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的内涵。
魏了翁對以上篇目的闡釋,從其摘録的要點即可得知。如《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序》云:“懼讒也。”根據《鄭箋》的解釋,《詩序》認為這首詩是出使在外的大臣擔心自己身不在朝,使得奸佞小人有機可乘,唯恐自己被讒言所毀,心中憂懼,故度日如年。而朱子認為,“採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在朱子看來,這純粹就是女子表達對情人的思念。《要義》云:
三月、三秋、三歲各從韻,不由事大憂深。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
《要義》認同《詩序》,“懼讒”是《采葛》的主題,故取“三月、三秋、三歲各從韻,不由事大憂深”為重,而不是作情詩講。又如《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在,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因“青衿”是學子的衣服,故《詩序》認為是刺亂世學校荒廢。朱子則認為,“子”謂男子,“衿”謂領,“我”是女子自己,這同樣是女子思念男子的情詩,“亦淫奔之詩”。《要義》云:
《箋》以鄭謂學為校。《疏》引公孫弘難之。《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正義》曰:鄭國衰亂不修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然明謂子産毀鄉校。《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宫也。
魏了翁摘録這麽一大段《正義》關於古時學校的稱謂,可見其對於《詩序》“刺學校廢”的贊同,而並不認同朱子“淫奔之詩”的説法。以上表中所列都被朱子標為“淫奔詩”,而《要義》均選擇遵從《詩序》,從政治教化、道德禮義的角度來摘取重點。
魏了翁遵從《詩序》是其認同毛詩學派以政教、以禮義為闡釋核心的突出表現,最明顯的就是認同將情詩講作政治教化詩。《蒹葭》從字面意義上看,就是一位期待、追尋夢中情人的男子所寫的情詩。《序》云:“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傳》云:“興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强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黄。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毛、鄭認為這首詩以蒹葭因白露而變蒼黄,喻國家行周禮然後民從政順,以此刺秦襄公不用周禮。這番闡釋是為了强調《詩經》“正得失”的政教功能,魏了翁認為這恰是要義所在,此篇即摘録“秦處周之舊土而襄公未能用周禮”“蒹葭得霜而成,興秦人用禮則可服”。魏了翁選擇在如今看來甚至有些牽强的説法,這份刻意表明他是十分關注《詩經》“諷上化下”的政教功能的,本質上是緣於其對詩禮文化的深刻理解。魏了翁為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作序,曾談到讀《詩》之法,云:“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徳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叅總衆説,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魏了翁讚賞吕祖謙致意於美刺教化,讀詩總是“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頗得“興觀群怨之旨”。從他對吕祖謙的推崇,到解讀《讀詩記》的特色,皆重在《詩經》的政教功能上可知,《要義》遵從《詩序》是出於對毛詩學派闡釋系統背後以“禮義”為關鍵的價值系統的認同,這便是為何作為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而魏了翁卻並没有像其他理學家一樣將情詩斥責為“淫詩”。當然,這其中也包含着魏了翁對於“天理人欲”的獨特見解。
三、“欲有善、不善”的理學主張
天理、人欲之辨是理學發展歷程中的經典論題。“理”是理學的核心。周敦頤云:“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①[宋]周敦頤:《周子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 頁。邵雍云:“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②[宋]邵雍著,卫绍生校理:《皇極經世書·觀物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53 頁。張載亦云:“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③[宋]張載:《正蒙·太和篇》,《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7 頁。馮友蘭先生指出:“雖諸家已言及理,但在道學家中確立理在道學中之地位者,為程氏兄弟。”④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8 頁。二程常言“天理”“義理”,但“理”的内涵總是缺乏明確定義,如云:“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⑤[宋]程顥、[宋]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2 頁。理如太虚,不可眼見、不可言狀,與人感知與否、遵循與否都無大關涉,是絶對的存在。即謝良佐云:
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所謂天者,理而已。衹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衹須明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移易不得①[宋]朱熹編,謝良佐語:《上蔡先生語録》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 頁。。
“天理是自然的道理”,不因人的意志而改變、而轉移,是謂“形而上者”。及至朱子,集周邵張程之大成,再次對“天理”等核心概念作闡釋,理學也方臻於完備。
朱子認為:“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朱子語類》) 以太極、陰陽而言,“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静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穆無朕,而動静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②[宋]朱熹:《太極圖説解》,見[宋]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 頁。。道無處不在、不限於時空,它灌注在具象之中,也抽離於具象之外。所謂“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要之‘理’ 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③[宋]朱熹撰,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答楊志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58 頁。。朱子曾舉舟車之例説明,物各有其理,舟行水上、車馬在途,都是顯現各自之理,此理在舟車發明之前就已存在,絶非因舟車的出現纔出現,是理體現在器物上,於是纔造出了舟車,故有“人人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之説(《朱子語類》)。人與物中存有一切事物的理,不過禀氣有偏差,故一切事物的理也有偏差地顯現,從而成為各色人等物種。
馮友蘭先生據朱子所言,提到“吾人之性中,不但有仁、義、禮智,且有太極之全體。但為氣禀所蔽,故不能全然顯露。所謂聖人者,即能去此氣禀之蔽,使太極之全體完全顯露者”④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267 頁。。人因理、氣而成性,朱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人格修養的核心宗旨“存天理,滅人欲”,云: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徳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徳”,《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衹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衹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説敬字,衹是謂我自有一個明底物事在這裏。把個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⑤[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7 頁。。
朱子認為一直以來聖賢所言不過是在闡明道心(即天理) 不易知曉,而人心(即人欲) 又易被諸多因素影響,要通過格物致知達到漸明天理則人欲自銷,即如消去隱藏寶珠的渾水。朱子云:“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嚴格對立二者;又説“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書,要去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讀書須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衹是分别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①[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5 頁。,認為衹有當人欲盡去,纔能到正心誠意、窮理盡性。那麽,究竟何為人欲? 朱子以飲食為例,説“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馮友蘭先生説:“人欲亦稱私欲,就其為因人之為具體的人而起之情之流至於濫者而言,則謂之人欲。”②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268 頁。即人欲是在滿足生命延續的基本需求之外,因起了私心、私情以至於泛濫者。在朱子看來,人欲都是不好的,故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而魏了翁卻與此不同。
魏了翁認為人欲也不全是惡,創造性地提出人欲也有善的部分。他説:“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③[宋]魏了翁:《鶴山集》卷三十二《又答虞永康》,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説“欲善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④[宋]魏了翁:《禮記要義》卷九《禮所以知人心》,《續修四庫全書》第96 册。。飲食男女是人的本性,魏了翁認為這是人心欲求的最大方面。蔡方鹿先生指出,魏了翁肯定吃飯穿衣、男女生活是正當欲望,對待這些出自人心的欲望要以客觀承認的態度,而不是滅絶它,用心加以節制⑤蔡方鹿:《魏了翁評傳》,第181 頁。。魏了翁並不將天理、人欲絶對對立,而是主張看到人欲裏合理的部分,加以節制使之不成為惡,如此人欲自然可與天理同時存在。魏了翁云: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即以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而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曰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 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棖,曷嘗以其欲為可乎? 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説備矣⑥[宋]朱熹:《濂溪先生祠堂記》,見[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鶴山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661 頁。。
魏了翁贊同胡宏的觀點,天理、人欲本是同時存在,對人性産生不同影響。古來聖賢也指出人性不能完全摒除欲望,有感即有欲。聖賢言“欲仁、欲立、欲達、欲善”,魏了翁領會其中深意,提出“以欲以求諸道”“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也就是説,人欲並不是一味要回避、要厭棄的陰暗面,若能以人欲為嚮善的動力,用道作為滿足欲望的標準,即“以欲以求諸道”,又何嘗不是美事? 反之,己所不欲者,即與道相悖,因從此曉明不與道相逆。而統攝人欲、使之歸之於道的,是人心。這是魏了翁與朱子學説的大不同。
魏了翁對朱子的理學有很多創造性的發展,提出“心者,人之太極”(《鶴山集·乙酉上殿劄子》,肯定人心對天地、宇宙的支配作用,“以主兩儀,以命萬物”(同上),成為朱學嚮陸學轉化的肇始之端①蔡方鹿:《魏了翁評傳》,第172 頁。;又提出“欲有善、不善存焉”,突破朱子“存天理、滅人欲”的權威,創造性地肯定人欲存在的價值,或者説是對人性的大包容。生於蜀地、長於蜀地的魏了翁,受地域文化的滋養與熏染,將天府文化精粹中的創造、包容融貫在學術研究、人生修為的多個方面。
因此,當朱子戴着一副“存天理、滅人欲”的眼鏡來讀《詩經》,自然容不下嘴裏説着“來即我謀”的女子們。“淫詩説”提出後,王柏主張删去《野有死麕》《静女》《桑中》《氓》等三十一篇,認為這些篇章是漢儒混雜其中以亂經。魏了翁卻尊重漢儒的解説,一是出於尊重《詩經》的時代背景,《詩經》産生在詩禮文化濃厚的先秦,後世闡釋《詩經》者皆不應强行植入後世的價值觀和學術思想;二是出於包容嚮善的人欲,這是魏了翁為何在朱學定為一尊的學術氛圍中可以獨樹一幟的原因,這也與天府文化創造、包容的精神内涵分不開。可見,魏了翁不贊同“淫詩説”與其“欲有善、有不善”的理學主張緊密有關,這一理學主張在天理、人欲之辯中大放異彩,也影響着理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