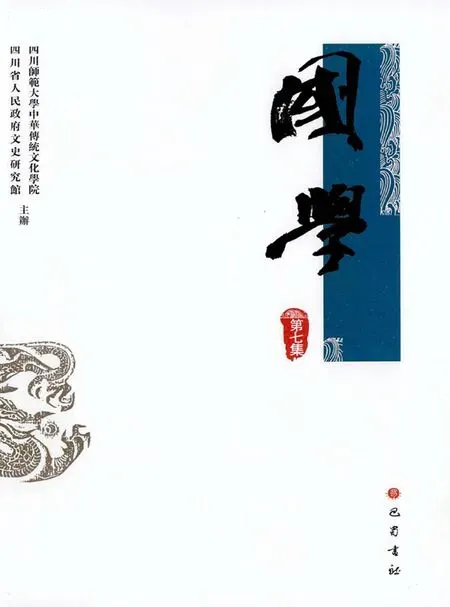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詩经·豳風·七月》雜用“陽曆”“陰曆”説
尹榮方
一、關於《七月》曆法的已知解釋
《詩經·豳風·七月》中“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之“日”,古代學者多以“月”解之,與詩中“七月”“九月”等月名同義。但何以一詩之中,或用月,或用日,《毛傳》《鄭箋》以下,大抵以為是夏、周二正互用,也有以為兼用殷曆者。而唐人孔穎達又用陰、陽之説解之:
此篇設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2—493 頁。。
王安石《詩説》云:
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 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 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①[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59 頁。。
王引之《經義述聞》則以“一之日”“二之日”為“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簡寫,無關乎陰陽。所以他駁斥王安石之説云:
介甫可謂不善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葽”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為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籜”,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 “蠶月條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稱月乎? 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説,而礙於“四月秀葽”之文,故彌縫其説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乃惠氏《周易述》尚取之以解“七日來復”,無乃惑於曲説邪②[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五,南京:鳳凰出版社,2000年,第140 頁。。
以陰、陽之别來説明《七月》中“日”“月”之義,確如王引之所説“終不可通”,也即無法作出合理解釋。
今人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則根據新發現的彝族十月太陽曆,認為《七月》所用曆法為十月太陽曆,詩中没有出現十一月、十二月,而詩中有“卒歲”“改歲”之語,是以十月為歲末。《七月》的“一之日”,《毛傳》解釋道:“一之日,十之餘也。”或相傳之古訓,其意為一年過完十個太陽月之後的餘日,即一年為三百六十五日,每月三十六日,十個月為三百六十日,餘下的五至六日就是餘日。《七月》中的“一之日”“二之日”等,便是這樣的餘日。這幾日的餘日,是重要的年節,主要安排宗教祭祀活動,如第一天為狩獵祭,第二天為武備祭,第三天為農具祭,第四天為農事祭等③劉毓慶:《詩義稽考》第5 册,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516 頁。。
此説新奇可喜,但並不能成立,因為《七月》所敘之物候、農事與“十月曆”不能相應,如詩中“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照《七月》十月曆之説,詩中“十月”相當於夏曆十二月,則十二月蟋蟀方入屋,無疑與事實不符。“十月獲稻”,以十二月收穫稻子,亦不合農事節律。又第七章“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若謂夏曆十一月方築場圃,十二月纔將莊稼收藏入庫,顯然也太晚了。而謂“一之日”“二之日”等“餘日”為年節,主要安排祭祀活動,則如此密集的祭祀活動根本不可能在四五日之内完成,如“一之日于貉”的“田猎之祭”,祭祀儀式還伴隨軍事訓練及狩田等活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所陳述者為鑿冰、藏冰、取冰等儀式,時間跨度相當長,再説《七月》還有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舉,若謂這些事與上述藏冰、取冰等儀式發生在二三日之内,更絶無可能。
二、上古有陽曆月、陰曆月兩種曆法,《七月》一詩雜用之。陽曆月用於天事,陰曆月用於人間之事,主要是農事
(一) 上古的陽曆月與陰曆月
上古曆法分為陽曆月與陰曆月兩種,陽曆月稱為月陽,也稱月雄;陰曆月又稱月陰、朔望月、月雌等。這兩種曆法,在《爾雅·釋天》中有明確記載。《爾雅·釋天》的十二月(月陰) 名為: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釋天》十月“月陽”名為: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尔雅注疏》,第170 頁。。
“月陽”“月陰”之名,郭璞、邢昺等注家,皆不明其義,故闕而不論。今天我們大致明白古人月分陰陽,月陽就是將一年分為十個月,即通過樹立圭表測太陽之影所確定之一年之季節月。月陽以冬至為一年之始,第二年冬至前為年末。初始之月為冬至後的約三十六日,依次類推,一年得三百六十日,一年實際三百六十五日或三百六十六日,餘下數日作為年節。此所謂十月太陽曆,除上古時代,還曾行於彝族等少數民族。
而“月陰”的十二月,則以月亮的陰晴圓缺為周期所確定,從《尚書·堯典》堯時“以閏月定四時”,及舜“五年一巡狩”的描述看,舜所使用的是陰曆月。陰曆月要制閏,所謂五年二閏,天道大備。陰曆月又稱朔望月,便於民間掌握與使用。《爾雅·釋天》十二月名與陰曆月相配,則主要着眼人事。當然人事須順應天時展開,把握天時,依月令天時行事,有利於獲得預期目標,這大約就是古人既名“月陽”又名“月陰”的緣由了。
《逸周書·周月解》:“周正歲道,數起於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這裏説到“時一而成於十”的“歲道”和“十有二月”的“四時成歲。”朱右曾注云:“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為一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成一歲。”①黄懷信、张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78 頁。
上古年和歲有區别,顧炎武《日知録》之《集釋》卷三十二云:“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 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吕命王,享國百年。’…… 《周禮》‘太史’ 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三百六十五日,實際即陽曆年)。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三百五十四日多,實即陰曆年)。’”②顧炎武又曰:“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矣。’”《集釋》引錢廣伯云:“ 《孟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 《趙策》:‘太后曰:年幾何矣?’ 對曰:‘十五歲矣。’ 則言歲不始於太史公。”見[清]顧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誠点校:《日知録集釋》,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第1137—1138 頁。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十一:“《玉海·天文》引《三禮義宗》云:“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為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為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③[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083 頁。這種區别,反映的也是上述兩種不同曆法的存在。陽曆月與陰曆月兩種曆法,始見於《山海經》,可見其古老。《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生月十有二,指創造了分一年為十二個月的曆法;而生十日,則是指創造了分一年為十個月的曆法。正如陳久金先生指出的:“十日是與十二月相對應的,中國遠古不但使用一歲十二個月的農曆,同時還使用過一歲分為十日(月) 的太陽曆。所謂羲和生十日,應當理解為羲和創造並使用了十月太陽曆,别的解釋是没有的。”④陳久金等:《中國天文大發現》,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第37 頁。又很多學者指出,中國干支的“十干”與“十二子”,“十干”對應的是十月曆,而“十二子”對應的則是十二月曆。
上古時代,陽月與陰月這兩種曆法是同時存在的,同時應用的。陽月主要應用於指示節气、祭祀等國之大事;陰月則用於指示物候、農事,是一種人事生産曆。《七月》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等用的是陽曆月,“五月”“六月”等用的是陰曆月。
“日”字本有“節”義,《廣雅》:“日、纇,節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三云:
日為節度之節,纇為絲節之節。《開元佔經·日佔篇》引《春秋元命苞》云:“日之為言節也,開度立節,使物咸别。”《白虎通義》:“日之為言實也,節也,常滿有節也。”
“日”可以解釋為“節”,則十“月陽”也就是十個時節的意思,節的功能為“開度立節,使物咸别”。十日之名,有利於對天時的把握,有利於進行所謂的“天事”。“一之日”也就是陽曆月的一月,“二之日”就是陽曆月的二月,依次類推。“一之日”指示的日子是冬至日起始的三十六天,略等同於夏曆的十一月,所以前人每以夏之十一月當之,但“一之日”即陽曆月的一月與夏曆的十一月是不能完全對應的。“二之日”指的是一月三十六天之後的第二個三十六天,其餘可以依次類推。
(二) 《七月》“一之日”“二之日”等用的是陽曆月,所陳述的大體是“天事”,與詩中用“月”陳述人事生産者有明顯的區别
且讓我們先看《七月》的有關陳述。首章“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描寫的是冬至後的節候,强調其寒冷,且不説。第四章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裳。二之日其同,載纉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我們細揆詩意,知“于貉”與“取彼狐狸”是兩事,《毛傳》“于貉”之解非為確解。“貉”是祭名,宋人羅願《爾雅翼》卷二十一:“ ‘于貉’ 者,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為貉。”①[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十一,合肥:黄山書社,2013年,第263 頁。可見“于貉”的意思就是行獵祭。又貉讀為禡,清人馬瑞辰説:
貉與禡古通用。鄭司農注《周禮·大司馬職》“有司表貉”曰:“貉讀為禡。書亦或為禡。”是禡即貉之或體字也。鄭康成注《甸祝》“表貉”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田有貉祭也。此詩“于貉”,當謂往貉,即《周禮·甸祝》表貉之祭,《傳》《箋》均讀貉為狐貉之貉,失之②[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59 頁。。
上古田獵,特别是冬狩,是確定時節、墾殖土地、軍事訓練、祭祀神靈等結合進行的大事,絶非單純為獵取野獸。田獵前往往先要祭社,狩獵結束又要用獵獲的野獸祭祀神靈。所以《爾雅》將“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這四時“狩獵”歸入《釋天》,視為天事。冬狩是大事,聚衆出發前,先有所謂的“宜”祭。《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郭璞注:“有事祭也。”③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尔雅注疏》,第183 頁。《七月》詩的“于貉”,指的顯然是冬狩前的祭祀。
而“二之日其同”之“其同”,《鄭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同就是行“會同”之禮,以狩獵、訓練也。而陳奂用《詩·小雅·車攻》“我馬既同”之同解釋“其同”:“同讀如我馬既同之同。《車攻》傳云:‘同,齊也,田獵齊足。’”①[清]陈奂:《詩毛氏傳疏》卷十五,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本。强調的都是會獵之舉。當然鄭玄、陳奂都有以後代禮制釋“其同”之嫌。《七月》時代,大約尚處於氏族社會,未必如後代周王出行那樣等級森嚴、軍容壯盛,但他們之以“田獵”解“其同”,應該没有什麽問題。
第八章“二之日鑿冰沖沖”,所説乃祭事甚明顯,因為下面接着就説:“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淩陰指冰室,陽月的三月藏冰於室。獻羔祭韭,説的是出冰的儀式。藏冰、出冰之禮一直傳於後世,《左傳·昭公四年》載申豐之言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②[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606 頁。《七月》於“納于淩陰”的藏冰儀式言之甚簡,據《左傳》,有用“黑牡”“秬黍”以祭享“司寒”之神的儀式。詩不妨一筆帶過,散文則可以從容敘述也。
再看第一章“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傳》解“三之日于耜”云:“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我以為《毛傳》此解必誤,此句當同於《夏小正》正月之“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畼”。什麽叫“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畼”? 盧辨注:“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畼也。畼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③方嚮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5 頁。
則“于耜”乃初歲農事開始之際所行之祭祀禮儀。方嚮東引元人金履祥之言曰:“祭始為耒耜之人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耜藉,則鬱人薦鬯。鬯之為言暢也。祭耒而用鬯也。”④同上,第155 頁。歲初祈農,上古所重,《七月》詩鄭重記載,當屬自然。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句之主人公,《毛傳》:“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然而我們揆諸《詩經》的其他篇目,可知此句所陳述者,仍關乎祭事,此句之主人,非泛指農夫,而是特指主祭之人,也即所謂的“周王”也。如范文瀾所言:“周先公居豳時,始耕舉行饁禮。”⑤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 第一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45 頁。《小雅·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又《小雅·大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兩詩的句式字句同於《七月》,其所及之人、意亦必相同。鄭玄箋《小雅·甫田》:“曾孫,謂成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第842 頁。雖有用後世之事繩上古事之嫌,然以此句之主人非指農夫,而指周王,卻是無可懷疑的。然則《七月》“四之日舉趾”者,周王也,也即主祭者也,他偕同婦子,以酒食祭祀“田畯”。田畯,上古主要有二義,一指農神,一指農官。這裏的田畯,非農官田大夫之謂,當如鄭司農注《周禮·春官·籥章》“以樂田畯”时所説“田畯,古之先教田者”②[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春官·籥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08 頁。即農神。“田畯至喜”,喜同饎,應讀為“至喜田畯”,即嚮“先農”之類的神靈祭獻,祭畢則衆人共嘗其肴也。
後世論者亦有懷疑《甫田》《大田》之“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應繫於曾孫(周王)者,以為王后衹有親蠶之事,王后從行勸農,不合上古禮制。此亦為以後世禮制繩上古禮俗。一年農業生産開始之際,《七月》行祀“田畯”之禮,後世則演為所謂“藉田”之禮。上古質樸,禮俗自然較為簡單,而從上古典籍記載看,“藉田”之禮,亦有王后參與之徵。周悦讓《倦遊庵槧記·經隱·毛詩》云:
據《周禮·内宰》:“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穀梁春秋·桓公十四年傳》:“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而藏之御廪。”是甸籍之事,后與有勞,故勸農報賽,後必從行,此亦可據以補《禮》經之缺也③劉毓慶等撰:《詩義稽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500 頁。。
至周代,王后及宫人猶有力田勸農之事,上古質樸,《七月》時代或尚屬氏族社會,君民之等級意識遠遜後世,則“周王”攜其妻兒“饁彼南畝”,祭神祈農為必有之事也。
(三) 《七月》詩中用“月”陳述者為物候與人事(農事)
由於“一之日”“二之日”等所陳述者皆為“天事”(含戎事),《七月》詩中用“月”(陰曆月) 陳述者則大抵為物候與人事(農事),現將《七月》詩各月的物候與人事(農事) 排列如下:
可見,繫於“月”下的,無非物候與人事(農事),《七月》詩明顯地表現為用“一之日”等陽曆月記載天事,用某“月”(陰曆月) 記載人事(主要是農事) 的形式。
這裏我們聯想到上古所謂的“三正”問題。傳統有一個説法,謂夏、商、周曆元不同為“三正”,即夏建寅,以正月為正;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周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書·甘誓》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語,馬融注:“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之三正也。”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10 頁。《甘誓》照一般的理解説的是夏代之事,此時尚無商,不要説周了,哪裏會有三正之説! 張汝舟先生曾指出:在四分曆産生之前,還衹是觀象授時,不存在完整的行用於夏代的夏曆、行用於商代的殷曆、行用於兩周的周曆,所謂夏殷曆、周曆,純係後人的概念。郭沫若及日人新城新藏也否定上古實行過所謂三正②新城新藏説:“關於三正論之文獻,由來頗古。然由研究春秋長曆之結果,可知其斷非春秋以前之歷史上之事實。余以為,蓋在戰國中葉以降,將所行之冬至正月曆(建子) 撥遲兩個月,改為立春正月曆(建寅) 時,因須示一般民衆以改曆之理由,遂倡三正論而篤宣傳耳。其後,因秦代施行十月歲首曆(建亥),更加以漢代之宣傳,遂至認三正交替為上古歷史上之事實。時至今日,信者尚不乏人,此於中國上古天文曆法發展史之闡明,繫累非淺,誠可謂憾事。”郭沫若引新城氏之説後申論道:“所謂三正論係出於後人捏造,毫無疑問,唯造此説之時代不當在戰國中葉,而當在春秋末年。”見郭沫若:《青銅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5—86 頁。。《毛傳》以下的解詩者,多有以為《七月》雜用三正者。我以為此必古人誤解,所謂三正,本義當指“天”“地”“人”也,鄭玄所謂“天、地、人之正道”。《漢書·律曆志》以“三統”同於三正:“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黄鐘子為天正,林鐘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之始。”
以三正為天地人之説,實際上與夏商周三代之三正的説法有所不同。三正之説後來被説得神乎其神,其實多有不通之處,它傳承的或許是上古存在分别用於“天”及用於“人”的不同曆法而已。
從《爾雅·釋天》《書·堯典》等上古典籍所載之上古曆法看,所謂“三正”之説,或源於《爾雅·釋天》的“月陽”“月陰”所揭示的曆法之不同,《堯典》雖無“月陽”“月陰”之名,但所載為兩種曆法則甚明。從所謂的堯、舜時代開始,就存在兩種曆法並存的局面。“陽曆月”主要用於對一年時節的把握,即分至啓閉等節氣的測定。統治者通過對時節的確定與相應的祭祀活動,强化其對“天”的尊重,以顯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但對一年時節的把握並不能直接應用於人事活動,所以古人又創“陰曆月”這樣的人事曆法,便於民間的生産、生活。《國語·楚語下》觀射父答昭王問,有“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①《國語》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2、563 頁。之説,包含了分别運用“屬神”與“屬民”兩種不同曆法的意藴。而“屬民”之曆法為“火正”黎所掌,火正就是以觀測大火星出没沉降來判定時節,以指導人們從事農業生産活動的專職人員②龐朴指出:“火正的職稱,標明其職務是觀察大火。‘司地’ 即‘司土’,也就是後世的‘司徒’,同農事民事有關,故‘屬民’。”見龐朴:《火曆鈎沉——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曆之發現》,《中國文化》1989年第1 期。。而《七月》開首便言“七月流火”,所反映的正是民事活動對“火曆”的應用。“南正”以下,照韋昭注:“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群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③《國語》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2、563 頁。“南正”是觀測太陽及星辰的運行以定季節,確定祭祀神靈日子的專職人員。“火正”與“南正”各有職司,不相干擾。
古代史家有所謂民事與天事之分,認為上古時代人們更重天事,天事指對天象、天文的觀測及曆法的制定及相應的祭祀、佔卜等禮儀事項。虞夏以後,轉嚮以生産及衣食住行等人事為急。鄭樵《通志》卷二《五帝紀二》:“上古之時,民淳俗熙。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為務,故其治略於人而詳於天。……唐虞之後,以民事為急,故其治詳於人而略於天。”從《七月》詩反映的情況看,《七月》時代無疑早進入“詳於人而略於天”的時代,但晚周之人猶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七月》時代,“奉天事神”必仍在氏族或國家事務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然無論“奉天事神”還是以“民事為急”,在上古農業社會,治曆明時都是必須面對的絶大之事。在所謂的虞夏以後出現嚮民事的轉嚮後,形成奉天地分司的歷史,可追溯到《山海經》時代。《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即《國語·楚語》所謂重、黎“絶地天通”也。“事神”之曆與“民事”之曆並舉的情況,是並不奇怪的。
(四) 《七月》“曰為改歲”原意解
《七月》五章:“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嚮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章所云“改歲”,前人解者紛紜,或謂此證明彼時民間通行“三正”。《朱子語類》卷八十一: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吕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①[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112 頁。
吕東萊、朱子之謂《七月》迭用“三正”,是不知上古曆法原分“天事”“人事”兩種,此不足怪也。而持《七月》曆法為十月太陽曆者,則據此以為十月曆之堅證,然《七月》十月曆之不可通,前面我們已加證明。那麽《七月》為何言“曰為改歲”? 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云: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②[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9 頁。
王應麟此説,為古今很多學者所贊同,但我們聯繫前面顧炎武指出的上古“歲”與“年”的區别,則可以斷定這裏的“改歲”,是指陽曆月而言的。清人馬瑞辰曰:
“曰為改歲”,猶曰“歲聿云莫(暮)”,特先時戒民入室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不得以為十月,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異也③[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58 頁。。
馬氏雖不知《七月》陽曆月、陰曆月雜用,但他指出“改歲”就是説“歲聿云莫(暮)”,是預先告誡民衆做好歲末“入室”的準備,則是正確的。“穹窒熏鼠,塞嚮墐户”以及表面繫於十月的“于茅”“索綯”“乘屋”等,俱為年終行事,詩中統而言之也。
三、比較《七月》農事與《爾雅·釋天》十二月名
《爾雅·釋天》十二月名實際是一種人事(主要是農事) 曆,以一年中各月的主要人事活動名月,構成一種人事曆,這在很多民族的早期階段都能看到。如哈尼族的十二月名依次為:送舊月、迎新月、草死月、地濕月、種穀月、踩粑月、黴雨月、拔草月、熬酒月、嘗新月、入庫月、櫻花月,雲南虎家白族“直接以當月的物候和人們的生産活動來作為月名,順次為太陽不動月、太陽起來月、樹枝發芽月、開始種地月、農忙月、再種也不收月、饑餓月、無力氣月、糧食始熟月、完全成熟月、狩獵月、酒醉月”①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彝族天文學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3 頁。。彝族創世史詩《梅葛》第三章《農事》説道:“四季如何分? 楊柳發芽,布穀鳥叫,春季就到;蛤蟆叫,青蛙叫,夏季到;知了叫,秋季到;雁鵝叫,冬季到。一年十二月農事如何安排? 正月去背糞,二月砍蕎把,三月撒蕎子,四月割大麥,五月忙栽秧,六月蓐種忙,七月割苦蕎,八月撒苞穀,九月割了甜蕎撒大麥,十月糧食裝進倉,冬月撒小麥,臘月砍柴忙過年。”②馬學良等:《彝族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5 頁。
將《七月》各月人事活動與《爾雅·釋天》十二月名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兩者大致可以對應。
(一) “蠶月”與“三月為寎”
《七月》第三章有“蠶月”,雖不以數位名,但可以看作農事曆的殘餘,顯然指的是三月。蠶月的農事活動為:“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説的都是採桑養蠶之事。《釋天》:“三月為寎。”《釋文》:“ ‘寎’,本或作‘窉’,字同。”阮元校云:
按《廣韻·三十八梗》:“窉,《爾雅》云:‘三月為寎。’ 《四十三映》:‘寎,驚病。’ 《玉篇·穴部》:‘窉’,筆永切,穴也。”部無寎字。是此經本作“窉”也③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第170 頁。。
“三月為寎”之“寎”為“窉”之誤,而“窉”義為穴。此穴,當是指蠶室。三月人們忙於蠶事,故三月又名“蠶月”。除了《詩·七月》有“蠶月條桑”等語,《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宫事。”《禮記·月令》載三月:“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籩,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吕氏春秋·季春紀》記載略同。故三月稱“窉”者,以名蠶室、蠶事也。《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宫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説古代天子、諸侯都築有蠶室用來養蠶,自非虚言。《説文》穴部:“穴,土室也。”《禮記》所謂“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的蠶室正是土室。蠶蟻畏風畏寒,故蠶室須密封。《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注:“蠶室,宫刑獄名。宫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①[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80 頁。受宫刑的人要進入“蠶室”,這裏的蠶室不是養蠶之室,而是獄室之名,因為關押的是接受宫刑者,這些人“畏風,須暖”,所以要挖地下室處置他們。由此可見養蠶之室也是穴室,“窉”義為穴,當是蠶室之專名。
則《釋天》“三月為寎”言三月為養蠶之月,與《七月》所載“蠶月”農事完全相應。
(二) “四月秀葽”與“四月為余”
《七月》:“四月秀葽。”《毛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鄭玄箋:“ 《夏小正》:‘四月,王萯秀。’ 葽其是乎?”而魯詩謂:“此味苦,苦葽也。”韓詩則曰:“葽草如出穗。”②[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16 頁。可見,“葽”到底是什麽植物,毛、鄭不能確定。魯詩“苦葽”之説,影響較大。《説文解字》草部:“葽,草也。從草要聲。《詩》曰:‘四月秀葽。’ 劉嚮説:此味苦,苦葽也。”許慎雖引劉嚮之説,同魯詩説為苦葽,但何為苦葽,後人仍難以確定,故段玉裁注云:
《小正》“四月秀幽”,幽、葽一語之轉,必是一物,似鄭不當援王萯也。劉嚮説“此味苦,苦葽也”,苦葽當是漢人有此語。漢時目驗,今則不識。其味苦則應夏令也。小徐按:“ 《字書》云:‘狗尾草。’ 夫狗尾即莠,莠四月未秀,非莠明矣。”③[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62 頁。
後人又有葽為遠志、狗尾草之説,實難以成立。我以為,作為農事標志的植物,必是對民衆具有重大意義者。四月秀葽,不僅説物候,亦云農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至今本《夏小正》“王萯秀”之下、“秀幽”之上多“取荼”一句,金仁山本作“取荼秀”,此當在“秀幽”句下,乃《傳》釋“秀幽”之文,謂於時取荼秀也①[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58 頁。。
《夏小正》“取荼”後有“秀幽”,“幽”與“葽”音近可通,則《七月》“四月秀葽”意為取“荼秀”也。惟這裏的“荼”,究指何物? 不少古人包括馬瑞辰以為指苦菜。而《七月》九月有“采荼薪”之語,則此“葽”必非苦菜之荼也。荼之一字,有二義,一指苦菜,一指六穀之一的“苽”。這裏的“荼”,乃為“苽”,“苽”是上古的一種穀物,是“六穀”之一,又名蔣。所以盧辨注:“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②[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6 頁。以荼為蔣,則四月為“取荼(蔣) 之月”。
《釋天》:“四月為余。”郝懿行疏引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余”,《釋文》:“余、舒二音。”③[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中之四》,北京:中國書店1982年據咸豐六年刻本影印。我以為余為荼,不必以舒為解也。此即《夏小正》四月“取荼”“秀幽”之“荼”(蔣) 也即苽也,與《七月》“四月秀葽”意藴一致。《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鄭玄注引鄭司農之説:“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④[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彭林整理:《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 頁。。《説文》草部:“苽,彫苽,一名蔣。”關於“苽”,孫詒讓廣引經籍,言之甚詳:
《西京雜記》云:“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廣雅·釋草》云:“菰,蔣也。其米謂之彫胡。”《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菰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楚辭·大召》:“五穀六仞,設菰粱兮。”王逸注云:“菰粱,蔣實,謂彫胡也。”案:苽、菰,彫、胡、葫,字並同。……《古文苑》宋玉《諷賦》云:“為炊彫胡之飯。”《内則》云:“苽食”。《論語·鄉黨篇》云:“雖疏食菜羹苽祭,必齊如也。”故二鄭以充六穀之一。但苽非常食,劉嚮《烈女傳·母儀篇》云:“精五飯”,蓋以六穀去苽是為五飯矣⑤[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85 頁。。
可見,苽是古代重要作物,孔子時代尚作為祭品使用,曾被稱為“六穀”之一,《爾雅》四月稱為“余月”,意四月為“取荼”之月,實指取苽也。蓋“余(荼)”與“苽”音近,上古或通言之也。然則《七月》“四月秀葽”與《爾雅》“四月為余”意藴相同。
(三) 五月無農事與“五月為皋”
《七月》五月載“鳴蜩”“斯螽動股”這樣的物候,而無農事項目。有意思的是,《釋天》五月名“皋”。為什麽五月叫皋月? 郝懿行疏曰:“皋者,《釋文》或作高。今按皋、高音義同,皋者皋韜在下也。”《書·堯典》:“仲夏……其民因。”什麽叫“因”? 《説文》口部:“因,就也。”而“就”,《説文》京部:“就,就高也。”段玉裁注“因”:“就下曰:‘就高也。’ 為高必因丘陵,為大必就基阯,故因從口、大,就其區域而擴充之也。”然則“因”者,謂民就高也。《禮記·月令》五月:“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高陵,可以處臺榭。”《淮南子·時則訓》記載略同:“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説的就是民之就高。仲夏高温,又加濕蓐,於是民避居高曠涼爽處。則五月為皋,謂民居高處之月也。
然則《七月》五月無農事項目,百姓轉移到高曠涼爽處避暑了。
(四) “食鬱及奧”與“六月為且”
《七月》六月農事為“食鬱及奧”,《毛傳》:“鬱,棣屬。薁,蘡薁也。”鬱,棠棣之類,果實像李子,赤色。蘡薁,俗名山葡萄、野葡萄。六月的“食鬱及奧”,説的是六月是棠棣、山葡萄等果物成熟嘗食的季節。
《釋天》:“六月為且。”郝懿行疏:“且者次且行不進也。六月陰漸起,欲遂上畏陽,猶次且也。”把“且”解釋成趔趄之“趄”,無與民人活動之事。《夏小正》六月事甚簡,惟記:“煮桃。”盧辨注:“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桃等果類很早就是人們嘗食與腌製的食品。《周禮·天官·籩人》曰:“饋食之籩,其實桃。”《禮記·内則》記有:“桃諸,梅諸,卵鹽。”孔穎達正義云:
言食桃諸、梅諸之時,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乾之。”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845 頁。《釋名·釋飲食》:“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用之也。”《詩·大雅·韓奕》:“籩豆有且。”鄭箋:“且,多貌。”然此多乃是從食物之多引申之語。則“且”或由“俎”而通“菹”。“六月為且”者,謂六月為用鹽(卵鹽,指一種大鹽) 菹製桃、李、梅等果物之月也。六月為果物成熟之節,除了食用,古人還加以醃製收藏。上古食品種類較簡,桃、李、梅等果品必是重要食品,菹製桃、李、梅等果物,可使此類食品長期保藏,自是彼時重要民生工程,故古人以之名月也。
我們可以想象,《七月》時代的人們,六月之時,除了嘗食各類成熟的果物,吃不完的,大約也會醃製收藏的,衹是在詩中無法完全表達罷了。
(五) “萑葦”與“七月為相”
《七月》七月農事主要為“烹葵及菽”“食瓜”。《釋天》七月為“相”。《夏小正》七月有“灌荼”之舉,盧辨注:“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我以為相義為視,審視也,審視土宜,以待燒田開發,此相之所以名七月也。《詩·鄭風》鄭玄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則“灌荼”為割聚茅、葦之類的野草,有用者取為製作材料,餘下的乾後燒掉。《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凡開荒山澤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幹即放火,至春而開墾。其林木大者殺之,葉死不扇,便任耕種。三歲後,根枯莖朽,以火燒之。”①[北魏]贾思勰:《齊民要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草割除曬乾後方能燒田,大樹則切割一圈樹皮使樹枯死,葉子枯死,不再遮陰,就可以耕種了,三年後再燒樹。所以芟草之舉絶不可少。所以七月為相,意為七月為審視土宜,割草開發之月也。
《七月》之農事似與《釋天》不合,但《七月》八月有“萑葦”。《毛傳》:“薍為萑,葭為葦。豫蓄萑葦,可以為曲也。”②李學勤主編:《十三经注疏·毛詩正義》,第496 頁。曲,指養蠶器皿。可見割取茅、葦之類的野草是上古重要的農事活動,過去認為此類農事活動的目的為製器,但除了製器取材,更重要的是燒荒墾田。而燒荒墾田,要相“視”土宜,遵循時令,《禮記·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燒田之時同時也是圍取獵物之時,所以“田”字又可作“田獵”解。又古人將圍獵與軍事操練結合,所以《禮記·月令》七月每冠以“出征”等所謂軍事活動,蓋以此也。然則《釋天》七月名“相”,與《七月》八月之農事仍相應也。
(六) “八月其獲”與“八月為壯”
《七月》八月農事主要為“其獲”“載績”“剥棗”“斷壺”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獲”,收穫禾穀。“其獲”,《毛傳》:“禾可獲也。”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经注疏·毛詩正義》,第500 頁。禾,今謂小米。古稱“穀”或“嘉穀”。《説文》禾部:“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則八月是重要的糧食作物小米及瓜果等成熟之月,是農忙之月。
《釋天》:“八月為壯。”以壯名月,説的顯然也是八月乃禾穀、瓜果等作物壯大成熟之月。
(七) “九月授衣”與“九月為玄”
《七月》九月農事主要為“授衣”、“叔苴”(拾取麻子)、“採荼薪樗”(採荼指採荼為菜,薪樗指砍取樗以為柴火)、“築場圃”等。
《釋天》:“九月為玄。”《夏小正》八月有“玄校”,説的是染織之事。盧辨注:“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緑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王聘珍注謂:
《説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為玄。”校讀曰絞。鄭注《雜記》云:“採青黄之間曰絞。”傳云“絞也者,若緑色然”者,《説文》云:“緑,帛青黄色也。”玄絞之為色,五采皆備②[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2 頁。。
上古染織雖有五色,但以玄色為主,故以玄言染事也。《七月》云:“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所染之色有玄、黄、朱(紅) 等颜色。
然則九月為玄者,九月為染織之月也。《七月》染織之事在八月,蓋環境有不同,地有寒暖,人事、農事或略有先後也。
(八) 十月“納禾稼”與“十月為陽”
《七月》十月農事主要為“獲稻”“納禾稼”“塞嚮墐户”“于茅”(取茅草) “索綯”(搓繩) “乘屋”(修治房屋) 等。“獲稻”“納禾稼,黍稷重,禾麻菽麥”。《七月》農夫,需收穫、收藏的糧食種類很多。
《釋天》:“十月為陽。”《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命之曰暢月。”何謂“暢”? 鄭玄注:“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孔穎達解曰:
“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曰: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553 頁。。
“暢月”,《淮南子·時則訓》作“畼月”,高誘注:“陰氣在上,民人空閑,故命曰畼月。”段玉裁説:“今之暢,蓋即此字(畼) 之隸變。”②[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1212 頁。《禮記·月令》:“季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也講的是收藏。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律中應鐘。”《漢書·律曆志》曰:“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陽”與“暢”形近,或“陽月”為“暢月”之訛,暢月者,收藏之月也。春種、夏耘、秋收、冬藏,十月進入冬季,乃收藏季節,所收藏者主要是糧食作物。
則《釋天》“十月為陽”之名與《七月》農事之“納禾稼”等相應。
四、比較《七月》“天事”與《爾雅·釋天》十“月陽”名
《七月》各月之農事與《釋天》月名所昭示的農事大體一致。而《七月》“一之日”“二之日”等“日”名所繫之“天事”,似也與《釋天》“陽曆月”之名吻合。
(一) “一之日于貉”與“月在甲曰畢”
《七月》第四章“一之日于貉”,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指的是仲冬田獵之舉。《釋天》:“月在甲曰畢。”畢,古代田獵用的長柄網叫畢。畢又為天上星宿名,為白虎七宿的第五宿,有星八顆,似田獵用畢網,故名。畢星升於中天之際,正是地上狩獵之節,故以畢名星,示可行獵矣。上古兵、獵一事,故以畢星主兵。《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索隠》:“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③[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0 頁。“畢”月為冬至後第一月,冬至節處於農曆之十一月,上古正有十一月(仲冬) 田獵之事,《釋天》又有“冬獵為狩”之説。《夏小正》十一月“王狩”,盧辨注:“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又田獵與“紀時”結合,《夏小正》又言“隕麋角”,盧辨注:“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嚮生皆濛濛符矣。故麋角隕,紀時焉耳。”可見田獵與紀時授時結合,不僅王者參與,且有一定儀式,故屬“天事”。然則《七月》“一之日于貉”與《釋天》“月在甲曰畢”含義可通也。
《釋天》:“月在乙曰橘。”郝懿行疏云:
橘本或作,《廣韻》云:“月在乙也。”然則橘月者,畢星象,匕橘之言矞,以錐穿物之名。月在甲乙,盛德在木,象萌芽穿地而出也①[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中之四》,中國書店影印本。。
畢假為匕,匕者,箭鏃。而“矞”,《説文》:“矞,以錐有所穿也。”“匕”“矞”屬於同一物類,連屬成詞,形容甲乙之月陽氣萌動,穿地而出之狀。郝疏或得之。而畢又星象名,畢所象徵者為田獵、兵事,則“月在乙曰橘”之“橘”,當即指“矞”,此“矞”,《説文》謂以錐有所穿,《廣雅·釋詁》:“矞,穿也。”②[清]王念孫著,鍾宇訊點校:《广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6 頁。必古田獵(兵器) 名,用於田獵、兵事,上古田獵持續時間很長,“月在乙曰橘”,所言者,仍為田獵事。而“二之日其同”者,亦承“于貉”言之,言會同,説的也是田獵之事也。
(二) “三之日于耜”與“在丙曰修”
《七月》“三之日于耜”,指陽曆月的第三月,約相當於夏曆的正月祭祀耒耜之舉。《釋天》:“月在丙曰修。”《毛傳》解“于耜”為“始修耒耜也”。後人多以為正月有修治耒耜之舉,《月令》季冬有“修耒耜”。則《釋天》“月在丙曰修”或關乎“修耒耜”之事,惟修字每用於祭事,如《史記·封禪書》:“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漢書·郊祀志》:“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論衡·祭義》:“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這裏的修字都有祭義。然則《釋天》“月在丙曰修”,謂三月(丙月) 為祀月,由於三月為人所共知的準備農耕之月,則此月名修,意謂“祀耒耜”之月,與《七月》之“三之日于耜”正可通也。
(三)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與“月在丁曰圉”
《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略當於夏曆二三月間,獻羔祭韭,説的是出冰的儀式。《禮記·月令》仲春也有“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儀式,需要用羔羊祭祀祖先神靈。羊在上古人們的祭祀生活中佔有如此地位,而圈養祭祀所用之羊等牲畜也必然會成為人們生産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釋天》四月名“圉”,《左傳·哀公十四年》:“孟孺子洩将圉馬于成。”杜預注:“圉,畜養也。”①[春秋]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李夢生整理:《春秋左傳集解》,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869 頁。“圉”義為養,而《夏小正》二月有“初俊羔,助厥母粥”。盧辨注:“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②[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0 頁。“粥”與“鬻”同,都是養的意思。“初俊羔,助厥母粥”的意思為,羔羊開始長大,可以自己食草,不用吃其母之乳了,其母可以再孕育小羔,因為羊之性,要等待已生小羊羔不再吃母乳,離母羊而去,纔會再生育小羊羔。盧辨注“或曰”以下,王聘珍《解詁》云:
云“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者,《爾雅》曰:“夏,大也。”《説文》云:“煮,亯(享) 也。”謂大烹而祭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曰:“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云“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者,為猶助也。言是時獻羔之祭《小正》不記,而記羔之助厥母粥也。云“與羔羊腹時也”者,與,許也,嘉美之辭。《爾雅》曰:“腹,厚也。”善羔羊厚生之時也③同上,第30—31 頁。夏有煮祭之“夏”,一本誤作“憂”。但于鬯曰:“此憂當非誤字。諸家皆據傅崧卿《夏小正》本改為夏,反覺未妥,以為夏之夏與? 則二月乃春也,非夏也。以為夏后氏之夏與? 則既在《夏小正》篇中,何煩特出夏字? 且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疑‘煮’ 當作‘暑’,後儒皆從之。是即《周禮籥章職》所謂仲春晝擊工鼓歈《豳詩》以逆暑者,周人亦有之矣,不獨夏有也。下文云“祭也者用羔是時也”,然則煮祭用羔,用羔必殺羔矣,是可憂也,故曰‘憂有煮祭’。下文又云‘不足喜樂’,正以羔而殺之非喜樂之事。不足喜樂,與此‘憂’ 字其義相貫,則足見此‘憂’ 字之不誤。”可參方嚮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第189—190 頁。。
可見,“月在丁曰圉”之“圉”,强調的正是養育祭祀所用之犧牲之意,與《七月》及《夏小正》之記載相通。
五、《七月》曆法為“殷曆”説
從上述比較可知,《七月》之農事與《爾雅·釋天》十二月(陰) 名及十月(陽) 名大致可以對應,這説明《七月》與《釋天》所産生的時代、社會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七月》的作者,過去多認為是周公,《詩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禝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雖説是周公作,但陳述的卻是周先人之事迹。《朱子語類》卷八十一: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或以為此詩是“周公遭管蔡之變而作”①[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112 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傳承《七月》作於公劉之世。《孔叢子·記義》載有孔子之語:“ (吾) 於《七月》見豳公之造周也。”②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4 頁。《漢書·地理志》也以為此詩作於公劉處豳時期,宋代范處義、胡宏等皆以為《七月》作於公劉之世。崔述《豐鎬考信録》以為“此詩當為大王以前豳之舊詩,蓋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誤為周公所作耳”③[清]崔述撰,(日) 那珂通世校點:《崔東壁先生遺書十九種》上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542—543 頁。。
公劉之世,與周公、成王之時相距極遠,但謂此詩周公作者,也常强調所述是周先王之事,則此詩之古老,前人的看法大體是一致的。但徐中舒説《七月》是魯詩④徐中舒:《豳風説》,載徐中舒:《徐中舒論先秦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77 頁。,蔣立甫謂“其寫定的年代,不能早於西周中期”⑤蔣立甫:《詩經選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56 頁。。郭沫若甚至以為《七月》寫作時代“當在春秋末年或以後”,理由是:“自春秋中葉至戰國中葉所實施的曆法即是所謂‘周正’,那麽合於周正時令的《七月》一詩是作於春秋中葉以後,可以説是毫無疑問的了。”⑥郭沫若:《青銅時代》,第85 頁。此説與傳統説法相去太遠,且《七月》曆法,不是所謂的“周正”,郭沫若此説顯然不能成立。
古今學者之所以認為《七月》曆法是所謂“周正”者,與此詩為周公所作或所編的認識有關,既然《七月》為周公所作或所編,則其曆法自然要用所謂的“周正”了。
我以為,要判定《七月》的曆法文化諸問題,還是離不開《爾雅》的有關記載,因為《七月》與《爾雅·釋天》的曆法文化背景是一致的。《爾雅》雖有後世竄入的成分,今本《商頌》所言“龍旂十乘”,必是白色。《釋天》:“練旈九。”郝懿行疏:“ ‘練旈九’ 者,必是殷制,與周不同,周制天子十二旈。”又《釋地》:“齊曰營州。”郭璞注:“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郝懿行疏:
《爾雅》成書也甚晚,但有迹象表明,《爾雅》書中多言殷商文化。如《釋天》“素升龍於縿”。郭注:“畫白龍於縿令上嚮。”郝懿行疏:“ 《爾雅》綢杠升龍皆用素,蓋旂從殷制。”
郭云此蓋殷制者,《釋文》引李、郭同。《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是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周禮》異,故疑為殷制。今按十藪多異《職方》,疑亦殷制①[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中之四》,中國書店影印本。。
《爾雅》九州之名,注家都以為是殷制②《書·禹貢》中已出現九州,我認為此九州出自《山海經·海内經》的“禹卒佈土以定九州”,但《海内經》的“九州”是個與天地開闢神話有關的概念,完全不能和後來的神州九州對應。這點其實從“州”這個字的本義也可看出。《説文》:“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衆川。昔禹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今本《山海經》有九州而無九州具體之名。《書·禹貢》九州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後世九州中任何一州,有周遭為水環繞者乎? 可見後世之九州,決不是上古人們“治水”後劃定的九州。上古九州,與禹迹、九有、九土、九圍等概念相同,是人們在認識宇宙天地結構時形成的地理概念,它與四方及八方位的空間概念具有密切的聯繫,八方加上中間就是九土或九州。九州在上古,絶非實際的行政區域。今本《山海經》的《海内經》《海外經》《大荒經》都按東、南、西、北方位編排,四海與四極都有四方極地,也就是最遠之地的意思,它們的結構是相同的。。郝懿行還懷疑《爾雅》“十藪”之名,也是殷制。上古天地相應,則其《釋天》《釋地》多用殷制,可證所言曆法制度也必涉殷制。
《七月》類《月令》,而《禮記·月令》所言制度,前人指出多用殷制,如鄭玄注《月令》孟春:“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③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456 頁。又云:“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 蓋殷禮也。”甚至連一些季節性的祭祀之名反映的也是殷禮,如《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
周禮因於殷禮,《論語》孔子已道之,這自然不是出於孔子的直覺,而是孔子基於歷史傳承以及文獻記載所做的判斷。周代貴族子弟將學習傳承前代文化特别是殷商文化放在極重要的位置,《禮記·文王世子》記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什麽是瞽宗? 《禮記·明堂位》:“瞽宗,殷學也。”鄭玄注:“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④同上,第626 頁。
月令是殷商禮樂的基礎性因數,周人嚮殷人學禮樂,自然也會繼承殷人的月令及曆法制度。當然周人對前代禮樂是有所損益的,但有些文化制度如曆法等主要還是繼承前代。從《七月》“七月流火”等文字看,《七月》詩叙人事所用者實乃“殷曆”,因為據《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傳·昭公元年》也有“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之説。殷商卜辭有很多商王、商巫祭祀“火”的文辭,指的也是大火星。
無論周先王抑或西周甚至東周時代,用的都是丑正。張汝舟先生對古書古器留下的四十一個西周曆詳加考證,結論是建丑居多,少數失閏建子建寅。他的《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表解》更以大量確證,論定西周承用殷曆建丑①陳久金等:《中國天文大發現》,第50 頁。又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春秋長曆的研究》,發現在魯文公與宣公的時代,曆法上有過重大的變化。以此時期為界,其前半葉以含有冬至之月份的次月為歲首(所謂建丑),其後半葉則以含有冬至之月份為歲首(所謂建子)。他這個發現,是根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三十七次日蝕(其中有四次應係訛誤),用現代較精確的天文學知識所逆推出來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很有科學的根據。(見郭沫若《青銅時代》第85 頁引),可見“殷曆”對周人影響之巨。
張聞玉先生指出,不唯西周,春秋用曆亦並不建子為正,而多用丑正:
春秋用曆,有記載可考。隱公三年寅月己巳朔,經書“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當是建丑為正;桓公三年未月定朔壬辰,經書“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亦是建丑為正。其他春秋紀日,皆可定出月建。事實是,僖公以前,春秋初期是建丑為正。這自然是賡續西周。不能設想,西周建子為正,到春秋突來一段丑正。正因為是觀象授時,無曆法以確定置閏,確定朔日餘分,失閏失朔便極為自然。少置一閏,丑正就成了子正;多置一閏,丑正就成了寅正。到僖公以後,出現建子為正,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到了戰國時期,各國普遍行用四分曆,建正不同是事實②同上。。
張聞玉的意見,與日本學者新城新藏的看法大體相同。《爾雅》多言殷制,《釋天》曆法當為殷制,加之周人曾長期使用丑正,而《七月》曆法同於《爾雅·釋天》,則《七月》所反映的曆法必為殷曆也。
六、《七月》與《夏小正》之比較
將《七月》物候、農事與《夏小正》物候、農事比較,我們發現兩者高度契合。
《七月》物候、農事與《夏小正》物候吻合之處甚多,而《夏小正》記物候、天、人之事總體多於《七月》。《七月》事分“日”“月”,可見其形態之古老。《夏小正》渾然不分天事、人事,顯然經過後人的整理、編輯。但兩者所由産生的文化社會背景一定是相同的,過去很多人認為《夏小正》是所謂夏人的曆法,笔者以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夏小正》曆法與《七月》《爾雅》十二月曆出於同一系統,它們都屬於“殷曆”,有殷文化的背景。《逸周書·周月解》:“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七月》與周先民關係密切,所以有人以為詩中或用周曆,而《周月解》指出周人“敬授民時,巡狩祭享”(注意,這裏將人、天之事做了區分) 所用乃“夏(曆) 焉”,這裏的夏,實際乃是殷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