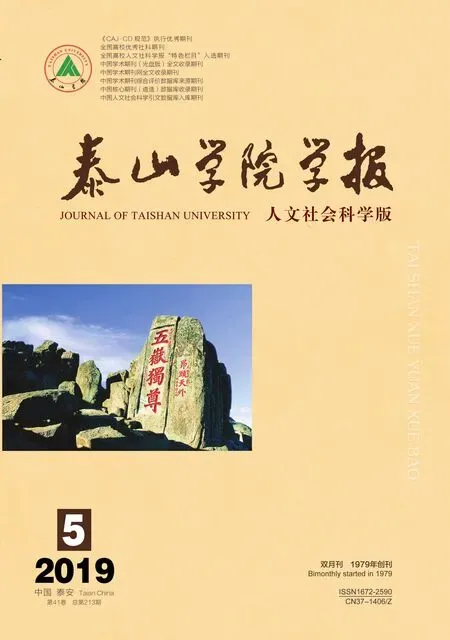现象学的召唤:走向个人真实发声的教师教育
魏建培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传统教师教育模式,是被技术理性和工业效率主义的话语所建构,它以普适教育理论知识和方法性知识为核心,通过投入、产出的流水线的工厂化模式,训练“技术熟练者”。由此建构了一种沉默的教育——个体生活经验遭到禁止,掩盖了教师教育者和准教师个体的经验与声音,个体成为远离自己生活经验的沉默者,通过沉默压抑身体和心灵而带来了与自我的疏离。这造成了教师教育的异化。这种教师教育的痼疾,随着准教师成为教师,会扩散、蔓延、流行到基础教育中,导致基础教育异化。现象学是对启蒙理性控制取向的反思,在教师教育领域引入现象学,可以起到阻止这种异化的作用。本文基于现象学精神,首先对技术理性及其建构的教师教育展开批判性反思;其次,建构一种个性化教师教育,引发个人真实发声、打破沉默,最终克服异化、走向解放。
一、现象学对技术理性及其教师教育的批判
现象学者认为,技术理性“表现了对控制的工具主义兴趣”[1],它基于“二元论”,把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割裂开来,把环境设置为“客体”,人这个“主体”则借助于规律、规则、程序而控制环境,人最终也被控制了。技术理性还坚持,事物是有秩序的、有等级制度组织;事物的本质是确定的、可预见性的和可控制的。教育心理科学能够预测人类行为,教师教育中的个体是可控的,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目标管理、能力本位的教育、执迷于标准化考试和行为目标,最终实施工厂化流水线生产教师客体。这与现象学的认知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以下从几个方面分别对此予以现象学批判。
(一)现象学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当代现象学教育哲学家瑪克辛·格林对技术主义的批判令人印象深刻,她说,我们处在“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2],这是造成人被动,把现实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源。技术统治源于人类的精神匮乏而对物质无尽追求。“这种痼疾反映在,对物质进步来满足人类精神的文明怀有一种无力感——追求更高的收入、更营养的食物、特效药、应用物理和化学的胜利等”。[3]格林通过对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描述的一个场景,展开了对技术理性痼疾的批判:
在浓雾的笼罩下,哈克和杰姆刚刚乘着小木筏漂流经过开罗,……忽然之间,下游传来了汽船开过来的声音,他们急忙点亮一盏灯……(意思是让汽船)避开他们的木筏子。但是,汽船从木筏上径直开过,……这些轮船根本没有把木筏子上的工人放在眼里。哈克所能做的只是聆听汽船搅动流水的声音,和杰姆在水里挣扎,无助地寻找彼此。
格林说,“气垫船”的机械意象隐喻了技术主义的危害。个人被迎面而来的强大轰鸣的气垫船撞得人仰马翻。面对气垫船,个人是什么?马克·吐温在科技时代到来之前,就天才地预见到了——组织化社会中的操纵和制约对社会的危害;他通过气垫船象征性地揭露了个体面对科技的困境——丧失了主体和主体性,浸没在了强大轰鸣的气垫船的机械声之中。机械意象的描述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巨大而吓人”,被烤得发红、好似畸形牙齿的大门,巨大的重量、令人恐惧的联想……统统暗示了约翰·杜威所描述的“社会被……个人行为中非个人化的新型机械模式所侵入”。[4]木筏上工人的价值正在被迅速低估。杜威也曾指出,“现在,机械力量和强大的非个人化组织决定了事物的框架”。[5]
回顾教师教育理论的发展,几乎在所有的教师教育理论中都难以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论证清晰机械理论和强大的非个人组织制约了该领域的人的生活和社区。这些力量和组织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教师教育进步的正常表现,只能顺应,无法抑制,也从来未受到质疑。我们和年轻人都被教导,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所有的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我们曾经天真地幻想,网络科技和虚拟世界能够实现个人追求自由和自发性。
人类正处虚拟网络技术时代,对其有着美好的期待——自由与解放的空间。教师教育也以热烈的态度拥抱这一新技术,期望能够解决工厂化流水线、标准化教师教育中的弊端。存在现象学课程理论家派纳,独立于网络化浪潮之外,冷眼观察,清醒地提醒我们,虚拟世界——尤其是互联网——当初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能突破环境的限制,一个我们可以自主地创作自己的空间。数十年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梦想已死: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另一套更先进的制约系统,因为它是由促其运作的网络技术公司所塑造的。
从机械意象到网络意象,技术进步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是强化了。教师教育也希望抓住虚拟技术这根救命稻草,但在标准化和虚拟化的世界里,技术化正强迫着个人经验的不断蒸发。标准化扼杀了经验的个人性,虚拟化使经验脱离了个体真实生活世界,丧失与他者在场的具身相遇,虚拟经验无法代替真实生活中的具象经验。现象学以其对个人生活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坚持,提醒我们,在屏幕上浏览,只是一种观赏运动,形成的虚拟经验,丧失了来自真实生活经验中的精华与活力。正如格林所言,只有通过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知识的学习,才“可以引发变革,可以打开新的前景,可以提供新的方式建构现实世界”。[6]然而,在今天,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消融在各种数字技术编辑的大数据之中,消融在虚拟世界中,我们极易被操作和控制而变成行尸走肉。
事实上,现象学作为对启蒙理性控制取向反思的哲学传统,从胡塞尔、梅洛-庞蒂到格林等等,所有的现象学家都拒绝决定论,认为意识不是被动的,意识指向世界,人们通过意识行动认识世界各个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有意识的生物,通常采用自己创造的解释方式来创造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理所当然地将世界视为给定的或某种客观存在,便是不加辨别、惟命是从的浸没其中。如梅洛-庞蒂所言,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其中包括科学知识,都源于我们的个人观点。由于人的存在表现出意愿、想象以及依据他们自己是“视域”进行认知,而技术决定论却是一个客观化的世界,如奥凯所言,技术决定论“是一个客观化的世界,甚至人都转化为客体,他们的主体性被削弱”。[7]从现象学传统来看,技术理性认识论是不可能的,在伦理上也是无法想象的。
(二)现象学对技术理性下传统教师教育的批判
技术理性话语下教师专业形象是技术熟练者,专业基础是普适的教育理论知识与技能,教师教育就是以普适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并技术性应用于实践为核心。基于上述技术理性话语具体设计的工厂化流水线教师教育实践模式,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工厂化流水线的教师教育过程分割为四个变量群。教师教育者人力资源变量群+学生资源及社会文化资源变量群,上述两个资源变量群作为工厂化流水线生产投入的生产→投入生产过程变量群→最终形成产品输出——产出变量群。这个模型在当今的教师教育实践中,发挥了主流模型的作用。
工厂化流水线模型的基础是以追求生产性、效率性的工业化与科学行为主义的合体,其实质是追求控制的技术主义。这一过程被视为价值中立的技术性过程,个体内在经验被视为“暗箱”而被有意无意禁止了;个体内部经验的个性与整体性,被分解为可观察、可量化的投入与产出要素,转换成指向生产性和效率性的技术性过程。个体浸没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失声了,被生产为客体化、角色化和标准化的符号,致使其个性丧失殆尽。正如派纳所言,“依赖他人,且自主性发展受到禁锢——自我疏离,且疏离的自我影响了个性化过程的进行——将外在自我内化,将压迫者内化——导致真实的个性遭到异化。”[8]
从现象学传统来看,这无疑是对教师教育的根本宗旨的背叛,工厂化流水线模式,是对教师的工具化、资源化、队伍化。教育也被工具化,被视为服务于经济技术进步的工具。为达到对教师生成制造的目的,将其与自我的个人生活世界分离开来,将其置于社会选择和强大的非个人化组织决定的事物框架之中。正如格特·比斯塔所言,这“是在许多方面没有理解教育的要领”。[9]
二、现象学对教师教育的重构:引发个人真实发声的个性化教师教育
现象学通过批判技术理性及其教师教育模式对个人性经验的禁闭,召唤教师教育要回归它生活源泉和基础,恢复个体的直接体验,恢复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体验感觉,发挥意识能动性,挣脱工厂化流水线的控制,寻求建构一种从技术决定论中解放的教师教育——个性化教师教育,以引发个人真实发声,打破沉默,建构一个民主空间和思想的市场,克服被动、异化。
首先,现象学强调现象,而反对对现象的归纳、概括和抽象,尊重事物的“复杂性”、“个性”或“独特性”,作为教师专业形象的“独特性”,就是成为他自己,即教师作为具体的“个人”,实现个性化;其次,现象学研究考察生活体验。研究被直接体验到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我们所概念化的世界。现象学者寻求对世界的直接的体验和际遇。所以,现象学特别关注知识或认知的“原创性”,故专业基础不再是普适的理论与技能,而是具有体验性的、原创性的个人知识,即便理论知识也必须与体验相结合;再次,教师专业发展是个体主体和主体性的不断生成,消除被动与消极,实现意识提升和全面觉醒。个性化教师教育致力于培养个性化教师,个性化的教师能够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对自我、对教育、对公共领域提出关键性问题,并坚定地发出自己个人真实的声音。
(一)个性化的前提是建构“教师作为个人”
成为教师,并不是通过工厂化流水把个人封装在标准化的角色中,把个人浸没于技术掩盖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建构的复杂过程之中,这些需要解码、阐释;但是,个人的身体、好奇与惊异的情感、想象、原初自我的个人性不能丧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寻求其他的环境,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们自己的环境,并且我们走出自己之外,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然而,就算我们踩到高跷上我们也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腿走路。即使在世界最崇高的宝座上,我们也只是坐在自己的臀部上。”[10]我们不能离开自己,个人是教师教育的基点和动力源泉,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概念中来寻求个体行动的依据。个性化教师教育是推动准教师越来越成为他自己,从封装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个人相对于理论、技术规则具有优先性。在受教育整个过程中,必须致力于引导准教师坚持自我主体性的觉醒、与自己的前概念经验进行直接的触摸,发展自己的视角,这个视角根植自己的前概念经验中,当然要接受集体审视与批判。
首先,个性化教师的专业形象是教师作为“个人”,这是坚持第一人称的主体性具有优先性。正如威廉·厄尔所言,“与别人对我而言我是什么,对我自己而言我是什么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我可能有时被别人客体化,……但对我的第一人称主体性没有影响。于是,我的主体性强于任何推导出的客体化。”[11]在技术理性的教师教育中,个体被外部导向了,过度的社会化。当然,把自己从工厂化流水线的客体化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并不是把外部导向替换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这种自主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
其次,教师作为个人,这不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或心理上自我沉醉。个体存在于某一天的某个特定的时刻的独特性,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复杂体。聚焦于对个体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致力于把人从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方法,这些影响也许被埋藏在意识的视野之外,但是却是构成我们传记情境的生活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复杂结构聚合到这个‘地点’上,即具体存在着的个体生活中。”[12]通过生活体验研究,准教师开始理解政治、经济、文化在自我主体性建构中被内化的深度,开始从技术决定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约中恢复自己,与预先定义和给定的概念切断联系。通过对自我的理解,准教师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对公共问题“沉默”的技术专家,而是一个对公共领域能够发出个人真实声音的“基础性”专家——即具备了对教育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学生主体建构的影响进行阐释的能力,并能够引导学生发出个人真实的声音,发展批判性思维。这样,就能达成格林所建议的,“在教师教育领域为‘基础性’专家留出一个位置”[13]的诉求。
再次,与技术理性话语相比较,现象学的话语是面向事情本身、强调生活体验研究,无意归纳推论出一般意义的规律、法则,而是强调个人体验意义的原始性、情境性、真实性和中心性,是理智发展的根基。技术理性话语把个人的情感、愿望、态度、价值观等视为主观的、无价值东西,使个人性遭到了有意无意的禁止,个人沦于浸没、沉默状态。这种倾向使准教师远离了具体认识,转向了抽象的概念、结论和概括,失去了对真实儿童或学科现象独特性的敏锐和洞察力。现象学精神恰恰相反,它认为学习者个人的原初知觉经验是理智发展的基础,其专业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生活世界的,生活体验中处处体现着学习者个人的思考与筹划,具有强烈的个人性。这些“主观”的个人原初经验,正说明了其真实性、价值性,是学习者发展的起点和归宿。现象学把个体体验看作是人类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存在方式和认知方式。现象学通过对个人体验严肃的、艰辛的描述与写作,努力去深刻地、真实地理解经验。“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现象学探究考察每个个体的独特的人类感知,并描述这种感知”,[14]以此寻求经验的本质。现象学“通过回访直接的个人经验、恢复对自我和世界的体验感觉——和完全是概念的感觉形成对比,来寻求从抽象概念中获得解放”。[15]这样才能保持对教育情境的高度敏感性,去反思与保护每一个儿童的独特性。
(二)个性化的核心是发展专业的个人知识
个性化的核心是推动准教师的专业发展,奠基于个人直接经验基础之上,创造自己的专业智慧和自己的实际学科,利用理论的洞察力发展个人自己的洞察力。避免一种诱惑,根除理论的洞察力,把理论直接应用于实践的简单做法,这会导致准教师个人理智的停滞,以及伪实践和伪发展。
首先,强调个人知识,不是反理论的。它反对的是机械地、教条地对待理论,把理论作为概念进行演绎和机械地翻译到实践中的技术性做法,这导致了理论的神秘化,导致个人理智停滞。理论的力量在于它提升个人的洞察力,使个人经验提升为理论,产生思想运动与转变,变成个人化的理论。理论倘若没有个人生活的基础,没有个体经验的独特性,这样的理论很容易以政治上和理智上反动的方式起作用。而作为教师专业的个人知识,强调的不再是静态的由专家制造的“跑道”,而是个体围绕跑道奔跑的动态过程——个体奔跑的体验。
其次,梅洛庞蒂认为,认知是建立在个体直接体验的世界之上的,“我们必须唤醒对世界的基本体验开始,其中科学知识只是间接经验”。[16]教师教育“是那些亲自体验那些情境的人的主体性建构”,[17]他们不是局外人,必须尊重那些生活于“此时此地”情境中的个体的个性化探究。个体的情境性“自我理解和反思培养拥有‘所有权’和‘占有权’的经验”。[18]
再次,通过对个体体验的探寻,寻求描述每一个主体是如何理解自己产生的行为,“即便是最纯粹的科学研究也植根于经验和无法回避的人类现实当中”。[19]科学知识源于我们个人的观点或从世界中获至的经验。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在经验基础上建立科学发现的必要性,或者承认迈克·波兰蒂尼所称的‘个人知识’的必要性”。[20]个人乃是其自身专业知识的创造者。这样,“主体的生活就是客观构成;自我知识变成了作为世界之认知者的知识,不是作为客观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也不是作为潜在的主体的表现者,而是作为这两个领域的桥梁和中介。”[21]作为学习者,由于每个人经历、规划、所处位置的不同,个人会以独特的视角参与学科,使学科认知与自己的记忆、直觉、感受、想象、信念融入一体,参与学科对世界的阐释,实现学科理论的个性化,研究重新创造学科所创造的东西,从而创造另一个“个性化的学科”——学科的认知者的自我知识,既来源于他的体验和想象的实质内容,也来源于学科本身。通过学科个性化研究,发展准教师的专家思维,也可称为专家决策思维,是指在未来教育情境中,当所有标准化的教育教学的方法均告失败时,发明个人方法以解决复杂教学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认知能力的专业素养。另外,通过对儿童的现象学探究,保持对生活故事的情境敏感,反思儿童的生活,发展准教师的复杂交往能力,这种能力是指在复杂的、不可预测的教学情境中,理解儿童的动机、感受,机智地对待儿童,并通过提供各种解释和示例以帮助儿童、促进复杂对话延续和发展能力;以及未来同事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这是一种非认知的专业素养。这样,个体乃知识与文化的创造者。个人知识因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的基点——不仅有助于理解教师行为的意义,而且还能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找到切实可行的出发点。
(三)个性化的根本是推动个体全面觉醒
真实的个性存在于全面觉醒之中,根植于创造的情境中。全面觉醒“源自对生活及其要求的全面关注。”[22]这种关注试图让我们从惯常的活动的机械声的浸没之中浮现出来,拒绝无动于衷和麻木被动的态度。在“结束机械生活行为”[23]的同时,开启“行动的选择”和踏上“自我型塑”[24]的有意识的创造行动。如果缺乏全面觉醒,个体就会默许客体化、模式化、标准化的传统教师教育施加在自己的身上,个体就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丧失个性化的成长。
乔治·赫伯特·米德在《自我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自我结构的两个维度: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25]。宾格的我是在过往的历史和行动中被内化的他人或社会的文化经验,是社会传统和习惯,它约束着主格的我;而主格的我是指自我的自发性、自由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主格的我负责在过去经验背景下做出当下的抉择。过去的经验构成宾格的我,总是试图依据过去的经验来实现自我认同。此外,主格的我是一种冲动、生成性的我,需要对宾格的我进行反思和批判,需要借助选择的未来项目对自我进行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宾格的我往往是屈从于现实,是现实主义;主格的我是变革现实结构的动力。
当宾格的我占据主导,主格的我处于弱势,日常生活会持续地阻碍自我发挥解放的能动性,个体卷入了工厂化流水线的生产性之中,不假思索地默认了那些几乎不被理解的解释,默默顺从那些身份不明的技术力量,这意味着对主格我的禁锢和对意义的限制;反之,自我不断对技术规则和禁令发起挑战,对实验性价值观和观点的坚持,以及对给定现实的质疑,自我就能进入创造而成的生活中,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价值观的世界,自我不允许自己的想象力被单维度的视角束缚,以开放的姿态,将自己视为能够发挥想象力、运用直觉、感受世界并作为全面觉醒的存在。
通过想象将注意力聚集到自己当下的生活上,即所处教师教育过程中,在该过程中与一系列想象性或先锋艺术家保持联系,引导准教师发现自己并从浸没中浮现出来,对现实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与艺术相遇、做现象学探究、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发展主格我的能动性,实现全面觉醒,突破理所当然的感受和思考,如工厂化流水线对自我的客体化和模式化过程,自我作为他人定义的角色等。此外,全面觉醒的准教师,将把自己视为道德存在,创造新自我,把道德维度渗透到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将变得活力四射,强烈地影响他人,致力于激发他人潜能、帮助他人克服无助感和浸没感,促使他人通过自己的双眼来观察共享的现实,促进觉醒与解放。
总之,针对技术理性下的工厂化流水线教师教育对人的控制,现象学强调意识不是被动的、要面向事情本身,强调生活世界和个体的生活体验,对教师教育来讲,就是要悬置盘旋在教师教育这一空间上的喧器的、客观的、抽象的、概念的、结论式的压抑个人、扭曲教师教育的声音,让沉默已久的前客观、前反思的个人生活体验领域本身发声、并打破沉默,坚定地发出个人真实声音,“声音是存在于个人之内的意义,促使个人参与共同体的活动”[26],并以此生成个人知识,不断生成主体和主体性,实现全面觉醒,迈向解放的个性化教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