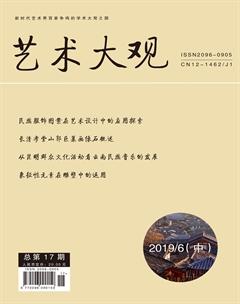渗透与解构
郭俊峰

摘要:戏曲是我国的传统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与绘画是息息相关的,戏曲的虚拟性无疑是影响艺术家画作的一个关键点,“画中有戏,百观不腻”,画面即是舞台,以简代繁、以虚拟实、以假当真,用笔墨将戏曲这种时空艺术转化为空间艺术,笔墨浓淡,轻重缓急正是对戏曲虚拟性的一种物化呈现。
关键词:戏曲绘画创作;虚拟性;渗透;碰撞
戏曲是我国的传统艺术,它由多种艺术形式综合而成,种类多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的发展,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作为中国早期最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与绘画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中国传统绘画、民间艺术还是现当代绘画创作,把戏剧题材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在美术史上为数不少,我国汉代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杂剧题材,到了清代,戏曲人物画更是数不胜数,多为细腻的工笔画或者是简洁质朴的年画。到了现代,戏曲绘画在民间日益衰退,好在关良开创了戏曲绘画的新格局,另外林风眠、朱新建、韩羽等以戏曲人物为题材的画家也创作了大量戏曲绘画作品,虽然每个人对戏曲绘画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是戏曲的虚拟性无疑是影响他们画作的一个关键点。
一、虚拟性是戏曲艺术的主要特征
戏曲具有虚拟性,这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显著特征,可以说虚拟是产生戏曲程式的理论依据。所谓的虚拟性是戏曲在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层层提炼和过滤形成的,使戏曲不受舞台的限制,利用演员细致化的描摹现实的动作进行表演,表现和制造特定的环境、事件、情节,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无限的空间。虚拟性使戏曲有了某种自由,但是同时又陷入某种程式化中,在挣脱时空束缚的同时又需要程式化的动作、表情等来表现特定情节和场景。在戏曲表演中这种虚拟性有相对固定的模式,比如乘船的时候,划船的演员手拿桨,坐船的演员随着船桨的动势左右前后晃动表现在水面上行进;比如表演骑马演员手执马鞭,表现上马、下马、骑马疾驰;比如双手做出虚掩的动作表示关门,抬步表示跨入另一个空间,这些虚拟的动作既富有美感又具有典型性。这种有鞭无马、有桨无船的虚拟为观众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为戏曲表演艺术家拓宽了表现形式,而程式化的动作、表情等也为戏曲的传承提供了模式化的依据。
戏曲的虚拟性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的“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突破了现实的限制与制约,自由地展现对时间、空间、自然环境、物体、动作的虚拟。这种虚拟性就像绘画中的写意,用独特的表现形式展现丰富的内涵,用简单的道具表现广袤的场景,戏剧和绘画可以用“小舞台大乾坤,小画面大世界”概括了。
二、渗透在绘画中静态的虚拟性
戏曲与绘画的关联最早应出现在民间民俗的艺术之中,在民间的剪纸、戏曲年画、刺绣、民间玩具、瓷器花纹中,都可以看到戏曲题材的踪影。而表现戏曲最多的是形式就是绘画了, 这样一动一静两种表现形式互相关联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除了脸谱、装扮,主要靠演员的肢体语言和唱腔来表现故事情节,用虚拟的手法自由地转换时间和空间。通过声音与形体刺激感官,被观众准确地感知,这是戏曲的魅力和韵味所在,而我们在观赏某些画作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官体验,只不过戏曲带给我们的是动态的感受,而绘画则是通过笔触、线条、色彩、氛围呈现出来静态的虚拟性的直观美感。这两种艺术各成体系,各自有独特的艺术语言,但内在的美学精神是相通的。
戏曲绘画以中国戏曲为题材,表现舞台上的戲曲故事、戏曲人物、演出场景等。但戏曲绘画绝不是简单地对戏曲的记录和描摹,戏曲绘画在创作的过程中已经把动态、立体的世界经过提炼、删减、叠加加以作者的主观感受呈现出来。戏曲的虚拟性对戏曲绘画的影响是慢慢渗透的,二者必须达到精神上的契合才能很好地呈现出作者要表达的感受与思想。作为戏曲人物画的开山鼻祖,关良能唱能画,以他对戏曲的热爱和深刻理解,把戏曲人物画画到了极致,他把戏曲的虚拟性用简洁的构图、朴拙的造型、传神的形态呈现出来。空白的画面就像空旷的舞台,既是代表一个具象的舞台,又是抽象时空的象征,给观众以充分遐想的空间。
戏曲绘画中的虚拟性是静态的,这种虚拟性一方面表现为记录戏曲中动态、场景的虚拟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作者构建的抽象氛围。不管是客观的记录还是主观的表现都要依靠构图的处理、绘画语言、造型刻画、色彩构成、技法处理等。即便表现的对象是用写实的手法,但对整个氛围的营造、空间的体现等还是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这是戏曲题材绘画难以把握和表现的部分。戏曲绘画在创作过程中深受戏曲的影响,戏曲中伴奏的韵律、唱腔的抑扬顿挫、剧情的跌宕起伏在观众脑海里构建出一个抽象的世界,绘画中这种抽象的虚拟性是通过笔触的轻重缓急、干湿浓淡、藏与露,隐与显来呈现的,可以说虚拟性是想象力的另一种展现。[1]
戏曲的虚拟性对戏曲绘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首先接受了戏曲,认同戏曲中对空间时间的虚拟处理,认同戏曲中对人物造型,认同戏曲中对动作的程式化处理,认同戏曲中夸张的表情和装扮,在这些认同的基础上再进行戏曲绘画创作,那么戏曲对戏曲绘画就形成了指引性的作用。这种指引性的作用让我们认识到戏曲的虚拟性对绘画形成作用就是理所当然了,这种理所当然是在观念里慢慢渗透,而不是强制叠加。
三、时空的解构是戏曲中动态的虚拟性在绘画中的呈现
解构是指对有形而上学稳固性的结构及其中心进行消解,每一次解构都表现为结构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但是每一次解构的结果又都是产生新的结构。我们简单理解为理性将某种结构拆解,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结构。
那么在戏曲绘画中画面呈现的某种抽象性空间,实际上是对戏曲舞台时空的一种解构。动态的戏曲艺术要用静态的绘画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维度的变化,更是一种对戏曲艺术精华的高度提炼概括。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戏曲中的动态、内涵、时空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有足够的表现能力,从而使戏曲在二维的画面中表现出来,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理性的头脑和感性的思维,充分地理解、概括、分解、重构才能把这些在画面中呈现出来。在戏曲绘画中关良老先生关注的更多的是笔墨意趣,林风眠老先生则是对画面的构图形式更感兴趣。同样是戏曲绘画,同样是虚拟性的呈现,关良老先生和林风眠老先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果说关良老先生作品呈现的是舞台的一个定格,那么林风眠老先生的作品则是呈现出时空的纵深伸,他用几何形结构和平面堆积构成空间的方式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戏曲人物画,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重组,用时空的碰撞堆积充分表达了对戏曲中动态虚拟性的深刻理解。[2]
戏曲绘画没有固定的模式,每个画家对戏曲理解和关注点不同,那么创作的戏曲绘画也是千姿百态,无论是关注形式还是关注笔墨,戏曲中的虚拟性在绘画中都是回避不掉的,这需要在画面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呈现,林风眠老先生画面中人物的重叠展现的正是戏曲中不同时空的叠加,让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时间的轨迹和空间的叠置。让静止的画面有了时间性。这是一种高级的表现形式,也是对戏曲虚拟性最大化的体现,除了表现出了戏曲的虚拟性,也让画面有了意趣。
在现代戏曲绘画创作中有更多的画家思考戏曲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与冲突。现代生活的嘈杂与繁忙、拥挤与浮躁跟戏曲的意味深长、蜿蜒缠绵、广袤深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看到很多青年艺术家关注戏曲绘画,说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艺术传承的重要性,越来越意识到传统艺术中的可贵之处,这不是简单的一种绘画行为,而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把绘画作为一种途径,试图通过绘画的方式去捕捉戏曲的精神,去关注民族文化衰败兴盛呈现的沧桑,去唤起人们对传统艺术的热情。
在现代诸多的戏曲绘画,特别是油画创作中,不再只是简单地呈现舞台画面,而是通过西方油画艺术这个载体把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绘画相结合,呈现历史人文与现实情景的纠葛,往往用写实的手法结合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展现戏曲的虚拟与神秘,自由与规范。正是戏曲的虚拟性给了戏曲绘画创作无限可能,艺术家才能通过对虚拟性的充分把握构建出自己的绘画语言。
四、结束语
戏曲绘画之于戏曲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呈现,戏曲之于戏曲绘画是灵感和生命之源。我们应该注重虚拟性在戏曲绘画创作中的应用,推动戏曲绘画创作行业不断发展,使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王晓明.再论林风眠的“调和中西”艺术思想[J].艺术百家,2011(S1).
[2]孙欣,研齋.风格入境——丁立人采访录[J].东方艺术,2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