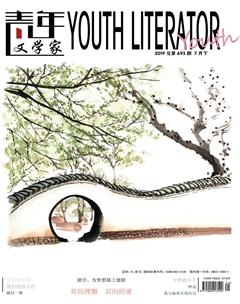刘震云小说的乡土文化与历史重构
摘 要:刘震云的小说大都以故乡为题材,以平民视角观察现实生活,体悟历史与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刘震云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对乡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以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对乡村进行重构,展现着对乡村文化中人性、女性以及历史深刻的反省。
关键词:刘震云;小说;乡土文化;历史重构
作者简介:王平(1985-),女,河南许昌人,郑州财经学院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03
丁凡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指出:“农民文化的概念是和传统的民族文化概念等同的,我们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农业社会的状态。因此文化心态基本上是属于农业型的,描写农民题材则是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最佳突破口。”[1]丁凡这样评论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整个中国民族文化心态最基本的因子来源于乡土文化。因此,乡土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选择,乡土文化成为他们反思历史的核心内容。刘震云的小说一直以其故乡河南省延津县作为创作的基点,无论是在“故乡”小说系列当中还是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均流露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他对乡土文化有着深刻的接触与审视,对土地和农民有着深刻的情感基础,在其小说中以简单质朴的情怀和乡村生活经历向读者展示着真实的乡土生活。
一、刘震云小说中的乡土文化
中国面积辽阔,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因为所处地域的不同,他们的文化形态、民俗风情以及审美取向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也会体现在作家的创作当中。刘震云作为一个有着自己鲜明生活印记的作家,其作品当中也必然留下自己生活的烙印,他的笔触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情愫,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1.乡土文化中的“人性”
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千百年来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地方,面朝黄土背朝天。因此,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们之间是依托着家族建立起来的关系。这种关系极为复杂,充斥着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下,乡村当中的人不可能以个体的形态存在,他们常常是团体化的,但是当个体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常常又会出现猜忌、嫉妒,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矛盾。刘震云小说所展示的主要是这种乡土“关系”背后人精神异化的现实。[2]
《塔铺》是一部展现学子备战高考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没有从歌颂和热爱故乡的笔触来着墨,而是基于理性的立场进行了一场犀利的审判。小说对大家参加高考的初衷和目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城市孩子是被迫参加高考,同时以游戏的态度想要在这里“猎艳”,农村的孩子也并非渴求知识而是想要脱离贫穷的生活……在作者犀利的笔触下,高考只是众人用来逆转人生的工具,知识也因此不再崇高。此外,作者还对高考的严酷和竞争的惨烈做了详细描述,面对高考,人人在低头的同时也被虚伪和自私吞噬着。《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中较为著名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更是毫不留情地描述了人与人之间明显的私利关系。当饥荒使得孬舅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从炊事员岗位上换下曾经的“小情人”,“现在一个人都吃不饱,还管她做什么?”人性的自私、异化被刘震云刻画得入木三分。
2.乡土文化中的“女性”
在刘震云所塑造的文学世界中,对于女性的描写着墨不多,鲜明的女性形象更是罕见,《我不是潘金莲》的出现则成为其女性形象塑造的里程碑。
主人公李雪莲是一个充满反叛特性的女子,她对众人、对许多既定的社会准则都充满了反抗精神。她是一个较为独立自主的女性,在生活中有相当的话语权:在按计划到医院堕胎的时候,突然感受到肚子中的孩子,就自作主张要生下孩子。出于躲避计划生育的目的,她想到了通过离婚的办法来解决困境,当真的离婚以后认识到自己受了欺骗,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访。而表面的叛逆并不能掩盖李雪莲作为典型传统乡村女性的本质属性:她其实并不具备完全的自我意识,而是在男权社会重压下的附属品般的存在。在因为偶然怀孕而引发的系列事件的背后,是她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千百年来所要承担的性别期待——通过生育进行傳宗接代。尽管李雪莲的顺从是在自身都未发觉的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其对男权社会顺从的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传统社会之于女性生育的价值要求,却导致了她被丈夫秦玉河抛弃而家庭破裂的现实,她作为千万女性个体中的一员,从此遭遇到令她倍感绝望的被否定的性别困境。她长期不懈地坚持上访,貌似是反抗强权并维护个体的利益,实则是“她心里不服,想把这事说清楚”,是“想当面问一问秦玉河,去年离婚到底是真还是假”,是只要“世上有一个人承认她是对的,她就从此偃旗息鼓”。但是,秦玉河简单的一句“你是潘金莲”,就将她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得她回归传统秩序的可能性被完全封锁。李雪莲竭尽全力想要抹去自己“潘金莲”的符号,实际上显示了她内心深处对这个道德符号的无意识认同,而“潘金莲”这个符号本身便是男权社会定义的!李雪莲实际上受到传统社会的深重影响,认为背负潘金莲的名声会对她的生活和生命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她在自认为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上访维护名誉。李雪莲之所以要竭尽全力抗争,实际上是要在男权掌控的社会中赢得作为女人的话语权,实现作为女性的自我期待。而前夫秦玉河的死亡让她感受到女性自身最基础的要求也实现不了,便只能选择以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3.乡土文化中的“民俗风情”
刘震云除了对乡土文化中“人性”的复杂、“女性”的无意识进行刻画外,还对乡土文化中的“民俗风情”给予独特的展现。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丢了羊不敢回家,在饥寒交迫之际与同乡老裴到镇上吃了一碗羊肉烩面。羊肉烩面代表着河南的饮食文化,只有真正的河南人才能了解一碗羊肉烩面的分量。杨百顺结婚的时候呈现出河南乡村的婚俗特色,如前八桌安排娘家人,而且婆家人要找见过世面的人陪桌说话。寻常夫妻吵架、朋友“喷空”(聊天)、婚丧嫁娶、卖豆腐的“粗吆喝和细吆喝”,染坊八口大染锅的赤橙黄绿,展示了乡村生活的特色。另外,小说开篇写杨百业小时候喜欢听罗长礼“喊丧”,这是乡土中原葬礼仪式上的独特声调。小说中,刘震云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罗长礼喊丧的过程。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号哭。”刘震云站在乡村文化的视角,再现了中原乡村婚丧嫁娶的民俗文化,将独特的乡村文化的风貌展现给读者。
对于刘震云来讲,他自幼生活在中原大地,深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各种民俗以及历史,而对于乡土中国来说,中原的乡村文化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典型代表。刘震云通过对乡土中原的描写所要揭示的正是生存、人性、文化的问题,而相对于其他乡土文学、历史小说,刘震云的小说对于历史的反思成了他与现实的碰撞并不断延续下去的最重要的特点。[3]
二、刘震云小说中的历史重构与反思
“刘震云的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是对中国历史的一次非常有趣的后现代主义的重写”[4],这是来自国外理论家对于刘震云小说的一句评价,显示了刘震云小说的独特之处。诚然,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揭示了中原地域的独特的文化特点,但刘震云的小说却并未被“故乡”题材所限制,而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传统的“乡土小说”进行了历史的重构,他的“历史叙事”中嵌入了个人对历史、社会的理解与评价。
1.平民化的历史
《温故一九四二》是刘震云站在普通农民的立场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所做的历史“重写”。作品通过对被长期淹没的史料的搜集和重新演绎,力图还原一个平民视野中的历史本相。
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幸、灾难、饥饿常常与之相伴,甚至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唯一记忆,于是,“吃饱饭”“穿暖衣”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对那段悲惨的历史进行了还原。1942年的河南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同时那一年河南还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旱灾和蝗灾,在严重的天灾人祸之下,吃的问题得不到满足,很多人甚至饿死,这个数目竟然高达300万。当时的河南浮尸满地,饿殍遍野。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开篇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历史背景,如果仅仅如此,那就没有什么了,然而刘震云却在之后写道:“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的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后,……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5]这看似是一处闲笔却向我们叙述着这段历史,当丘吉尔感冒这样的事情都足以载入史册,河南这段饿死了300万人的历史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竟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淡出了历史的视野。刘震云正是通过挖掘、引证各种琐碎的资料,来重构1942年的河南饥荒史,以民间的视角进行历史的叙述。从延津出发,由避难到被迫逃荒的沈殿元一家形成故事主线。军机狂轰滥炸,溃兵趁火打劫,“他们成了最终灾难的承受者和付出者”。“早死早超生,死了就不受罪了”的韧性生存哲学,构成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近似幽默荒诞的生存逻辑。
刘震云放弃了传统的历史思维,将历史的视角从战争的场景上转移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上来,将历史聚焦到1942年的河南大地,聚焦到当时的“政治三不管”地带上,从地主家的逃荒路线上,看当时的河南大地流民流离失所、浮尸遍野,国民党政府却歌舞升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政治讽喻不言而喻。
2.人性化的历史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强调,历史始终是“为谁的历史”,而从不曾单纯是“谁的历史”。[6]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按照自己的理解,基于那个时代弱势群体的视角,来解读“为谁的历史”。
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当同一场灾难发生之后,地位、身份不一样的人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映,当然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也是各不一样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只会将历史定格在组成历史轴心的特定话题中,而往往那些历史大事件或名人才是这个轴心的构成者。在1942年,重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是中国的轴心,美国的白宫、前苏联的克里姆林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日本东京、德国希特勒的指挥部是世界的轴心,这些都是关乎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而1942年的河南灾民被历史遗忘,蒋委员长认为“河南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尽管那些大人物大事件会在青史上留名,但是我们毕竟只是普通的大众。如果我们回到1942那个特殊的年份,我们只能是河南灾区随时面临饥饿、死亡威胁的一员。刘震云没有从历史大局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他关注平民百姓的生存,并以此作为评判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他对于历史的不断追寻。
新历史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超越历史,文学并非是还原历史的工具,而是揭示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最隐秘的部分,从而使历史的目的凸显出来。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中,他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件重新解读历史,以历史之惯性和惰性演绎其进步的动力。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将空间打乱,通过“异托邦”重组,并置入故乡,将三国、清朝、民国各个时期打乱,使各个时期的人物行走其中,同台表演。这些人物时间跨度1700多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了世俗生活中的一份子。他们,作为曾经在历史上受到众人敬仰的大英雄,在小说中被去掉了身份和权利的外衣,老百姓重新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在充满喜剧化的效果和颇具讽刺意味的氛围中,小说中的故事在进行着。《故乡天下黄花》在横跨七十多年的时空之中,围绕着马村这个地方,通过分别演绎在民国初期、1940、1949和“文革”特定时期的故事,将中国农村社会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坎坷历程浓缩其中,给人以深深的感慨。作者选取在中国历史上颇具意义的四个典型时期,将人物置于时代过渡的转折点上,通过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深刻、彻底地暴露了人性,引发今人的自我审视。作者通过荒诞或者离奇的笔法,摆脱了叙述历史的厚重感,利用“胡编乱造”的方式,以别样的手法演绎历史演绎人性,是对历史的再度审视。
3.民间立场的历史价值观
传统的历史叙事是由宏大的历史事件构成,是一种“国家叙事”、“英雄伟人的大事记”,而刘震云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历史”、“私人空间的叙事”。历史不仅仅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宫殿,它还走在简陋的街道上,还停在破旧的民屋中。每个个体都是历史的一员,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正是基于这样的个人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平民的立场看待历史,他对历史的演绎也是基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展开的,并未从历史教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事件。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理解、同情并尊重广大的灾民在饥饿面前所做的选择,尊重灾民的真实欲求。在1942年的大灾中,农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饥饿史,当时的农民最关注的就是生存。《故乡天下黄花》从尘封的往事中掀开历史的篇章,对历史进行了再一次挖掘和演绎,尽力将平民心中的历史展现在今天的人们面前。故事中并未塑造纯粹的好人或坏人,也没有进行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批判。在作者的笔下,人性只是在普通人的生存历程中,于某一个特定的瞬间呈现出的诸多面貌中的一个而已。在故乡系列小说中,刘震云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并没有从道德的角度被冠上好人或坏人的帽子,刘震云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据此可窥一斑: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规范,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所有好的或坏的一面,都是为了活下去。
以“民间立场”看待历史,显然与宏大叙事、英雄叙事为中心的“历史观念”迥然有别。作者打破传统历史观念,以新的视角和思想重构和重评历史,尊重农民最本质、最真实的人性的追求,将平凡的个体拉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填补了传统历史叙述的空白。
三、小结
“故乡”始终是刘震云小说中永恒的情怀寄托,是他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他站在平民的角度上审视并书写故乡的人事和历史,在直面乡土的热忱目光中,理解乡土民间生存,关注乡土众生的命运,在对历史平民化与人性化的关照中,形成一种近乎于荒诞的历史。我们无法证明这种历史是虚假的,正如我们无法证明正史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一样,我们只能够通过刘震云小说中的视角,去看他为我们呈现的原生态的乡村世界,建构起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以重构当代人“心中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丁凡.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143.
[2]张东旭.论刘震云小说中的乡土文化[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37.
[3]张立群.“历史”的缩减与重构——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0(3):45.
[4]D.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J].范智红,译.文学评论,1999(6):146.
[5]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4.
[6]费鹏,刘雨.历史记忆与文学的重构——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历史叙事[J].文艺评论,2013(11):86.